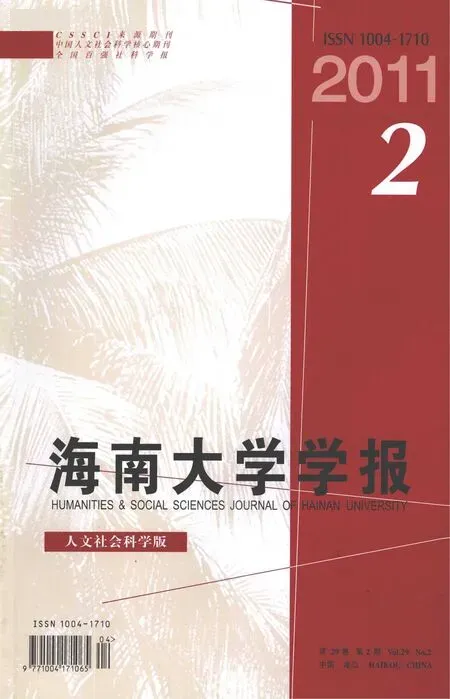防卫权行使困局的成因及其破解
2011-04-08杨路生
杨路生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防卫权行使困局的成因及其破解
杨路生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出于节省资源、提高效率的部门利益需要,不少防卫人被作为“斗殴”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往往按照“不得已”标准考量防卫人的行为性质;防卫人在罪犯逃离现场从而获得防卫机会时进行防卫,往往被一刀切地认定为“防卫不适时”;公、检、法受理防卫类案件的程序和特点,使得防卫人经常被定性为“伤害 (杀人)”而得不到制度性的制约和救济,最终,形成公民不能、不愿行使防卫权之困局。破解对策为:规范涉及“斗殴”定性处理相关案件的程序和要求;明确不得按照“不得已”标准判定行为性质;确定犯罪嫌疑人携赃物逃离现场行为性质为“正在进行”;对“扭送权”相关内容及其范围、对象和损害后果之责任,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和细化,使其切实可行。
防卫权;斗殴;不得已;防卫时间;司法懒惰;扭送权
鉴于治安形势的持续紧张,97刑法修订时,在依然追求公权力与公民防卫私权利、侵害人与被侵害人权利同时平衡保护的价值目标下,立法明显将天平向防卫方倾斜,以期鼓励、诱导公民更多地使用防卫权参与制止、抑制违法犯罪活动。遗憾的是,立法的价值取向似乎并未得到预期的回应,而使用防卫权的被侵害人发现自己经常成为被告 (犯罪嫌疑人)且难以脱罪。这又反过来形成恶例,阻滞了公民对防卫权的选择和使用,以致被寄予厚望的防卫权的行使形成困局。本文致力于研究其形成原因,探寻破解之道,以期抛砖引玉。
一、滥用“斗殴”定案对困局形成的影响
相互斗殴,是指双方以侵害对方身体的意图进行相互攻击的行为。作为主流观点,防卫权成立的条件之一是针对不法侵害,而因为琐事引起的斗殴,是双方违法行为,不承认任何一方存在合法性问题。“由于斗殴双方具有积极地不法侵害他人的意图与行为,客观上也是侵害对方法益的行为,故不属于正当防卫。”[1]264从法理上讲,这种分析与认定并无不当。之所以说“斗殴”妨碍、抑制了防卫权的行使,是因为结合防卫的时间、对象等条件,这种看似端正无瑕的“斗殴”观给司法敞开了模糊处理相关案件的合法大门,从而普遍性地形成恶例,严重影响公民防卫权的行使与选择。
首先,从防卫时间来看,当双方产生冲突时,人们会努力把冲突控制在言辞、说理范围内,而当一方(往往是强势一方)开始使用武力时,几乎所有的相对方都会认为:“他是犯法的,他先动手,我可以自卫了,我是合法的。”而当其中的部分人选择了针锋相对,他很快会发现法律似乎在和他开玩笑——他和对方都被认定为斗殴。虽然从理论上,防卫人自不法侵害人“开始着手”之时就可以防卫,但此时的防卫人即使精通法律,也很难向司法机关证实:对方是连续侵害、是“行凶”。甚至是在对方连续使用武力侵害的情况下,防卫人除了有较严重的伤情事实,仍然面临非常大的危险,被认定为斗殴——对轻微侵害是不成立防卫的。而即使有伤,也难以证明是在冲突之前对方的单方侵害造成的。
其次,从冲突双方力量对比来看,由于侵害方总是处于主动、攻击态势,而相伴随的是往往强于被侵害人的力量 (人数、器械或体格甚至熟悉环境程度之类的心理优势等)优势,而被侵害人则总是处于被动、劣势[2]。自然,防卫人只能选择双方力量相对均衡的情况才有机会进行防卫。如果必须等到对方表现出攻击的连续性,攻击的强度确已达到“严重”甚至是“行凶”的程度而不至于事后被认定为“因琐事斗殴”,则原本微弱的平衡已经遭到破坏,同时也会动摇是否进行防卫的决心,除非防卫人经得起连续性打击或者有很强的隐性优势。
再次,从涉嫌刑事案件的程序来看,冲突造成较严重损伤的,一般都会经当事人告诉或者目击者报警而由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公安机关由于治安形势紧张,案件多、压力大,即使不考虑当事人对办案人施加的不正常影响,从速、从快解决也是符合办案单位利益最大化的,而不认真勘验、调查与对人证的审查,仅根据伤情把案件定性为“斗殴”,直接追究致伤一方,无疑是办案单位成本最小、效益最大并且几乎没有风险的最优选择。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选择对构成国家刑事司法机器的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也同样是最优的,虽然从理论及法律规定来看,检、法两家的任何一家都可以对公安办案单位的事实及法律追究予以程序上或者实体上的否定。
由此可见,“斗殴”观以及司法的习惯性处理,对于防卫权行使困局之形成有重大影响。防卫人一旦进行防卫,必将处于被草率地认定为“斗殴”而不被承认合法性的危险境地,而他自己也很难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抗辩。97刑法对于防卫是否过当作了更为科学的规定,解决了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否“过当”从而减少了刑事追究的司法随意性,降低了防卫行为被定性为防卫过当形式犯罪的风险,但其前提是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是“防卫”,对于司法机关轻率地以“斗殴”否定防卫之情形,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和动摇。几乎全国所有的同类案件,争议都集中在“斗殴”还是“防卫”上,充分证明了“斗殴”观及其司法习惯处理对于防卫权行使困局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事实上,在原本公权范畴内所授予私权有条件合法性的情形下,由于限制该私权被滥用的需要,往往设置并使得该私权行使需要很高的技术要求,加之司法技术限制,导致公众无法接受,并最终形成法律确认的私权被虚无化。
二、“不得已”司法标准对于困局形成的影响
无论是 79刑法还是 97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条件中,均未把被侵害人的防卫行为必须出于“不得已”作为成立正当防卫之条件。也即防卫人在可以防卫也可以不防卫的情况下,选择了防卫,并不影响对于防卫行为合法性的认定。事实上,为了鼓励公民与不法侵害作斗争,防卫人还可以是并未受到侵害的第三人。
但是,司法实践中只有那些明显表现出躲避、退让而躲无可躲、退无可退且侵害人变本加厉施行侵害的情形下进行的防卫,才有机会获得司法机关的合法性评价,也就是说,防卫行为必须出于“不得已”,实际上已经成为行为成立正当防卫的条件。正如有学者认为“有的违法侵害行为非常一般,行为人有充分的躲避、求救、防止条件,没有必要进行防卫。”[3]
一方面立法并没有要求防卫必须出于“不得已”,而另一方面,司法却在其自身运作过程中创立了“不得已”的法律标准,这种情形就像没有立法价值的侵占罪,经过立法之后,仍然得不到司法响应一样[4],反映出立法与司法互动关系中,司法对于立法的反动。而司法的这种反动,毫无疑问会增加防卫人的刑事风险,并最终反映在防卫权行使困局之中。
早在 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第 5条,对正当防卫确有“不得已”的规定:“为了防卫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的人身和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犯罪侵害,不得已而对犯罪人实行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认为是犯罪。但是防卫行为显然超过必要限度,应当认为犯罪,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处罚。”这个规定把正当防卫的起因概括为犯罪侵害,并把正当防卫实施的前提限定为“不得已”,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人民群众有效地行使正当防卫权利[5]。所以,自 1957年第 22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始起,便不再要求防卫出于“不得已”,并一直保持至今。
那么,这一立法上已有定论而并非被忽视的问题,为什么会被司法实践否定并反其道而行之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不法侵害与斗殴的分辨与确定难度超出想象,无奈之中司法机关“不得已”选择了把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出于“不得已”作为判断辅助标准,来解决案件定性问题。
首先,防卫人成立正当防卫所对抗的“不法侵害”,至少有三种主张:其一认为“不法侵害”一般是指犯罪分子有预谋、有准备的正在进行的犯罪活动,即把“不法侵害”限于直接故意犯罪的范围内[6];其二认为“不法侵害”包括犯罪行为与违法行为[7];其三认为“不法侵害”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其他违法行为,但又不是泛指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也即有些犯罪并不需要防卫,而有些形成紧迫性的违法行为也属于可以予以防卫的不法侵害[8][1]258。不法侵害的模糊性,必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各行其是,加之一般“轻微”侵害不允许防卫的精神引导,防卫人的行为属于合法还是非法,难以确认。
其次,防卫人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要求行为人具有防卫意图,而基于愤怒、报复等情绪化原因的攻击行为不被承认具有合法性。如果对方一开始侵害,被侵害人则立即还击,由此进入新的循环争斗,被侵害人的还击更易于被认定为报复性攻击、“斗殴”而非合法性防卫,因为此时尚难以确认侵害人的最初攻击已经达到了“不法侵害”从而可以防卫的强度,同时,对方的侵害行为尚未表现出连续、持续状态,因而也难以认定反击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而不是报复、斗殴。
由此不难看出,司法实践按照“不得已”标准从严掌握行为人成立正当防卫的条件,是因为“不法侵害”难以掌握,又由于一般轻微侵害不主张防卫,所以,司法机关久而久之便创造出借助于防卫人的攻击行为是否出于“不得已”,进而探知不法侵害具有持续性、强烈性特点,防卫人也因而易于被承认具有了防卫意图而非“斗殴”意图,同时也证明了侵害行为已经达到了可以予以防卫的程度。司法在此与立法渐行渐远,同时也意味着防卫一方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将命运多舛。如果寻求例证,则可以说俯仰皆是,而 2002年发生在陕西延安的董伟“刀下留人”案最有代表性。
三、防卫时间的理解偏差对困局产生的影响
防卫人实行的防卫行为,必须在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期间。但如前所述,除非侵害人持刀拿枪,在侵害一发生即行防卫,必然被司法机关按照“不得已”标准判断为不成立防卫,而是因琐事“斗殴”,2002年发生在陕西的董伟“刀下留人”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9]。如果不仅仅关注该案摄人心魄的戏剧化过程和结果,而是研究案件本身的问题,就不难发现,该案的悲剧性结果是由长期形成的成立防卫壁垒所早已决定了的,而死刑判决及执行不过是把刑事立法及司法中一直存在的问题集中暴露了出来。
在此,鉴于对甫一发生侵害即行防卫的风险前文已叙,下文着重研讨行为人对犯罪嫌疑人 (而非不法侵害人)的攻击行为发生在后者逃离过程中的行为性质及所面临的风险,并尝试证明严格的时间条件限制并不具有法理依据,且已成为防卫权行使困局的重要原因。
首先,法院处理发生在犯罪嫌疑人逃离现场过程中的攻击行为,均以犯罪行为已经结束为基本判断,进而得出行为属于非法性质的故意伤害,是防卫不适时[10]。相信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也普遍地持同样的观点。如果这种流行的观点在法律上是成立的,那就意味着荒诞披着法律的外衣站在世人面前:任何人都只能在劫匪实施抢劫、刀枪相加时予以对抗、防卫,而当劫匪结束抢劫行为开始逃离,则立即获取法律的严格保护,他人只能报警或者温和地“扭送”,趁机攻击的,则是故意伤害。也即:客观上无法、不能防卫时,法律允许防卫;因歹徒逃离而有机会防卫时,法律禁止防卫。笔者相信,这决不是法律设定正当防卫制度所追求的,虽然正当防卫制度并不以绝对牺牲不法侵害人的权益为代价,需要在防卫人与侵害人之间进行权利平衡,而这种理解及判例已经导致二者之间极端不平衡了 (关于“扭送”,下文另行分析)。
其次,从犯罪形态研究入手,可以准确理解犯罪性质的侵害“已经结束”的真正含义 (所以讨论内容限定在针对犯罪层次的不法侵害)。众所周知,故意犯罪的完整形态包括预备、未遂、中止和既遂,而以时间顺序,又可以将其划分为预备阶段和实行阶段,实行行为结束后,并非所有犯罪立即成立既遂,尤其是涉及财产性犯罪 (如盗窃)或者既涉及人身又涉及财产性犯罪 (如抢劫)。一般认为,前者以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且犯罪人实现对财物的自由支配、控制为既遂;后者也应当以行为人实现对财物的控制和支配为既遂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0条规定,具备劫取财物或者致人轻伤以上后果两种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因此并不限于财物一项既遂标准。。罪犯逃离现场行为,性质和进入现场一样,都属于犯罪实行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逻辑上看,属于“着手实行犯罪”的进入现场行为,并未开始直接的“盗取”、“劫取”实行行为,法律性质上定性为实行,那么,逃离现场行为自然属于实行,也即必须对实行行为按照一个标准予以确定:要么发生在实行阶段的行为内容都是实行行为性质——此为广义的实行行为概念,所对应的是实行阶段的行为内容;要么仅限于犯罪构成所规定的具体行为才是实行行为——此为狭义的实行行为,所对应的是犯罪构成规定的具体的实行行为。惟独不能判断进入现场用广义的实行行为概念,也即进入行为是实行阶段的行为,因而是实行行为,属于“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对离开现场行为,又按照狭义实行行为概念,因其发生在具体实行行为之后,而否认逃离行为性质上仍然是实行阶段的行为。而只有逃离现场后,犯罪嫌疑人实现了对财物的非法占有目的,“已得逞”,才构成“既遂”。
再次,正是由于进入、实行、逃离这三项行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行阶段,财产性犯罪人的逃离行为当然属于实行性质,是为了既遂——实现自由控制支配财物目的所不可或缺的,《刑法》第 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罪,有使用暴力或者以使用暴力相威胁必须“当场”的要求,强调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与先行行为有时间及空间上的密切联系,从而构成一个抢劫罪。同时,也证明了刑法对于与逃离相关的毁灭证据、窝藏赃物和抗拒抓捕所采取行动的支持与保护。
上述广为流传的“已经结束”观点的谬误在于曲解了行为“已经结束”的含义,把取得财物行为等同于犯罪行为。需要强调的是,有些犯罪如强奸,其行为特点决定了无论既遂还是未遂,自逃离始,不法侵害即告结束[11]336。而盗窃、抢劫等财产性犯罪,即使犯罪嫌疑人占有了财物,也属于暂时性的,被害人也只是暂时脱离了对财物的直接掌握和控制,犯罪并未结束——尚未达到既遂程度的控制财物,被害人也未完全丧失对财物的控制,逃离行为正是努力达到既遂的实行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对其实施防卫,重新实现权利人对财物的控制。当然,对于盗窃、诈骗、抢夺等逃离现场所采取防卫的强度,以阻止其逃离和控制人身为必要限度,除非其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抗拒;而对于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人携带非法暂时占有的财物逃离,性质上仍属于行为“尚未结束”,可以直接行使特殊防卫权。
笔者并不主张对于所有的犯罪判断其是否“已经结束”均按照是否既遂进行划分,比如强奸,即使在未遂的情形下,自逃离便意味着侵害“已经结束”,即使予以抓捕,也是在行使“扭送权”而不能行使特殊防卫权。马克昌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所谓“已经结束”,一方面危害结果已经造成,即使实行防卫,也不能阻止危害后果的发生或者即时即地地挽回损失;另一方面,或者即使不再实行防卫,也不会再发生危害后果或者危害后果不再扩大[12]。有些侵害行为,虽已占有财物,但尚未逃离现场,仍应视为“尚未结束”,可以实行正当防卫[11]336。笔者深以为然,并在此寻求法理依据,以期拨乱反正。
四、司法懒惰对困局产生的影响
涉及防卫与否的刑事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管辖之规定,全部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其侦查活动包括专门的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前者是查明案件事实,以“谁干的”为核心,后者则以抓获犯罪嫌疑人为核心,通常所谓“破案”与否的标志,就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所谓复杂疑难案件,通常是指难以查明行为人并缉捕其到案的案件,而不是检法两家在办理案件中遇到的证据或者定性困难的案件。搞清楚这一点,对于公安机关经常以斗殴对防卫人予以定性并对案件的最终处理产生引导性影响,进而成为防卫权行使困局形成的重要原因,就很易于理解和认识了。
首先,防卫类案件一经发生,对侦查机关而言,就属于已经告破。案件的两个核心问题:“谁干的”和“抓获嫌疑人”大多已经解决。究其原因,此类案件一般属于突发性质,没有预谋,行为人事后愿意接受司法机关的处理并期待着承认,即使不清楚是否犯罪,也会基于自首的法律制度诱导而自动投案。如此,办案单位就如同评卷人遇到白卷一样,既不用工作,又有工作量。在治安形势持续严峻、案件侦破压力巨大的现实条件下,防卫类案件注定得不到公安机关的重视,注定被以最经济、高效的方式处理——案件无须再查再破再费工夫,定性“斗殴”,直接要求检察机关追究致伤 (亡)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其次,公安机关不愿在法律定性上承担责任,而更愿意把问题交由检察机关解决。按照刑诉法的规定,侦查机关在侦查终结后,必须就案件性质予以程序性定性,虽然起诉权在检察机关,审判权在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的定性只有程序意义,但法律制度追求的是三机关在互相制约的情况下运作的结果,无论有罪还是无罪。现实情况经常是:公安侦查机关不愿花费时间、人力、物力细查并研究定性,同时其法律能力相对低下,简单地定性“斗殴”,如果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把关。如此,防卫人轻易丧失了依赖侦查机关查明事件起因、详细过程、双方力量对比及使用暴力情况及全部证据,进而得出事实真相、得到公正处理的最原始机会。
再次,对于案件的准确定性,依赖于对事实的查明,依赖于侦查机关像侦办其他案件一样投入,对于影响最终定性的事实细节全部调查取证,并在此基础上审查、分析证据,去伪存真。而这一切,恰恰需要办案单位大量的资源投入,其工作量并不一定亚于其他案件。现实情况却是:对于案件因证据不足而被检察机关或者审判机关予以否定的情形,侦查机关高度重视并加强工作,而对于定性导致案件被检法两家予以否定的情形重视不足,事实上,这种否定并不常见,并且即使偶有发生,也无法动摇公安机关依照现行“斗殴”模式处理防卫类案件的普遍性。归根结底,直接原因是效率,效率的背后是侦查机关的利益最大化。
更次,按照刑事诉讼制度设计,检法两家有权对侦查机关的错误定性予以否定,但当事人的这种愿望虽然美好却很难实现。哪怕公安机关再随意、经不起推敲和细究的案件处理结果,也会对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办案产生影响,它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刑事诉讼这架国家机器,任何一家欲予以否定,都要使用较之大得多的力量;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即使发现疑点,由于没有侦查权而只能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由于前述原因,公安机关对此大多持消极态度,敷衍了事,即使经两次退查,检察机关大多选择了把问题交给法院来处理而不是依法不起诉,因为后者需要对案件负起终局性处理的责任,远不如把问题交给法院来得便宜。如果遭到法院不于支持,还可以撤回起诉以避免错案追究。因此,防卫人依靠检察机关否定侦查机关的定性而获得清白的机会并不大。同样,对于公、检两家取得一致的“斗殴”定性,法院更难以否定,况且以“斗殴”定罪处罚对法院也一样是最有利的。
综上所述,司法机关以“斗殴”定性防卫类案件,原因是怠于行使职权,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达到利益最大化。而只要治安形势的压力和资源不足的现实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情况就难以改变,并成为防卫权行使困局产生的重要原因。
五、防卫权困局的破解
对于上述防卫权困局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归纳,不难看出无非是司法机关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以及对于效率的追求而偏离立法精神。因此,相对应的破解方法,也集中于这两个方面。
1.以公安部、最高检、最高院联合发布的形式,出台规范以“因琐事”斗殴处理案件定性的相关司法解释,以便共同执行。(1)明确突发性伤害 (致死)类案件的工作重点在于全面收集证据,准确定性,确定罪与非罪,不得轻率地一概按照“斗殴”处理。(2)斗殴的情形一般表现为双方确因琐事发生矛盾而互不相让,后因言语、动作同时对抗且升级,双方力量 (包括心理、身体及第三方支持情况)基本平衡;而一方具有且依仗优势,无事生非、寻衅滋事,以言语、动作挑衅、侵犯他人人身和人格尊严的,应确认为侵害,被侵害方对应采取的警告或轻微对抗性动作,应视为合法。侵害方若因此采取进一步的侵害,受侵害方有权采取与侵害相应的防卫措施[13]。(3)明确规定不得按照“不得已”标准衡量行为人是否具有合法性。若一方确实表现为具有攻击性、侵害性的非法行为时,应当确认其违法性以及对方抵抗行为的合法性,不能因抵抗行为不是“不得已”而否定其合法性,对于此后发生的对抗及相互攻击,当然确认为由非法侵害一方引起并承担违法侵害升级的法律后果,被侵害方的行为则是在侵害行为升级情况下所采取的防卫性质[13]。(4)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切实履行相关职能,互相制约,防止出现为提高效率而忽视办案质量,草率定案的情形发生。
2.已经发布的有关审理盗窃、抢劫案件司法解释之基础上,补充规定涉及财产类犯罪携赃物逃离现场的行为性质是“正在进行”,公民可以行使防卫权;其中,所谓现场,结合《刑法》第 269条“当场”的立法精神,是指与实施犯罪的特定时间、空间相联系的区域,并不限于被害人或者目击者目力所及的范围。
3.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63条所规定的“扭送权”,应当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包括其与防卫权的区别以及实施该权利可能产生损害的责任承担,如果被扭送人驾乘机动车辆或者仍然持有凶器,或者不放弃逃离的,则允许公民以造成其损害的方式实施扭送权,不能以“行为可能致其受到伤害 (死亡),而其生命、健康权利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为由,否定公民扭送行为的合法性。无论是谁,只要他造成战争状态并且是这种状态的侵犯者,就置身于这种危险的境地[14]。不能因为实施扭送权有危险,就停止扭送,就像不能因为被告人绝食,就放弃对其审判一样,毕竟,这种危险是被扭送人自己造成的。
六、结 语
防卫行为的合法与否,一直在公权与私权的平衡、防卫权与侵害人人身权的平衡之中进行着艰难的抉择。在对立法进行体会并反思司法活动,可以发现有些看似无瑕、合理的观点和主张,和社会生活实际脱离,并成为阻滞公民信仰并尊崇法律的障碍。与此同时,司法必须设身处地地从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理解和适用法律。惟此,司法和社会生活才会形成良性互动,共筑和谐。
[1]张明楷.刑法学[M].第 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田宏杰.防卫权及其限度——评关于正当防卫的修订[M]∥陈兴良.刑事法法评论:第 2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53.
[3]赵秉志.刑法教学案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6.
[4]杨路生.侵占罪研究[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325-331.
[5]赵秉志.刑法总则问题专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02.
[6]李道重.正当防卫的强度可以大于不法侵害的强度[J].河北法学,1984(2):36-38.
[7]高铭暄.刑法专论:上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34.
[8]陈兴良.正当防卫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84.
[9]枪下留人赶在行刑前四分钟[N].华商报,2002-07-12(1).
[10]辽宁营口的哥撞死劫匪被判 11年[N].华商晨报,2006-06-08(1).
[11]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
[12]马克昌.犯罪通论[M].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705.
[13]杨路生.中国刑法若干问题研究[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93.
[14]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
[责任编辑:王 怡 ]
Abstract:In order to meet the department interest need of saving resources and boosting efficiency,many defenders are taken as“assaulting”and ascertained their cr iminal responsibility;judicial organs usually verify the behavior nature of defender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reluctance”;defenders only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o defend themselveswhen the cr iminals fled,thus they are absolutely accused as“untimely defense”;the proced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cepted cases of the public organs make the defenders often be regarded as“har m(murder),thus unable to be restrained or relieved from institutions.Finally,the dilemma that citizens are not able and notwilling to use their defense rights formed.The solutions are as follows:to specify the procedure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related cases of“assaulting”;to clarify that the behavior nature should not be ascertained by“reluctance”;to make certain that the criminal“fleeing with booty”is“crime in progress”;to clarify and specify the judicial explanation of the content,scope,targetperson,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arresting right”to make it feasible.
Key words:defense right;assaulting;reluctance;defending time;judicial indolence;arresting right
On the Reasons and Solutions of Defense Right ImplementD ilemma
YANG Lu-sheng
(Law School,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D 924.1
A
1004-1710(2011)02-0037-06
2009-11-17
杨路生 (1964-),男,河南洛阳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刑事法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