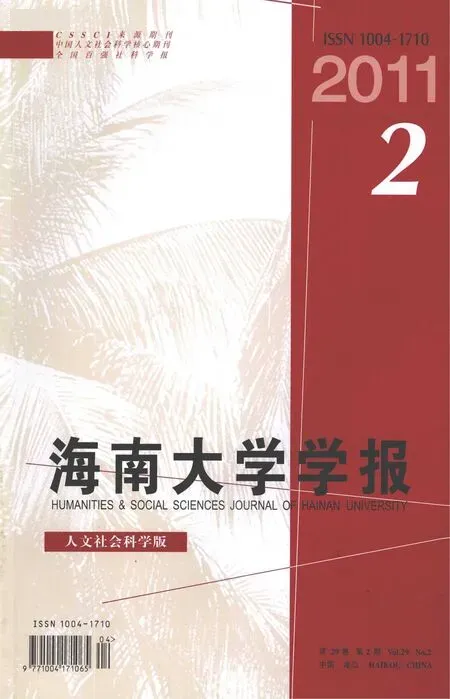从技术的本质看现代技术发展的条件
2011-04-08詹秀娟
詹秀娟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从技术的本质看现代技术发展的条件
詹秀娟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现代技术发展的条件居于技术的历史性之中。历史性拓展出未来。技艺在古希腊的产出方式、现代技术咄咄逼人的订造方式都源出于技术的历史性。对两者的沉思和理解,让人们把握了技术的本质要素以及现代技术发展的条件。现代技术归属于解蔽之天命。现代技术由于其无以伦比的渗透力和辐射力所带来的尴尬处境,惟有通过响应更高的东西的召唤,才能得到改变;现代技术藉此将对更高的东西呈现出开放和完全敞开的状态,使自己真正归属于解蔽之天命。
技艺;现代技术;展现;解蔽
现代技术肇始于技术的历史。技术本质的踪影不是让目光循望在对技术的发展及其演变进迁的历史考古学之中,这种追问与考察只会令技术的本质在其视线的隙缝中逃遁而不见其踪迹,这种视野永远不能切中技术本质的地平线;对技术发展的历史学考察仅是把目光专注于技术史发展的表层,而忽视甚至遗忘了表层下活跃的生命力,失去生命力,表层之发展将迅速干涸。这种生命力深蕴于技术本质的要素,这种要素是一种真正的力量,这种力量贯穿和支配着技术的本质及其在历史河流中的变迁与发展。“要素是真正有能力的东西,即能力。”[1]这种要素与能力支撑着技术的发展并在其之中把技术带入真正属于自己的本质之境,在本质中现代技术才能达于自己的完成状态,而不只是专注于技术手段与设备的更新及现代化;要素完全地展示着技术的内蕴,现代技术惟建基于此基地之上才能深谙其本质。技术的本质要素贯穿于技术的历史性之中,历史性的旨意是面向未来;现代技术在正面遭遇自己的历史性本质的过程中,触摸到了自己发展的条件的脉搏。
一
海德格尔认为考察技术漫长的历史,首先并且十分紧要地,就是必须认真地倾听希腊文中的技术在我们面前质朴地呈现着什么[2]931。希腊文中的技术意味着技艺所包含的东西。着眼于“技艺”这个词的含义,海德格尔提醒人们必须注意两点:“首先一点,就是技艺不只是表示手工行为和技能的名称,它也是表示精湛技艺和各种美好的名称。技艺属于产出,它乃是某种创作;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早期直到柏拉图时代,技艺一词就与认识一词交织在一起。这两个词乃是表示最广义的认识的名称。它们指的是对某物的精通、对某物的理解、认识给出启发。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这种解蔽并非作为制作,而是一种产出。”[2]931人们倾听着希腊技艺的诉说,只有这种倾听才可能把人们带到技艺的近处。希腊人是不大愿意使用“技术”这个词,而偏爱“技艺”这个词,技术之于技艺失之偏颇。亚里士多德在论《机械学》里谈到过技术,他认为我们在自然面前失败的事物,可以靠技术完成,而这种技术是在机械学的功能之下加以认识的,这种技术充其量只能是技能的一种,这种技术还不能堪称为技艺,技艺的涵义非常广泛。对技艺的偏爱,可以在一个层面认为古希腊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达及现代技术所展示的强悍力量,没有占据显要位置,但更为重要的一点却在于技术还不足于全面丰富地展现希腊人的技艺生活——技艺不仅仅作为技术来呈现,技术的本质深蕴于其中。希腊人的技艺透露给人们的是各种美好的名称,它不仅表示像作坊这类手工行为与医术这类技能的名称,代表各类精湛的技艺,更为紧要的是这类技艺之所以美好和精湛在于对其所表现出来的精通,它可以完全被视作精湛的认识,而不仅仅是在制作的层面被对待。因为如果它仅是作为制作来表现的话有悖于希腊人整体生活风格,难以契合希腊人的生活氛围。技艺在古希腊作解蔽如是解,技艺是一种认识——是对物的精通的认识,这种认识创作和产出物,这种认识把物产出来,把物带出来;物在认识的创作之中在场,出现在我们面前,展显自身;此番展显只是基于认识层面上的展显;此番展显也是为了更突出此种精通的认识,希腊人的认识在技艺的基础上得以提升,技艺的功能完全在于为认识服务。
技艺在希腊人思想中扮演着非常有意思的角色,这种角色不仅由技艺本身形成,并且这种角色根本上由希腊思想所赋予。希腊是一个崇尚思的时代,希腊人认为只有在思中才能展现自我,才能把握其时代精神。柏拉图推崇其理念,在论述与著作中,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笔墨描述行动者怎样通过思来认识和趋近理念,惟有思才能在自身之中认识和接近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形式因才能切中自然——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和运动本源——的表达方式和运动本质,人通过沉思就可以通达这种神的境界和最高的幸福。
那么在古希腊技艺和技艺者之位为何呢?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任何技艺都不是为它本身的,而只是为它的对象服务的。”[3]技艺的目的不在自身,技艺的目的在于其对象,技艺的本质功能就是完全为其对象谋取利益;技艺的完善体现在为其对象尽善尽美地服务和谋取利益,技艺的本质除了为其对象谋取利益而没有其他。骑术没有本身的利益而只有其对象——马的利益。技艺本身不是作为目的而存在就不完善,在柏拉图的体系中自然占据不到显要的位置,但技艺却不能被忽略。技艺这种事物的形相虽然不能相比于作为目的本身的最高的理念,但以自身为目的的理念却可以在技艺形相的基础上得到理解和演绎。
亚里士多德认为“技艺同存在的事物,同必然要生成的事物,以及同出于自然而生成的事物无关,这些事物的始因在它们自身之中。”[4]技艺的始因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制作者,技艺不能作为自然的存在方式而得以表达,因之它自身不具有致动的根源;这种始因不在自身的技艺,由于其本性决定了它也不能成为自身的目的。技艺总是以它物为梏的。这与亚里士多德所称羡的生活相差很远,它不能成为表达人本性的最高形态,但亚里士多德却没有因此而放弃技艺。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由经验易识的小节探求宇宙中的大义可以看出,技艺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进路。技艺作为一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不同于个别经验,它通过经验积累和思维的参与可以通达普遍的知识,只是这种普遍知识不会投入创制之中,它会以自身为目的得到最高的幸福。
在思的时代,技艺服膺于认识;技艺把自己投入创制之中,这在当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技艺的创制却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技艺是在人们从事思的精神氛围之中,凭着对某物的精通,把某物展现在思者的面前,思者观看某物,以使之质朴地开放自身而到场;技艺的认识服务于创制,但作为最后的归宿却听从另一个召唤,这个召唤不在于人,而在于人的思。思把技艺的认识召唤入一个更高的理念和最为自然的存在方式之中,具有此种理念和方式才能最为真实地展现自我,技艺者才能在其中体会到不朽和永恒的幸福。“作为制造者和制作者,其工作是对自然施予暴力,以为自己建造一个永恒的家,现在,他被说服将暴力连同所有的活动一起抛弃,使东西保留其原貌,并在不朽和永恒附近的沉思处找到他的家。”[5]297技艺者听从思的召唤无需改变更多,只需放弃自己的创制,反转目光思有关技艺的认识本身就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的家。退一步讲,如果技艺者没能放弃自己的创制,技艺者只能为真正的思者开辟一条小路通达幸福的家园,这样,技艺本身就不能在最高的意义上最完全地展现真实的自己,只能服务于思,让思者在最为崇高的意义上展现自己,找到真正幸福的家园。
二
现代技术之为现代技术,不在于什么现代技术因素,不在于先进的机械工具,而在于技术的本质要素,现代技术只有镶嵌在自己的本质要素中,才能窥见自己发展的天命。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之中。“座架归属于解蔽之命运。”[2]943古代技艺聚集了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渊薮。现代技术之本质亦在于解蔽,但这种解蔽却与座架相属相与。座架意味着聚集,但却不是由于自然本性而表现出一种天然的应和天命之聚集,这种聚集针对摆置而言,把物摆置入座架之中,现代技术之本质就居于此座架之中。就座架之摆置而言,首先能被摆置的就是自然,自然再也不是围绕自己的存在方式而得以展现,自然设在摆置之下。摆置把自然作为能量的储存器和转换器而不断地开发、开采和利用,这里没有为自身而存在的东西,只有不断地被计算、被控制,并且不断地被加以利用的没有永恒的现存物,这种现存物不断地受到摆置和订造,充其量只能被认作是在无限的摆置和订造过程中的一个链条。当受摆置和订造的自然不能充分供应和满足这一链条之时,摆置和订造的目光已然转向了太空和宇宙,在对其不断加以摆置和订造中,使链条能无限地具有生命力而被链接。摆置和订造不是其他,它们归属于解蔽的天命,因为它把解蔽之命运引向了深渊,深渊之上悬挂的是摆置和订造的旗帜;摆置和订造让深渊不断地得以开凿和下沉,又是什么赋予摆置和订造在现代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
人从中世纪解放出来似乎宣告了这一生命力的诞生,人最大的自由在于人不再作为上帝的受造物而存在。笛卡尔的“我思,我在”预告了时代的走向与发展。人不仅不是上帝的受造物,人反而成了世界的造物主和上帝,世界的存在是在思中得以过滤和展现,我思确证了万物存在的有效性,作为我思的主体亦一跃成为世界的主宰。我作为表象者把世界置于自己的面前,让世界由此得以显现,我思不再被召唤去倾听最高者和最根本的目的,我思是绝对的主宰,世界被召唤入我思之中,在这种思中,我作为一个绝对的表象者让世界在场。当我响应现代技术呼应之时,我作为一个绝对的表象者就把万物摆置和订造到现代技术的发展之中,万物和世界就在这种促逼之中展现自己。现代技术疯狂地订造和促逼,伴随我的绝对表象,似乎是将我作为一个绝对的目的而加以对待。在摆置之中,没有什么永恒的存在,有的只是链条上不断更换的环节,而持存其中的就是表象者自身;表象者是作为订造的目的而存在,但在同时,表象者也是作为一个订造者而存在;人作为表象者俨然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人可以在摆置和订造中促逼世界交出自己所有的能量来服务于自己,人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肆意地展现自己、宣泄自己的意愿、满足自己的欲望。
现代数学让所有的表象者都落入自己的计算之中,被表象者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得以预定的表现和展现;表象者借助于这种方法计算和测量出所有有待被表象的万物,万物和世界都被充塞到表象者的目的之下。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就认为一切技艺都不缺少的就是数数,这种数数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用语中用到的一般的计算总和做出标志,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它是一种数学因素,是一种学,这种真正的学只在那种地方,在那里,对人们已有的东西的取是一种自身赋予并且被真正经验到了。”[2]854人们学的、取的都是人们自身之内已经拥有的、对自己经验到的物的认识,这种认识是自身赋予的,而不是外界赋予的,也不是上帝预先设定在人们之中的;它属于先验认识。一切被表象者都在先验认识的表征之下失去了自身,它们只是被思在自我意识之内构造和计算出来,然后被投入到不断的订造之中。现代数学让古代的数数经验达到最高的完成状态,表象者在自我中不断地对世界进行计算和筹划,把万物都摆置和订造到思的面前,同时这种思又是不断地为物——物不断地受到被摆置和订造——服务的。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看起来所思与表象者成为它的最终目的,其实与它如影相随的是——表象者已经被设定为摆置和订造得以运行的最好的工具,表象者成为最为深重和最彻底的根本上受到摆置的对象。因为只有表象者的所思所计才能运转如此疯狂庞大的摆置和订造;古希腊技艺的创制者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人已经完全成了技艺的制作者,并且彻底地为技艺的制作服务。“人就其是一个技艺者而言已经被工具化了,这一工具化意味着所有事物都堕落成为手段,意味着这些事物丧失了其内在的和独立的价值。”[5]152现在是真正的所有的万物都被沦为工具了,包括最高的目的——人自身在内,这里所有的一切可能都不能发现自己内在的独立的价值。曾经神气活现地自称是地球的主人,其实也已经被摆置到订造之中,人在这种订造之中,茫然无头绪。所以,“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2]945主人在这种不断地被假象充斥的过程中,再也找不到真正的自己了,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真正的本质,每个自身的灵魂在订造的上空不断地漂移,无着无落;人再也找不到真正地属于自己的家,人生活在这种居无定所、无家可归的状态之中,与这种状态为伍的是人的恐惧,恐惧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处于链条的哪个环节的被计算和算计之中。
三
现代技术作为座架的本质归于解蔽之天命现代技术的本质以解蔽的方式呈现自己,但这种解蔽却对天命形成了一定的遮蔽;天命作为一种发送,将把某物遣送到自己的本质特征之中,使其真正地在场。座架作为一种聚集,它也是把某物集中到本质之中而使其展现出来,但这个本质已非天然地属于此物自身,此物在此本质中失却了自身,找不到自身存在的根据。虽然它会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但这种方式亦远离了此物的本质属性;物现在是在咄咄逼人的订造和摆置中展现其原貌,它归属于这种摆置,摆置成了疯狂的工具。在摆置的深渊,虽然凡物都得以展现,可但凡此物都失去了自身,其真正的本质在其中逃遁全无,所以这种解蔽对天命形成了遮蔽,在这种遮蔽中天命滑向了深渊。
古希腊技艺之解蔽听从一种更高的东西,这种东西把此番解蔽召唤入真正属于自己的本质之中;技艺的解蔽归属于更高的理念和最为自然的方式。人惟有倾听,才能让解蔽进入本质的途中,在这里不存在咄咄逼人的摆置和无限地受到促逼之订造,在这里只有响应天命自然地产出;人没有把自己置入摆置和订造的中心与目的中,人只是在解蔽的近处观看更高的指示,这种专注使人归属于指示,在指示的遣送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乐园;这个过程中,人自然地展现着自己,不失之本质与居所,在这里可以找到真正幸福的家乡。亚里士多德认为凡物运动都有等级秩序,最后所有的运动都得向中心趋近,中心是最为优越的运动;物的本性隶属于运动的本性;最为自然的物是最为优越的,而制作之物最后都得归属于自然之物;人不能成为自然之物的主宰,但人可以在思中倾听和观看这一最为自然之物,从而找到真正的幸福居所。
现代技术让这种运动和自然之物的神秘性消失全无,人替代了这个神秘之物;人揭去了它的面纱,人失去了古希腊倾听和观看的本质,但人却没有忘却它,而是用一种粗暴的强力把它运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从深层被作为一个根本上的被摆置的对象,只能使技术之解蔽把自己投入到不断地被订造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没有终点,也没有最高的能令其止步的可畏惧的对象,这就像一个永动的搅拌器,所有的只能进入其中接受其搅拌从而被其订造。古希腊早就道出了技术本身不能自为目的,换言之,它需要其他的目的指导,技艺只能为其对象服务。如果对象一味地依赖于技艺,那从反面的角度来看,技艺就支配和控制了对象。人在现代技术中把自己设为最高的目的,但由于其也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订造者而存在,所以人在其中就失去了目的自身,技术在这种状况中也失去了最高的目的。因然,技术在不断地投入订造和摆置的过程中,这个过程竟成了它暂时可以以之为目的的所有;这个过程的最后演变只能是技术控制和支配了其所有服务的对象,而对象在现代技术中反而失去了自身,再也遭遇不到真实的自己。
现代技术作为座架之解蔽,鼓励人作为最高的订造者选择征服自然、挑战世界的存在方式。这一存在向度通过疯狂的订造和摆置,促逼思之维丧失,以预定的方式把自然和世界都展现为备用物和存货。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当人遭遇如此的自然和世界时,人同时是在把自己预定为具有最高“价值”的备用物和存货。纵使蕴涵无法衡量的“价值”,备用物和存货之所以为备用物和存货已经丢失了意义生长的能力,失却了自由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但这种自由的丧失却是可以忍受的,因为技术让人的目光跃过不自由,停留在它为人类带来的物质丰富和经济繁荣之上。面对这些备用物和存货,技术使人的不自由合理化了。“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6]当人以现代技术所鼓励的存在向度来审视自己的进步和发展,并认为自己从中得到了满足和享受时,人的异化观念好像成了问题,人的进步、享受和满足才是实实在在的。人认同由技术引向的存在方式,并让这种所谓的“真实”意识主宰自己。然而正是这种客观的现实达到了异化的最高阶段。不自由被认同为“真实”的存在,意义生长能力的丧失具备作为代价应该存在的充足理由,并被认为完全可以接受。异化的存在吞没了异化的主体,异化的主体却视之为当然。不合理性合法化了,不合理性成了合理性的归宿,最为真实的自己陌生化了。
技术在现代状况中的完成,已经遭遇不到自身,技术在无法抑制的订造中也无法经验到技术之本质,目的—手段、不断接受订造的悖论,让现代技术已经失去了自己持存的根基特质,现代技术的尺寸没有了基础,能拿什么去遭遇和经验自己的本质,人又如何能在现代技术的不断订造中展现真实的自己呢?一切都是枉然,在这种状态中,只能表现为异化,自身已经缺席。如果任其不可控制地订造的话,将会变得无比危险。我们应该做出转变,以新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来展现自己。
四
在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就认为人类在自然面前失败的事物可以靠技术来完成,更何况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可能也大可不必从根本上摆脱技术,相反,可以让技术发挥最大的功效,为我们的生活服务;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这种物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相反,它本身依赖于更高的东西,这就是“对于物的泰然任之”[2]1239。对我们来说,最根本的是,应该改变自己的态度,技术不能控制我们自己及我们的生活,我们自身最为内在和最为本真的东西根本是不能依靠技术来提供的,技术最为本真的东西必须依赖于一个更高的东西,更何况于我们作为技术的最高表象者?技术作为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在我们有所欠缺的方面帮助我们展现自己,但技术却不能因故成为我们展现自己的最为根本的惟一的方式,它只是展现的一种方式而已;在展现自我的最本真的方面,应让技术栖身于自己的本然位置,而不能越俎代庖。内在本真地展现自己之时,我们依赖的是一个更高的东西,这个更高的东西作为不可回避之物主宰着我们最为本质的自然的生活方式,就像古希腊的技艺和沉思者最终都只能栖身于自然这一根本存在方式的天空之下,惟有这样,最后才能踏上甜憩的路途,回到自己的本质之中。这个更高的东西和不可回避之物并不是作为现成之物持存展现在我们面前,它往往在向我们昭示之时已然遮蔽了自己,它是不可理解的,表现得如此神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专注地倾听;在沉思中对它毫无保留地开放和敞开,这被认作是“对神秘的虚怀敞开”[2]1240。惟有专注于沉思和观看,在它的近处,才可能经验和体会到神秘之物向我们的显现和召唤。
技术在这个时代不可避免地展示自己为庞然大物,人们在思和观看中经验着这个庞然大物;在它肆无忌惮地辐射到社会和生活的每一角落时,人们惊恐地注视着这个异己的庞然大物,畏惧着这个庞然大物,惟恐它终有一天将会吞噬我们生命的全部。但当人们深入到技术的本质要素中,发现技术的本质居于更高的东西之中。在技术的历史性之中,人们窥探到了技术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服膺于更高的东西;技术在现代发展的条件,让我们遭遇到的不再是异己的庞然大物,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自身。“人在技术中不是被迫屈从于某种异己的东西,实际上遇到的是自己本身。无论他卷入技术有多深,[但 ]技术都不像一个从外部闯入到我们的社会或我们的思想中来的殖民力量,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将我们与技术捆在一起”[7],赫费如是说。技术在现代得到了解放,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和创造力。在技术的外部,我们一方面享受着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好处和利益,另一方面胆颤心惊地排斥和批判着技术涉入我们的生活。这两个方面都无益于我们深入到技术的发展条件之中,不能改变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处的双重的尴尬情境;惟有深入到技术的历史性,才能洞悉现代技术发展的未来景观,改变它现在的尴尬处境。在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本质的“虚怀敞开”中,人们倾听到的是更高的东西对现代技术这个庞然大物的召唤和拯救,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对现代技术“泰然任之”,而不必使自己处于对庞然大物的畏惧和焦虑的情感之中。技术不能自成目的,更不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思想、社会施行暴力。现代技术是在人类的需要和利益得到无限膨胀的时候才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在现代技术拓展的视域空间里,人们享受着自己的生命成长,当需要和利益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现代技术的展现成了一股可怕的力量。借助于思和观看我们审慎地批判着自身的需要和利益,让它们处于恰当的位置和合适的度中,现代技术藉此真正归属于解蔽之天命。
[1]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70.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4.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71.
[5]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王世雄,胡泳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2.
[7]奥特弗利德·赫费.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M].邓安庆,朱更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20.
[责任编辑:靳香玲 ]
Abstract:The developing conditions ofmodern technology lies in historicity of technology,which bring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derives both the productive method of the workmanship in ancient Greek and the aggressive manufacturing approach of modern technology.Contemplation and comprehension on them let us grasp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ing conditions ofmodern technology.Modern technology is fated to disclose natural secrets.The embarrassing predicament,brought by its incomparable osmotic power and radiation force,can only be removed when being called up by greater missions,to which modern technology would completely open and indeed undertake its fate of disclosure.
Key words:technique;modern technology;releasing;disclosure
Discussing the Developing Conditions ofModern Technology from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ZHAN Xiu-juan
(College of Humanity,Southeast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B 82-057
A
1004-1710(2011)02-0032-05
2010-09-06
詹秀娟 (1983-),女,江西九江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伦理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