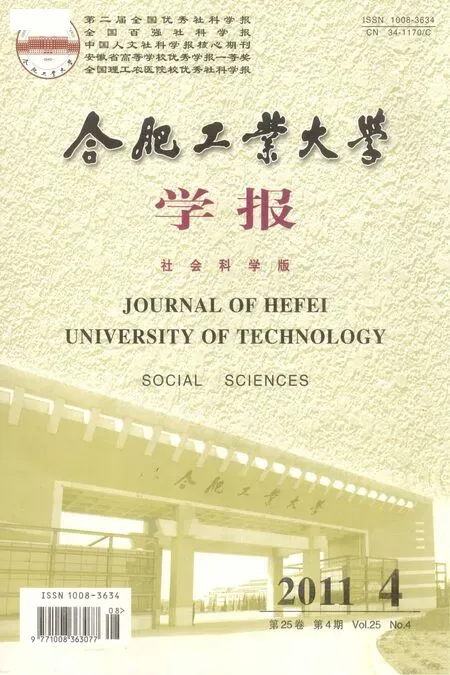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村城镇化”——论乡村、城市文化在乡土作家内心深处的纠结与嬗变
2011-04-08赵斌
赵 斌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 230039)
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村城镇化”
——论乡村、城市文化在乡土作家内心深处的纠结与嬗变
赵 斌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 230039)
纵观现当代文学,乡土作家的内心深处自始至终都被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纠结着,而且乡土作家对两种文化还要忍痛作出选择。由于这种选择受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宰制和牵引,其选择从整个历程上看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村城镇化”的演进过程。
乡土作家;乡村文化;城市文化;“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城镇化”
一般认为乡土作家的内心深处只有温热的乡村文化,没有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只储存在都市作家的心中。其实不然,乡村、城市的二元对立使乡土作家们在叙写描摹乡村文化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城市文化作为参照体系,且作家对两种文化的体认有各自潜在的价值标准。“一般来说,文化大致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制度文化。”[1]文化内涵非常广泛,而乡村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在乡土作家们的眼里却有明显的个人的倾向化认识。如果乡村是传统文化的符码,城市就是现代文化的符码;乡村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城市则是物质欲望的发泄场。乡土作家的内心深处自始至终都被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纠结着,对两种文化都要作出痛苦选择。当然,作家做不出切割式非此即彼的选择,两种文化只能在内心冲突着、碰撞着和纠结着,只是在作品的缝隙中做出各自的倾向化选择。
如果再细心一点,会看到乡土作家的文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宰制和牵引,乡土作家的文化选择从整个历程上看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村城镇化”的演进过程。原因是中国的现代化与欧美等西方国家是不同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总是拖曳着古旧庞大的传统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所以历史的每一次进程都是挟裹着对悠久而丰赡的剥离和进化。一些现代观念融入进来时,自然要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产生一系列复杂的交碰和撞击,也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心理的根深蒂固,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始终被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受这种传统思想影响的许多中国人在走向现代性的同时,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捍卫着这种民族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的现代性是一次次痛苦的剥离过程。”[2]而乡土作家作为时代的歌者,对这种疼痛感体悟得更深切,对渐渐强势的城市文化攻击下的乡村文化的迷失探索更是竭心尽力。作品不仅映射他们的心路历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时代人生的变迁。因为“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不能承受生命之轻》)[3]在这种探索过程中,乡土作家的文化选择不仅伴随政治政策的转变在腹中阵痛成长,而且伴随经济转型的步伐阵痛分娩。又因为近一个世纪中国乡村经历了三次大的文化变迁,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到集体制社会,再到工业化社会,由此笔者认为,从文化选择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前期乡村文化的胜利到后期城市文化的强势登场是一个量的累积过程,如果非要找一个质变点的话,放在1978年这个经济全面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上应更合适些,而不是1949年。1978年以前的乡土作家更倾向于乡村文化,倾向的程度基本上逐渐增强,即“农村包围城市”;以后的乡土作家更倾向于城市文化,倾向的程度基本上也逐渐增强,即“农村城镇化”。
一、“农村包围城市”
非常遗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古老国度来说,农村一直无缘存活于中国文学的沃土里。“五四”伊始,中国乡土文学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追求裹挟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登上舞台,同时也开始了传统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文化纠缠。这种“悖论”式的乡土文学看似有些滑稽,其实大力宣扬“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五四现代作家把目光投向乡土也是有时代背景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使作家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变革的真正的力量是民众,只有民众觉醒了,社会变革才有希望。另外,作为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封建文化的受害者,是乡土作家用来诊治社会病因的最好标本。“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4]可见,乡土文学的出现是政治需求的呼请,时代的呼请。所以回看1978年以前的乡土文学,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使当时各文学派别的文学观念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倾向性。而乡土作家们大都在小说的缝隙中对乡村文化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热情;对现代城市文化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疏离。
作为乡土文学的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代表人物鲁迅一生情系乡土世界,对乡村文化的诠释却是悖论式叙事。一方面,作者笔下的阿Q、华老栓、祥林嫂等愚昧、麻木的农民形象蓄积着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诉求;另一方面,在《社戏》、《故乡》等作品里又表达了乡村“诗意地栖居”,乡村的质朴、恬静和诗意又跃然纸上,传统、现代文化在作者内心的碰撞已昭然若揭。鲁迅一生是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在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方面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卓越贡献,对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但鲁迅作为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文化思维在他身上的力量是不可能完全消退的。也就是说“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从理智上是异常清醒的,但是从文化情感的角度来说,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有与传统文化割不断的血脉关系……”[5]222虽然他也曾追求过西方新知识,也鼓吹过科学精神,但他对现代化只处在朦胧的认知阶段,认为现代化只是“器用”、“技用”的现代化,并且他很快便转向了。正如他写到:“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磬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句以忧国忧民的屈原自比,决心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出路。所以,虽然鲁迅作品富有乡土批判、乡土眷恋等多重内涵,但最终作者还是渴望故乡尽早过上新生活。即使在强烈的批判中,作者对故乡的热情也洋溢在字里行间,以至于他的反对派们批判其为“封建余孽”,虽是对文本的误读,也还是有点依据的。其实,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全面的批判否定,而是进行了糟粕的清理。剥离鬼神等封建文化的糟粕,是想在传统文化具有现代内核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性重构。
作为主流作家在一边呼喊现代化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排斥城市文化是“悖论”,同样受到主流作家排挤的“京派”作家们是“乡土恋歌”的书写者,对痴迷城市文化的“海派”的排斥则是为了争夺文学话语权。“京派”代表人物是沈从文,同时,他也是三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其对“海派”的评论与鲁迅有惊人的相似。他认为“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6]10当然,由于左翼思潮的传播和阶级意识的普遍觉醒,三四十年代文学创作的语境较之于20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融入不了大都市的“乡下人”的特殊经历,沈从文的乡土文化心理比鲁迅更为复杂。“他一方面是鄙视‘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袭;一方面又渴求得到现代文化的熏陶,他甚至想得到一张大学生的文凭,甘愿受郁达夫这样的名家所奚落和小视。”[5]224沈从文复杂的文化心理使评论者对《边城》解读很困难。一般认为其笔下的“边城”一直是一个世外桃源:安详宁静,民情质朴,民风醇厚,是心灵停靠的港湾。然而现实的乡村已经异化,在‘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袭下,乡村也不再是世外桃源般的净土。但相对物欲横流、人情冷漠的城市,乡村还是人情敦厚、灵魂清净、精神纯洁的净土。当沈从文走不进城市,不能融入城市时,乡村一定会成为他美好的记忆,甚至是他自恋的乌托邦。这种阐释也有理有据,然而作品中更丰富和复杂的文化情感却被“乡村恋歌”遮蔽了。《边城》既有现实和命运层面的意义,又有象征层面的意义。碾坊和渡船的对立,就“象征着社会现实和田园诗意的对立,堕落的城市文明与淳朴的乡村文明的对抗。”[7]“边城”写作是为了表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无法用其他国家和民族经验做简单比附,因为它肩负更漫长的历史,具有更复杂的文化基因,也带来更丰富多样的文学想象和文化选择……在现代性面前鸣奏出作家内心倔强而复杂的音律。”[8]所以面对作品的误读,他很遗憾地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是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习作选集代序》)可见,乡村牧歌的背后有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思索,文化选择的疼痛也同样折磨着沈从文。
到了40年代,解放区首先进入了集体制社会。所以和沈从文等“京派”乡村恋歌者相比,“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对乡村文化和现代文化也表现出更复杂的心理选择。一方面,在传统文化的自然熏陶过程中,形成了赵树理对乡村文化忠贞不渝的血缘感情;另一方面,五四文化的理性批判意识日渐发挥着主导功能。并且,两种文化的纠结还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赵树理和鲁迅、沈从文等作家一样,在艺术上也一直追求着人格的独立(这是其后来悲剧的根本原因),但其同时也受到时代政治的牵制。和二三十年代传统的小农社会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政治革命的需要,农民阶层被置于革命运动的前台,经济、政治压迫激发出潜在的反抗意识,形成了起着决定生死的革命推动力量。在此语境中,农民身上的劣根性完全被农民的革命精神所遮蔽了。一时间“工农兵”成为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又加之乡土对赵树理的哺育之情,他对农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切与同情。所以,赵树理的所有精力都聚焦在乡村,其作品几乎无暇直接观照城市文化的发展,但小说中新式农民似乎有城市人的身影。如小二黑和小芹虽然未进城,却可以像城里人那样自由恋爱,作精神的都市追随者。然而受主流政治意识的影响,赵树理对城市文化只有遥想,对传统的农民文化在现代民主文化的烛照下所显示的“落后性”虽不能熟视无睹,但“相对于20年代,对农民整体文化属性的批判意识在赵树理走红的40年代被大大减弱了。动情的赞美代替了冷峻的剖析。”[9]无论前期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还是后期作品《邪不压正》和《传家宝》,只或多或少流露出作家对农民劣根性的焦虑。而赵树理必定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赵树理从事创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意即用五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想去驱除农民兄弟思想上的封建意识,即进行现代性“思想启蒙”。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一方面,承接了40年代的乡土叙事。如赵树理及“山药蛋派”作家和丁玲等主流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的事件上。《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是代表作。六七十年代浩然的《金光大道》把这一阶级政治叙事推向了极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乡土作家的作品立足乡村文化的基础上,对城市文化表现了一定的关注。因为,前30年乡村虽然参与了革命叙事,二元文化也在乡土作家的内心深处有所搏斗和冲突,但两种文化似乎还相隔太遥远,乡村文化还相对固守在封闭的自我的桃源净土中,乡村文化在乡土作家的心中是绝对的胜利者。随着革命的结束,新政权建立了,现代化的进程也推进了一步,二元文化的对立突显出来。乡村文化绝对主体地位也开始动摇了。作家在关心乡村文化的同时,也关心城市文化的发展。如柳青的《创业史》是描写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巨制。小说的创作意图和主题非常明了。梁生宝既是一个有着新思想的青年,在他内心深处又有着乡土农民的传统观念,通过这个形象的塑造展现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初期革命的史诗。但在反映农村面貌的同时,作家也常常将自己的笔触从广袤的农村大地伸向了城市的天空,描绘了城市工业化建设的热潮以及农村对城市的热情。如蛤蟆滩“三大能人”之一的郭振山既是村代表主任,又是共产党员。一直关注城市工业化建设,常常“谈论大城市里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更知道“工人比农民挣得多”,并且一直鼓励徐改霞等人到城市参加工业化建设。虽然徐改霞的“心沉沉地下坠,她感到难受,觉得别扭”,但她“打消不了参加工业这个诱人的念头”,还是觉得进城“更有意义,更理想,更有出息。”[1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冲突呢?因为建国后,国家建设的中心已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城市对劳动力需求激增,大量农村青年被吸收到城市,城市生活逐渐成为许多农村青年内心的一种理想和追求。所以作家柳青扎根农村多年,广袤的农村大地也自然成了他书写生命的全部意义。但他身处乡村,却始终关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城乡二元文化在作家柳青的心灵深处既纠结着,又融合着。
二、“农村城镇化”
“农村包围城市”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伟大正确的政治、军事战略,在这一历史时期,农民很显然是历史的推动者,在夺取城市政权的同时,也获得了文化、道德上的全面胜利。然而,城市虽有许多消极的因素及文化污垢,但“城市”必定是现代文化的标志,包含着更多历史进步的成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文化的道德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冲突慢慢露出端倪来,乡村文化的优势地位动摇了。当然,由于思维的惯性,在1978年思想没有获得全面解放之前,这一动摇在乡土作家的心中还没有得到真正认可,只在文字的缝隙里流露出零零星星的认知。1978年之后的乡土作家虽然一直对乡村文化唱颂歌、挽歌,表面文字里表现着对乡村文化的留恋,实际上却是一种疏离。也许是心理作怪,是一种思维习惯,人往往对自己倾心的人或物会做出批判的姿态,希望其更加完美。就好像一个严父会看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有很多缺点,别人的孩子身上有很多优点。其实作家往往也是一样的。现代文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不可一世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随着城市化的加快,乡村天然的和谐被撕裂了,乡村被强力注入城市的魔力,“农村城镇化”终于被提到了现代化的日程表上。相对改革开放之前的乡土作家对城市文化的隐晦书写,之后的乡土作家逐渐撕掉了遮羞的面纱。
20世纪80年代,经济政治的改革使乡土作家文化心理发生了大动荡。在工业文明和商品化的侵袭下,乡村文化面临着生死考验,“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传统道德观受到了严重威胁。“正如铁凝在《哦,香雪》中流露出的那种对于两种文化形态双重诱惑难以摆脱的少女情境那样:在象征着物质文明的商品经济文化的火车头冲进那平静原始的农村处女地时,一方面给香雪们带来了物质的经济的文明;另一方面,……带来的不适症使她们陷入思考的困境,因为她们的祖祖辈辈是从未遇到过这样严峻的生活文化思考和选择的。”[5]230就这样,城市文化以崭新的姿态、新奇的魔力打破了农村少女们原始的平静,同时也让乡土作家们在新的文化审美面前措手不及。如1982年路遥在小说《人生》中对乡村姑娘巧珍倾注了太多的同情,对高加林走进城市则过于批判,并明确告知只有乡村乌托邦才能拯救高加林,使他的小说仍然流于传统。虽然作家和小说人物高加林一样,对城市文化有着羡慕与嫉妒、热情与仇视等多种复杂情感,然而“农村城镇化”的心理图驱已明确了向度,只是撕裂的疼痛让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们一时还无法完全接受。所以小说和电影与读者、观众见面之后,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地偏向了巧珍而斥责高加林。也许这是作家路遥意料之中的事,所以作家站立在小说中的“城乡交叉地带”时,总会产生“诗意的赞美与行动上乖离的奇异现象。”但总的来说,“从动态的观点来看,路遥文化心理图式是由乡→城的位移与互渗构成的。”[11]64-65作家已经从香雪的“彷徨”中走出,已经踏上通向城市文化的征程。然而当路遥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作深情的徘徊”,[11]278作深情呼吸时,梁晓声似乎完全要抛弃落后而又劣根的乡村文化,朝着现代的城市走来,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小说以乡村人的眼光去看待城市的发展变化,反映农民的精神状态。小说所要表现的,是中国农民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背负着历史的重荷,在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冲突下的落后感和自卑感使陈奂生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城市是一个陌生新奇的迷宫,令他无所适从。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乡土作家们因为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带来的不适让他们畏手畏脚、裹足不前、彷徨徘徊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乡村对城市的守望已变得习以为常,城乡的冲突一方面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又逐渐融合,“农村城镇化”的号角也吹响了。经过八十年代前期的成功改革,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随着商品化潮流、市场经济对农村的步步深入,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和新兴“国学热”的合流与碰撞,形成纷繁复杂的文化格局。市场经济带来的个体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集体意识彼此冲突和融合,冲击着乡村人传统的单元价值观。很多人已经走向城市,已经或多或少对城市有了些了解,对于城市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情感上的认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已经是耳熟能详的词语,他们已经不再把城市当作故事来期待,而是当作生活的内容和方向来看待。特别新世纪以来,农民工群体的兴起,乡村人对于城市和物质的现代性的渴望甚至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温热的乡村也离他们越来越远。所以孟繁华说:“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因此,从乡下到城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乡村文化来说,应该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12]47。”乡村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低级文化,它缺乏与城市文化抗衡的资本,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越来越显露出文化劣势。如贾平凹九十年代的两部长篇《土门》和《高老庄》,就是以《高老庄》的颓败和“仁厚村”的消亡,寓言性地昭示了代表传统文化的乡村的现实困境。在《土门》中,小说描写了地处城郊的仁厚村抵抗城市进逼,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碾为平地,坚守精神价值的仁厚村被寻求经济实利的房地产商打败。小说展现了城市化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现象。在长篇小说《高老庄》中,山村的旧俗古语仍在,但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正在迅速地城市化。尽管贾平凹对乡村文明被侵袭有不少披露,但依然可以看到作者立足乡村的新的建构立场。而阎连科的《寻找土地》似乎在寻找失落的乡村理想。作者通过对比马家峪人和刘家集对佚祥的丧葬的不同态度,抨击了商业文化对乡村文明的污染,唱响一曲乡村文化的挽歌。另外还有一类小说展现了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乡村人对现代资本的渴望,甘愿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礼。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令人震撼地表现了工业文明对淳朴乡村的无情冲击与渗透。企业家倪土改在村里建了几个小厂子,使村子大变样,村民也有了钱。但同时也使村里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更惨痛的是,当倪土改残忍地强暴了单纯美丽的少女倪豆豆时,村人、上级以及家人居然联合起来阻挠倪豆豆上告,甚至迫害她,因为村民需要的是物质、金钱。关仁山《太极地》里有一个邱满子,从村里借到乡里写材料,整天想的就是资金,“邱满子不懂企业不懂股份,他的任务就是变尽法子使劲儿将外商拉进村。村里有了外资就会奔小康,奔了小康他便有了政绩,有了政绩就能升官”。从中可以看到乡村也充满了物质欲望。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和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两部小说也展现了现代资本阴影笼罩下的乡村景象。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两部作品中的田毛毛和九月两少女和倪豆豆遭遇一样,他们分别成为资本权贵洪塔山和冯经理的性工具(九月是志愿的)。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有很深的寓意:少女和资本权贵的对立,隐喻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对立,并且隐喻着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的堕落与毁灭。
到了新世纪,乡土文学一方面承续,20世纪90年代乡村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另一方面,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打工文学的兴起。当然,农民进城已经不是陌生的事情,如果把现当代小说中的农民工列举出来的话,人物谱系应该很长。从祥林嫂、祥子到徐改霞、陈奂生、高加林等。但新世纪的很多农民工对城市比以前的农民工有更多的物质欲望,并且乡村文化的美好记忆也丧失一空,而城市文化烙印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如刘庆邦在小说《神木》中展现了城市生活对离开土地的底层人的观念和心理造成的影响,令人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具有的时代特征的关系变化。特别是十五岁的孩子走出“小姐”房间后的号啕哭声,尖锐地揭示了乡村文化危机的无可避免。吴玄的小说《西地》和《发廊》也是同样表现乡村危机。小说《西地》写了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但吴玄要表达的并不只是“父亲”的风流史,他要揭示的是“父亲”的欲望与“现代”的关系。他偷卖了家里被命名为“老虎”的那头牛,换回了一只标志现代生活或文明的手表,于是他在西地女性那里便身价百倍,女性艳羡也招致了男人的嫉妒或怨恨。更有意义的是,他在外面做生意带回来一个女人。虽然最终“父亲”仍然与现代无缘而死在欲望无边的渴求中,但现代文化对乡村文化的解构在作者的内心深处留下很深的印记。这种印记在邢永贵的《忏悔》中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演。小说《忏悔》讲述了农村妇女王满桂由于由于丈夫长期外出打工耐不住寂寞,或许也受物质方面诱惑,而导致感情“出轨”的事。又加之丈夫的死,女主人公便处在了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的“忏悔”之中。可令人意外的是,故事即将结束时,作者笔锋一转,通过小叔子李青的口,道出了丈夫的真实死因——为一个在牧区打工时相好的藏族女人偷木头被木头砸伤下身而亡。故事很平常,且正在发生着。但却表现了现代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双重解构。其一、王满桂已经成了婆婆“贞节观”的叛逆者,永远无法在这件事上与婆婆达成共识并成为同道者。瞎眼婆婆的乡村文化、道德可能永远“瞎”了,将后继无人。其二、丈夫李福也受城市文化的熏染游离与乡村之外,连魂灵都在城市的上空飘荡,永远不得超生。
三、结 论
当下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世纪的农民无论在生产、生活方式,还是在思想价值观念上,都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是理想之所在。因为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乡村文化有其精华也有糟粕,而城市文化也是如此。所以乡土作家面对城市时总是摆出遥望淳朴乡村姿态,而在写乡村时又总是以城市的眼光来观察乡村。每一个乡土作家都不能逃离这种情感的碰撞和纠葛。并且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在乡土作家内心深处的纠结不会马上断裂,还会继续。但正在发生嬗变——乡村文化的优势不在,城市文化正走进主宰的殿堂;两种文化的对立和冲突正在淡化,正走向融合、重建的新路。
[1]王建疆.审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52
[2]王 杰,肖 琼.现代性与悲剧观念[J].文学评论.2009,(6):157.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4.
[4]鲁 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7.
[5]丁 帆.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与文本分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沈从文.论“海派”[N].大公报·文艺,1934,(1):10.
[7]赵 斌.论<边城>中“乡下人”的人道主义[J].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0,(3):34-36.
[8]董之林.盈尺集——当代文学思辨与随想[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49.
[9]席 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2.
[10]冯 牧.初读〈创业史〉[J].文艺报.1960,(1):
[11]雷 达.路遥研究资料[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12]孟繁华.“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J].文艺争鸣,2007,(6):47.
From“Encircling Cities from Rural Areas”to“Rural Urbanization”-On Entanglement and Evolution of Rural and Urban Culture in the Minds of Country Writers
ZHAO 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In view of the modem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the minds of country writers have always been entangled by rural culture and urban culture,and they have suffered a lot from choosing one or the other.Controlled and orientated by the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their choices show the evolution from the“encircling cities from rural areas”to the“rural urbanization”.
country writer;rural culture;urban culture;encircling cities from rural areas;rural urbanization
I04
A
1008-3634(2011)04-0098-06
2010-09-17
赵斌(1982-),男,安徽霍邱人,硕士生。
(责任编辑 刘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