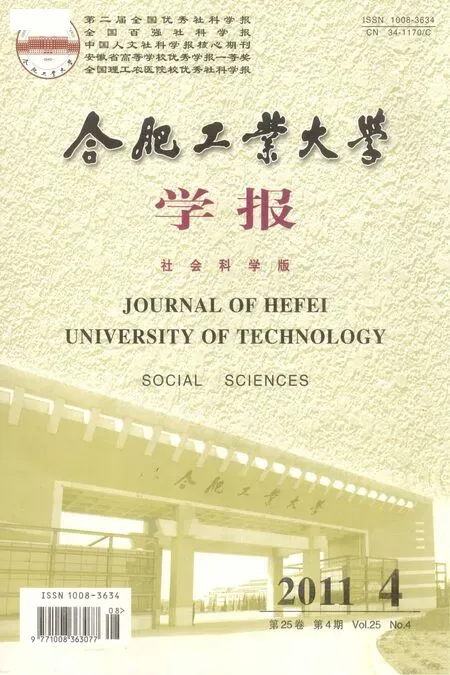清代王琦诗学思想述略
2011-04-08蒋晓光
蒋晓光
(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93)
清代王琦诗学思想述略
蒋晓光
(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93)
王琦作为清代前中期杭州地区较为著名的学者,以辑注《李太白全集》和《李长吉歌诗汇解》两部著作闻名于世,其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性,体现了他成熟的诗学思想。王琦以情景理论和儒家诗学观念观照诗歌,并在解读之中对前人理论有所超越。在运用情景理论之时,重于情与景的融通;在理解儒家诗学观念时,侧重于文学艺术本身的思考,这是体现王琦诗学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
王琦;诗学;情景理论;儒家诗学
王琦,浙江钱塘人,撰有辑注《李太白全集》和《李长吉歌诗汇解》两部著作。一直以来,他的生平及学术造诣均不为人所知。据《清代王琦生平考证》一文所说[1],王琦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卒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原名士琦,字载韩,号载庵,又号琢崖、紫阳山民,晚年自称胥山老人,详于六经,精通释典,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如齐召南、杭世骏、赵信、赵殿成以及全祖望、厉鹗等都有往来,并得到他们的大力赞许,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中佛典的注释大多得益于王琦的帮助,王琦是当时杭州地区一位著名的学者。辑注《李太白全集》撰成后,时人誉为“一注可以敌千家”[2]1685;《李长吉歌诗汇解》成书后,论者将之与辑注《李太白全集》并列,称王琦“仙鬼才华穷二李”①语见清赵信《琢崖次韵见答谦谢再用前韵寄之》,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王氏宝笏楼刻本影印《李长吉歌诗汇解》卷首。,充分说明了王琦在学术上的造诣。
李白与李贺作为唐代杰出的诗人,乃有“诗仙”、“诗鬼”之目。“诗仙”、“诗鬼”实际指称的是两人飘逸洒脱、奇崛高妙的诗歌面貌。对二李诗歌的解读自唐以来即争议不少,王琦在注释中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除学识之外,必然在方法上有过人之处。赵殿成曾在《王右丞集笺注》中引王琦论诗观点称:
王友琢崖曰:诗有二义,或寄怀于景物,或寓情于讽谕,各有指归[3]。
王琦此说在辑注《李太白全集》、《李长吉歌诗汇解》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或寄怀于景物,或寓情于讽谕”即是王琦说诗的两个维度,或洞察诗中景物所寄寓的情怀,或深究诗中与政治、社会相关联之微言大义。若仅论至此,则王琦与前人无有大不同,更何谈成就?但细读辑注《李太白全集》、《李长吉歌诗汇解》两书发现,王琦在此两点上确实对前人有所突破,这是他的两部著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基石,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上两个维度去探讨王琦的诗学思想及取得的成就。
一、“或寄怀于景物”:王琦的情景理论
“或寄怀于景物”,从方法上说,即是传统的情景理论。中国诗学中情景理论的发展有着创作与批评两方面的经验,然而隋唐之前,“情”与“景”仍然是互相感发的关系,至隋唐之后,情景理论的发展开始向互相交融的层次发展。权德舆《左武卫胄曹许君集序》:“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疏导情性,含写飞动,得之于静,故所趣皆远。”[4]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5]这里的“意”与“境”、“思”与“境”等都是“情”与“景”概念的不同表达。最重要的是南宋末年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提出了“意中有景,景中有意”[6]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使得“情”与“景”融合为一。然而成熟的表达,就今天诸多《文学理论》教科书的表述来看,是以王夫之与王国维为标志的。王夫之的“景生情,情生景”[7],“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1],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8],都是情景交融的话语表达。然而检视介于两者时代之间的王琦诸论,实与王夫之、王国维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我们去关注。
(1)“似景似情,似虚似实”:虚实相生 “虚”与“实”是文学创作上的两种表现手法,与景色相互关联之后又有“实景”与“虚景”的使用,而无论是“实景”还是“虚景”,都是情景理论中的重要元素。王琦在注释中,体会情与景的同时将其与虚实相互结合起来,深化了对情景理论的认识,并有所开拓。
《李凭箜篌引》——李贺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
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王琦注释说:
琦玩诗意,当是初弹之时,凝云满空,继之而秋雨骤作,洎乎曲终声歇,则露气已下,朗月在天,皆一时实景也。而自诗人言之,则以为凝云满空者,乃箜篌之声遏之而不流,秋雨骤至者,乃箜篌之声感之而旋应,似景似情,似虚似实,读者徒赏其琢句之奇,解者又昧其用意之巧,显然明白之辞,而反以为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误矣[9]35-36。
李贺作此诗的时间和当时的环境已不可考,王琦认为,这些自然现象皆“一时实景”,诗人听了优美的音乐之后则将自然环境的景象与音乐的影响联系起来,所以“而自诗人言之,则以为凝云满空者,乃箜篌之声遏之而不流,秋雨骤至者,乃箜篌之声感之而旋应”,达到了“似景似情,似虚似实”的完美意境。
以诗而解,“空山凝云颓不流”、“石破天惊逗秋雨”可虚可实。如果纯粹认为虚写,那么这些意象只是对美好音乐的感受描述,存在于意识之中,只是人的心理活动,从诗歌的表现手法上看,似乎不能觉察出作者的机心;如果将这些景象先作为实景,则可以看见在当时演奏音乐的同时,美妙的音乐在变化,而天气也在变化,似乎大自然与人有心灵感应,出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此场景感召之下作者才能够创作出如此美妙的诗歌,说明了诗歌“用意之巧”的“巧”字。所以王琦认为所写之景为“实景”是很有道理的,需要“实景”来表现情感,把握住了诗歌的艺术美。把“天人合一”的感受融入了诗歌解释之中,将艺术中的景色当作“实景”,且不评论是否正确,至少在诗歌意境上是注释者的一次再创造。
王琦以“实景”作解,体现了景色为情感服务的基调,为“似景似情,似虚似实”意境的营造奠定了基础,所谓的“似景似情,似虚似实”就是“天人合一”的主观感受。在“天人合一”的主观感受下,诗歌的意境就能够左右融通,“实景”也是“虚景”,那么在虚实难分,也不必要分清楚的景物下,人的情感也不知是“实情”还是“虚情”了,“实”则为人,“虚”则为神仙,江娥、素女、昆山、凤凰、芙蓉、香兰、紫皇、女娲等等的意象才能活起来,于是有了“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的仙境,“似景似情,似虚似实”的意境就达到了。
王琦解诗,能够出入于“实景”、“虚景”,“实情”、“虚情”之间,使仙境与人境互相跳跃,情景之间虚实相生、左右逢源,无论是“情”还是“景”,都在虚实之中变幻,虚与实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实际即是“情景交融”理论的另一表达,王琦的诗学修养得到了极大体现。
(2)“因情绪之荒凉,而月色亦觉为之荒凉”:景因情异 由于景物的改变而使人的心情发生改变,前人已经论述很多,而王琦在此基础之上能够认识到诗歌中“景因情异”的特点,即情与景融为一体,情感居于主导地位,而作为客体存在的景物服从于情感,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完全实现了情景的交融。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牛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王琦注释说:
本是铜人离却汉宫花木而去,却以衰兰送客为词,盖反言之。又铜人本无知觉,因迁徙而潸然泪下,是无情者变为有情,况本有情者乎?长吉以天若有情天亦老,反衬出之,则有情之物见铜仙下泪,其情更何如耶?至于既出宫门,所携而俱往者,惟盘而已,所随行而见者,惟月而已。因情绪之荒凉,而月色亦觉为之荒凉。及乎离渭城渐远,则渭水波声亦渐不闻。一路情景,更不堪言矣[9]66-67。
“因情绪之荒凉,而月色亦觉为之荒凉”一语是这首诗注释的精彩之处。“荒凉”本指自然,而王琦首先把它用于人,“情绪之荒凉”的提出是为了说明“月色亦觉为之荒凉”,很显然人的心情影响了对景物的观感。“荒凉”一词既能够指人,又能指物,以指物之词指人,说明了人与物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同时也就说明了物也具有感情,客观的“月色”被赋予了人的情感,这样才能实现人的情感影响物的“情感”。
李贺·洛阳城外别皇甫湜
洛阳吹别风,龙门起断烟。
冬树束生涩,晚紫凝华天。
单身野霜上,疲马飞蓬间。
凭轩一双泪,奉坠绿衣前。
王琦在解“洛阳吹别风,龙门起断烟”一句时称:
以人之离别而风亦为别风,以交际断隔而烟亦为断烟,黯然神伤,不觉景因情异矣[9]157。
“风”与“烟”本为自然界所有,然而“别风”与“断烟”则实来自诗人之想象,为情感表达需要而作。王琦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明确指出出现“别风”与“断烟”的原因是“人之离别”和“交际断隔”。
“因情绪之荒凉,而月色亦觉为之荒凉”与“黯然神伤,不觉景因情异矣”说明的是同一个道理即心情决定景物喜怒哀乐的性质,这是王琦对诗歌认识的高明之处。因为景物的改变而心情发生改变即“情随景转”很好理解,看见亮丽的景色则使人高兴,看见灰暗的景色则使人悲伤,这是外界对人的刺激,而“景因情异”是一种哲学化的思考。景物是客观存在的,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我们之所以讲“景因情异”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的,是人的感情的外延和将景物对象化。作家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投射到所欣赏的景物上,把人的感情赋予景物。由于是人的情感的外延,所以作者高兴则看见的景物也就与作者一起“高兴”,作者悲伤则景物与作者一起“悲伤”,人通过对象化,使景物成为了人的情感的一部分,即通过人的情感和人的情感的对象化把一切景物都统一成为情感,情与景融合为“情”,这是情与景的完美圆融。
“似景似情,似虚似实”,“因情绪之荒凉,而月色亦觉为之荒凉”,“黯然神伤,不觉景因情异矣”等等的表述,都反映了王琦的一个倾向,即“情”与“景”本就是相通的,所以在他解读诗歌之时能够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作者的情感,无疑是有理论价值的。
二、“或寓情于讽谕”:王琦的儒家诗学观
“讽谕”实为儒家诗学的核心内容,源自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教”传统。“诗”指《诗经》,“诗教”明确提出是在《礼记·经解》中:“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10]当然,《诗经》的作用还不仅仅在于塑造人格,其更大的用处在于对于政治之态度。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11]《诗经》是承接“王道”的产物,《春秋》之旨在微言大义,以一字传褒贬,则《诗经》亦当有此功能。合而言之,对于社会、政治的批判必须以温柔敦厚为原则,即是“讽谕”,“讽”为婉转表达,“谕”为使之明白——委婉地使之明白,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汉儒说《诗》上,从而成为中国诗学思想的传统。汉儒说《诗》最终形成了“美刺”的批判维度,或赞美,或批评。
具体言及“讽谕”之实现,实际仍自《诗经》而来,即《诗》之六义。“六义”的内容首次出现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12]1824将“六义”直接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是《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重点在“赋、比、兴”[13],郑玄注释《周礼·春官·大师》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12]1842-1843在郑玄以及汉儒眼中,赋、比、兴意义的实现是在对现实政治的观照。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儒学的地位逐渐动摇,“赋、比、兴”也被赋予了文学的理解。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14]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15]钟嵘的《诗品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6]很明显,政治的意味减少了,人们关心的是诗歌艺术的本身,赋就是铺陈,比就是比喻,兴就是意兴发挥,这是艺术的理念取代了政治的理念。这样,中国诗歌对于“六义”或者说是“赋、比、兴”的理解就分成了两路:政治的或艺术的,此后的诗人和学者都是在这两条路上前行。就王琦而言,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政治和艺术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同时又有所偏重,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的儒家诗学观念。
(1)合政治与艺术为一的比兴观 唐代初年陈子昂就已经开始反对六朝“为艺术”的文风;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逐渐衰落,众多知识分子和诗人如韩愈、白居易等开始提倡或践行“为政治的”的比兴观,或批评现实,或试图挽救社会;两宋时期理学兴起,诗歌的艺术性依然不高;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和个人都得到巨大解放,虽然关于“比兴”的论述不多,但整个文学思潮是解放的,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清朝前期重视诗歌艺术性的文学潮流。在这种文学发展的环境下,王琦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政治和艺术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诗歌“比兴”观。
如果从创作方法上讲,“比兴”在大多数诗歌创作中均会运用,“比兴”的用意都是在彼不在此,这对于诗歌的理解十分重要,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非常需要辨明的问题:是政治的“比兴”还是艺术的“比兴”。王琦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既强调政治,又强调艺术,将两者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在《李长吉歌诗汇解序》中说:
朱子论诗,谓长吉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夫太白之诗,世以为飘逸;长吉之诗,世以为奇险,是以宋人有仙才鬼才之目。而朱子顾谓其与太白相去不过些子间,盖会意于比兴风雅之微,而不赏其雕章刻句之迹,所谓得其精而遗其麄者耶!人能体朱子之说,以探求长吉诗中之微意,而以解楚辞汉魏古乐府之解以解之,其于六义之旨庶几有合,所谓鲸呿鳌掷、牛鬼蛇神者,又何足以骇夫观听哉[9]3。
朱熹认为李白与李贺的诗歌相差不大,王琦将其理解为“盖会意于比兴风雅之微,而不赏其雕章刻句之迹”。朱熹的本意是李白与李贺的诗歌“相去不过些子间”,差别不大,这个小小的差别即在“长吉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李白与李贺的诗歌在艺术上差别自然很大,否则作为晚出的诗人,李贺的诗如果与前辈李白的差不多就不会被人称为“鬼才”了,但是朱熹为什么会认为“相去不过些子间”呢?并且王琦还认为是“得其精”。通过上下文的分析我们发现,王琦的意思是:两者在运用“比兴风雅”上具有一致性,这是创作方法的精神;“不赏其雕章刻句之迹”就是说两者在创作方法的形式上具有差别,所以朱熹对于两者诗歌精神的判断为相差不大是“得其精而遗其麄”。王琦认为的“精”是这里的关键,诗歌存在的价值当然不是相同点,但是从内在的精神上讲,作诗必须有一定的主导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融入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比兴”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精神,更深层次地讲是儒家的价值观取向,王琦认为李白与李贺都具备了这种价值观取向并且持非常认可的态度,所以他才这样理解朱熹的话并大力称赞他。王琦曾在《李太白全集》跋中说:“后之文士,左袒太白者不甘其说,而思以矫之,……读者当尽去一切偏曲泛駮之说,惟深溯其源流,熟参其指趣,反复玩味于二体六义之间,而明夫敷陈情理、托物比兴之各有攸当,即事感时、是非美刺之不可淆混”[2]1694,主要精神是强调政治上的理解。很明显,这里的创作方法的精神、儒家的价值观取向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比兴”观。
王琦不仅强调政治意义上的理解,并且也注重将其与艺术性结合起来。在这段话中,“人能体朱子之说,以探求长吉诗中之微意,而以解楚辞汉魏古乐府之解以解之,其于六义之旨庶几有合,所谓鲸呿鳌掷、牛鬼蛇神者,又何足以骇夫观听哉?”[9]3意思是说,既要注重朱熹提出的“比兴”精神,而且还要“以解楚辞汉魏古乐府之解以解之”,这样才能正确理解李贺的诗歌,不会认为他的诗歌怪异了,达到就像王琦所说的“人皆以贺诗为怪,独朱子以贺诗为巧,……知朱子论诗真有卓见”[9]75的目的。“比兴”我们已经分析,既然能说明李贺在价值观上是儒家的,就不能怀疑他的创作动机问题了。我们重点分析“以解楚辞汉魏古乐府之解以解之”这一原则。
王琦曾言:“长吉下笔,务为劲拔,不屑作经人道过语,然其源实出自楚骚,步趋于汉魏古乐府。”[9]3王琦的意思则是我们必须了解作者的创作的“源”,才能更好、更准确地运用“比兴”的方法来分析诗歌,否则就会认为“鲸呿鳌掷、牛鬼蛇神”。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1]本意是论述“尚友”,但实际上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知人论世”往往强调理解作家的生平,王琦在这里增加了诗人的文学背景,师法不同,其风格也会不同。首先清楚“源”的风格才能更好地理解学习者的风格,这是理解诗歌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琦是十分重视诗歌理解的艺术性的。将政治与艺术相互结合才能“其于六义之旨庶几有合”,“六义”在创作方法上重要的是“比、兴”,所以王琦的“比兴”观是将政治的理解与艺术的理解两种原则互相结合的,对前人大多偏重一个方面来说,用这种方法解诗是对前人的超越。
(2)“圣于诗”的再解读 “圣于诗”这一命题首先是由朱熹评论李白时提出的:“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17]
这里的理解的关键是“法度”,朱熹没有直接说明,我们可以看看距他时间最近的元代萧士赟对“圣于诗”的认识(均为王琦注释中所引,原诗略去)。
对《玉阶怨》(李白)中“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一句,萧士赟曰:水精帘外以水精为之,如今之琉璃帘也。无一字言怨,而隐然幽怨之意见于言外,晦菴所谓圣于诗者,此欤?[2]294“无一字言怨”则是温柔敦厚,“而隐然幽怨之意见于言外”乃是春秋笔法,即“讽谕”。
对《拟古十二首·其一》(李白),萧士赟曰:“此篇伤穷兵黩武,行役无期,男女怨旷,不得遂其室家之情,感时而悲者焉。哀而不伤,怨而不诽,真有国风之体。此晦庵之所谓‘圣于诗’者与?”[2]1093
“哀而不伤,怨而不诽”讲的还是温柔敦厚,他认为“真有国风之体”的“国风之体”重要特点在于“哀而不伤,怨而不诽”,仍是婉而言之。综合而言,萧士赟所谓的“圣于诗”包括以下几个特点:温柔敦厚、春秋笔法。“讽谕”的目标既已实现,却不具备艺术性的考虑,萧士赟的理解应该是代表了朱熹的思想。
王琦在运用“圣于诗”评价李白时完全从艺术性的方面去考虑,将原有的儒家政教文学的一个概念转换成为了一个艺术评价的概念,没有拿政治标准去衡量,这是对“圣于诗”的超越。他对《于阗采花》(李白)“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一句注释道:
琦按:昭君事,本是画工丑图其形,以致不得召见。太白则谓“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熟事化新,精采一变,真所谓圣于诗者也[2]231。
对《白头吟·其二》(李白)“城崩杞梁妻,谁道土无心”句注释道:
《论衡》:传书言,杞梁之妻向城而哭,城为之崩。言杞梁从军不还,其妻痛之,向城而哭,至诚悲痛,精气动城,故城为之崩也。夫言向城而哭者,实也。城为之崩者,虚也。城,土也,无心腹之藏,安能为悲哭感动而崩?太白“土无心”句,似借其言而反之。用古若此,左右逢源,非圣于诗者不能。
“熟事化新,精采一变,真所谓圣于诗者也”,“用古若此,左右逢源,非圣于诗者不能”两句评价看重的是诗歌创作中典故的创新使用,因为创新使用了典故所以才“精采”和“左右逢源”,突出的是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强调的是诗歌达到意境效果。王琦赋予“圣于诗”艺术的特质,艺术评价取代了政治评价,表达了作者由政治评价向艺术评价转移的倾向,是对朱熹“圣于诗”理念的超越。
综上所述,王琦之所以能够以辑注《李太白全集》、《李长吉歌诗汇解》赢得时誉,究其原因,在学识、功力之外,则是他独特的说诗视角决定的。正由于他极高的学术造诣和艺术理解能力,方才取得“一注敌千家”的成就,而“仙鬼才华穷二李”亦非虚言。王琦生活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之下,处于清代各种文学观念和学术潮流兴盛之时,创造性地以“情景交融”思维和文学性的“讽谕”观照诗学,这是他取得巨大成就、突出前人的原因,而他在这个过程中的说诗理论和方法在诗学史上也是极具价值的。
[1]程国赋,蒋晓光.清代王琦生平考证[J].文学遗产,2008,(5):145-148.
[2]李 白.李太白全集[M].(清)王 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唐)王 维.王右丞集笺注[M].(清)赵殿成,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5.
[4]陈伯海.历代唐诗论评选[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7.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17.
[6](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682.
[7](清)王夫之.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
[8]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1955:47.
[9](清)王 琦,姚文燮,方扶南.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元)陈 澔.礼记集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3.
[11](南宋)朱 熹.孟子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3.
[12](清)孙诒让.周礼正义[M].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南宋)朱熹.诗经集传[M].(清)方玉润,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
[14]郁 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79.
[15](清)黄叔琳.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李 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0:456.
[16]曹 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9.
[17](南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 326.
A Study of Wang Qi's Poetic Thought
JIANG Xiao-gu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Wang Qi,a famous scholar in Hangzhou area in the first half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accomplished two masterpieces named“The Complete Collections of Li Bai by Wang Qi”and“The Compilation and Annotations of Li Changji's Poems”.His mature poetic thoughts were fully demonstrated by theses academic annotations.Wang Qi used the scene theory and Confucian poetics to annotate poetry,and broke through the previous theories by his own interpretations.While using the scene theory,he tended to the amalgamation of sentiment and scene and in terms of the Confucian poetics,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rtistic quality of poetry,these constituted his two major poetic thoughts.
Wang Qi;poetics;scene theory;Confucian poetics
I206.2
A
1008-3634(2011)04-0087-06
2011-04-08
蒋晓光(1984-),男,湖北钟祥人,博士生。
(责任编辑 蒋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