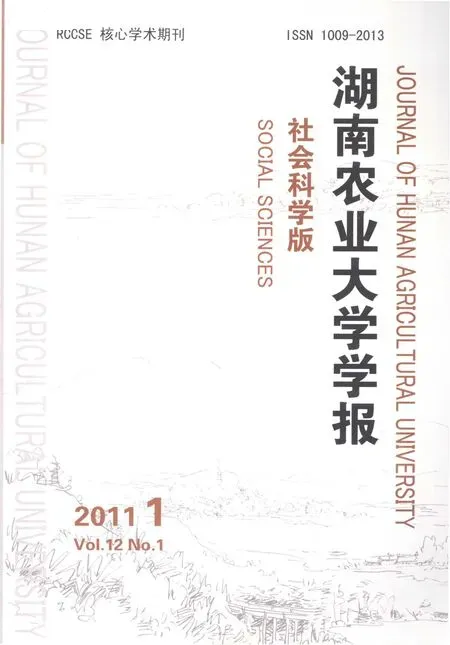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性合谋及特点
——基于A、B两县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
2011-04-08郑文换
郑文换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性合谋及特点
——基于A、B两县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
郑文换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基于对中西部两省份两个县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推行情况的调研,发现无论是基层执行方还是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农民,两者均借新农保政策获益,并在最低程度上落实了新农保政策。研究发现新农保政策(制度)结构本身为这一合谋提供了驱动力量,同时,制度性遗产——双方之前形成的互不信任的互动模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合谋。
制度性合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结构;制度遗产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reading process of the new rural pension policy, and found that both the primary executive body and the peasantry benefited from the process respectively and the policy is also carried out to a least extent.The mechanism is the institutional energy, namely policy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pattern between the primary executive body and the peasantry, which drove and finished up the collusion.
Key words:institutional collusion; rural society;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heritage
一、问题的提出
自 1991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以来,中国社会保障领域逐渐进入一个社会保障政策兴发期,国家级的社会政策纷纷出台,覆盖人群范围也逐渐扩大。最近几年来,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驱动下,农村人口也被纳入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来,国家于2009年9月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即《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其中规定“2009年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在全国普遍实施,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
因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要求,农村也具有了越来越紧要的政策位置。在农村老龄化、贫困现象严重的现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以下简称“新农保”)作为连接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中间环节,其基层政策执行效果可谓关系重大。实际上,在国家政策出台以前,已经有不少地区自行开展了有政府财政补贴的新农保试点工作①;对于某些地方来说,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已有几年时间,应该可以对新农保政策的实施过程及其引发的社会后果进行初步研究,但目前关于新农保政策的出版物多是宣传性的新闻报道以及政府宣传资料,或者是对某地新农保试点工作的归纳性整理,而实质性政策实施过程研究还很少,由此,笔者拟在实地调研所获得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新农保政策的实施过程进行分析。
本研究基于 2010年春对中西部两个省份两个县(A县和B县)的新农保工作实施情况的调研资料,发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两县的新农保参保率普遍都很高,但绝大多数参保农民都选择当地最低档参保。根据A县C地的统计数据,该地各村综合参保率分别高达60%-95%(数据来源于A县C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统计表,2009-07-20),但是绝大部分参保人选择的缴费档次是最低档②,其比例高达96%-100%,18个村中选最低档的比例占全部参保人的98%(数据根据A县C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统计表(2009-07-20)的相关数据计算而来)。这一基本事实折射出新农保政策实施中的一个困局:一方面是参保率较高,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选择政策的最低档缴费。这导致政策只能在低水平上平铺开来,缴费人群的分布呈现极度偏态。然而,这一困局并没有招致农民不满,也没有引起基层执行人员的忧虑。
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某些因素导致政策变形这一论题并不新鲜,一般来说,在研究政策执行的文献中,政策扭曲的可能来源包括基层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政策执行环节链条之间关系等方面,比如行政执行亏空等等。[1]根据调研地区的情况来看,试点地区的追求目标是参保率,并且通过对参保率的“任务分解”、“层层加压”、“自我加压”、“目标考核”等手段确保自下而上行政层级汇总上来的参保率能达到或超过上一级政府原定目标率。因此,在参保率这一硬性指标的考量下,自由裁量权和执行环节链条引发的政策变形问题并不显著。
新农保政策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向社会的延伸,这一延伸过程首先表现为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在国家和社会关系方面,政治社会学家(如杜赞奇,1994)强调处于国家和社区之间的“经纪人”(broker)的作用。[2-4]国内对政策执行的一般看法也与此相关,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将政策变形归咎于基层执行人员的以权谋私,并且认为越是底层的官员越不规矩。但是,新农保政策推行过程与上述解释明显不同的是,新农保执行人员受到诸如“事钱分开”、养老金发放经由银行系统等条件约束,其以职权谋一己之私利的现象在村一级及乡一级受到抑制。同时,不论是“自由裁量权”还是“经纪人”的概念,均表现出强烈的行动者(actor)取向,但实际上,单纯的行动者取向的视角并不能充分描述出新农保政策的矛盾困境。因此,需要对这一现象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意义上的解释。本文在“合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制度性合谋”这一概念来阐释上述现象。
二、对新农保政策执行过程的研究视角:制度性合谋
对于“合谋”现象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大块。首先是经济学领域,国内经济学领域内利用这一概念进行的研究比较多,[5]该类研究对于合谋的分析一般是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分析。此外,还有些研究将委托-代理理论框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对政企合谋[6]、政策走样[7,8]等领域。
其次是组织制度主义领域内的研究,周雪光利用组织理论中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了中国基层政府间的合谋行为,认为这一合谋行为的出现是组织所处制度环境和组织结构的产物,具有广泛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已经成为了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并通过对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激励强度与目标替代、科层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人缘化三对悖论的理论分析,将这一行为出现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过程与行政过程分离的结果,同时也是集权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所强化的结果。[9,10]
第三块是社会学中的布迪厄的“合谋”概念分析。无论是经济学中的“合谋”理论还是周雪光的制度分析,其共同点在于产生的合谋现象都具有非常强的双方沟通、采取一致行动的特点,比如委托-代理中代理方与监督方合谋对付委托方以及基层政府合谋共同应付上级政府的检查等等。但是,实际上,合谋现象本身还有另外一面,即双方在利益并不一致甚至相互违背的情况下,并不经过双方有意的沟通交流,也会有合谋现象的产生。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分析过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合谋现象,布迪厄之“合谋”概念来自于对“符号暴力”的分析,其具体含义是在权力行使语境中对上下阶层间通过符号资本的运用完成权利行使。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力的实施只有通过那些并不想知道他们臣属于符号权力甚至他们自己就是在实施符号权力的人的合谋才能实现。[11-13]“合谋”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特点。在布迪厄这里,这一合谋并不是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彼此有意识的思考的结果,布迪厄认为符号资本是一种沉默的、柔性的暴力,掩盖了赤裸裸的暴力,这一暴力的实行是通过下层阶级的“误识”以及跟上层阶级的“合谋”完成的,“误识”是符号实践造成的人们注意力的一种偏离,“这个错误知觉把这些实践合法化并因而有助于这些实践嵌于其中的社会秩序的再生产。”[14]通过“误识”这一机制,双方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暴力过程就完成了权力行使过程,表现为一种合谋。
在社会政策领域,也存在着类似布迪厄描述的“合谋”现象,这种“合谋”虽然不能明确地归结为符号权力行使语境,合谋的形成也不是“误识”机制发挥的作用,但是,在社会政策向目标群体渗透过程中的行动者之间彼此关系的“不自觉”、结果方面的“合谋”表现以及这一过程的结构色彩方面,却很类似。具体到新农保政策经由基层执行方向目标群体——农民——渗透的过程来说,作为行动者的基层执行方和作为目标群体的农民都在其中体现出了作为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但两者并不存在有意识的“双方协商”的互动过程,而是在各自的逻辑指导下参与了这一过程,并且使这一政策过程得以完成;同时两者都从政策实施过程中获得了益处,农民利用“以小易大”的计算公式参与并获利,而基层执行方则在“业绩指向”的逻辑下参与这一过程,结果在事实上两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均借新农保政策实现了各自的利益或业绩任务。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与权力行使语境下的合谋不同的是,两方行动者之间并不存在“误识”这一弥合机制,而是在明确的互不信任的状态下利用新农保政策(制度)的实施过程完成了“合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将两者弥合在一起的是新农保政策(制度)③本身,并因制度性遗产(双方互不信任的互动关系)而得以实现。因此,本文将这一“合谋”称为“制度性合谋”。
在探讨“制度性合谋”概念之前,有必要对何为制度进行一下明晰。无论是理性选择学派的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理论)的制度主义还是历史制度主义,三者在制度定义方面还是存在某种程度的交集,即制度可以是正式的、成文的规则,可以是不可见的、隐性的约定俗成的规范或既定激励结构条件下行为人的系统化策略(奥斯特罗姆,2004),以及组织方式(organizational form)的结构关系④。在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方面,虽然存在孰重孰轻的不同,三者都承认制度对于行动者的约束作用。[15]本文将在两重含义上使用制度性合谋这个概念。第一重含义是,政策的结构本身成为合谋实现的前提和驱动力量,政策的开展过程本身即带动了基层执行方业绩以及资源的结构化,其制度模式本身成为基层执行方、农民参与进来的必要条件。第二重含义是,基层执行方和农民群体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的制度遗产(institutional legacy)⑤——互不信任⑥的互动关系模式——对新农保政策执行过程施加的控制,使得这一合谋过程得以完成;中国官民之间的张力体现在基层机构对农村资源的抽取过程的斗争中,尽管农民群体中普遍承认“皇粮国税”的合法性,但是,长期以来的一平二调、乱收费、干部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负面体验,使得农民将基层执行方的公家形象私化,因此,即使在新农保基层执行方在推进政策过程中并未侵犯农民利益的条件下,农民群体即使在自身也确实需要农保制度覆盖的情况下,宁可选择参加商保,也不会将富裕的钱投在新农保制度里。因此,制度性合谋,与周雪光的结论“共谋行为是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的产物”类似。
三、新农保政策的推行过程分析
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新农保政策的任务目标是“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采取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农村居民普遍参保;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从对国家及地方新农保政策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出,政府力图将这一制度建立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持续的、能解决中青年农村居民将来养老问题的制度。
从试点地区经验来看,新农保政策的扩面速度非常快,新农保覆盖率非常高。如果仅从参保率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地方新农保政策的推行非常成功,农民参保非常积极。但是,在这一表象的背后,可以发现新农保推行过程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是基层执行方想尽办法、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参保率;二是农民经过最初的疑虑阶段后,也的确是积极参与。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新农保政策的推行过程中,促成双方合谋形成的机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新农保政策结构本身给双方无协商沟通的合谋结果创造了前提条件并提供了驱动力量;另一个是基层执行方和农民群体之间之前形成的制度遗产——互不信任的互动模式最终形成了合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合谋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执行方素质低下或者农民群体的目光短浅等所谓小农意识造成的,而是制度性力量驱动的结果。
首先,政策结构本身为合谋创造了前提条件并成为驱动力量。新农保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从资源结构来看,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拨款(国家试点地区)或上级(省、市试点)出大头或全额拨款;个人账户由农民个人缴纳,由县级统筹。从制度结构跟基层执行方的业绩关系角度来看,基础养老金的业务处理非常简单,由财政专户通过国有银行系统发放到农民养老金领取账户中,但需要注意的是,财政补贴的基础养老金对于吸引农民参保、提高参保率非常关键,对合谋这一过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而个人账户与参保率则与基层执行方的业绩关系极为密切,在这一逻辑里,财政补贴和个人账户彼此成为彼此的必要条件,两者相辅相成,为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提供了驱动力量。
对于基层执行方来说,参保率是其整个业务流程中追求的中心环节,参保率是将从上流入的资源——基础养老金和从下流入的业务量——参保农民个人账户量的增加能够很好结合起来的一个点,高参保率这一指标能很好地体现基层执行方的主要业绩。因此,基层执行方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提高参保率,比如严格贯彻“捆绑缴费”和“多缴多得”的原则。
但是,高参保率这一指标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绝大部分的参保农民都选择了最低档缴费。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参保农民都选择最低档缴费呢?是因为目光短浅的小农意识导致的吗?是因为家庭经济水平低下导致的吗?如果是因为所谓小农意识,那么就意味着农民群体不想接受任何缴费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如果是因为经济水平低下,那么也就意味着农民群体不会参加任何缴费高于新农保缴费的商业保险项目。但是,事实否证了上述两种解释。参保农民中参加商业保险的人也并不少见,笔者所做的近 40份问卷中就有五六个人给自己或家人买了商保,同时据经办人员的了解,许多农民都买了商保,至今商保业务在这些地区都很活跃。就笔者在两县访谈的案例来看,买商保(主要是太平洋保险、新华保险)一年需要花费上千到近万元不等,并且需连续缴满 10年。那么,农民在选择进入新农保过程中的考虑是什么呢?A县在跟国家新农保政策接轨之前,是按上年度农民平均收入的10%—30%设立缴费档次,但是农民并不了解、也并不按这一规定算帐、缴纳保险费。访谈发现,农民采取的计算公式是“如果家里有两个人交费,一年缴费400元,1个老人一年就能领到700多元,两个老人领就是1000多块钱,700元>400元、1 000元>400元,所以是合算的,应当参加。”反映了农民“以小易大”的理性逻辑。该村某位老人尽管曾在乡镇任公职,但对于缴费也充满忧虑(家里其他人是农民),他及其他农民担心养老保险费年年涨,去年新农保每人交100多元,今年就交200元/人;他们还举例说,新农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费就由10元长到20元再长到了30元。农民计算比例的公式与政府政策的调整公式不一致,政府是按上年度农民的人均收入为基数计算保费,而农民是按上年缴纳的保费为基数计算的,对农民来说,新农合缴费由10元长到20元,增长了100%;他们就担心养老缴费第二年长到230元或250元,对调查人员反复强调保费维持在 200元左右就行了。
其次,制度遗产造成了农民的投机行为以及基层执行方追求高参保率的动机。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并不是农民的小农意识和经济水平低下导致了绝大多数农民选择最低水平缴费。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对新农保政策采取这种“以小易大”的投机性行为呢?这涉及到制度性合谋的第二重含义,即基层执行方和农民群体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的制度遗产(institutional legacy)——互不信任的互动关系模式。
作为政策对象的农民在传统上被看作被动的接受者,认为他们对政府的政策会感恩戴德。但是实际上,农民基于数十年的经验,常常对政策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王思斌,2005)。调查中,农民普遍认为新农保这个政策“事儿是个好事儿”,但就怕办不好。根据深度访谈发现,农民对于制度(政策)的理解是跟农民的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访谈的1个案例(32岁,女)明确说“不关心政策上面的事”,她对于政策的体验是与她跟村干部打交道中得出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她举例说当她因为独生子女补助的事情咨询村干部时,对方往往敷衍她,因为村干部给她的钱少于邻村,也少于她在镇上看到的宣传资料上的记录,于是她就认为村干部在骗她,再加上她并不清楚现在缴费将来能拿多少钱,所以对由村干部经办的新农保并不信任,只是随大流,交了最低档的钱。她还谈到在参与了修建村休闲广场劳务后,一直没能领到钱,所以对村干部不信任。她对乡镇、村干部不信任,反而更信任银行系统,在县-乡镇-村这一途径与县-银行这一途径进行选择时,她选择银行,其理由是“银行是公家的”,暗含的意思是乡镇-村这一基层行政序列不是公家的。这一个案例反映出来的对乡镇、村级干部的不信任并不是个别现象。访谈发现,随着交流的深入,农民一般会流露一些“真心话”出来。在问及他们对新农保政策的看法时,很多人都说“这个事儿倒是好事”,但不愿经过村干部的手进行操作,给出的理由是“村干部老换(人)”。其实,“村干部老换”这句话并不是希望村干部不换人,而是希望“最好不经过村干部手”,因为他们认为村干部换谁都一样,总担心自己缴纳的钱会被挪用。而且不论是农民希望养老金的发放走银行系统、不走基层行政系统,还是宁可参加似懂非懂的商保⑦而不理会社保“多缴多得”这些情况,均折射出这样的事实,即在农民眼中,“公家”已不再是“公家”,“经营性质”的单位却成了“公家”。“公”“私”之分别不在于制度规定、所有权性质,而在于农民的日常体验。农民因为跟乡镇、村级干部(比起跟县级以上干部)的接触相对频繁,从公事中看到了太多的私事,因此将国家行政序列的基层机构“私化”了。而银行系统、保险公司等经营部门因为业务的技术化、流程化和硬化,使得这些机构在农民意识里“公家”化了,即使在银行系统领取养老补助时钱差了 10元钱时,农民也不会觉得是银行私自扣下了这 10元钱,而认为是上面就没给银行这个钱,“这 10块钱可能是上边替农民交(玉树)地震捐款了,就算是这样,也该给在折子上记上一笔啊”⑧。调研中还发现,即便是对作为“购买服务”的帮办人员,农民也不信任他们,而这些人员也往往自动将自己身份行政化,以使自身区别于农民。
基层执行方并不是不了解农民的担忧,但是某些人对农民的印象也如同农民看待他们一样不好。一般来说,乡、村干部对农民的印象是农民是不服管束的,比如B县一乡干部认为老百姓“刁”,认为国家照顾农民,免除农业税还增加农业补贴,现又有低保等补助制度,但并没有得到农民方面应有的感恩回馈。他举例说在农村卫生方面(因为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如果不给农民工钱,农民根本不管自己村子的卫生状况,“你说让他义务劳动吧,根本不可能,他出工一天要80块钱”。而另一村长认为,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总的来说属于“政策超前”,谈到的例子是在征地事情上,村长的权限越来越控制不住农民的举动,村长越来越控制不住农民。还有一个基层执行方的司机在去调研的路上跟笔者抱怨农民无知,说明明新农保政策是为他们(农民)好,他们反而不领情,还得追着他们参加。
总之,当地农民与基层执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互不信任,但是,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基层执行方和农民群体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互动模式的形成并不是新农保政策推行过程中双方间的不良互动造成的,无论是农民群体对基层执行方的不信任、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体验描述和担心,还是基层执行方对农民群体的不信任、不服管束、“刁”、无知、小农意识的描述,都不是来自新农保政策推行过程中互动体验本身,而是来自于以往双方打交道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投射到了新农保推行过程中。这种不良互动体验和新农保推行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因此,可以说,基层执行方和农民群体间以往的不良互动形成的互不信任的制度性遗产导致了双方在新农保制度上在缺乏互动的情况下,各自做出了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基层执行方和农民群体利用新农保政策的推行,在双方没有沟通协商的情况下,都各自实现了自己的利益,但同时他们还是在最低程度上落实了这项政策,形成了类似于布迪厄的无意识、无事先交流沟通的合谋,跟布迪厄的“误识”机制的不同,首先表现在制度结构(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由地方执行、农民自愿参保)本身给合谋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和驱动力量;其次是制度性遗产,即双方以往体验形成的互不信任的互动模式,最终促成了合谋并赋予其不同于其他“合谋”现象的特点。
四、结语
影响政策实施成效的因素很多,但是这些因素作用的大小并不是普适性的,而是因时因地的不同而作用不同,在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那里,这表现为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制度化影响(周雪光,2003);在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那里,表现为制度对行动者策略组合的结构化约束;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表现为背景脉络环境(context,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制度),具现着一种制度偏见(institutional bias)。尽管有上述不同,但是,制度主义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行动者与后果之间直接关联的看法和理论解释,摒弃了行动主义的研究取向,具体到新农保政策的推行过程,制度主义的看法推翻了执行方素质低下的解释;同时也否证了对农民群体所谓小农意识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正是政策(制度)结构本身以及政策实施的环境脉络中负载的制度性遗产积极促成了基层执行方和农民群体之间“合谋”的完成。因为制度结构与制度性遗产两者均先于新农保政策推行中产生的“合谋”现象,表现出了更强的因果关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研究认为,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的制度结构为“合谋”提供了动力基础,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本身就有问题,模式本身是中性的,我们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及其推行过程对其成效进行评价。如果基层执行方和农民群体之间互动关系良好,就可能不会在执行中发生这种政策目标偏离。尽管在新农保推行过程中,存在这种目标偏离现象,但是新农保政策本身又具有“诱导性政策”的积极意义,应会使得农民群体逐渐积极参与到新农保事业中来。
注释:
① 从2003年开始,北京、江苏、陕西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00多个县(市、区、旗)自行开展了有政府财政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青连斌,《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有益尝试——对陕西省宝鸡市‘新农保试点的调查’》,中国养老金网,2010-03-05)。
② 国家新农保缴费档次分5档,分别是100元、200元、300元、400元和500元。但是在国家政策出台之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新农保政策,在跟国家政策接轨之后,仍将最低档规定为200元(A市)。
③ 在制度和政策两者关系方面,Pierson(2004)将重要的政策亦视为重要的制度,因为这些政策比起政治制度/实体更为直接和紧密地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March等学者(1984)认为政策一旦被采纳就会被嵌入(embedded)制度之中,通过影响政治参与者的注意(attention)和意愿(aspiration)来影响其未来的行为。由此来看,制度与政策均对人的行为具有某种约束作用,两者具有重叠的内容;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是将新农保政策当作因变量来分析的。
④ 比如 Skocpol(1995)声称对制度采取组织实在论者(an organizational realist approach)的视角,将其视为各种制度和各种组织之间的交流联络和行动的实际类型,而不是基本将其视为价值、规范或者正式规则。
⑤ 跟Collier(2002)在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一书中提到的“legacy”略微不同之处在于,本文的“制度性遗产”指的是更具有偏社会学意味的双方间的信任关系问题。
⑥ 农民与基层行政执行方之间的信任问题不再单纯是心理问题,而是具有了社会化行动的稳定特点,因此是一种制度遗产。
⑦ 在笔者就新农保进行调研期间,许多农民反而向我咨询商保的事情。
⑧ 因在村里调查期间,反映钱少发的农民有3位(据他们说村里还有其他人也是这样),笔者就此事两次询问了A县C区相关人员,该人的解释是 “可能那10块钱是邮局(当地发放养老金业务由邮局承担)留下来看账户的吧”。
[1] 米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2] 埃里诺·奥斯特罗姆.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评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3] 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 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5] 罗建兵,许敏兰.合谋理论的演进与新发展[J].产业经济研究,2007(3):56-61.
[6] 聂辉华,李金波.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J].经济学,2006,6(1):83-87.
[7] 谭秋成.农村政策为什么在执行中容易走样[J].中国农村观察,2008(4):4-19.
[8] 王思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政策过程分析[J].文史博览,2005(5):22-24.
[9]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 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8(6):5-25.
[11] Collier,Ruth B.and David Collie.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the Labor Movement,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M].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2.
[12] Skocpol,Theda.Why I Am a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J].Polity,1995,28(1):103-106.
[13] Pierson,Paul.Politics in Time: History,Institutions,and Social Analysis[M].U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14] March,James G.and Johan POlse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4,78(3):734-749.
[15] Immergut,Ellen M.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J].Politics & Society,1998,26(1):5-34.
责任编辑:陈向科
Institutional collus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rural pension: Based on the policy spreading process in County A and County B
ZHEN Wen-hu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671, China)
C913.7
A
1009-2013(2011)01-0026-07
2011-01-05
郑文换(1974—),女,河北定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