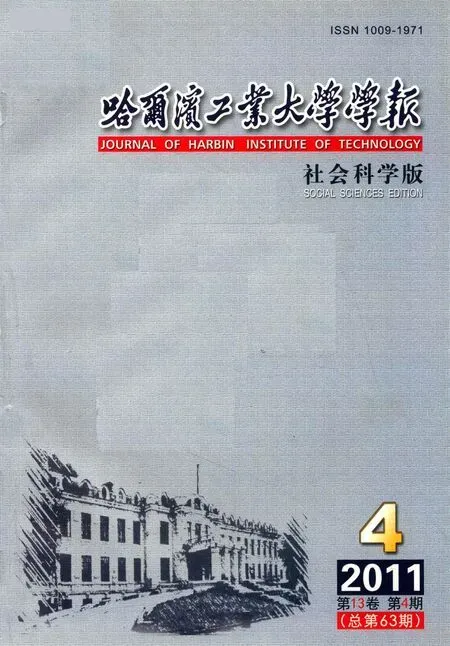建立法官、民意与判文解释三位一体的刑事司法适用机制——化解司法和民意冲突的第三条道路
2011-04-07付其运
付其运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建立法官、民意与判文解释三位一体的刑事司法适用机制
——化解司法和民意冲突的第三条道路
付其运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在我国,司法解释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判文解释不属于司法解释,因而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在现实生活中,法官的能动性常常受到抑制,多数法官只是机械地适用法律,这就远远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的司法需求。这样一来,严格依法办事的结果与“民意”相背的情形难以避免。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吸纳民意已成为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参与司法和对司法实施监督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正确认识司法实践中运用判文解释的必然性,探讨其与吸纳民意的内在关系,并通过法官建构判文解释以有效吸纳民意,是化解社会矛盾和司法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法官;判文解释;建构性;民意
一、判文解释:司法实践的必然需求
如何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已成为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一些引起媒体热议的刑事案件直面公众的“拷问”,显示了司法机关与民众在法律理解和适用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偏差。案件的判决结果和法律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都触动了民众的敏感神经和道德情感,这其中涉及司法判决如何面对民意与法官如何吸纳和体现民意。审判案件是法官的职责,司法判决以准确合理地适用法律为前提,而适用法律需要以解释作为中介环节,如何准确合理地适用法律与法官对刑法的理解和阐明息息相关。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法官有权解释法律,这一点如我国学者所言,“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司法解释就是法官对制定法的解释,这是明白无误的。尽管在他们的法律里可能找不到一个司法解释或法官释法的字眼,但这几乎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1]。
在我国,“依照法律和司法实践,法律解释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法律解释,被称为司法解释……其明确依据主要是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另一种是由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判决中对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所作的解释,可称之为判文解释”[2]23。
根据上文学者的界定,判文解释是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判决中对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所作的解释。笔者认为,此定义虽然基本阐明了判文解释的含义,但不够周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7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至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7条的规定不难看出,我国法院合议庭的组成不仅有法官而且有人民陪审员,显然人民陪审员不属于法官;并且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这里的审判员显然是法官。这样,司法实践中对案件所适用的法律作出解释的主体,可能是法官或者由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也可能是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的法官。但是,在审判实践中,我国合议制一直存在着名为合议庭审判、实为单个法官独自办案、合议庭其他人员署名的做法,大多数案件实际上只有一位法官担任承办人,由承办人对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负重要责任。因此,审判实践中合议庭对案件所适用法律所作的解释等同于法官对所适用法律所作的建构性解释。即使是实行实质的合议制,合议庭对所适用法律所抉择的解释也是多数法官根据多种因素所达成共识而建构的解释。因此,本文认为审判案件的法官是建构判文解释的主体。判文解释应该这样界定:判文解释是指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依法审理案件时在裁判文书中就本案如何具体适用法律所作的解释。各级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针对本案案件事实就如何适用和解释法律及其理由进行分析和阐述,才是在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但是根据200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换言之,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才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法律所作的解释被称作司法解释,它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判文解释在我国就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法官的能动性受到抑制,大多数法官只能机械地适用法律。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没有法官对法律的合理解释,司法判决有时不能被公众所接受,法律正义就不能得到彰显。没有理解和解释,法官不可能作出合理的判决,并在司法判决中叙明判决理由。成文法向判决的转换不仅是一个事实过程,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它是有生命主体的参与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不可缺少的便是对法律与事实的理解和解释[3]。
因为法律解释与个案之间具有天然的关联,法官在适用法律处理具体案件时必然要对所适用的法律进行理解并将其在判文中以解释的形式进行表现,否则司法权的行使就无法实现。不仅如此,而且法官解释法律时需要考虑公众的可接受性。在司法实践中,只有为公众所接受的法律解释才是合理的解释,只有合理的法律解释才有合理的判决,也只有合理的判决才是可以接受的。正是这种对刑法文本理解和解释的必要性及对其合理性的追问构成了法官建构判文解释的原因和动力,也是判文解释存在的根据。因此,判文解释虽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解释,但它是司法权的当然组成部分[2]24。
承认判文解释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法官在审判案件时才能发挥能动性,才能根据案件事实对法律文本进行合理建构,才能实现现实的正义。正如有些学者所言,“法律解释的实质是法官活化法律,司法职业的实质是法官塑造人类正义生活。法律的生命开始于职业法官的职业法律活动,法律解释的展开过程是法官赋予法律以生命的过程,是法官恢复其职业灵魂、获得其职业生命力、实现其职业价值的过程,是法律的正义价值与法官的职业价值实现融合统一的过程,是人类由此在向彼在善的筹划过程。在这里,解释法律不仅成了法官唯一的社会生存方式,而且还成了法律获得生命的唯一方式。”[4]
二、判文解释①为行文方便,下文在与“判文解释”同一意义上使用“刑法解释”、“法律解释”。的建构性特征及其理论根据
自从法律现实主义者们揭示了司法实践的真实面目之后,法官的“自动售货机”形象已被破除,“概念法学”也已经破产。无论如何,当下已经很少有人会相信,司法判决不过是一些演绎前提的逻辑后承。即使如德沃金那样推崇“法律帝国”、坚信“唯一正确”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司法判决毕竟是一个“建构性解释”的产物,而无法仅仅依靠逻辑操作取得[5]。而实践中司法裁判的过程就是解释的过程,裁判的结果就是解释的结果,因此法律解释同样是“建构性解释”的产物。作为哲学诠释学创始人之一的施拉依马赫曾说:“我们(指解释者)可能比作者自己还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6]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理解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复制,而是对原始文本的一种创造和建构。
建构判文解释不是消极、被动接受刑法文本思想的过程,而是“解释者必然对其有一种意义期待和筹划”[7]774。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所有正确的解释都必须避免随心所欲的偶发奇想和难以觉察的思想习惯的局限性……谁想理解某个文本,谁总是在完成一种建构。在文本意义最终被明确地确定之前,各种相互竞争的筹划可以彼此同时出现,解释开始于前把握、前见,而前把握、前见可以被更合适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筹划和建构的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在理解文本时……而是要求我们对他人的和文本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8]344-347。“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8]383。
理解判文解释的建构性,首先应理解“建构”(tectonic)一词,它是一个建筑学的词语。建构与解构相对,解构着重文本间的剖析、解析,而建构着重系统的建立,其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认识和理解不是独立于个体之外的客观存在,是主体通过其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包括主体间的互动和对话,逐步形成和建构起关于事物本身的知识。随着人们对认知规律研究的不断深入,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即“互动理论”和“对话理论”在社会学和法学领域逐渐盛行。将建构主义理论观点特别是“互动理论”和“对话理论”运用到法律解释领域,可能会有利于深化我们对法学的认识。在法律解释领域,建构主义观点认为,知识包括有关法律和犯罪的知识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绝对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律的解释和理解是一定地区范围内人群共同体共同认同的结果。正如伽达默尔所认为的,“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视阈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阈,使它与其他视阈相交融。”在视阈融合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9]。因此,判文解释因其建构性特征理应是一定地区范围内人群共同体共同认同的结果,是与他者视阈相交融的结果,是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的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达至此种结果的前提就是一定地区的人们在某种可行的方式下进行“互动”和“对话”,由此方能形成这一地区的人们大致可以接受的结论和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判文解释是立足于人们共同“互动”和“对话”的解释结论,其作为司法实践的必然需求有其自身的理论根据,同时因其自身的理论根据而使其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经过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判文解释绝非单纯的解释技艺问题,而是一种刑法解释理论的创新,其理论根据为“互动理论”和“对话理论”。
第一,“互动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杜威提出的核心观点。杜威认为,“社会由互动的个人组成,他们的行动不只是反应,而且还是领悟、解释、行动与创造。个人不是一组确定的态度……社会环境不是某种外在静止的东西,它一直在影响着和塑造着我们,但这本质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为环境是互动的产物。”[10]也就是说,社会即由于个人之间的互动过程而产生的思想与感情的共同体。社会不仅通过交往、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交往中、在沟通中生存。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交往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式……保证人们参与共同理智的交往,可以促成相同的情感和理智倾向[11]。我们将杜威社会学思想的核心观点运用到刑法解释领域,并将之作为刑法解释的理论根基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体现共同的价值和共识。因此,法律解释结论必然是社会成员“互动”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学者、某个法官或者某个人的主观之见。
第二,“对话理论”是哈贝马斯提出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法律设定的“权利体系”需要通过公共讨论和对话来阐释和塑造,权利体系的内容不是不证自明、一成不变的。他认为,民主的立法程序和公正的司法程序都是在解释、塑造和阐明权利体系。哈贝马斯的理想是把普遍理性根植于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沟通交往的行为之中。他尤其重视对话(或商谈)理论,即真正能寻求真理或达成共识的理性对话理论[12]39。
“对话”和“互动”是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达成合意的一种方式。在杜威那里,只有“互动”,社会才得以生存,社会共识才得以达成;在伽达默尔那里,“互动”就是“视阈融合”,是解释者现在视阈与过去视阈融合的过程,也是自我视阈与他者视阈融合的过程;在哈贝马斯那里,“互动”就是“对话”,就是沟通和商谈。虽然他们表述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人类社会,只有通过“对话”和“互动”才可以消除误解、彼此的不信任以及语言的歧义,才能增进人们对事物、规范的理解,从而达成某种利益的平衡、双方心悦诚服的妥协和共识。①这种共识可能是罗尔斯提出的“多元的、重叠的共识”,也可能是我国刑法学家陈忠林提出的“常识”、“常理”、“常情”。这样,立足“互动”和“对话”理论根基的法律解释才具有合法性,依据其作出的司法判决才能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受。正如学者所言,“刑法文本的意义不是由其作者即立法者所决定的,而是由处于不同境遇之中的解释者和刑法文本的互动作用所决定的。”[7]775
三、刑事司法体制内法官、民意在判文解释建构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基础性地位
(一)刑事司法体制内法官在建构判文解释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
1.法官的良心——建构判文解释的主体的内在支点
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陈忠林指出:现代法治归根结底应该是人性之治、良心之治。在很多会议或讲座中,他反复强调:“现代法治,归根结底应该是人性之治、良心之治,而绝不应归结为机械的规则之治”;“我们要实行法治,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但绝不能将法与理对立起来,绝不能显失公平、绝不能违背常理、绝不能不顾人情”;“我们的(法律)是人民的法律,绝不应该对其作出根本背离老百姓所共同认可的常识、常理、常情的解释”;“我们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和人民群众,包括刑事被告人,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过程”;“我们的司法人员只能为了维护法律所保护的价值而维护法律的权威,但绝不能仅仅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而维护法律的权威”[13]。我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永升也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律职业人,对刑法的解释要从老百姓所共同认可的常识、常理、常情的立场来解释。李永升强调的良心或者“常识、常理、常情”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灵魂,因为良心是特定社会中的人性、人心最本源的形态,社会的最低要求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共识。不论何种形态的法律,凡是与人类的基本良心或者“常识、常理、常情”相背离的法律,都不可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良心或者“常识、常理、常情”是建立现代法治最基本的价值基础和社会伦理基础,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是非标准的准则。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官只有坚持“人性”、“良心”或者“常识、常理、常情”在适用法律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根据自己的良心建构合乎民意的判文解释,才能保证该国的法治在真正反映人性需要、顺应时代要求、体现民心民意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2.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建构判文解释的主体的外在支点
在人类追求司法公正这一永恒的价值目标的过程中,司法公正要从一种理念倡导变为生动的社会现实,法官便是其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因此,法官适用和解释法律的过程就是实现正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保证法官形成内心的确信与合理性,显现为建构合理的判文解释以解决纠纷与实现公平正义。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是法官从事职业活动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社会道德在司法适用中的体现,它是国家司法部门中从事法律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运用法律解决社会争议时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它的目的是使法官能够运用法律正确处理和协调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以期达到定纷止争、维护公平正义的目的,保证法官凭自己的良心来解释和适用法律。这些道德规范在思想意识、品德修养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它是评价司法工作者职业活动正确与否的道德标准。根据2010年12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目的是保证法官正确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其中核心是公正、廉洁、为民。基本要求是忠诚于司法事业、保证司法公正、确保司法廉洁、坚持司法为民、维护司法形象。其第6、第19、第20条规定法官要热爱司法事业,珍惜法官荣誉,坚持职业操守,恪守法官良知,牢固树立司法核心价值观,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认真履行法官职责。法官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理念,强化群众观念,重视群众诉求,关注群众感受,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法官要注重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积极寻求有利于案结事了的纠纷解决办法,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根据上述要求,法官在建构判文解释时要凭良心或“常识、常理、常情”寻求一个合理合法的解释,要关注群众感受,这样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刑事司法体制内民意在建构判文解释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
根据判文解释和民意的内在本质,刑事司法体制内民意在建构判文解释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建构判文解释需要社会公众参与
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诠释学完成了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变,并且对法律解释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将法律解释从一个封闭体系带入一个面向现实生活世界多种因素并存的开放体系。同样如此,刑法解释结论的形成不再是一种孤立的对刑法条文的静态理解,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表现为一个科学、合理的建构过程。这一本体论转向越来越要求刑法解释理论具备面对现实生活的能力,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其目的就是获取一个合理性和正当性结论。对刑法解释结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追问成为当前司法话语的最强音。
正如我国有的刑法学者所言,“这些对热点案件的教义学分析却面临着两个无法克服的难题:第一,这些精细的教义学分析无法证明教义分析本身的正确性。当某一种教义分析得出的案件结论与其他教义分析结论不相同时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才具有妥当性,教义学分析无法自证。第二,教义分析的结论往往与一般公众对案件的期待和认同产生较大的偏差,司法机关对热点案件的定性与量刑难以为社会公众所接受。”[14]根据前文可知,判文解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来源于人类生活世界的内在原理和规律,这个原理和规律就是社会需要“互动”和“对话”。而传统的刑法解释恰恰缺少这一向度,而这一向度恰恰是人们形成规范共识和规范意义的正当性、合理性基础。否则,法律解释结论无论多么完美,都将缺少社会共同体理论根基,如同“海市蜃楼”,看起来虽然很美,但可望而不可即。
2.社会公众的参与赋予判文解释民意基础
在法学家对法律的理解中,我们可以典型地发现有一百个理解者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结论。期望任何一位法学家或司法工作者在他的认知视阈里全面深刻地理解法律,只能是一种奢望[15]270。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知识总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来阐述和立论的。而精英立场和行为并不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的合理发展以及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有时适得其反。某种程度上说,哲学诠释学将理解和解释问题从纯粹精英的视角中解放出来,成为历史的一种必然。商谈—对话理论则进一步将诠释学的普遍性引导到向操作化目标转化的人类实践领域。以往的诠释学是将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理解排除在外的。法学诠释学同样如此。直到今日,我们所关注的还主要是精英对法律的诠释,而对于民众视野中的法律几乎视而不见[15]203。在对法律理解和解释上,民众似乎只有接受精英教育的份,而不存在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看法。但是,必须申明,这是一种错误观念。世界是一个共同的世界,并且包括其他人的共在(Mitdasein)。它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总是自然而然地被预先设定为正当的。那么,这种正当性怎样由主体性的某种作为而证明呢?……所以,在这种方式下主体对世界的态度的可理解性就不存在于有意识的体验及其意识里,而是存在于生命的匿名性的“互动”里[8]321-323。同样,法律解释活动应当遵循这种人类生活世界规律,即通过不同解释主体之间互动和对话来理解和解释刑法文本。而主体间的互动和对话是指“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和法律家之间以及市民社会内部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16]49。
“实现沟通行动合理化最重要的途径是在建立共同价值规范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平等对话。人类社会的真理就是人们在理想对话情境下所达成的共识。”“对话是人们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交往活动;通过对话,人们才能相互沟通和理解;双方的愿望和要求都能成为对话的对象;每一方试图获得的东西都可以在对话中得到解释和认识,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考虑。”[16]51-52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的真理是一种共识真理,即参与交谈的所有人在理想对话情境下所达成的共识。其理想对话情境的程序设置要求有:一是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一切主体都可以参加讨论;二是每个人可以怀疑一切主张;可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愿望和看法;三是一切发言者在行使上述权利时,都不得受到支配议论场所内部和外部的强制力的妨碍[16]53-54。这样,社会公众的参与就赋予判文解释民意基础。
四、化解司法和民意冲突的第三条道路:建立法官、民意与判文解释三位一体的刑事司法适用机制
当前刑事司法领域的矛盾有不少是涉及司法和民意的冲突问题,如何化解此类矛盾,主要关涉司法(这里主要指判文解释)要不要吸纳民意以及如何吸纳民意的问题。正如苏力所言,“目前的争论其实不在于是否要吸纳民意,而在于如何吸纳民意,由谁吸纳民意,以及通过什么渠道吸纳民意。”[17]民意、特别是在司法领域的民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有时其表现为情绪化、娱乐化、群体极化[18]等特点。根据“静默的螺旋”理论,个体拥有一个多半是无意识的、可能源自遗传且根深蒂固的孤立恐惧。这种孤立恐惧使他们不断去确定,哪种意见及行为方式被环境所赞同或反对,以便采取哪种意见与行为方式[19]。这样,当一些“浪漫”、“冲动”、“激情”的民意诉求可能阻碍现代法治基本价值理念实现的时候,当民意与法理各执一词的时候,感性的民意与理性的法制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建构判文解释堪称为现代社会弥补理性主义与人类的情绪性倾向之间冲突和缺陷的一条康庄大道。在建构过程中,通过程序化的设计和民意调查制度的引入,神圣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进行联姻,彼此都得到了关照。这样既平息了民众的情绪,缓解了民众对法律信仰的危机,又将民众带有情绪化的倾向纳入法治的制度化轨道使社会的治理不至于脱离法治理性而陷入法治反面。
在西方,法律解释实践智慧是在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性、道德与法律、大众与精英、保守与灵活的互动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在尊重人们对已存法律形式崇拜与信仰的前提下,通过系统的、日常化的、制度化的法律解释活动,将新的法律解释规范融汇到古法的雅典形式中。这样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和尊重。哈耶克指出,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都可以预期的社会中,强制力可以降到最低限度[20]。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将邀请公众参与司法解释的工作制度化了。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关于审理侵权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时,将向全民征求意见行为提高到司法为民的高度。2007年肖扬院长强调要完善司法解释工作机制……通过互联网等媒体予以公布,广泛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意见。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2007年3月13日。对此,部分学者认为,“法律本来就是人民制定的,人民对法律应该如何解释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司法机关要想制定出高质量的、真正体现立法本意的司法解释,就必须倾听、采纳人民的意见。”[16]351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将邀请公众参与司法解释的工作制度化仅仅是尽量使司法解释合理化,但与本文所阐述法官建构判文解释吸纳和体现民意问题不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建构判文解释以吸纳和体现民意,大而言之,事关当下中国司法改革问题;小而言之,关系到司法判决能否为广大民众接受的问题。法官如何吸纳和体现民意,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向:
(一)在思维方式上:从“唯一正解”到“和合建构”
传统的刑法解释观是立足于“概念法学”和理性主义法学理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概念法学理论认为,成文法凌驾一切,法院的任务就是机械地“依章办事”。法官判案依照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过程。理性主义解释法律偏重形式逻辑,法官探求法律原意,寻找法律理由,仅可依“概念而计算”,无须进行目的考量、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12]45。这样,导致现实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讲法不讲理”、“合法不合理”的恶果。然而,“法的理念作为真正的正义的最终的和永恒的形态,人在这个世界上既未彻底认识也未充分实现,但是人的一切立法的行为都以这个理念为取向,法的理念的宏伟景象从未抛弃人们”[21]。对于法律解释,经验主义法学主张法律的目的解释,适用法律不能仅以书面上的法律为限,更为重要的是法律所追求的目的、公正合理和利益,在公正合理的支点上予以考量,最后达到均衡合理。由于成文刑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所以我们必须始终以追求正义、追求法律真理的良心解释法律文本。刑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但是,法生生的正义需要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发现和寻找,制定法的真实含义不只是隐藏在法条之中,而且也隐藏在具体的生活事实之中,生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22]。那么,中国当下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正义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华文明史,儒家伦理和孔孟之道曾长期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农业文明的衰落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儒家伦理与孔孟之道才逐渐走向衰落。传统社会的“德治”逐渐被市场经济社会的“法治”所代替,但是儒家伦理提供的以“仁”、“义”为中心的美德理想主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仁政”、“德政”的思想,不仅深深影响整个民族的思想意识,同时其本身也包含着跨时代的思想内容。而中国当下的“法治”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西方法治具有明显的法律与道德之二元对立思维的特征,有其传承和文化基础,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冲突。而中国普通民众意识里的“法治”是道德视角下的“法治”,中国的法治话语是道德延长线上的话语,而这正是当下中国纯法律人所痛恨而普通民众更乐于见到的“法治”。正如有的学者提出质疑:“中国的法学学术必须在批判旧的学统基础上来建构,但彻底背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学学术能成功吗?”[23]“承载着中华文明游荡了数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真的变成了“无枝可依的游魂”了吗?”[24]让我们看看西方法律与道德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里移植、生长所遭遇的尴尬境遇吧,现实中的司法判决屡屡触碰普通民众的道德情感的底线,比如梁丽案等等。消解这一时代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转变传统“唯一正解”刑法解释观而采取中国语境下“和合”之建构型刑法解释观。正如上文所述,中国法治本土化是法律和道德“和合”的本土化,民众视野中的“法治”蕴涵着对道德的深情厚意。中国语境下“和合”之建构型刑法解释观是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唯一正解”刑法解释观的超越和本土化。这里的“和合”是指法律与道德的和合,其对应于法律与道德的二元对立。在本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意”就是道德。中国语境下“和合”之建构型刑法解释观就是在对刑法文本进行解释和建构的过程中体现和吸纳民意。这样,或许会从源头上消解当前一些司法判决的民意困境和尴尬。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高人民参与司法的热情和兴趣,并且间接起到全民普法之效果,在一定层面可以消解民众对司法的怨言和误解。如此,中国法治理想之实现不再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二)在解释模式上:从“独白”到“对话”
传统刑法解释“独白”模式发韧于精英主义思想,其对精英主义思想有着悠久的情结。这种思想认为,唯有法学精英人士、学者才能深刻领悟和洞察法律背后的真谛,才能对法律文本作出唯一正确的理解和解释。这种“独白”模式下的解释基本上等同于司法人员的“一家之言”。其实,法官在解释法律文本时,离不开自己的前见、前理解乃至偏见,法官也有个人的情感和好恶。即使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使自己的认识符合法律文本的客观性,也难以避免其个人的“主观意识”。关于这一点,从持不同法律解释立场的法学专家对同一法律文本所持不同观点的事实可略见一斑,更遑论法官等司法职业人员。
正如施拉依马赫在区分“解释”和“说明”时谈到的,说明是说明者的看法和观点,说明者在说明的过程中,始终不考虑说明过程中对说明对象的各种可能的反映。而“解释”与说明不同,“解释”是整体性的。解释者所要考虑的,不只是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考虑由解释所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又要考虑环绕着这一解释的固有的现时的及潜在的条件,包括那些在解释活动之内和之外的一切因素[25]。传统的“独白”解释某种程度上就是“说明”,法官更倾向于沉醉于在现有的法律规则之严格逻辑推理思维的海洋里游弋和解释法律。然而,如果一个即使非常聪明的法官仅仅把法律解释的目标视作展示个人智慧的文字游戏和逻辑演绎,那么他也不会成为一名称职的法官。而要克服传统刑法解释模式的弊端,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刑法解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于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淡化法官的“主观意识”,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而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实现从“独白”模式向“对话”模式的转变。
法律解释必须采取“对话”模式,是基于法律解释的目的是让广大民众理解接受和认可。“法律解释是一种社会科学,法律解释结论是否正当,不取决于法律文本本来被赋予何意,而取决于法律适用时的社会共同体的共同的看法。”[16]312这种情况下并不会出现部分学者担心的“民主的暴政”,因为今天的他者可能就是明天的自我,自我和他者的机会是均等的,二者的身份和地位随时可以转换的。在对话中每个人都只是作为他人的他者而生活着,而且也只有与他者相协调,他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三)在实践操作上:实现从立法式的司法解释向司法实践的判文解释转向,建立法官、民意与判文解释三位一体的刑事司法适用机制
在国外的法学著作中、在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法学著作中讲法律解释,并不讲我们所谓的立法解释,也不讲我们所谓的司法解释,它讲的仅仅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所作的解释。在他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法官裁判案件当中所作的解释[26]。因此,实现从立法式的司法解释体制向审判实践的判文解释的转向,建立法官、民意与判文解释三位一体的刑事司法适用机制,才能使刑法解释体系既有面对大众的空间,能够吸纳和体现民意,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又能使法官在面对多方面综合信息、因素而建构刑法文本的意义时受到制度理性约束。
在实践操作上实现从立法式的司法解释向司法实践的判文解释转向,建立法官、民意与判文解释三位一体的刑事司法适用机制,目的是从程序上和内容上确保民众获得一个真实、全面的信息,从而使民众得出真实的、理性的意见和看法。其效果和意义是深远的。一方面,此种做法给民众一个参与司法过程的平台和渠道,民众可以充分、无约束地表达自己理性的看法,从而提高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以及对司法判决的认可。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司法过程中,若能给民意表达的机会和权利,可以树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从而强化公众的法规范意识,进一步发挥法律的行为引导功能。”[27]另一方面,可以实现“跨越西方法治话语的二元对立思维所建构起来的法律与道德的鸿沟,在中国‘和合’的思维语境里沟通起法律与道德的逻辑叙事,完成法律与道德的话语整合,建构中国人有尊严的一种公共生活”[28]195。通过建构判文解释,既满足了民众参与司法的需求,又调动了法官建构合理解释结论以及民众能够接受的司法判决的积极性,这是一种合作共赢模式。
五、结 语
本文提倡法官采取程序化和制度化方式吸纳民意、体现民意,并不是要简单地赞成“民意”甚至是否定“法治”,恰恰是为了呵护广大民众的法感情,为了体现法中的“人性”,是“通过纠纷解决机制的开放性运作进而将人民群众的矛盾和意见带到了法院或者纳入到了规范化的解决渠道”[28]196,是为了更好地实行一种契合本土的法治,寻求一种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法治生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聆听和感悟来自人民深处的声音和情感,并给予应有的回应、地位和尊重;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法治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这就需要司法“走进群众,更加主动地吸纳人民群众的意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28]196。为此,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和路线,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民意的重要性,也不应当消解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我们必须警醒,忽视乃至否定民意的司法活动(刑法解释)会让我们的法治付出惨痛的代价。当下,我们有必要用一双穿越历史隧道的慧眼去展望未来,法治的道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行”。
当然,本文倡导法官吸纳和体现民意,要求司法认真对待民意,主旨是在面对容易产生分歧以及重大、复杂甚至截然相反的刑法解释争议面前,我们不妨走出高高的象牙塔,放下身段,问计于民。这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司法的一种优良品格。通过此种努力,笔者期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营造出一个公共的司法话语社会,而这或许可能是我们千千万万真正的法律学人所向往和追寻的“理想的法治社会”。
[1]董皞.司法解释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
[2]董皞.法官释法的困惑与出路[J].法商研究,2004,(2).
[3]陈金钊.法律的特性与法律解释——法律解释的一种本体论探索[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2 -26.
[4]齐延平.人权与法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306-321.
[5]陈坤.法律、语言与司法判决的确定性[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4):61.
[6][德]施拉依马赫.1819年讲演纲要[G]//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61.
[7]胡东飞.认识论、法治与刑法解释的目标[J].中外法学,2010,(5).
[8][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9][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译者序言.
[10]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347-348.
[11]DEWEY J.Democracy and Education[G]//BOYDSTON J A(ed.).John Dewey’s Middles War RS.Vol.9.1980:7.
[12]尹洪阳.法律解释疏论——基于司法实践的视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13]陈忠林.刑法散得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7.
[14]俞小海.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J].现代法学,2010,(5):84-85.
[15]谢晖.法律的意义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6]杨艳霞.刑法解释的理论与方法: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7]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J].中外法学,2009,(1):105.
[18]ISENBERG D.Group Polarization: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 - analysis[G].50,Personality and Soc.Psych.1986:1141.
[19][德]伊丽莎白·诺尔-纽曼.民意:沉默螺旋的发现之旅[M].翁秀琪,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301.
[20]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赵晓力作的序言.
[21][德]H.科殷.法哲学[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0.
[22]张明楷.实质解释再提倡[J].中国法学,2010,(4):66-67.
[23]徐显明.人民立宪思想探源[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序.
[24]张辉.关心“形而下”[J].读书,2000,(4).
[25]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10.
[26]梁慧星.裁判的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2.
[27]傅贤国.司法裁判吸纳民意机制之建构[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4):30.
[28]方乐.司法如何面对道德[J].中外法学,2010,(2).
[责任编辑 张莲英]
Establishing the Criminal Justice Applicable Mechanism of Trinity about Judges,Public Opinion and Explanation of Decision Instrument——The Third Path of Dissolving the Conflict of the Judicial and the Opinion
FU Qi-yun
(School of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s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power,and the explanation of decision instrument does not belong to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which does not have the effect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In the reality the judge is suppressed,most judges are simply mechanical in judicial practice,this cannot adapt to the ever-changing social reality of judicial demand.In this way,there are frequently the decisions which depart seriously from"the public opinion"according to the law strictly.In the modern society,how to accept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a form of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management,participating in judicature and carrying on the surveillance to the judicature with the people.Therefore,understand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explanation of decision instrument correctly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exploring the intrins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explanation of decision instrument and the public opinion,and accepting th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he explanation of decision instrument,have become the subject of judicial modernization.
judge;explanation of decision instrument;constructivism;public opinion
D926
A
1009-1971(2011)04-0090-09
2011-05-15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重点项目“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如何面对民意的思考”(2010XZYJS144)
付其运(1978-),男,安徽阜阳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刑法学基本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