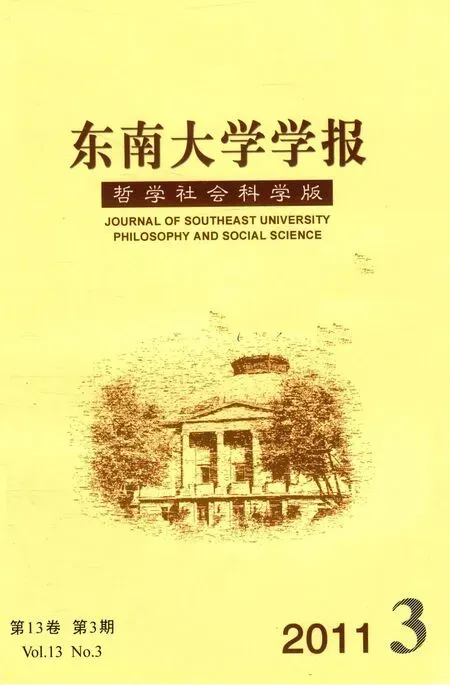汉语“名量”式复合词的几个相关问题
2011-04-04董志翘
董志翘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汉语“名量”式复合词的几个相关问题
董志翘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名量式复合词”是汉语中极具特色的一类复合词(如马匹、车辆、船只),它是随着汉语复音词的大量产生以及汉语中量词的趋向成熟而形成的。目前学界对此类词已讨论很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对于此类词的定义仍不相同;对于此类词的鉴别、认定也存在较大差异;至于此类词的起源,或上推到先秦,或着眼于近代,相差近千余年。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如:因为定义不同,于是鉴别认定各异,鉴别认定各异,故产生时代就不同。而产生时代看法不一,相应标准也就难以一致)。我们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必须放在整个汉语史的历时层面上来考察,而不能仅停留于现代汉语共时层面上的讨论。本文拟从汉语史的角度,从汉语词汇复音化及汉语量词的产生发展历史入手,比较各家对“名量式复合词”的定义,分析各家所举例词及鉴别标准,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想法,在此基础上,推测出“名量式复合词”的产生及成熟年代。
汉语;“名量”式;复合词;认定;起源
一
在汉语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双音节合成词,它们是由一个表事物的词素在前,一个表该事物计量单位的词素在后组合而成的。这类合成词在语法属性上体现为名词,从词义上看,这类名词的所指为该词中表事物词素所指事物的总称,具有集合义。比如“布匹”、“银两”等。
应该说,这是汉语词汇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产物,它们的数量不多,可以说是一种较为封闭的双音词形式。学术界对此类现象早有关注,也多有论及,但是直至今天,对于此类复合词的性质、命名、范围、内部结构类型以及词义,认识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且尚无定论。
李丽云[1]对于目前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作了初步的回顾总结,文章认为:“对于现代汉语‘名+量’式复合词,学者们已经有所探讨,而且讨论的焦点大多集中于这类词的语法结构类型归属以及范围广狭的界定。应该说,大家普遍地认识到了这类词在语素性质和结构方式上的独特性,但是对于是否将其划入汉语复合词的基本类型,具体应该归入哪一种类型的问题还存在一定的分歧。”然后论文将目前学界的观点分为五类,即:
(一)补充说:认为可以将“名+量”式复合词并入补充式,“因为后一表计量单位的词根,可以说用来补充说明前一表示物件的词根。”持此观点者有胡裕树[2]、张斌[3]、黄伯荣、廖序东[4]、葛本仪等[5]。
(二)偏正说:认为这类词属于“N—M类(N为名词性语素,M为量词性语素)”,有人认为“N—M类是名词性语素修饰量词性语素,其中量词性语素是整个词的中心”。有人则认为“定中格复合词中,还有一些逆序词,它们用作修饰、限定的字位置在后,被修饰、限定的字位置在前。其中一小类即‘事物 +单位’类,是单位修饰、限定事物”。持这种观点者有赵元任[6]、朱德熙[7]、周荐[8]等。
(三)附加说:认为“名词后面加上一个相应的量词,使原来的单音词变成双音词。……量词加入构词以后,意义虚化了,不再表量,所以可以看作近于词尾的构词法。”“附在成名词语素后面的成量词语素就是真词缀的一种。”这类词缀“由量词转化而来,意义虚化了,表示计量单位的意思已经丧失殆尽,读音上都有轻读的趋势。由成量词语素构成的词多半有[集合义]”。持这一观点的有任学良[9]、马庆株[10]等。
(四)并列说:列举了三点理由:“(1)一个量词由于经常与某个名词搭配,且可以单独指代名词,逐渐获得了名词的意义,或者至少是在语言使用者心中造成了与某个名词相关的联想,于是由于词汇双音化的作用,在说到某个名词时就将经常与其搭配的不同程度获得了与名词相同意义的量词联想到了一起。(2)这些词在产生的时候,量词应该是和名词搭配较为经常的,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搭配范围太宽的量词如“个、枚”等久没有构成这样的词,因为它不容易获得某一特定名词的意义和联想。(3)这些词多半有[集合义],这也和一般由同义语素并列构成的复合词是一样的,如房屋、土地、树木、牲畜、书籍、报刊、人民、粮食、村庄、坟墓、墙壁。”持这一观点者有李宗江[11]。
(五)另立他类说:有人认为“基于‘名+量’式合成词在构词成分和结构方式上的独特性,有必要将这类词独立出来,将其看作与其他基本类型平行的新的结构形式”,如“注释格”“表单位格”。持此观点者有武占坤、王勤[12]、刘叔新[13]等先生。
李丽云文中总结的五家,其实都是认定此类复合词为“名+量”结构,只是在内部结构关系的分类上不同而已。
其实,学界也有不承认此类词是“名 +量”结构者。持这一看法者最早为陆志韦先生,他认为:
诸如“个性、对虾、布匹、马匹、银两、船只、车辆、纸张、文件、案件、稿件、事项、事件、米粒”之类的复合词,不论是“量—名”还是“名—量”,实际上都不过是“名—名”。[14]52
而杨锡彭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名量”复合词的存在。他认为:
上古时期的N+(Num)+Mw(单位词Measure word,Mw)跟现代汉语中“车辆、船只、人口、物件、布匹、书本、画册、房间”之类合成词之间有何联系,还缺乏有力的历时研究成果的证据支持。我们认为,从共时平面上看现代汉语中这类词的内部结构,所谓“名 +量”复合词中的后一成分与出现在“数量(名)”短语中的量词,不管是功能还是意义,都是不同的。我们在上文曾指出,不能根据“绿”作为词出现时的功能、意义来代替“绿”以构词成分出现时的功能和意义。现代汉语中的“车辆、人口、物件、布匹、书本、画册、房间”之类的合成词中后一成分性质复杂,它们不仅不能划归量词,而且也不能简单、笼统地划一处理。比如“车辆、布匹、书本、船只”可以看作与“窗户、国家”相同的偏义复词,“物件(比照‘文件、工件、零件’等)、画册(比照‘分册、底册、名册’等)、房间(房子内隔成的各个部分)”则可以分析为偏正式复合词。
总之,不能把“车辆、船只、人口、物件、布匹、书本、画册、房间”之类的合成词中后一成分看作量词性的,它们与同形的量词不具有同一性,所谓“名量”复合词是不存在的。[15]233
李丽云是倾向于“另立他类说”的,在此基础上,她又为确定“名量”式复合词的范围,提出了四条判断标准:
(一)第二个构词成分必须是量词性的,语义上还没有衍生出名物义。(其中引用了朱彦文章中的一段话:“然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能产的构词量词由抽象的量词范畴义逐渐发展出具体的名物义。……‘朵、件’等语素已发展出名物义,构词能力强,在现代人的语感中更像名词而不是量词。”[16]25翘按:这一标准本身就存在着误区:从汉语史上看,大多数物量词是从名词转变而来的,孰先孰后不能颠倒)
(二)两个构成成分逆序之后,前加数词可以构成数量名结构。(如:马匹:一匹马;花朵:一朵花;人口:一口人;灯盏:一盏灯……)
(三)从语义上看,整个名量式合成词表示的是名词性语素所指事物的总称,具有集合义。
(四)从句法功能上看,名量式复合词不能受数量短语的修饰。
在此四条标准的对照下,李丽云遴选出了19个“最严格意义上的名量式复合词”,分别为:马匹、车辆、船只、枪支、书本、纸张、花朵、布匹、人口、银两、灯盏、田亩、地亩、皮张、煤斤、画幅、兵员、牲口、舰只。
二
笔者认为:讨论这一类词,不应该在现代汉语一个共时平面进行,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演变和发展,如果不是从汉语史的视野进行历时的研究,那么,有许多问题是无法讲清楚也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的。
首先,汉语中的物量词大多源于名词,而从名词发展到量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此在鉴别“名名”式复合词还是“名量”复合词时,就存在一些困难,这就是造成过去学界对“名量”式复合词的界定不一,对哪些词属“名量式”复合词归类结果也不同的主要原因。
刘世儒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指出:“因为‘缺乏历史的基础’,就会‘陷于被禁的领域中’;从平面上和表面上来观察、理解‘本国文的材料和形式’常常是不能深入乃至不能正确的。”[17]2
刘世儒先生将汉语的物量词分为三类:
(一)陪伴词(作用只在陪伴名物,不是核算分量的,这是虚量。这是纯然的语法范畴,同实际称量没有关系),其中又分为(1)泛用的陪伴词:这类量词的适应能力最强,几乎无所不能适应。如“枚”、“个”等。(2)次泛用陪伴词:这类量词数量最多,适应能力也最参差不齐。如:“口”、“本”、“支 (枝)”、“只”、“粒”、“片”、“间”、“件”、“幅”、“张”等。(3)专用陪伴词:这类量词适应能力最弱,和第一类量词正相反,除了某一种乃至某一个特定的事物可以适用外,其他事物虽在同一义类也一律不能援例使用(有时同次泛用的量词可能发生交叉,但这种情形不多),如:“两(辆)”、“匹(马、驼)”等。
(二)陪伴·称量词(既具陪伴词性质又具有称量词性质的一种量词,定数几何量词,如:一双,不定数集合词:一群)
(三)称量词(实际称量名物的,这是实量:度量衡制称量法:如“丈”、“匹(布帛)”“两(金银)”、“斤”、“亩”、“顷”、“里”等;普通称量法:一把、一聚。一般都是借来的,有借用名词,有借用动词)
在这三类中,第一类“陪伴词”中的“泛用陪伴词”,当不在讨论之列。因为它们称量之物太泛,正如李宗江所言:“这些词(“名量”复合词)在产生的时候,量词应该是和名词搭配较为经常的,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搭配范围太宽的量词如“个”、“枚”等就没有构成这样的词,因为它不容易获得某一特定名词的意义和联想。”[18]
只有第三类“称量词”才是最纯粹的量词,因此,也只有“名+度量衡称量”组成的复音词称为“‘名量’式复合词”才是最少歧解的,如“布匹”、“银两”、“煤斤”、“田亩”、“地亩”等。
那么,一般来讲,称量物的数量词可以用在名词之后,也可以用在名词之前,从构词的角度而言,正常的构成应该是表“量”的语素在前,而表“名”的语素在后,也就是说,应该构成“量名”复合词,而不是“名量”复合词。我想,最初大概是与当时的名量的用法有关,比如:
【布匹】
目前见到的“匹”作为量词量布帛的用例,如:
《世说新语·德行篇》:“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疋布赎之。”
《魏书·封懿传》:“赐布帛六百疋,粟六百石。”
梁慧皎《高僧传·诵经篇》:“神施以白马一匹、白羊五头、绢九十匹。”
《宋书·五行志》:“仰视若曳一匹练。”但是在古汉语中,当数词为“一”时,数词可以省略,单用“量词”来称量,如“匹布”、“疋帛”、“匹绢”、“匹练”,如:
三国·魏·嵇康《嵇中散集》卷十“家诫”:“过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
《晋书·载记 ·石季龙下》:“时东南有黄黑云大如数亩,稍分为三,状若匹布,东西经天。”
《晋书》:“九月甲寅申时,回风从东来,入入胤儿船中西过,状如匹练,长五六丈”
因此若以“量名”顺序结合,则义为“一匹布”、“一匹帛”、“一匹绢”、“一匹练”,当为偏正短语,不能成词。
而数量词用于表布帛的名词之后,当数为“一”时,数词亦可省略,不过,这时往往名词表示总称,而量词表示分述,如:
《南齐书·王敬则传》:“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令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其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此句唐杜佑《通典》卷五“食货五·赋税中”引为:“今入官好布,/疋下百余。其四人所送者,犹依旧制。”)
《魏书·张普惠传》:“今宫人请调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绢布/疋有尺丈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
唐杜佑《通典》卷九“食货”:“官欲知贵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三市卖之。绢/疋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
这种情况下,“布(帛、绢)”与“匹”不属一个层次,前面的“布(帛、绢)”乃总称,后面的“匹”乃分述(相当于“其中一匹”)。
然而,这种跨层单位在线性次序上的连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就凝结成了双音词——“布匹(帛匹、绢匹)”,在这个词的内部,“布(帛、绢)”还是表示总称,而“匹”的计量功能逐渐淡化,成了类似词缀一样的成分,就这一意义上,本人赞同任学良、马庆株先生的“附加说”。
正如董秀芳所云:
“跨层结构是指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上而只是在表层形式上相邻近的两个成分的组合。有一些跨层结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变成了词,由这一渠道产生的多是虚词(翘按: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虚词,就如同“地方”,可能最早是由“其地/方千里”这类跨层结构凝聚而成),其内部形式非常模糊。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变化,即从非语言单位变为语言单位的变化。”“这一类词的形成完全是由于两个单位在线性次序上紧密相连。在语句的理解过程中,两个邻近单位如果被聚合为一个组块而加以感知,二者之间原有的分界就可能被取消,造成结构的重新分析。由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在双音词总数中的比例很小,由此可知跨层结构的粘合是要受到很多限制的。”[19]273
因此,此类“名量”式复音词,其产生年代自然比这种跨层的用法要晚一些。
《汉语大词典》:“〔布匹〕布以匹计,故统称布为布匹。《东周列国志》第二回:“恰好有个姒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疋之类,转乞此女过门。”(翘按:《词典》未收“帛匹”、“绢匹”)
《东周列国志》乃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所撰,以此为首见例当然过晚,据本人调查,最早似见于唐宋时代,如:
唐李筌《太白阴经》卷八“暴兵氣”:“云气一道,上白下黄,白色如布疋,长数丈。”(按:这个句子,如果按照四字句节奏,当标点为“云气一道,上白下黄,白色如布,疋长数丈。”其实这就是处于“布匹”成词的初始时期)
到了宋代后,“布匹”(帛匹、绢匹)这类“名量”复合词即已成词: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后集》卷十八“占候三”:“白气起,广六丈,东西亘天者,兵起。有云如布疋,亘天者,兵起。”
宋王安礼等重修《灵台秘苑》卷四“气”:“赤气如堤、如坂,前后摩地。或如山堤、如林木、如大盖、如布疋、如旌旗、如粉沸楼台。”
宋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熙宁)七年十二月,天下免役计缗钱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谷石、帛疋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
宋袁甫撰《蒙斋集》卷七:“凡物十千之价者,只两千可得,米石、绢匹,色色如之。”
元陶宗仪撰《说郛》卷四一:“是时救左藏库人尤众,辇出金银、帛疋莫知其数,积于城墙之上。”至明代,则已多见:
明何孟春《何文简奏议》卷一“恤边疏”:“调征官军,俱给银两、布疋,无非欲大施惠泽,振作士气。”
明何孟春《何文简奏议》卷五“强贼激变疏”:“那受所积金银器皿、牛马、罗段、布疋等件,不知数目。”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二“边防记二”:“嫁娶富者以猪羊毛毡、布疋、粟麦为礼。”
【盐斤】
“斤(字亦作“觔”)”为度量衡量词,以“斤”称量“盐”,宋代已见:
宋张君房《云笈七籖》卷七六“修羽化河车法”:“待干,取五斤盐,用消石炼过两度了,细捣筛取。”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二九“兴国太守太守赠太保王公綯神道碑”:“令招集耕农,贷以种粮,初至斗米斤盐,率直三千。”
同理,数量词用于表盐(茶)类的名词之后,当数为“一”时,数词亦可省略,不过,这时,往往名词表示总称,而量词表示分述:如:
《宋史·光宗本纪》:“惟清曰:‘臣见官卖盐/,斤为钱六十四,民以三数斗稻价方可买一斤。’乃诏斤减十钱。”
《宋史·食货志下》:“两浙亭户额外中盐,斤增价三分。已而张察均定盐价视绍圣斤增二钱,诏从其说,仍斤增一钱。”
《宋史·食货志下》:“太平兴国三年,右拾遗郭泌上言:‘剑南诸州,官粜盐/斤为钱七十。”
这种情况下,“盐”与“斤”不属一个层次,前面的“盐”乃总称,后面的“斤”乃分述(相当于“其中一斤”)。
然而,就是这种跨层单位在线性次序上的连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就凝结成了双音词——“盐斤”,在这个词的内部,“盐”还是表示总称,而“斤”的计量功能逐渐淡化,成了类似词缀一样的成分。
《汉语大词典》:“〔盐斤〕亦作‘盐觔 ’。指盐。《儒林外史》第四三回:‘分明是你这奴才揽载了商人的盐斤,在路夥着押船的家人任意嫖赌花消,沿途偷卖了。’清黄六鸿《福惠全书·钱谷·解给》:‘恐有盐觔罪赎,不可早放。’建南《盐场》:‘今天的盐斤被秤手扣刻得太多了,明天的担子便加得重一点。’”
除《词典》所举,明清文献中用例甚众:
明倪元璐《倪文贞奏疏》卷九“胪陈生节疏”:“若无京引、纲引,不许过关桥,取掣其引价盐觔。及余课割没等项,悉照标盐往例,毋得故违损益。”
《明史 ·兵志》:“班军本处有大粮,到京有行粮,又有盐斤银,所费十余万金,今皆虚冒。”
清《御制诗集·五集》卷六八“书志一首戏用重字体”诗按语:“向来私贩盐斤,例禁綦严,尚难断绝。缘人情趋利,虽犯法而不顾。”
【田亩】
“亩”是计田亩的专用量词。《说文》:“畮,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亩”作为量词量田地的用例,先秦已见。如:
《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礼记·儒行》:“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
晋陶潜《归园田居五首》之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宋书·郭世道传》:“墓前有数十亩田。”
而数量词用于表田地的名词之后,当数为“一”时,亦可省略,这时,往往也是名词表示总称,而量词表示分述:如:
汉王符《潜夫论 ·实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金,人众地荒,无所容足。”
《后汉书·灵帝纪》:“税天下田,亩十钱。”
北齐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种谷第三”:“《汜胜之书》曰:‘稗既堪水旱,种无不熟之时,又特滋茂盛,易生芜薉,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
《齐民要术》卷二“小豆第七”:“《泛胜之书》曰:……故曰豆不可尽治养,美田/亩可十石,以薄田尚可亩取五石。”
唐杜佑《通典》卷六“赋税下”:“贞观二年四月,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
《宋史 ·贾似道传》:“买公田以罢和籴,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
宋郑樵《通志》·卷十下“晋纪”:“六月癸巳,初税田,/亩二升。”
《礼记·王制》:“司徒上地,家七人,八鸠而当一井。上地/亩一钟。”
《宋书·沈昙庆传》:“膏腴上地,/亩直一金。”
《宋史·兵志》:“视山坡川原,均给人二顷。其租秋一输,川地/亩五升,坂原地/亩三升,毋折变。”
这种情况下,“田(地)”与“亩”不属一个层次,前面的“田(地)”乃总称,后面的“亩”乃分述(相当于“其中一亩”)。
然而,就是这种跨层单位在线性次序上的连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就凝结成了双音词——“田亩”、“地亩”(翘按:《词典》未收“地亩”),在这类词的内部,“田(地)”还是表示总称,而“亩”的计量功能逐渐淡化,成了类似词缀一样的成分①“田亩”连用,出现的时代很早,如:《汉语大词典》:“〔田亩〕1.田地。《书·盘庚上》:‘惰农自安,不昬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东观汉记·郭丹传》:‘郭丹为三公,典牧州郡,田亩不增。’其中的‘亩’恐为‘田垄’之义,为名词。《诗·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朱熹集传:‘亩,垄也。’《国语·周语下》:‘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韦昭注:‘下曰畎,高曰亩。亩,垄也。’”故《词典》所举两例“田亩”尚为“名名”式复合词,且为偏正结构。。
《汉书·王莽传》:“外则王公列侯,内则帷幄侍御,翕然同时,各竭所有,或入金钱,或献田亩,以振贫穷。”
《晋书·冯跋传》:“今疆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令家给人足,不亦难乎?”
《旧唐书·杨炎传》:“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
《宋史 ·五行志上》:“是秋,荆湖北路江水注溢,浸田亩甚众。”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十“县令”:“如先无租税,即据所营地亩,且收半税,并放二年差徭。”
明马文升《端肃奏议》卷九“处置银两以济边饷事”:“自弘治十四年为始,每粮一石,暂增银二钱,每草一束,暂增银二分,则数十万两之银,可立而得。况出自地亩,分所当然。”
明《端肃奏议》卷九卷十一“一恤百姓以固邦本”:“虽丰收之年,度其仓廪,有余之处,亦量蠲免地亩税粮,什一而税。”
与此类似的还有“马匹”、“车两(辆)”等,因为“匹”、“两”属于“专用的陪伴词”(它们并非从名词演变而来,似来自于表单、双的数词),刘世儒云:“这类量词适应能力最弱,除了某一种乃至某一个特定的事物可以适用外,其它事物虽在同一义类也一律不能援例使用(有时同次泛用的量词可能发生交叉,但这种情形不多)”。
【马匹】
《汉语大词典》:“〔马匹〕亦作‘马疋’。马的总称。马以匹计,故称。《易·中孚》:‘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类说》卷三六引汉应劭《风俗通》:‘马疋,俗说马比君子,与人相疋,或说马夜目明照前四丈,或说马纵横适得一疋,或说马匹卖直一疋帛。’《水浒传》第二十回:‘见众头领尽把车辆扛上岸来,再叫撑船去载头口马匹,众头领大喜。’杜鹏程《保卫延安》第一章:‘他们有的人站在马匹和文件驮子旁边,有的在桃树林里来回走动。’”
从《词典》引例来看,似乎“马匹”一词先秦已见。其实这是误解《易》经文意所致。《易·中孚》之“马匹亡”不当分析为“马匹/亡”,而是应该分析为“马/匹亡”。
魏王弼《周易注》卷六:“月几望,马匹亡者,弃群类也。若夫居盛德之位而与物校,其竞争则失其所盛矣,故曰绝类而上,履正承尊,不与三争,乃得无咎也。”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二:“‘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虞翻曰:‘讼坎为月,离为日,兑西震东。月在兑二,离为震三,日月象对。故‘月几望’;乾坎两马匹,初四易位,震为奔走,体遁山中。乾坎不见,故‘马匹亡’,初四易位,故‘无咎’矣。”
从以上所引前人对于《易·中孚》:“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的解释,都可证明此中之“匹”乃“两马为匹”之“匹偶”义。
而《类说》引汉应劭《风俗通》“马疋”云云,此例亦值得怀疑,从所述内容看,应劭旨在说明“马”何以称“匹(疋),未必当时有“马匹”这样的“事物 +单位”复合词。查《太平御览》卷897“兽”部“马五”引《风俗通》作:“马一疋,俗说马比君子,与人相疋,或曰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说马从横适得一疋。或说马死卖得一疋帛。”《太平御览》是北宋太宗赵炅命李昉等14人编辑,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成于八年(983),为朝廷钦定之类书。而《类说》为南宋曾慥个人所辑汉以来笔记小说材料,所以引文明显有脱漏。且编于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六年(1136年),时代上也比《太平御览》晚 150年,故当以《御览》所引为准。
虽然说“匹”作为“马”的量词,似乎很早。如:
《书·文侯之命》:“用赍尔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左传 ·襄公二年》:“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
《宋书·符瑞志》:“魏武帝尝梦有三匹马在一槽中共食。”
但正如刘世儒云:“大约在当初,‘匹’是可以泛用于一切有‘匹偶’可说之物的。
比较下边的用法,最容易看出来这种关系:‘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子罕》皇疏:‘谓为匹夫者,言其贱,但夫妇相匹配而已也。’《文心雕龙 ·指瑕篇》:‘疋夫疋妇亦配义矣。’……可见‘匹’对于‘人’‘马’原本都是可以适用的。只是后来发展,‘匹’用成量词,才逐渐专用于‘马’,‘人’另配有量词,不再使用‘匹’来称量了。”
笔者认为:“马匹”成为一个真正的“名量式复合词”,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一)“匹”已经发展为真正的量词(已不带“匹偶”义),如:
《史记·大宛列传》:“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灌顶王法复有八万四千匹马,亦以纯金为诸乘具,金网覆上。”(2—68)(再如《宋书》中的“三匹马”。)
(二)因为名量式复合词的“马匹”往往表示对“马”这一名词类词根所表示的名物的总称,因此往往是无定的,至少不是单数的。
(三)在汉语中的双音词有了较大发展以后。(因为根据调查,“名量”结构的双音名词总体上比其他结构出现更晚。)当然,这些条件也适用于对于其他“名量式复合词”的鉴定。
另外,“马匹”一词的形成,笔者认为也是经过跨层单位在线性次序上的连用而凝结起来的。除了上举“月既望,马/匹亡”例(此例中的“匹”为“疋偶”义)之外,再如:
《汉书·武帝纪》卷六:“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
《颜氏家训·书证》:“周礼:圉人职,良马/匹一人;驽马丽一人。圉人所养亦非騲也。”
《隋书·炀帝纪》:“课天下富室,益市武马/,匹直十余万,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
因此,真正作为一个词出现的“马匹”,可能要到中古才见。但又肯定比《词典》所举的明代的《水浒传》及现代的《保卫延安》例要早。如:
《魏书·樊子鹄传》:“及(元)树众半出,子鹄中击,破之。擒树及(萧)衍、谯州刺史朱文开,俘馘甚多。班师,出帝赍马匹。迁吏部尚书,转尚书右仆射。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典选。”
《全唐诗续拾》卷四十《易静〈兵要望江南〉》:“临阵次,马匹忽然惊,欲悚欲谦多退缩,牵缠不动自迟情,回首免军惊。”①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关于汉语中的名量式复合词》一文中有详述,参见《汉语学报》2010年第2期。
因为有了一些真正的“名量”复合词以及这类词的造词模式,所以当后代量词比较成熟,词汇的复音化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就可能经过类推而造成一些新的“名量”复合词。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后周纪五·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下”:“丙午唐主遣冯延己献银、绢、钱、茶、谷共百万以犒军。”胡三省注:“银两、绢匹、钱贯、茶斤、谷石各以万计,其数共为百万。”
此例中,宋代司马光用“银”“绢”“钱”“茶”、“谷”几个单音词,而到了元代胡三省笔下,一律变成了“银两”、“绢匹”、“钱贯”、“茶斤”、“谷石”等“名量”复合词(虽然,它们仍处于成词的初始时期)。但是几乎同时期出现的一些例证,却已是确定无疑的“名量”复合词,如:
明通容述《丛林两序须知》:“库内要多发银两买办,当会议监寺,或知客,禀白方丈。”(续 63—674)
明曹学诠《蜀中广记》卷三一“边防记”:“下潘州白利等番挾牛羊毡毳來,或由阿玉岭、或由铁门墩出,抵寒盻,祈命诸寨贸易茶斤,岁以为常。稍失防防,衅端辄起。”
明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二一“奏兴利补弊以禆屯政事”:“逐年查考,收买谷石,贮积各仓。”
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九:“陛下不许科罚人户钱贯,今则有旬日之间追二三千户而科罚者。”
从中可见当时类推之势。
【船只】
“只(原应作“隻”,《说文》:“隻,鸟一枚”,所以单说一个的就可以用“隻”,它与“匹”、“两”似来源于表示单、偶的表数词)”作“船”的量词,且大都可置于“船”之前者,唐宋已见。
唐白居易《初到忠州赠李六》诗:“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
《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臣能止得吴军,不须寸兵尺剑,唯须小船一只,棹椑一枚,……。”
宋非浊集《三宝感应要略录》:“同行船有十只,忽遇恶风顿起,九只船沒。”(51—853)
宋宗晓编《乐邦文类》:“活计惟撑一只船,流行坎止只随缘。”(47—230)
正因为此,“船只”作为“名量式复合词”表“船”的总称,宋时已经多见(而《词典》首引例为元代)。如:
《太平御览》卷三二三“兵部五十四”引《三国典略》:“初,轨潜於清水入淮口,多竖大木以铁锁贯车轮,横截水流,遏断船只。”
宋廖刚《高峰文集》卷五:“臣自到官,尽籍管内所有船只。”
宋周密《癸辛杂识 ·前集》:“又命浙漕及绍兴府守臣办集船只,衹备师相回阙。”
宋岳珂《金佗续编》卷二十五:“掳劫出城避难人民船只,其势猖獗。”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诸色杂卖”:“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间处。”
因为“只”同时也可称量“牛”、“驼”等,所以,后来也类推出“牛只”、“驼只”等名量式复合词,不过仅昙花一现而已。
宋吴潜《履斋遗稿》卷四:“目前粮种、牛只、农具不知何所取用。”
元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二:“告元帅薛直千掳掠平民,夺要牛只,邀取金银等罪。”
明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四“军民利病奏”:“然军士贫窘者多,牛只、器具一时莫措。”
清《御制诗集》五集卷七一:“于正月二十四日前抵西宁,所有驼只、马匹及应行裹带之盐菜、口粮等项,预备敷余。”
清《钦定八旗通志》卷七七:“或用附近庄头车辆,或雇觅驼只车脚。”
三
除此以外,其他的物量词大多属于“次泛用陪伴量词”,这类量词数量最多,适应能力也最参差不齐,且原来大多来自于名词,所以,当它尚未发展为成熟的量词之时,当然属于名词。比如:
【花朵】
原来就当为“名+名”结构,《说文·木部》:“朵,树木垂朵朵也。”段玉裁注:“凡枝叶华实之垂者皆曰朵朵,今人但谓一华谓一朵。”故“朵”本指树木枝叶花实下垂堆聚貌,后多指堆聚之花实。所以早期的“花朵”实为偏正结构,乃“花之实”也。如: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复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皆缀花朵,俨若生人。”
唐刘禹锡《和乐天春词》:“新妆粉面下朱楼,深锁楼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唐输波迦罗译《苏悉地羯啰经》:“上色妙香花,中色香花,下色香花,随事分用。或用取花条,或用花朵,以献妃天等。”(18—608)
宋法天译《妙臂菩萨所问经》:“其色如金,或如珊瑚。或广或长,相状多异。或如虹霓,或如电闪,或如孔雀尾,或如莲花朵。”(18—756)
从上举例子中可见,“花朵”与“花条”相对而言,且“花朵”还不是“花”的总称,故可称“莲花朵”,可见此“朵”非量词。因此,当时还有“钗朵(钗头镶饰的花朵状珠宝)”、“钿朵(用金银贝玉等做成的花朵状饰物)”、“梅朵(梅树之花实)”等词。如:
北周庾信《春赋》:“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
唐元稹《送王十一郎游剡中》诗:“百里油盆镜湖水,千重钿朵会稽山。”
前蜀韦庄《和李秀才郊墅早春吟兴十韵》:“草根微吐翠,梅朵半含霜。”
此三词均出现在诗歌的对仗句中,以“钗朵”对“髻鬟”、“油盆”对“钿朵”、“草根”对“梅朵”,内部结构当相同(均为偏正)。况且在实际语言中,我们也没有“一朵钗”“一朵钿”、“一朵梅”这样的称量法,所以此中之“朵”非量词明矣。
《汉语大词典》虽将葛洪《西京杂记》中的“花朵”释为“花”,但绝对不可能是“名量”式复合词,只能是“名名”式复合词。因为“朵”作为花的称量词,王力先生认为最早见于唐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20]。而刘世儒先生认为南北朝已有萌芽,但是“在南北朝这还是个刚刚兴起的量词,使用频率还是很少的。”[17]189至于量词“朵”用来称量“花”且用在名词“花”之前(也就是量词“朵”的成熟形式),则最早见于宋代。
宋李幼武纂集《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五“邵雍”条:“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时,是将开;略放时,是正盛;烂漫时,是衰谢。”
宋苏轼《三朵花诗并序》:“房州通判许安世以书遗余,言吾州有异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
宋法贤译《众许摩诃帝经》:“王即以五朵花奉上于佛,然后头面著地礼其双足。”(3—962)
宋道原纂《景德传灯录》:“师与长庆保福入州见牡丹障子。保福云:‘好一朵牡丹花!’长庆云:“莫眼花。”师曰:‘可惜许一朵花。’”(51—371)
因此“花朵”原为“名名”式复合词,且内部结构为偏正关系,后来因为“梅朵”、“莲朵”等用法,使“朵”也具有了“花”的义位,所以“花朵”就成了“名名”式、内部结构为同义并列的复合词,而这类同义并列复合词也多数带有集合义。如:
《儿女英雄传》第十四回:“只见他家常打扮,穿条元青裙儿,罩件月白袄儿,头上戴些不村不俏的簪环花朵,年纪约有三十光景。”
《儿女英雄传》第十五回:“你打倒了我,立刻盘了银子去,那怕我身带重伤,一定抹了脂粉,带了花朵,凑这个趣儿。”“只是我要问问:“怎生输了的便该擦胭抹粉戴花?难道这胭粉花朵的里头便不许有个英雄不成?”
【灯盏】
原来也是“名+名”结构,《方言》卷五:“盏,杯也。”郭璞注:“盏,最小杯也。”故“盏”原指一种浅而小的杯子。
唐杜甫《送杨判官使西蕃》诗:“边酒排金盏,夷歌捧玉盘。”
因古人用油灯照明,故用来盛油的浅而小的器皿亦称盏。故“灯盏”原来即指“灯碗”:
东晋佛陀跋陀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瓦器者,从大瓮乃至灯盏,是名瓦器。”(22—244)
隋智通译《清净观世音普贤陀罗尼经》:“初四肘乃至八肘五色作,须十六罐子安水及花果子,须十六具香炉、十六灯盏。若作四肘坛,安四罐子、四具香炉、四枚灯盏。”(20—22)
唐输波迦罗译《苏悉地羯啰经》:“五色线,谓青黄赤白黑,童女所合线。金刚杵、灯炷、灯盏、瓦碗,五种彩色。”(18—622)
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次具灯盏,一一著油,各各然灯。”(18—889)
唐颜真卿《颜鲁公集》卷九“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姑与道流寻访,见龟在坛中央,其下得尊像、油瓮、枪刀、灯盏之类。”
上举例子中“香炉”与“灯盏”,“灯炷”与“灯盏”相对而言,且“灯盏”也不是“灯”的总称,故可称“四枚灯盏(量词是“枚”)”,可见此“盏”非量词。因此,当时还有“瓦盏(陶制的小酒杯)”、“酒盏(小酒杯)”等词。
根据刘世儒的调查:“(盏)后来发展,就用作‘灯’的个体量词,这是由‘灯盏’义引申出来的(如许浑诗‘小殿灯千盏’,又如《八相成道变文》:‘身上燃灯千盏’)。”
许浑(约公元 791—858年)为中晚唐人,而前举释智通(公元公元553—649年)为隋末人,亡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颜真卿(公元709——785年)为初唐人,均早于许浑,则例中“灯盏”之“盏”非量词明矣。至于量词“盏”用来称量“灯”且用在名词“灯”之前(也就是量词“盏”的成熟形式),则最早见于中唐:
张鷟《朝野佥载》卷三:“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
至宋代即多见。
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下:“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
《朱子语类》卷十五:“譬如一盏灯,用罩子盖住,则光之所及者固可见,光之所不及处则皆黑暗无所见。”
虽然此时“盏”已经成了成熟的量词,但据穷尽性调查,唐宋时期,所有的“灯盏”仍为“名名”复合词,且为偏正关系,目前能见到的“灯盏”泛指“灯”的用例,为元无名氏《锁魔镜》第二折:“我做妖魔一百个眼,个个眼似亮灯盏。”但这里面的“盏”仍然是名词性的,因为“灯盏”经常连用,故“盏”也可指“灯”,所以“油灯”也可称“油盏”,如许地山《萤灯》:“她却说:‘没有油盏,怎样点呢?’又一个说:‘就使有油盏,一千盏灯,得多少人来点?”“灯盏”的内部结构应该是同义并列。而同义并列的复合名词往往有集合义。
再如:
【人口】
“口”原名词,乃动物身体的局部,后因“以局部代全体”的借代法而用于表示动物的全体,如“人”,因此有:“男口(男性佣人)”“女口(为奴的女子)”“老口(老年人)”“小口(未成年人)”等一系列“偏正关系”的复合词。而“人口”则是“名名”式同义并列复合词,故带有集合义。类似的还有“丁口”、“民口”等词。
【书本】
“本”原为名词,《说文》:“木下曰本。”本义为“根”。引申为校勘或抄录所依据的底本。再引申为稿本、书册。因此有“账本”、“课本”、“稿本”、“院本”等“名名”式偏正结构复合词。因为“书”也有名词“书籍”义,因此“书本”又可作为“名名”式同义并列复合词,故带有集合义。类似的还有“书刊”“书籍”等词。①《汉语大词典》:“〔书本〕装订成册的著作。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后汉书》:“酷吏樊晔为天水郡守,凉州为之歌曰:‘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州府。’”而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学士因循,迷而不寤。’”其实,此例中的“书本”,乃“抄本”、“写本”之义,为偏正结构。而真正同义并列结构之“书本”,要到明代才见到,如:明何良骏《四友斋丛说》卷四:“今久不拈书本,传注皆已忘却,闲中将白文细细思索,颇能得其一二。”李乐《见闻杂记》卷十:“大学士徐文贞公语余曰:‘大凡书本上话头,听信不得多。’”详见笔者《关于汉语中的名量式复合词》一文,载《汉语学报》2010年第2期。
四
最后,本人认为:“名量”式复合词古代就有(最早中古已经出现),但数量有限,较少歧义的是由“度量衡称量词”及“专用的陪伴称量词”与名词构成的“名量”式复合词(前者如“布匹”、“盐斤”、“田亩”、“地亩”;后者如“马匹”、“车两”、“船只”等),而它们最初的结合可能是由两个跨层单位在线性次序上的连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凝结成了双音词。当然,当此类造词模式形成以后,后代也有些“度量衡称量词”根据类推原理,作为语素置于名词性语素之后,构成新的“名量”式复合词,如“银两”、“茶斤”、“煤斤”、“牛只”、“驼只”等(不过这些词始见时代较晚,一般都在宋元以后)。这些“名量”式复合词都是带有集合义的。
更多的“名量”式复合词,其量词属于“次泛用陪伴量词”,而它们多源于名词,故原来是“名名”式复合词,且大多内部结构为偏正结构(如“花朵”、“灯盏”、“牲口”、“房间”等)所以,它们好多原来没有集合义,前面可以受数量短语的修饰。如:
隋智通译《清净观世音普贤陀罗尼经》:“初四肘乃至八肘五色作,须十六罐子安水及花果子,须十六具香炉、十六灯盏。若作四肘坛,安四罐子、四具香炉、四枚灯盏。”(20—22)
明天然痴叟《石点头》卷十一“江都市孝妇屠身”:“我看孝妇分上,家中有一头牲口,遇水可涉,逢险可登,日行数百里,借你乘坐。”
《儿女英雄传》第十回:“就说我的话:合他们借两个牲口,添上帮套,拉这辆车。”①“牲口”与“人口”当作不同的分析,因为“口”可引申为“人”,如《新唐书·孔戣传》“:南方鬻口为货,掠人为奴婢。”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一“:其所给者,大口月三斗,小口半之,至五月蚕麦既收,随即住支。”另如我们口语中的“缺人少口”、“连家带口”等。“人口”可以分析为“名名”式同义并列复合词,故有集合义。而单音名词“口”始终未引申出“牲畜”义,我们不能说“圈中少口”,故“牲口”为“名名”式偏正复合词。也就没有集合义。
《官场现形记》第一回:“又转过一重屏门,方是一个大院子,上面五间大厅,居中是三间统厅,两头两个房间。上头悬着一块匾,是‘崇耻堂’三个字。”(按:“房间”原来指居旁的屋室,与“堂间”、“灶间”、“庋间(储藏室)”、“廒间(粮仓)”等相对应。)
《官场现形记》第三回:“况且有了这个房间,就是外国人来拜,也便当许多。”(按:这里是专指一间)
不过,此类词中,也有的虽同属“名名”式复合词,但随着后一名词意义的演变,内部结构成了同义并列复合词,如“花朵”、“灯盏”、“人口”、“书本”等(一般时代也较晚,大致都在明代以后),因为同义语素并列构成的复合词,多半也有集合义,所以这些词也就具有了集合义。又因为这些词中的后一个名词性语素后来也都演变为称量词,而“名量”式复合词也具有集合义,所以这类词到底是属于“名名”式复合词,还是“名量”式复合词,不太好区分,但从历时的角度观察,似乎将它们分析为“名名”式复合词更符合发展过程。
当然,还要注意的是,当已经产生“名量”式复合词的构词模式,而汉语中的许多名词又演变为成熟的称量词之后,根据类推原理也新造了一批“名量”式复合词,如“纸张”、“枪支”等,这些“名量”式复合词,一般都出现在近代晚期。
有鉴于此,我既同意刘世儒的说法,“名量”式复合词产生于中古时期(不过范围比刘说要小,仅指“马匹”、“车两(辆)”、“田亩”、“地亩”等)②向熹先生在《简明汉语史》(上)中认为“:上古晚期这类(笔者按:指名量式)复合词偶有出现。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吏员自佐使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其中‘吏员’就是官吏的泛称。”(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p.514)对此种说法,刘世儒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早已否定,并说“:(量词)词缀化构词法的形成——在这个时代以前(笔者按:指南北朝以前),这种构词法一般说还没有形成。偶然出现几个零星的例子,也只能说还是一种‘萌芽’,又因为数量太少,又多有问题,还不能形成为一种范畴。……但到了南北朝,情况就大有不同。因为这是量词空前发展的时代,而由这种方式构成的合成词又是如此之多,还说它仍然是‘名名’的构词法,那显然是说不通的。”(p.16)为了证明这一论断,刘先生列举了南北朝时期八个例子(车乘、钗朵、蒜颗、书本、书卷、马匹、首级、荆株),不过刘先生所举八例中,仅“马匹”一例可以成立。详见笔者《关于汉语中的名量式复合词》一文,载《汉语学报》2010年第2期。,但是从总体上看,王力先生的“直到宋元时代 ,单位词才用作词尾”[21]224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较多的根据“名量”式复合词的已有模式,类推新造(或重新分析的)的“名量”式复合词,是宋元以后才多起来的。
[1] 李丽云.汉语名量式合成词的结构及其界定[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5).
[2] 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3] 张斌.现代汉语[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4]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6]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 朱德熙.语法讲义(重印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8] 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9]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10] 马庆株.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87.
[11] 李宗江.语法化的逆过程:汉语量词的实义化[J].古汉语研究,2004(4).
[12]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纲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13]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重排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4] 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修订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15] 杨锡彭.汉语语素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6] 朱彦.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7]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 [M].北京:中华书局, 1964.
[18] 李宗江.语法化的逆过程:汉语量词的实义化[J].古汉语研究,2004.
[19]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 [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20] 王力.汉语语法纲要(新一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1] 王力.汉语史稿(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附注:
本文所引史书均为中华书局校点二十四史本,佛经材料为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正编、续编(例句后括号中前面数字为册数,后面数字为页数),其他均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
H146.1
A
1671-511X(2011)03-0097-09
2010-12-1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古汉语研究型语料库”(08BYY05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史语料库建设研究”(10&ZD117)的成果之一。本文的相关内容曾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五届学术年会(2010.8.呼和浩特)上作过大会主题报告,承蒙与会学者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董志翘(1950—),男,浙江嘉兴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语史,训诂学,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