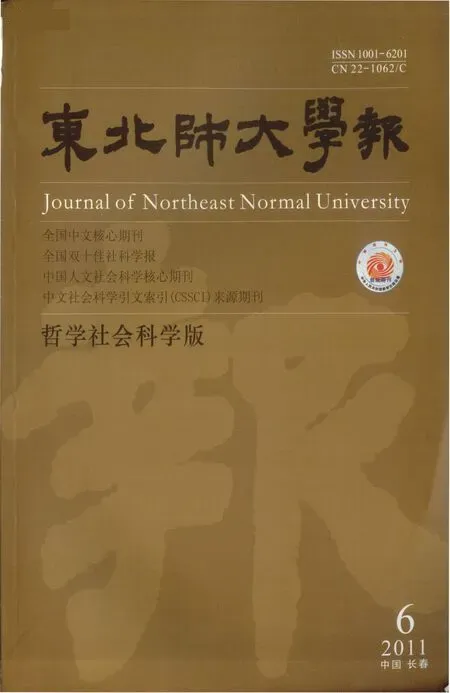论教育哲学研究问题意识的确定
2011-03-31赵万祥
赵万祥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论教育哲学研究问题意识的确定
赵万祥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教育哲学史就是由无数问题贯穿始终的教育问题史。那么确立教育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原因何在?一是通过“本体论”问题的追问与觉解进而厘清现代教育哲学层层叠进的学理线索,从而在差异对勘中寻觅现代教育领域中的症结所在。二是直接“面对事物本身”来提问,对既有问题持续进行“价值清理”与批判,以此证明教育哲学存在之合法性。而“正确地向生活的朴素性回归”,既颠覆了实践次于理论的古典关系,突出教育哲学研究的实践旨趣,同时拓展与转换了教育哲学思维方式与问题视阈,以及对人之生存境遇及未来发展的真切关怀。
问题意识;本体论;价值清理;生活世界
众所周知,教育哲学与哲学有着难以割断的渊源联系。从本源而言,哲学既是教育观形成的哲学理论前提,也是认识教育现象的理性工具。哲学作为“科学之王”,它一方面以各门具体科学所不能涵盖的整体的和无限的世界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探讨各门具体科学或学说的立论依据的非终极性和不完全的可靠性,并对其进行“哲学式”的解释性批判。这种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自我生成、自我否定的带有浓重“可能性”意味的动态思维方式,即人们在各学科领域研究中最具生命力的“问题意识”。
教育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反思性的“构造”过程,即把意义或本质辐射到对象上,从而“构造”对象。因此,“认识体验具有一种意向,这属于认识体验的本质,它们意指某物,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对象发生关系。”[1]人在建构自己的生存世界的同时,也在用“活”的思想活动将自己的生存环境与方式“观念化”,从而逐步完善心物相辅、内外合一的相对完整的二重结构。这种思考方式的确立包含着对追本溯源思路的合理性的承认。其次,它属于教育哲学的自我“解毒性”活动。教育哲学研究并非将哲学原理进行简单地搬运和堆砌,而在于其最为独特的理论性征即“哲学性”有所体现。美国教育哲学家奈尔·诺丁斯曾反复强调:“我们可以运用经验的方法来表明我们的选择确实达到了预期结果中的最好状态,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哲学的立论来说服别人:我们所寻求的结果应该是有价值的。”[2]2它以现实中的教育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鼓励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问题进行“构造”性解析,进而实现一种“自由想象的变换”(胡塞尔语),促使人们透过纷繁芜杂的教育现象认识其背后深藏的本质或者“不变项”。
一、本体论问题的追索与澄明
“本体”(ontology)的基本义理,是回答关于“世界是什么?”的追问。“‘本体’问题的提出表明,人们暗中已把‘对象’分裂为两种存在,一种是对人感官的存在,另一种是事物真正的实在。所谓探求本体,就是要超越感官事物的当下存在,去发现那个隐蔽着但却是真正实在的存在。”[3]本体论首先设定一种与现象世界相分离的“本质”,作为世界的“本原”或“真存在”,其逻辑进路围绕“是什么”、“如何是”、“应是什么”三个维度展开。其次,它探究人究竟如何达到这种可能性的认识,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提问即是“知识何以可能”的叩问。即使在以彻底地反形而上学、反本体论为其基本概念的现当代哲学之中,本体论问题仍然是哲学家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应该说,这种不断询问、回归原点的哲学努力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反观自身、反思当下的对照视角。教育哲学研究者唯有厘清现代教育哲学层层推进的学理线索,才能通晓教育哲学的古今之变,从而在差异对勘中寻觅现代教育领域中的症结所在。
“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换言之,我们或者必须说,每一件事情,包括现代科学最新理论的建立在内,都有一个起源的问题,或者必须说这样一些起源是无限地往回延伸的,因为一些最原始的阶段本身也总是以多少属于机体发生的一些阶段为其先导的。”[4]教育哲学研究所关切的本体论问题不仅包含着对当下教育生活的解读,而且更对人的超越性生存状态、样式充满希冀(人天生具有自我优化的意识,总想通过努力使自己活得“更好”),重新厘定教育与人生之间的内在关系,使教育从知识的简单传递过渡到激发人对自身生存意义的价值性探索,从而实现对“教育——人生”问题的全新解释。人为何而活?支撑人们面对挫折和压力奋斗不止的生活信念是什么?面对多种选择而又必须做出某种放弃的依据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人生问题,都与教育哲学研究的本体论问题密切相关。因而教育哲学必须更深入地探寻人类永远面临、无法回避的人与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及个体自我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才能给人们提供认识生活与人生的正确的价值尺度。具体言之,教育哲学本体论问题具有以下三种面相:
(一)哲学层面
教育哲学研究不能滞留在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而是使它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直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本体论特性,直面社会,直面我们的精神家园,充分发挥哲学所特有的批判与创新功能,给构筑教育活动的必然性王国提供自己的依据。而且教育哲学不能将人看成是已经定格的、僵化不变的承担者,而是用一种“生成性”思维把人理解成为可塑的、朝向未来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人。因而,其哲学层面的本体论问题是“人·教育·思维”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它的主题不外乎以下命题:第一,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生活需要教育吗?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人类通过教育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人类在实现教育目的的过程中自身又将得到怎样的发展?第二,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有规律可循吗?在人类的解放与社会的进步当中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第三,人类的思维能力有无限度?能否认清自身与世界间的关系?人类的思维能力能否在有意识的教育活动中得到提升?等等。
(二)生活层面
身处物质财富高度丰富的现代社会,感官欲望及其享受被过度激发,物质化、单面化成了现代人的一种生存危机。表面上,人拥有很多物质财富,但实质上,人已经沉沦,人性失落了,人失去了本真的存在。因此,教育哲学研究者极力反对将人的教育问题仅仅囿于认识论领域,而是强调唤起人对自身的觉醒,领悟人自己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以寻求解决社会危机和人的精神危机的路径,使人获得拯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基于此,教育哲学研究的本体论问题主要是廓清“生存·教育·存在”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其核心命题是:第一,人在其所生存的世界中的真正位置在哪里?人应当以什么样态去“存在”?人自身从自然生命开始,其生存发展方向和目的是什么?人的日常生活必须遵循某种理性根据吗?第二,教育的目的究竟是服务于人的“生存”还是“存在”?第三,教育究竟能否为人的生存或者存在提供某种指引?教育对人的塑造与人的自我塑造的根据是什么?等等。
(三)理想层面
教育哲学的导向性价值是指向未来的。它的特点是前瞻性、超前性和预示性。它本身就是对人类理想生活状态的终极期许,促使人类不断走向自我超越。“超越”是人类的天然本性。超越意识形成了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张力。人类生存的目的绝非满足于已有的存在,而是追求对“已有性”进行改良式的重构或重建。教育在绝对的意义上都是为或远或近的将来“准备着”,协助人完成理想,不断走向进步。因此,教育哲学理想层面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理性·教育·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它所探讨的命题如下:第一,完美的人性是什么?教育的理想模式是怎样的?实现该理想模式的可能性又有几何?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在发展中又如何协调?第二,教育理想模式的实现是否具有共同的规则?它的普遍性又有几何?教育的塑造功能与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组织之间应当建构怎样的合理性尺度?第三,教育的未来走势与社会进步、人的个性品质的塑造又具有怎样相互制约关系?等等。
由此可见,教育哲学的基本任务无疑应是紧紧围绕阐释“教育应是什么”这个本体论问题展开的,都是对教育意图、目的、目标等等的价值性确证和确认,是一种有关教育的前提性的本体论承诺。于是,教育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不仅是对教育的本原世界的揭示,而且更是对教育的意义世界的批判与构建。
二、“面向事物本身”与“价值清理”
教育哲学具有自身的独特规定,更侧重于对各种教育问题产生的理论前提进行批判性反思,探寻诸多教育现象纷呈的支撑点,并在逻辑上给予合理的推演和价值判断。“我们在理解和解释时,总是借助于我们的前瞻性的判断和成见,而这些预判和成见自身也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我们的目标永远是正确地理解什么是‘事物本身’,但随着我们的视界不断变化,我们提出的问题会有所不同,‘事物本身’到底呈现了什么也就不一样了。”[5]6然而,“事物本身”往往被显现的现实所遮蔽和扭曲,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成为束缚人思想自由的保守因素。研究者如何将事物放置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又如何透过现象深入把握事物本身的性质?福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必然的限定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概括起来,就是“对极限的分析和界限的反思”[6]。直接面对事物本身来提问,人与事物的关系就演化成最直接的“感受”和“体验”,唯有此时,事物的本质才能真正被人所全面描述和把握。
问题意识之所以贯穿于教育哲学研究之始终,根由存在于它隐含着特定的价值承诺和前提假设,能够折射出一定时间和空间、历史和文化的特性。这与教育本身的“传承性”相契合:“传”使得教育文化成为连续性的稳定存在,“承”的理念中又蕴涵着诸多的创新和发展元素。因为“历史的过去并不像是自然的过去,它是一种活着的过去,是历史思维活动本身使之活着的过去;从一种思想方式到另一种的历史变化并不是前一种的死亡,而是它的存活被结合到一种新的、包括它自己的观念的发展和批评也在内的脉络之中。”[7]22观照教育哲学的发展史,不同流派、思潮的更迭变异无不都是对当时的教育问题所蕴涵的前提予以反思,或者是把前提作为一种问题予以审查,在否定性思考的同时又催生出对教育问题的新的建构性认识。比如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哲学思想。“赫尔巴特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他忽视了活的有机体及其意图……教师必须从学生的目的出发,将学生领入潜在的丰富经验之中,仔细地观察他们成长的迹象。”[2]19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谢弗勒(Scheffler Israel)等教育哲学家为当时的教育哲学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就是要采用分析的立场,将教育哲学的任务界定为“清思”,即对教育理论以及与教育实践相关的概念、命题、术语和逻辑等进行澄清。他提出:“分析哲学应用于教育问题的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将分析哲学已有的成果应用到教育研究之中;二是将分析哲学的方法直接应用到教育研究之中。”[8]不过,又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分析哲学之方法似乎已抹杀了教育哲学所应具有之创造性与批判性目的,同时,又压抑一些较具批判性之其他教育思想。”[9]时下,后现代教育哲学又对现代主义教育哲学的传统资源进行新的颠覆与解构,为当代教育哲学的发展开辟出了一块新天地。上述教育哲学景观的演变无不充分体现出教育哲学研究之问题意识的统摄作用。
“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10]教育哲学的独特功能概括而言就是“价值清理”,即以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动为背景材料,以哲学思维和教育本真走势为凭借,不断重新审视教育既成既有的出发点、根据、真理性标准、价值性尺度,不断重新鉴别、选择、取舍和筛定其前提性认知和价值取向。即使我们对范式一词或者革命概念的适切性(adequacy)尚存保留意见,然而教育哲学仍将教育学赖以建立的支柱性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研究方法看成是可以进一步深入辩争和探讨的,而绝非“既定”的和“全真”的。换言之,教育哲学研究一旦缺乏哲学的“思辨性”,将严重背离“有思想”的学术研究宗旨,致使研究者逐渐丧失反思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新能力,进而形成所谓的“文化惰性”。而文化惰性是“语言作为文化符号丧失其原本文化意义的结果。因而,恢复对文化局限性(框架性)的觉悟,对旧文化(即已经成为生命活跃性的禁锢的文化)的批判,一般总是从产生(形成)新的人工话语(概念、口号等)和人工语言(新理论)开始”[11]。
总之,“价值清理”并不意味着对原始问题进行单纯的否定与反驳,而是一种立足于自身发展的价值意义上的“解蔽”与“超越”。“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12]所以“价值清理”就是一种辩证性质的批判,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它在以批判、超越传统为特征的创新思维与以认同、继承传统为特征的常规思维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促发教育理论的主体价值目标与客体运动规律的具体统一,从而形成能够把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的“生成视角”(growing-up perspective)。
三、“正确地向生活的朴素性回归”
人非生而知之,人也不是天生即是社会化的实践主体,他总是与社会成熟个体的标准要求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只能在其成长实践中由教育来解决。因而总结诸多教育实践经验,对教育实践中已经提出的问题进行评析,以确定其正确与否及其可行性如何,则是教育哲学的直接任务。由于深受近代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影响,尤其是实验方法的介入,使近代的实践演变成对客体的自然认知活动,造成了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人为的分离,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日益荒芜、无根。因此,愈来愈多的哲学家开始认为,只有变革理性对感性的至上统治地位,从“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哲学传统中解放出来,人的生活世界才可能消除危机,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拯救。“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7]100所以说,传统哲学追求形而上学绝对的学说,乃是为了某种永恒的本质而偏偏把最重要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那就是人的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处境、前途和命运,这是属于个人经验世界即“街市所属的世界”的境况,而不是抽象的本体世界的境况,这里居于首要地位的是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而不是永恒绝对的本性是什么的问题。“人所需要的不单单是坚定不移地追问终极问题,而且需要知道: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有可能的,什么是正确的。”[13]诸如主体性教育哲学等等,每一种人性化、生活化教育哲学理念的提出,都促使教育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走向更加现实化、科学化、个性化。教育理论去个性化的实质是忽视了本土问题,普遍主义说到底是对本土问题意识的抹杀[14]。这种看似纯粹的思维活动实质上严重地脱离了人的具体化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人生存的一个基本事实,生活世界赋予人生存所依赖的背景知识,激发人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是人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空间。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所膜拜的科学世界实质上而言并不外在于生活世界,正如胡塞尔所言,“科学世界和包含在它之中具有科学的真理性的东西,正如一切以某种目标为划分范围的世界一样,本身也属于生活世界。”[15]教育作为沟通个体与群体关系的中介性桥梁,不仅是一种传递历史文化的活动,还是一种建构人的生活方式以实现人的价值的创造活动。因而必须为教育哲学研究建构起一种“三维时空坐标系”,其中的“三维”是指教育史、哲学史和具体的教育生活实践领域。作为教育哲学研究者,绝不能将研究领域囿于纯粹的思辨的教育理论之上,而忽视了对生活现实性进行“直接关照”的机会,进而遗漏了更为原发性和基础性的教育问题。从历史角度而言,我们应对古今教育活动进行哲学反思,筛选出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主导性价值理念,转变为指导教育发展的理论原则。从即时角度而言,教育哲学研究之问题意识处在多学科视角以及多种研究进路的介入的理性争锋态势,诸如教育的公平、效率、自由以及平等等价值对立问题始终困扰当代教育哲学研究走向,因而唯有不断地消除与本土教育相悖的价值理念,彰显与本土教育旨趣相契合的价值原则、规律、尺度,才能推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生活世界是开放、动态、多元的领域,而单向度、“外向化”的问题意识确立模式无疑又将造成教育哲学发展难以摆脱的暧昧与两难困境。因而对于共同面临的教育问题,需要一种教育哲学研究上的包容意识,即一种世界主义的(或曰全球性的)学术心胸与眼光,即“将最为本土化的本土细节与最为全球化的全球结构以一种将双方同时带入视野的方法连续辩证地联结起来……我们在由那些使整体具体化的不同所构想出的整体与那些激发部分的整体所构想出的部分这二者之间来回跳跃,希望通过一种持续的智识运动将它们转化为对彼此的说明。”[5]6只有处理好“外向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博弈关系,才能凸显教育哲学的“中国”品质,逐步提高教育哲学本土化反思能力,促使教育哲学研究之问题意识更有特色与个性,进而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研究之问题意识的确立,当然脱离不开对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深刻洞察。教育哲学研究者应以人的生活世界为核心范畴,以更新的视角和更高的眼界,沿着逻辑与历史、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贯穿线索,在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教育发展整体过程中自觉形成教育哲学共通的问题意识,将更多目光投向当今时代发展进程中存在和发生的现实问题,并做出理性的调适与选择。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一种朝向生活实践的、问题导向的和真正稳健的研究风格,使教育哲学的学术研究日趋成熟。
[1][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8.
[2]Nel Noddings.Philosophy of Education[M].New York:Westview Press,2007.
[3]高清海.哲学的憧憬——《形而上学》的沉思[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165.
[4][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宪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7.
[5]于泽元.教育理论本土构建的方法论论纲[J].教育研究,2010(5).
[6][法]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539.
[7]周东启.科学实践概念的起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11).
[8]Scheffler Israel.Reason and Teaching[M].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4:13-14.
[9][英]卡尔.新教育学[M].温明丽,译.台北:台湾师大书苑,1998:33.
[10][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7.
[11]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00.
[13][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王才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8.
[14]于伟,秦玉友.本土问题意识与教育理论本土化[J].教育研究,2009(6):27.
[15][德]胡塞尔.胡塞尔选集[M].倪梁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087.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ZHAO Wan-xi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istory is full of millions of problems.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s saving itself from embarrassment.Firstly,we should trace back to noumenon problems,which could embody the whole education period from root and entirety.Secondly,the basis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s critical reflection,which constitutes its unique theory direction and interest,and could identify its own position.It inquires into the true life world,which sets off practice feature,and displays human care about modern and future life.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Noumenon;Value critique;Life world
G40-02
A
1001-6201(2011)06-0159-05
2011-06-30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B165)。
赵万祥(1971-),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何宏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