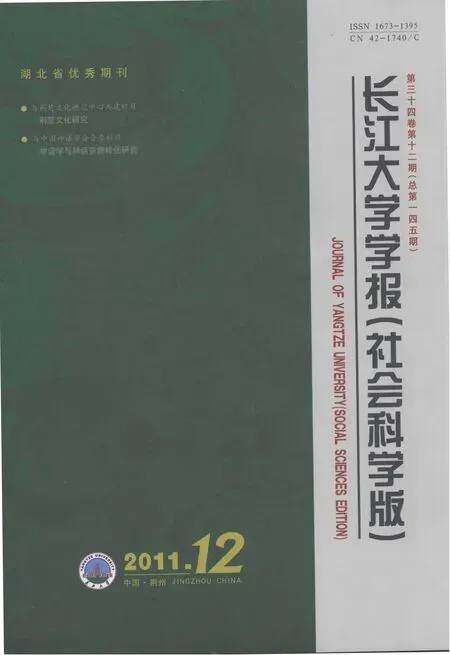论30年代林语堂的名士心态
2011-03-31郑英明
郑英明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论30年代林语堂的名士心态
郑英明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受30年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林语堂自身的经历以及他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林语堂在这一时期极力推崇道家,并在老庄哲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了他名士式的心态:在对待政治的态度上,他标榜“不涉政治”,当纯粹的文化人,主张“超政治”和“近人生(情)”;在文学上,他创立了独特的远离政治现实的文艺理论体系;在生活上,他用幽默和闲适等手段来借以逃避现实,表明取向。这种名士式的心态也显示出林语堂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别的存在”。
林语堂;30年代;名士;心态
一、惜头颅,不涉政治;心不甘,讥评时弊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令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蓬勃兴起。就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文艺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英勇的斗争”的时代背景下,20年代时期的林语堂对政治充满极大热情,对社会现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主张“必谈政治”,认为“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勿谈政治是中国民族病态的表现”。[1](P12)然而,到了30年代,他为了苟全身家性命,迫不得已地选择了一条如他自己所述的是“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中间道路,是社会政治的中间物。他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刊物,均打出了“不涉政治”和“超政治”的自由主义中间旗帜。
在林语堂30年代的文艺观中,文艺与政治是对立的。他反复强调文艺的“超政治”,如他在《人间世》第2期的“编辑室语”中曾直接宣称“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不愿涉及要人之所谓政治”,并将“超政治”或“不问政治”作为其办刊的指导方针。在强调文艺的“超政治”的同时,他还强调文艺必须“近人生”、“近人情”,作为文艺须“超政治”观的一个补充和具体实施。他认为,文学与其“钻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在林语堂看来,要使文艺“近人生”,就必须使文艺言自我之志,抒人生之情,表述身边琐事的存在价值,那些“近人生的文学作品并不一定呐喊”,但却是“怡养性情有关人生之作”。
在对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林语堂的前后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前期他主张“必谈政治”,强调“学术与政治”联系密切,而反对“勿谈政治”。“政治思想不清的人要叫他对学术有清晰的思想,‘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这是林语堂对政治与文艺二者关系的明确表述。这充分表明林语堂鲜明的介入政治的文艺倾向。
事实上,林语堂“超政治”的文艺观念和主张正是受30年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他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西方个人主义的直接影响所致。30年代之初,国民党大规模清党反共,国民党统治集团严厉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新文学运动所进行的压迫,较之旧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1933年,与林语堂关系密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成员杨杏佛被刺,林语堂在家乡开展抗日活动的侄儿林惠元被国民党杀害。这两件事对林语堂的文艺、生活观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这样一种险恶的政治斗争现实和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林语堂对国民党政策惧怕的同时,又感觉看不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希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持怀疑疏远的态度。他抱着身家性命之虞,不愿再招惹杀头之祸,只想远离残酷的现实生活,做一个“年轻的顺民”,独善其身。此后,他开始以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自居,以此来作为对当时国共两党尖锐对抗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回答。
我们还应该看到,林语堂是一个留过洋,接受过欧美式民主政治思想熏陶的自由资产阶级文化人,这种经历对他前后期政治观的转变亦有相当的影响。他带着否定“关注政治和必谈政治”的非功利主义文艺思想回国,对30年代国共两党尖锐对抗的社会现实持双重不满,且失望且恐惧的心态,反映在对待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上,便是无政府主义、中间立场和超政治文艺。
尽管林语堂在30年代以不问政治标榜自己,但从林语堂的文学实践看,却并非全部超然于政治之外。他虽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但他并没有完全隐退,遁入深林,还未能做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他在文学创作上,常常是信手拈来,在谈“再启”,谈“牙刷”,谈“西装”的同时,他也写了一些有抨击时弊倾向的文章,如《论政治病》、《文字国》等文,它们是以一种特别的角度用亦庄亦谐的轻松笔调来讥评和讽刺时弊。
二、鼓吹幽默,提倡闲适,名士生活艺术呈异彩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第一个引进西方“幽默”概念并加以鼓吹的重要人物。在30年代,他更获得了“幽默大师”的荣誉。除了“幽默大师”的头衔外,林语堂还是现代中国文坛上“以闲适闻名”的人。幽默与闲适共同构成了林语堂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名士式生活艺术观。
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这种幽默的人生观是一种超脱和达观,是以这样的审美眼光来看待生活:“冷眼旁观,不带功利色彩地自我审视,抛弃孜孜求利求义的野心和欲望,超脱政治是非,也超脱生老病死苦乐荣辱,排除生活中的烦恼与困惑。”同时,林语堂认为,“超(排)脱”或“达观”不能“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因为“到了愤与嫉,就失去了幽默温厚之旨”。看来林语堂之真正的幽默人生观是“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具有温厚的性质,强调借助心理机能的自我调节,排除各种困惑与烦恼,保持开放的心灵,以便领略生活的乐趣。
林语堂喜欢闲适,认为闲适是最高贵的一种精神之乐,推崇闲适小品文,甚至将整部中国文学史的价值都归功于闲适。其实,林语堂并不真正理解中国文学中的闲适精神内核。中国古典文学中颇多闲适之作,但“中国文学史上闲适诗文的作者多是‘闲’而不‘适’。有志于世而不得用,只好故作旷达,表面仙风佛骨、轻快飘逸,内心却苦不堪言”[2]。这种舒适、雅逸的闲适生活观,反应在文学上,便是30年代林语堂所提倡的闲适小品文。小品文与名士向来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林语堂追求文学审美风格上的闲适出世的观点和倾向,继《论语》鼓吹幽默文学之后,《人间世》、《宇宙风》都以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为主。林语堂认为,闲适论之主旨便是小品文应该成为自我的闲情偶寄。也就是说,文学表现自我的闲情别致,应该是超时空,没有任何现实理由的。可见,“超政治”和“近人生(情)”乃林语堂所提倡的闲适小品文的实质、价值和功能。
综合以上对林语堂30年代心态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林语堂在政治上走着一条“不涉政治”的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以不问政治来标榜自己,开始当“纯粹”的文化人,主张文艺必须要接近人生(情)。而最为直接鲜明地体现出林语堂“超政治”和“近人生”(情)这一文艺思想指导原则的创作理论主题便是“表现—性灵”论和“幽默—闲适”论。于是林语堂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开始有了足够令人称羡的闲适:他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一反方巾气,站在道家的立场来选择中国文化,便有了更多的超乎当时社会政治的行为举止,幽默态度和隐逸精神陡然倍增。这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的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种叛逆,而叛逆的动力的确来自于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来自于无法兼济天下而只能独善其身。
[1]林语堂.读书救国谬论一束[A].林语堂.剪拂集[C].上海:北新书局,1928.
[2]陈平原.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3).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I206.6
A
1673-1395(2011)12-0020-02
2011 -10 26
郑英明(1971-),男,福建大田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法律文书、应用写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