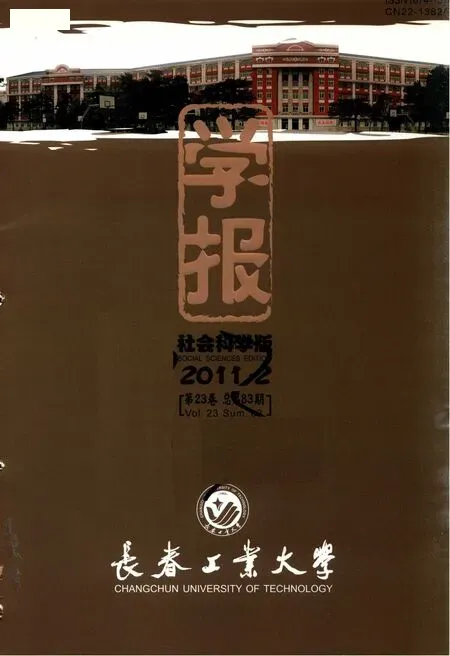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著述特点
2011-03-31康桂英
康桂英
(安徽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安徽淮南232001)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著述特点
康桂英
(安徽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安徽淮南232001)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成书于抗战时期,该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各派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积极准备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著述特点
何干之(1906——1969),广东台山人,原名谭毓钧,学名谭秀峰。1936年应时任上海生活书店总编辑张仲实稿约,开始用何干之为笔名发表文章。此后,就改名为何干之。何干之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生著述宏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是何干之对1927年以来中国知识界有关“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性评述”。[1](P182)全书从中国经济的特性着眼,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驳斥了种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认识,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特征,也为研究中国的抗战提供了理论探索。
一、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明确的著述宗旨
1937年,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该书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发行了10版,可见影响之大。何干之“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十分重视实践的要求,即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革命实践提出来的种种问题”,[2]故其“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理论问题”。[3](P4)因此,《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紧扣时代脉搏的应时之作,有着非常明确的抗战救亡的著述宗旨。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中国革命的起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人开始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联合形式以及各阶层的历史任务等方面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而“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呢?那是一切问题的中心”,[1](P209)因为只有“认识了中国社会,才配谈改造中国社会”。[1](P187)因此,何干之认为1927年知识界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是一场有历史价值的论争”,因为通过这场论争使国人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现在试任意执住一些肯和实际问题接近的青年,问他们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我想除了极少数头脑已经僵化的不算以外,一定会回答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1](P183)这个正确的认识可以“作为决定未来抗争的战略战术的前提,作为再出发的基础”。[1](P209)在日本大举入侵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就更“有助于救亡”。[1](P183)何干之的观点,后被毛泽东加以发展。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4](P646)
基于“抗战救亡”的著述宗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专设了“由社会性质的论争到国防经济的论争”一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驳斥了“中国经济派”只把“技术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认为技术的研究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手段,而经济学研究目的则在于“更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为着要准备战时的物力”。[1](P258)何干之认为,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以前中国是国际财政资本的半殖民地,现在已渐渐变为远东侵略者的全殖民地”,[1](P257)亡国灭种的灾祸刺激了每个爱国爱民族的中国人。为了更好地为抗战服务,“目前研究中国经济,不应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上,最要紧的是应注意这五六年来中国社会的剧变,应注意这种剧变在救亡运动中所发生的结果,以建立我们抗敌的物质基础”。[1](P184)抗敌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发动一切可能的革命力量,共赴国难”,[1](P263)“集中全国的一切物力,来制服敌人”。[1](P264)因此,“国防经济的对象,也是以生产关系为主,技术关系为末”,“技术的新任务,乃由阶级的新任务所决定,阶级的新任务,又由社会关系所决定”。[1](P263)何干之的这些论述表明了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关注抗战时局的态度。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何干之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延安,毛泽东曾有意让何干之做他的秘书,并同何干之就一些问题通过几次信,“故一般认为,何干之的研究对毛泽东发生过直接影响”。[5]日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吸收了何干之的上述观点。何干之说,“如果这本小小的读物,对于热心救亡的青年研究中国问题,有点补益的话,那我就感到无上的快慰了”。[1](P184)事实的结果是,他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不但促进了国人对抗战的理解,而且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他的愿望实现了。
二、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鲜明的指导思想
何干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素养深厚的历史学家。早在1925年广东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读书期间,他就曾广泛阅读“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编辑出版的进步文学刊物,阅读中国共产党的党刊《向导》周报和《新青年》等杂志”,[6](P2)并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1929年在日本求学期间,他完整系统地自学了马克思主义文献,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6](P5)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思维方法,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1934年,何干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这时起,何干之在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运动中,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奋笔写作”,[6](P10)撰写了《中国经济读本》、《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一系列的作品,也奠定了何干之“成为国内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地位,“不少青年就是读了这些书后,思想转变走上革命的道路”。[3](P2)“何干之认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要有深厚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2]而《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就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讨中国革命问题的代表性著作。
何干之认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症结,在对于帝国主义、民族资本和封建残余那三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的了解,所以这根本的认识,是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关于这问题的论争的焦点。只有正确地了解这种相互关系,对于目前中国社会性质的估计,才能有可靠的保证。因此各党各派对这问题的认识不同,就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发生了种种式式的争论”。[1](P216-217)这种争论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意义的。通过这场争论,最终使国人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为未来的革命奠定了理论基调。在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何干之“鲜明地站在进步的社会科学家一边,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6](P11)这里进步的社会科学家主要指的是新思潮派,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主要是指托派和机械派的观点。
新思潮派认为,中国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下的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强有力的封建关系”。何干之积极支持这种观点,认为“站在目前的理论水准,来评价当日各位战士的观察,当然发现许多幼稚、空疏、不够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拿出历史的眼光,来追寻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确有了划时代的贡献,有极大的历史价值”,而且他们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上已经初具雏形;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理论的草创时期,他们做出的这种大胆尝试,“功绩是不可磨灭的”。[1](P214)从中可以看出何干之的态度。托派认为“中国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农村没有封建势力的地位”,“中国革命是一种反海关的革命”。何干之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是中国不单单只有海关被帝国主义国家把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体都有帝国主义的烙印与封建势力的踪迹”。因此,“反帝反封建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唯一出路”。[1](P205)机械派则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绝对地破坏了封建势力,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外资的发展,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对于机械派的观点,何干之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何干之说,机械派之认为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出现错误的认识,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中国现实的经济状况。而事实却是“资本主义是已经出现了,前途却暗淡无光,封建制度也已经在崩溃的过程中,但因为有帝国主义的有意无意的扶助,它到今日还占着优势的作用”。因此,机械派的观点是“不求内容,只求形式,不问本质,只问现象,乃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的产物”,[1](P234)他们忽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在生产关系的范围外来观察生产力的运动,这是无意义的瞎说”,所以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就是在很多问号之后、各派的争执之中最终产生,《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客观地记述了这个过程。
三、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独特的论证角度
成仿吾说,何干之早年在上海时就认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并认为“这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了解中国革命问题的基础”。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何干之注重“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入手,研究中国革命理论问题和中国现代革命史”,[3](P4)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方法。早在1934年,何干之撰写的《中国经济读本》一书中,就“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以真实的材料为纬,使理论与实际纵横交错,把中国经济的真相,和盘托出”。[7](P31)193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也是从经济的角度着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驳斥了种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认识,进一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
何干之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准就是中国政治理论的测量器”,“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准是中国革命观的最后试金石”。[1](P205)因此,要想真正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必须要从中国的经济入手。无论是托派还是机械派,他们之所以错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够很好的认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究竟是什么状况呢?何干之从工业、农业和金融货币三个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何干之说,“资本主义入侵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因为社会的一切都建筑在农民的剩余劳动之上”;[1](P154)可就“在中国历史刚踏上新旧转变的紧急关头,外来的力量已冲破了闭着门不闻外事的天朝了”,[1](P188)中国自身发展的步伐被彻底打乱,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无尽的深渊。从工业上看,“近代中国工业并非自发的,乃由外来的压力所迫成”,[1](P188)洋务派官员虽曾积极创办洋务,可列强凭着雄厚的资本和政治军事力量,早已巩固了支配中国经济命脉的根基。在外资左右中国经济的前提下,虽然中国的工业在一战后曾经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但不久就昙花一谢了,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从农业上看,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不惜用最野蛮的方法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或者扶植一切前资本主义关系;土地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农民和地主存在着主奴关系,在外资的入侵面前,均无力发展经济。所以“这种农业经济既不是自然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乃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商品经济”。[1](P196)农业“确是朝着商品化的大道大步前进,可是并不能够转化为资本主义”;[1](P192)从金融货币上看,中国金融资本是买办高利贷资本的变相,具有十足的寄生性,对民族工业起着阻滞作用,“他们为帝国主义的榨取网作经理人,推动中国向着全殖民地的路子走,企图分一部分殖民地的利润。他们又和军事机构结成一条战线,支持半封建的榨取网,从中来分一份肥利”。[1](P198)据此,何干之认为,“在殖民政策下,中国工业休想能够自由发展,休想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P199)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的革命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向,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它具备两重的任务,那是过去英法德美俄日土的历史所没有的。同时,革命的执行者不是上层,乃是千千万万的下层国民”。[1](P209)
“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是了解中国社会性质的关键。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结论,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理论指导”,[8]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使何干之非常准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关键。
综上所述,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其为抗战服务的著述宗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从经济视角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鲜明特点而扬名于世。1941年6月,该书被国民党政府以“触犯审查标准”为由停止发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书的影响之大。斯人已逝,其学术精华却永放光芒。今天,当我们重新研读《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时,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的时代性、斗争性以及向导性。
[1]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A].何干之文集(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2]刘炼.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史学思想[J].史学史研究,1981,(4).
[3]成仿吾.我与干之[A].何干之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4]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A).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J].新华文摘,2004,(9).
[6]胡华,刘炼.何干之传[A].何干之文集(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7]何干之.中国经济读本[A].何干之文集(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8]洪认清.何干之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探讨[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1).
康桂英(1975-),女,安徽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