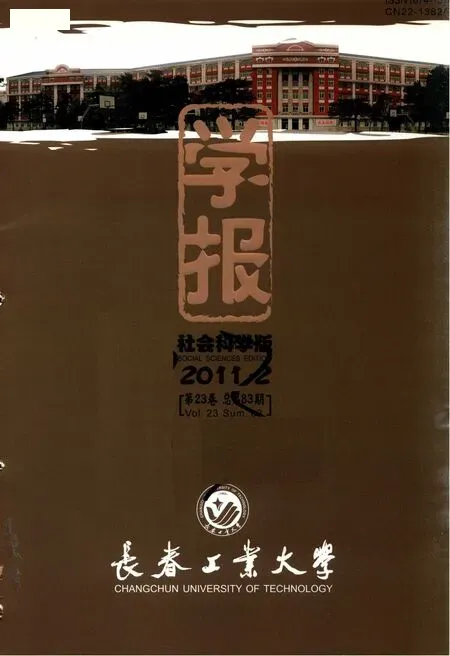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探析
2011-03-31张传泉
张传泉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探析
张传泉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主要表现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的回答上。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德里达着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德里达主要强调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参考价值。
德里达;马克思主义观;内容;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浪甚嚣尘上的时候,作为世界级的学者,法国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挺身而出,公开向马克思致敬,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德里达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它集中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观两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上。
一
马克思主义观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此,德里达从三个方面作出自己的回答: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德里达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弥赛亚”,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发明创造,不是只属于19世纪的经典理论,而是随时就要降临的东西。“诚然,那幽灵的徘徊是历史的,但它没有确定的日期,根本就没有办法按照历书的预定次序在当下的时间链条中一天接一天轻而易举地给定一个日期。”[1](P6)“它的恶魔般的威胁一直在20世纪的上空徘徊。”[1](P94)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从事纪念马克思的活动,哀悼马克思的精神,“哀悼的意图常常在于试图使遗骸本体论化,使它出场”。[1](P10)“值此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它的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位置之际,任何断然的否认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所有各种幽灵们的纠缠。”[1](P37)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幽灵是不会现身的,幽灵不会降临到场,幽灵永远不会站到我们面前。共产主义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是要到来或复活的鬼魂,马克思的幽灵在当今世界徘徊。并且,德里达指出,今天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马克思的幽灵不再需要载体。对于明天的马克思主义、它的遗产或遗嘱的遭遇的思考,应当包括对政党的某种现实性和某种概念的有限性的思考,对它的国家相关物的有限性的思考。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德里达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秩序”和马克思生前一样,仍然需要永不停歇的批判。“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如果人们知道如何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不论是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与知识的占有,还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话语与实践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资格和国籍的种种新问题等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1](P83)在德里达眼里,自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精神,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遗产。德里达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路易·波拿巴雾月八十日》等著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存在多种不同的精神,要求把批判精神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区别开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建立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此同时,德里达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认为这份马克思的遗产是永恒不灭,德里达称为“解放”、“弥赛亚性”的精神。相比较批判精神,德里达更看重解放精神,他坚持这种“弥赛亚式”的许诺“正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安身之所在”。根据解构主义的一贯立场,德里达认定解放精神是“摆脱任何的教义,甚至任何形而上学的宗教的规定性和任何弥赛亚主义的经验”。[1](P86)
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特征论的问题上,德里达主要回答了以下三点:首先,德里达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他几部伟大著作之后,我得承认,我对哲学传统中的文本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假若我们思考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有关他们自己可能变得过时和他们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的言论(例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再版序言中的论述),就会觉得他们的教训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1](P14)德里达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明白的警告,正视马克思学说的时代局限性,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就是让我们发展、变革他们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是复杂的和不断发展的。其次,德里达认为马克思分析社会历史之所以深刻,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这样一种‘自觉自愿’的批判必然是根深蒂固的”,[1](P85)马克思主义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批判因为眼下西方社会的“十大溃疡”而显得更为迫切。“但需要借助于批判性的分析,而不是某种反魔术。”[1](P46)最后,德里达宣称给马克思的幽灵们预言一个未来,呼吁他们的异质性。“这意味着可能有一撮,尽管不是一伙、一帮或一个社会,要不然就是一群与人或不与人共处的鬼魂,或某个有或没有头领的社团——而且是完完全全散居各处的一小撮。”[1](P5)但是,德里达认识到马克思遗产的根本的和必要的异质性,他着重指出,马克思的幽灵们绝对不可能聚集在一起。“如果那帮幽灵一直是从一种精神获得生命的话,人们就会思忖有谁敢谈论一种马克思的精神,或者更严肃地说,谈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1](P5)
二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观的又一个基本问题,对此,德里达着重从三个方面作了回答:
第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我们要通过对它科学地重读和哀悼,使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活力。一方面,德里达强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德里达认为,人们只有通过阅读马克思文本才能寻找到马克思的精神,“把《共产党宣言》中最为醒目的东西忘得如此彻底,这肯定是一个错误。”[1](P1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回答“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德里达建议在所谓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消亡后进行阐释,对历史的马克思和今日马克思的反复阅读,“对马克思的遗产进行重新诠释”。[2](P93)另一方面,德里达指出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文本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列,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需要从边缘出发。选择幽灵作为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线索,德里达十分满意,他谈到:“在提出‘马克思的幽灵们’这个题目时,我最初考虑过某种徘徊不去的思想情感的所有各种形式,这种思想情感,在我看来,似乎对今天的话语发挥了主导的影响。”[1](P37)德里达在谈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联系社会实际,这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
第二,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首先,德里达解释了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他指出,当今世界存在“十种祸害”,“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1](P76)德里达告诫人们“忠实于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面对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与知识的占有,还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话语与实践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资格和国籍的种种新问题等等,马克思主义仍然能够结出丰硕果实。其次,德里达公然宣称:我挑选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敬。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低毁者都在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的确已是一个摆在和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面前的问题了。”[1](P15)经过深思熟虑后,德里达提出,“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1](P5)最后,德里达明确指出,知识界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捍卫负有很大责任。这种责任要求我们一贯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霸权”;对新老保守主义进行毫不留情地斗争,高高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解构的方式不停地进行批判,千方百计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武器;保存马克思幽灵的异质性和发展性,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批判精神和解放精神。
第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德里达表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我们必须加以继承。德里达告诉我们,马克思遗产的继承者是复数,即是众多的言说形式的继承者,“也是一个本身已经脱节的指令的继承者。”[1](P17)无论是我们喜欢与否,知道与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继承这份遗产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德里达虽然说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自认为继承了马克思的某种精神。德里达坚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继承它的最有“活力”的部分。在德里达看来,我们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承担责任。继承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责任是消化、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德里达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经院化,强调必须忠实于马克思的本意。他强调突破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论断和现有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按照德里达的看法,马克思思想不应局限于理论学说之上,还要成为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新思维。在此,德里达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幽灵呼唤的就是以“新国际”来批判和颠覆当今霸权国家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国际政治秩序。
三
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观两个基本问题进行了富有特色的回答,见解独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第一,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德里达的理论是当今时代人文学科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其解构主义所向披靡,广泛渗透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很多领域。当一些原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纷纷远离马克思,德里达公然宣称“我们都是马克思的遗产的继承者”,在整个世界引起广泛的影响和强烈共鸣,推动更多的人反思资本主义,关注马克思主义。1993年4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思想与社会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国际讨论会,德里达被邀请并做了两次专题发言,发言的题目是:“马克思的幽灵们——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会后整理出版,一经出世,便引起轩然大波。全球化的视野下,德里达时刻关注中国改革式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的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德里达承担着继承“马克思遗产”的重任,他要“重整乾坤”,如同哈姆雷特的出场。德里达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与时代命运联系起来,积极倡导“新国际”思想,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助于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问之事,本无中西,与西方学界的对话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之一。解构主义的出现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作为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德里达认定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解放精神,开创了解构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德里达的老师、同乡、同事与朋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著文《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提倡“症候阅读法”,通过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保卫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些立场”,[3](P254)反对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实用主义、进化论、经济主义、哲学唯心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危险的形式。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声势渐弱。西方四大思想家德里达、哈贝马斯、詹姆逊和吉登斯并肩作战,不约而同地走进马克思。德里达自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有史以来最低谷的时候,他却毅然举起捍卫马克思的大旗,宣称“向马克思致敬”;[1](P84)詹姆逊一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他声称自己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出自兴趣”;[4](P22)哈贝马斯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庸俗化,认为苏东剧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终结,他宣布“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吉登斯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他直言“虽然不再时髦,但我仍看重马克思”。[5](P3)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诱发了欧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针对《可怖的分界:对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的讨论》的挑战,德里达以《马克思和儿子们》一文迎战。他们的交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幽灵》这本著作的精神,除此之外,这次论战直接地涉及到革命、阶级与解放等问题,为我们了解西方学界对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参考价值。树立和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路径选择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路径是充分借鉴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全球化的语境中,积极与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对话,有助于实现范式革命。首先,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发生论、本质论、结构论、特征论和功能论的回答,描述了马克思主义来临的形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解放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价值,使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客观存在的,是随时就要降临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是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强大的精神支柱,科学的方法论,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为我们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德里达强调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忠实于马克思的精神,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继承马克思的遗产,为我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目标导向。最后,德里达对马克思解读的“工作”还在于揭示了马克思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展示了广阔的视域;强调批判、选择和过滤马克思主义,提出“新国际”的思想,积极回应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种种困境。必须肯定的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深刻,振聋发聩,在某些方面远远超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程度。不仅如此,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有着独到的发现,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出人意表的判定,发人深思。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进一步发掘其学术价值,对于我们坚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法〕雅克·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M].杜小真,张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张传泉(1987-),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