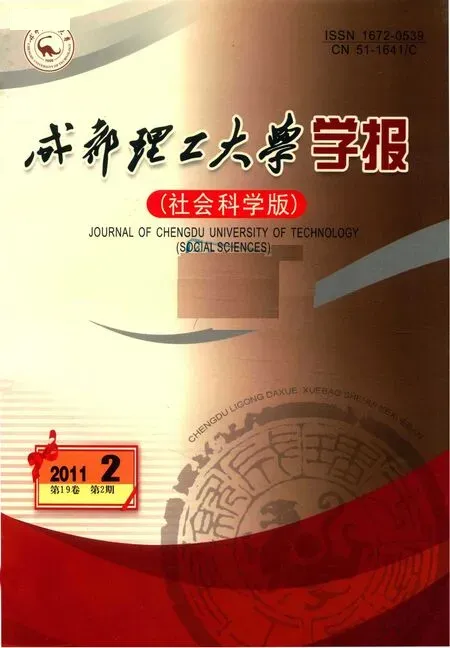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研究
2011-03-31龙建明
龙建明
(吉首大学 法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研究
龙建明
(吉首大学 法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在权利易受权力侵犯的刑事诉讼场域,建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是有权利必有救济理论、诉讼主体理论以及人性恶预设理论的必然要求。权利救济内容不完善、救济义务主体不中立以及重要权利救济方式的缺失,是当前我国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我国应树立程序正义、救济为民的理念,在刑事诉讼中进一步完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内容、设置相对中立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以及增设财产保护令等。
被追诉人;财产权;强制处分;救济制度
在西方经典政治理论中,财产权被誉为“最根本之自由”,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道被视为公民最基本的人权。[1]但在权力与权利冲突激烈的刑事诉讼场域,为收集和保全犯罪证据,确保诉讼顺利进行,有必要赋予特定国家机关对被追诉人财产进行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强制处分权力(1)。然而,司法实践表明,权力有易被滥用的危险,(2)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合法财产往往易受到来自国家公权力的不法侵犯。这样,如何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追诉人财产权进行救济,便成为民主正义的刑事诉讼制度设计所面临的一个永恒话题。正是基于此,本文拟就我国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3)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
一、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理论基础
(一)有权利必有救济
“有权利必有救济”,是西方国家人们所熟知的法律格言。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认为,“对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比宣示人的权利更为重要和实在。只有具备有效的救济方法,法律之下的权利才能受到尊重,名义上的权利也才能转化为实在权利。”[2]就国家而言,宣示公民权利并不困难,但如何将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则绝非易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利救济是权利实现的有力保障,只有能够得到救济的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否则,有权利而没有救济,就犹如是纸上谈兵,说起来好听,却无多大的实际作用。财产权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同其他权利一样有赖于救济权保障。如果宪法和法律仅列举和宣示公民(包括被追诉人)享有财产权,但当这种财产权遭受侵犯时却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那这样的财产权赋予就犹如签发一张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特别是在侵权与被侵权的刑事追诉和被追诉双方力量先天失衡的情形下,赋予遭受强大公权力侵害的被追诉人救济权利就更显得迫切和重要。否则,宪法和法律所赋予被追诉人财产权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法定财产权利也就难以转化成为其所能实际享有的真实权利。
(二)被追诉人诉讼主体理论
被追诉人权利救济制度是建立在被追诉人具有独立人格主体的基础之上的,在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中,被追诉人自身往往只是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一种手段,其诉讼主体地位难以得到确立,人之为人的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在这种诉讼模式中,很难谈得上将财产权救济作为一种制度进行构建。但自近代以来,伴随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主体理论的产生,(4)被追诉人从诉讼客体逐渐转变为与国家追诉机关一样被视为平等的诉讼主体,双方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存在诉讼角色的区别。而“作为主体,个人必须拥有参与涉及自身利益的决定过程及改善自身处境的机会和手段。”[3]这样,在诉讼过程中,对被追诉人人格尊严给予重视,赋予其参与诉讼的机会以及对被侵害财产权利进行救济,便成为必然。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被追诉人诉讼主体理论,就不会有被追诉人财产权利的享有,也就没有对其财产权救济,当然就无所谓对其财产权救济制度的构建。为此可以说,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理论是对其财产权进行救济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三)“人性恶”预设理论
将“人性恶”预设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构建之理论基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其与人性离得有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4]具体到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基于对被追诉人财产进行强制处分的公权力主体的“不信任”,因为公权力行使者和常人一样,也具有恶性潜在,其有滥用权力的可能。当然,以性恶论为预设,加强对刑事诉讼权力谨慎防范的财产权救济制度设计,并不等于说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天生就是“坏”的,而是采取了类似“先小人后君子”的策略,把人往最坏处着想,从最坏处着眼来对人进行防范,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这往往能获得较好的效果。在西方国家,人性恶是主流思想,这并非说西方人天生就喜欢性恶。但这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因为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具有恶性潜在。为此,必须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贪婪成分的恶性膨胀。可以说,西方法治就是以防恶为逻辑起点,以保障个体权利为归宿。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一方面是为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亦是为了防止社会个体权利滥用。[5]这种基于对人性不信任的理论预设,不仅对我国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的生成与运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也是该制度构建的人性基础。
二、我国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现状
(一)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相关立法内容
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内容是指宪法和法律赋予被追诉人哪些财产权利,只有当这些法定财产权受到侵犯后,被追诉人才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行体现国家意志的财产权救济。可以说,法律赋予被追诉人财产权的多少直接决定着被追诉人财产权受保护的范围和程度。就我国而言,现行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39条),2004年宪法第四次修正案亦明确指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但作为保障宪法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对宪法所确立的公民财产权却没有提供有效保障,如刑诉法没有规定被追诉人财产受到搜查、扣押、查封和冻结时,其享有被告知搜查、扣押、查封及冻结的理由等相关权利,由此导致被追诉人财产受到不法强制处分时,因知情权的严重缺失而难以获得及时有效救济。又如刑诉法仅规定了“对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没收,上缴国库。”但对被追诉人就自己财产作为赃款赃物处理中所享有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加之刑诉法对何谓赃款赃物及其认定以及处理程序等也没有明确,由此导致国家权力机关随意扩大赃款赃物的范围,动辄以赃款赃物为名对被追诉人财产进行截留、挪用的情形经常发生,而财产权受侵害的被追诉人却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途径。此外,刑诉法在设置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对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收取、管理和没收的制度中,被追诉人享有哪些权利也未予以明确规定,由于有关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内容之规定存在诸多的不合理,这就难免出现被追诉人的保证金本应退还却遭到执行机关不法没收时,被追诉人难以通过法律渠道获得救济。
(二)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
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主要是指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财产权受到国家公权力不法侵犯时,谁有义务对被侵害人的财产权进行救济。一般而言,权利救济义务主体的相对中立,是受害者的被侵犯权利得以公正裁决的前提条件。从我国目前法律关于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之规定来看,救济义务主要是由被控侵权机关来承担。以刑事赔偿为例,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具有侵犯《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财产权情形之一的,被追诉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根据新修改的赔偿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财产权受侵害的刑事赔偿首先必须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而赔偿义务机关就是被控侵权机关。这种过分信任侵权机关自我纠错的能力和品质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受害者获得赔偿的难度增大。尽管财产权受侵害者对赔偿义务机关的裁决不服的,可以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且对复议机关不予复议或对复议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请求裁决。然而,我国刑事赔偿程序主要是采取行政性程序方式来进行的,其司法化的程度较低,受害者财产权受到侵犯却无权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途径获得司法救济,这对公民特别是对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极为不利。为此,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刑事诉讼中被控侵权国家机关承担的客观义务及其所具有的公正法律意识,但无论怎样,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有违程序正义,有时即便实体处理公正,也难免使人产生司法不公之合理怀疑。因此,有必要设立相对中立的赔偿义务机关,这对遭受国家权力不法侵害的财产权救济十分重要。
(三)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方式
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方式,是指被追诉人合法财产受到刑事侦查权、检察权以及审判权的侵犯时,可以通过什么法律途径或渠道对被侵害财产进行恢复、弥补或补救。由此可见,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方式的设置是否科学、合理,不仅有利于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保障被追诉人自身合法财产权益,而且有利于追究侵权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就我国目前而言,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方式虽然较多,如申诉、控告都是被追诉人财产权的救济方式,鉴于申诉、控告缺乏可操作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其更倾向属于民主政治权利。因此,在我国比较切实可行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方式主要是刑事赔偿。新国家赔偿法虽对原赔偿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修改,但仍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如对财产权侵害的赔偿范围过于狭窄、财产赔偿标准单一等。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缺乏有效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渠道,也尚未规定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诉讼行为无效、通过诉权行使进行司法救济等一些重要的财产权救济方式。
三、我国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内容
1.在宪法中规定对被追诉人财产强制处分必须遵守的正当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一词表征的是一种规范或者说正统执法的理念,在本源上,主要是指刑事诉讼必须采取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6],其核心是指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对他人生命、自由及财产进行限制与剥夺。倘若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可以对他人财产予以限制和剥夺,那么,必然导致的是国家公权力滥用、人治的横行。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所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绝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7]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宪法,在根本法中确立对被追诉人财产强制处分必须遵守的正当程序,这有助于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最终有利于保护被追诉人的财产权利。
2.在刑诉法中确立被追诉人享有对财产强制处分的被告知权利
在权利与权力冲突激烈的刑事诉讼场域,被追诉人对特定国家机关就自己财产所采取的强制处分虽有接受的义务,但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当对被追诉人财产强制处分时必须实行权利告知,这不仅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民主和正义底线。因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现行刑诉立法关于被追诉人财产的各种强制处分,除了搜查必须出示搜查证、扣押物品须将扣押清单交给持有人等间接告知外,几乎没有关于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时权利告知的直接明文规定,这对其合法财产之保障极为不利。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被追诉人对自己财产被强制处分时享有被告知的权利,并明确规定告知理由、告知公权力主体身份、告知享有证据保全请求权、告知时间和方式以及不告知的法律后果。
3.在刑诉法中赋予被追诉人享有对财产后续强制处分听证权利(5)
“听证”是一个广泛运用于行政领域的概念,一般是指有关当事人权益的行政决定作成之前,给予当事人就重要事实发表意见的机会,借以避免行政权之恣意专断,保障当事人之权益。[8]听证之所以在行政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在某种程度上,是行政权不断扩张与公民权利保障诉求不断博弈的结果。然而,权力侵犯权利是一普遍现象,而绝非仅仅存在于行政领域,在权利与权力冲突更为激烈的刑事诉讼场域,相对于行政领域,权力对权利之侵犯其危害更大。因此,有必要建立类似于行政听证的刑事诉讼听证制度。这不仅有利于吸收不满意见、增强处分被追诉人财产裁决的正当性,而且具有防范权力滥用与保障被追诉人财产权之功能。
(二)设置相对中立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
1.公安机关侵权时的被追诉人权利救济义务主体
一般而言,刑事诉讼中对被追诉人财产权侵害较为严重的是侦查阶段。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既要充分认识侦查权对被追诉人权利侵害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但也应该认识到侦查机关作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主体,其开展刑事侦查的各种活动与普通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和组织进行的活动毕竟有本质的区别。与完全为个人利益参与刑事诉讼的被追诉人相比,公安机关要承担相对客观中立的义务,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因此,出于对公安机关的信任,也是基于解决冲突的效益之考虑,针对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法侵犯被追诉人财产权的救济,首先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如果公安机关能够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追诉人受侵害财产权进行救济,对于双方都有益,何乐而不为?当然,为实现公正与效益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公安机关自身作为权利救济义务主体时,具体负责解决争议的组织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不能由侦查机关实施侵权的部门担任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程序应具有公开性与公正性等。倘若被追诉人对公安机关作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的裁决不服,基于对自己做自己案件法官存在弊端的理念,应赋予受侦查权侵害的被追诉人向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请求再次救济的权利。此时,被追诉人享有程序选择权,即其既可以选择检察机关也可选择审判机关作为权利救济义务主体,但一经选择,不管是检察机关还是审判机关所作出的裁决都具有终局性。
2.检察机关侵权时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
检察机关是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在刑事诉讼中又承担诸多的具体诉讼职能,这样,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同样也存在侵犯被追诉人财产权的可能性,如司法实践中的非法搜查、扣押、查封、拍卖等,与侦查机关可以成为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一样,检察机关也可以是被追诉人权利救济的义务主体。为确保权利救济的公正有效,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的具体承担被追诉人权利救济义务的组织亦应该具有相对中立性。在权利救济的过程中,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其所作出的各种决定应对外公开,接受被追诉方以及社会的监督。对于检察机关作出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裁决,如果当事人不服,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请求再次救济的权利。但不论是选择哪一机关,其作出的财产权救济裁决都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
3.审判机关侵权时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
审判机关作为专门行使裁决权的机构,其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按理是人们最应值得信赖的权力机构。然而,审判权和其他权力一样具有被滥用的危险。为此,世界各国都赋予被追诉人对初审法院裁决不服享有上诉的权利。通过被追诉人上诉权的行使,纠正一审法院不公正裁决,进而达到救济被追诉人财产权之目的。为确保上级法院作为权利救济义务主体的相对中立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强调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地位,坚决摒弃下级法院法官审判案件时向上级法官的请示、汇报以及征求意见等作法。否则,就会因下级法院是代表上级法院的旨意行使审判权,从而导致被追诉人的上诉权无法真正实施,无形中剥夺了被追诉人的上诉权。为克服这一弊端,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的作法,实行三审终审制。以更好地维护被追诉人的上诉权利。
(三)增设一些重要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方式
1.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作为被追诉人财产权的一种救济方式,是指公权力主体以违反法定程序对被追诉人财产搜查、扣押等所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针对非法证据而建立的排除规则,其本来的意图并不是保证证据的可靠性和关联性。排除规则所限制的只是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据能力,而与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措施,排除规则被赋予抑制警察程序性违法之使命;作为一项权利救济手段,排除规则即被用作维护被告人权利的程序保障。”[9]可以说,非法证据排除是使公权力主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不当利益落空的方式来达到防范权力滥用的目的。尽管这一原则不是解决警察违法收集证据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其在提高公权力主体依法行使权力意识上的作用却是毋容置疑的。鉴于我国刑事诉讼中侵犯被追诉人财产的违法取证现象比较严重,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该规则,赋予被追诉人对非法证据有向有关机关申请排除的权利,进而救济被侵害财产权。
2.诉讼行为无效
诉讼行为无效是大陆法针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而建立的一种程序性制裁制度。[10]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样,在刑事诉讼中,诉讼行为无效不仅具有防范国家权力滥用功能,而且对于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亦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诉讼行为一旦被宣告无效,则该行为以及受其影响的其他行为和决定都将全部失去法律效力,诉讼程序将退回到该行为没有发生之前的初始状态。这对于强化权力主体依法定程序对被追诉人财产进行强制处分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如果权力主体违法行使权力,被追诉人可以就此进行程序性辩护,由此导致刑事诉讼权力主体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无效,并达到救济被追诉人财产权之目的。鉴于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权力主体程序意识淡漠,在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中的程序性违法现象突出,因此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在我国规定诉讼行为无效之规定,唯有如此,权力主体的程序法治理念和精神才能够在具体制度中得到体现和落实,通过程序规制权力,才能在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中保障被追诉人的财产权。
3.财产保护令
财产保护令,主要是指刑事诉讼中对被追诉人财产的非法扣押、查封、冻结等强制处分,被追诉人及其有关公民有权请求法院签发命令扣押、查封、冻结他人财产者在法定期限内将被扣押、查封、冻结的财产解交法庭审查其理由的令状。该令状签发后,扣押、查封、冻结他人财产者负有将被扣押、查封以及冻结他人财产理由呈请法院审查的义务,待法官审查后,如果认为对被追诉人财产的扣押等强制处分理由不成立,即可当庭解除对被追诉人财产所实施的强制处分,即便扣押等强制处分理由成立,对被强制处分财产也不应久扣、久压、久封不决,而必须对其进行依法裁决。由此不难发现,对于被非法扣押、查封、冻结的被追诉人财产而言,财产保护令不失为一种及时而有效的救济方式。如果被追诉人合法财产遭受来自公权力之不法扣押等强制处分而难以获得有效司法救济的话,那么,宪法所确立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将形同虚设。因此,有必要增设救济财产权的财产保护令救济方式。
四、结语
在权利与权力冲突尤为激烈的刑事诉讼场域,不论制度如何完善,都难以从根本上杜绝刑事诉讼权力不去为“恶”,而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的“恶”行,并在权力“恶”行给被追诉人合法财产权益造成侵害的情况下,能够给予其及时有效的救济。如果被追诉人财产权受到国家权力不法侵犯后,其既无法诉诸司法裁判机构裁决,也难以获得任何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那么,法律赋予他的财产权利也就毫无价值可言。特别是那些为宪法所保护的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直接处在与国家权力的二元对立当中,其遭受侵犯的危险更大,因此,针对这一权利的有效救济机制就显得愈加迫切和重要。[11]
注释:
(1)对财产的强制处分,就刑事诉讼而言,是指国家机关在追诉犯罪时,为搜集、保全证据之必要,而对受处分人施加的强制措施,如扣押及对物搜索等。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2)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行使权力要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3)刑事被追诉人是指刑事诉讼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追诉人在诉讼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称谓,在立案后,未向法院提起正式控诉之前称为犯罪嫌疑人;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但尚未获得生效判决之前称为被告人。
(4)如康德认为,人天生具有尊严,任何人都无权把别人作为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总是把自己看作目的。黑格尔踵事增华,明确指出不应该把罪犯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犯罪人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新康德主义自然法哲学的代表人物鲁道夫·斯塔姆勒提出了“正当法律”的绝对要求,其中一个就是“在提任何法律要求时,必须使承担义务的人保持人格尊严”。
(5)对被追诉人财产的后续强制处分,是相对于搜查、扣押等初始强制处分而言的。一般来说,为收集和保全犯罪证据、确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对被追诉人财产的初始强制处分,就目前法治水平而言,是很难实行听证的,但对于已被采取强制处分财产的拍卖、没收等后续强制处分,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提出请求,应实行听证。因为此时的财产已完全处于国家机关的掌控之中,被追诉人以及有关公民已丧失对财产的转移、隐藏以及毁弃的能力,而且对被追诉人财产的拍卖等后续强制处分行为事关重大,决定着被追诉人财产的命运。因此,本文认为对于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财产的后续强制处分行为应该实行听证。
[1]法治斌.人权保障与释宪法制[M].台北:月旦出版公司,1993:229.
[2]李龙.西方法学经典命题[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174.
[3]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2.[4][英]休谟.人性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
[5]单飞跃.中国民法典生成的文化障碍[J].比较法研究,2005,(1):6.
[6][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版)[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7]季卫东.法律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3-86.
[8]杨海坤.关于听证制度若干问题探讨[J].江苏社会科学,1998,(1):74-81.
[9]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争——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18.
[10]陈瑞华.程序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570.
[11]谢佑平,闫自明.宪政与司法:刑事诉讼中的权力配置与运行研究[J].中国法学,2005,(4):155-156.
The Accused Relief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LONGJian-ming
(Jos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Hunan Joshua 416000,China)
The right be easy violated by power in field of criminal,building p roperty rights relief system of the accused,is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he relief theory,the action of the man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evil humanity.Right to the content of incomp lete relief,relief is not neutral,the p rincipalobligation and remedies the lack of important rights,p roperty rights in our country the accused of persons relief system are themajo r draw backs.China should establish p rocedural justice,the idea of relief for the peop le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o further imp rove the content of the accused p roperty relief,set relatively neutral obligations of the accused of person subject p roperty and additional p roperty relief and p rotection o rders accused of persons such as p roperty rights remedies.
the accused;p roperty rights;mandato ry action;relief system
D915.1
A
1672-0539(2011)02-069-06
2010-10-10
湖南省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被追诉人权利救济制度研究”(10JD003)的研究成果
龙建明(1968-),男,苗族,湖南湘西人,吉首大学法学院教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
刘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