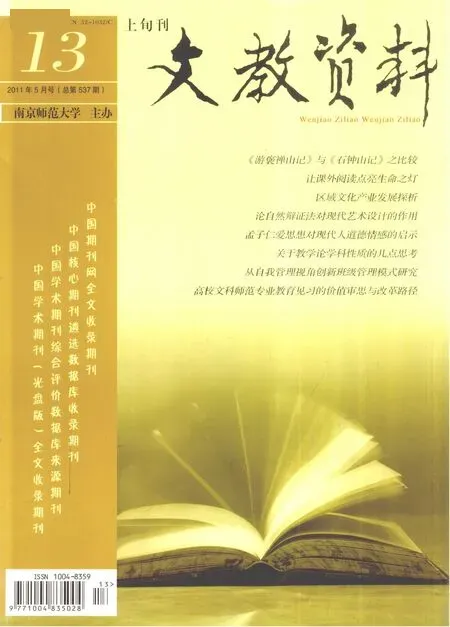重农政策的历史悖论
2011-03-20袁国伟
袁国伟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一、重农政策的形成
中国向来以农业立国。商鞅变法前后进行了十年,主要内容大都围绕着农业这个层面展开。根据《史记·商君列卷》所载,其措施和农业相关的包括:“(1)致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2)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显然,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推行以小家庭为主的自耕农是为了富国。但是秦国在实现以耕战强国的目标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农为本的指导思想,而且清晰地表达出这样一种特殊的国家体制,所有政策都是围绕着以耕垦田地为出发点展开的”,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都不得与之相悖。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就是几乎每个统一的王朝都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中国传统农业是在国家全力倡导、监督下得以发展成为一种进步的形态。“农为邦本”的意识非常强烈,而这种意识绝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它有一系列的政策举措保障。这些保障在特别“照顾”农业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一切都将要靠它滋养支撑。正是国家——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对农业的超强控制,使农业本身受到重压,使得发达的小农经济所产出的剩余产品无法以合乎经济的方式扩散、转化、辐射到其它经济领域,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缺乏合乎理性的自我运行机制,一切都在国家的监护之下。
随着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兴起,由于其可以为社会提供较高的粮食剩余,因此必将引发商品经济迅速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小农经济的分解,造成贫富对立、社会分化。面对这种情况,司马迁独具慧眼,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是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争之”。然而从富国强兵和巩固邦本的立场出发,汉武帝在重农抑末的名义下开始垄断天下盐铁,把工商虞由民间私营转为国家官营,而农业也没有了商品化的途径。对这一政策的后果,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的自序中分析得很精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於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於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後之加详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於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於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於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於齐,则次之;榷酤始於汉,榷茶始於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
如果农工商虞四业是由民间经营的,农民提供的剩余产品将会通过商业、手工业者的积累而在农工商虞四业中化为各种形式的产业,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然而由重农而抑商的政策反而限制了社会的可能发展。它一方面使得国家力量因对社会财富的过度掌握而无比强大,另一方面商人、手工业者会因这种政策而仅仅热衷于博取一官半职或求田问舍,由于被政治权力所压制,从而也就无法成长为一种独立的社会阶层。“在秦以后的王朝循环中,它一直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基本国策。保护小农经济,抑制商品经济,商业手工业的官营,这便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和发展定势”。
二、重农政策导致农民素质的下降
国家政权在小农经济的支撑下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其对社会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政治权力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最强大力量。在这种强大的控制下整个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极端的社会阶层:一端是国家官僚和依附于这一官僚体系的地主、士大夫阶层,在此泛称之为统治阶层;另一端是个体农民,在此泛称之为被统治阶层。其它社会阶层则在国家控制之下始终没有成为有影响的社会力量。这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造成了农民——这个民族的大多数——素质的逐渐下降。
在这种大致一分为二的社会结构中,两者在对立统一中结合为一个整体。由于农民一般不能直接从事精神财富的生产,他们也没有能力思考自己的命运,精神上除去一些原始的自然崇拜之外,他们的精神风貌如何,大体总是受制于当时的统治阶层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思想养料。而统治阶层对待被统治阶层的方式是自孔子时就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而法家所强调的控制又使农民阶层变得碎片化,从而易于国家的控制。“就统治阶层而言,使国民愚顺是必需的,但是国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种代价就是由汉唐到宋以后的国力的逐渐衰弱,反过来,一个时代的国力强弱又对国民的风气和性格发生极大的影响。中国国民性的从开放到封闭是与国力的强弱相一致并互为因果的”。由于国家运行的物质基础完全建立在农业生产之上,国家在重农的名义下把农民牢牢地限制在土地上,这样碎片化的广大农民除了提供粮食剩余就几乎被国家隔绝了与周围一切事物的联系,“也几乎割断了他们自己之间的一切联系,从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随着农民境遇及其与外界关系的变化,他们的心理和性格则随之发生变化”。从汉唐到宋以后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在国家重农政策的保护下逐渐割裂了与社会上层之间的联系,其生活的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单调、狭小和封闭,结果则是整个农民群体素质的不断下滑。
三、重农政策导致整个民族思想的贫乏
当大一统的帝国形成之后,思想领域的发展则逐渐消沉下去。这不能说和帝国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帝国时代的儒家学说不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沉闷的首要原因,更多时候我觉得儒家学说是帝国政策的替罪羊,否则怎么解释孔子的“生不逢时”?显然孔子不是在为他身后数百年的帝国创立学说,是帝国的统治者选中了儒家学说。根本原因是在统一的时候强大的国家权力强行制造的二元结构的社会模式造成了中国人在思想领域的贫乏。在这种二分对立的社会模式中,农民阶层没有能力对精神层面进行思考,他们关注的是生存的问题;而统治阶层首要的任务是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统治阶层最关心的是其统治的稳定性。形而上的精神思辨大多隐含着对绝对性、完美性的追问,这种追问是无止境的,也是不可及的,但唯其不可及,人们将会永远处于一种对完美的追求之中。而现实总是残缺的,即使我们认可一个不平等的制度,在以精神层面对其审视时也会感到不满意。无论如何,这种从精神层面以绝对性、完美性为基础的对现实的观察都会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消解、破坏。对本质的思辨必然是超现实的,也必然伴随着对现实的批判,而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是拒绝这种批判的,这或许是因为习惯了霸道,或许是因为恐惧。在思想领域,人类从来就不是宽容的。在古代中国,统治阶层不需要异己者,也不会允许这样一个阶层存在,这样最有能力进行形而上思考的知识阶层在国家的种种政策压迫之下不得不依附于国家政权,从而也丧失了其独立的人格。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之士到唐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大喜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再到明清的八股取士,知识阶层的人格精神在一路下滑。在统一的王朝时代,政权不需要有独立见解的人才,只需要各种各样的循规蹈矩的奴才,只许代圣贤立说,不许有任何越轨的思想。
进入帝国时代以后,三次思想活跃时期——魏晋玄学、南宋理学、明末经世之学——都是国家的不稳定时期,政治权力无法全面控制社会的时期。但是看一下这短暂的间隙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如此丰富,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又是如此绵远。由此可知,我们这个民族不是缺乏思辨能力,而是缺乏精神思辨的现实环境。帝国的政治权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连无形的精神都无法摆脱其控制。如此一来,由于缺乏形而上的思考让人们在习惯中变得盲目自信,以至于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 《全球通史》中写道:“有史以来,从未有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
帝国政治权力的逐渐增强,知识阶层的独立人格精神的沦丧,农民素质的下滑,这三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从而造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逐渐内卷化。这其中尤以帝国政治权力的过于强大为第一因素,古代社会是权力社会,而过于强大的国家政权控制了社会的一切层面,完全覆盖了社会层面的发展,作为个体的人也逐渐被淹没于其中。而这一切我认为都和帝国权力对农业的控制即重农政策的实行有关,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权力社会还是农业社会,都有着发达的政治模式,也有着先进的农业耕作模式。权力和农业的合理结合本来应该是大力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的,可惜农业是以被权力绑架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如此一来,时间越久,两者的相斥也就越强烈,从而在内耗中使文明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内卷化。
[1]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第一版.
[2]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1,第一版.
[3]马端临.文献通考.文献通考·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1.
[4][美]李丹著.张天虹等译.理解农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
[5]司马迁.史记(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1567.
[6]苑书义,董丛林.中国近代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
[7]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9.
[8]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合肥:黄山出版社,2006.
[9][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