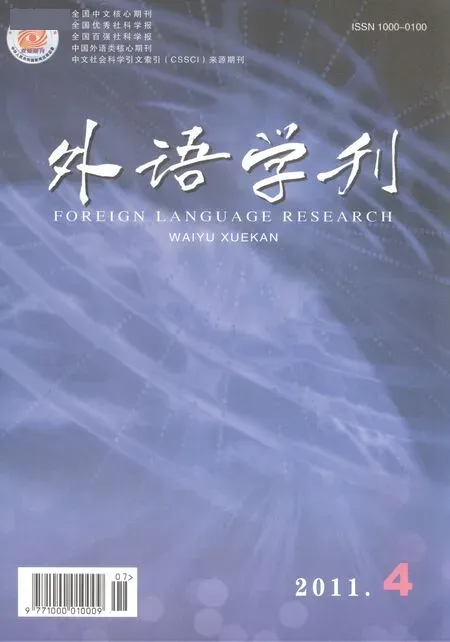论冯内古特的元小说文本*
2011-03-20陈世丹司若武
陈世丹 司若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美国当代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是美国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一,被“公认为重要的美国作家”(Allen 1991:174),“当代最受尊敬的小说家之一”(Vincent 2001:436)。后现代主义小说是对小说形式和叙事本身的反思、解构和颠覆。它造成了传统小说和叙事的瓦解。因此,这种小说被称作反传统小说或元小说,也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即在小说内包含对自身叙事和语言特性的评论”,元小说是“大部分‘后现代世界’文化形式的例证”(Hutcheon 1980:4)。元小说是指“一种有意地、系统地引起人们关注其人工制品地位的虚构作品,其目的是使人们对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产生疑问。这种作品在对自己的构筑方法提供一种批评时,不仅考查叙述体小说的结构,而且探讨文学虚构文本外面世界的可能的虚构性”(Waugh 1984:2)。元小说作者们声称现实是用语言构成的,虚假的语言制造了虚假的现实。元小说的主要任务就是暴露这种欺骗,把现实的虚假和虚构故事的虚假暴露在读者的眼前,从而迫使他们去思考。元小说作者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探索这个语言体系与小说外那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作品经常揭示他们有意识地使用的文学语言和他们清楚、明确地表现人造产品特征的习惯做法,暴露危机感、异化感和感觉印象与不再适合表现后现代人类经验的传统文学形式(例如现实主义)之间的脱节。我们将通过研究冯内古特如何用元小说解构小说世界并在解构中进行艺术创新,来考查元小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1 《五号屠场》:如何写这部小说的元小说
根据元小说的观点,现实与历史都是短暂的。在现实主义小说中,有完全虚构的情节、依照时间顺序的连贯叙述、全知全能的作者或叙述者、人物行为与身份之间的合理联系,以及详细的外表描写与深层科学规律之间的因果关系。元小说作者认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形式设法与有秩序的社会现实一致起来,但是现在的世界不再是永久的现实,而是一系列构成和非持久的结构。因此,传统小说的形式不再适合表现这种现实,元语言(语言分析用的语言)应该被用来建构能够适合表现这种现实的小说形式。元小说重视对小说形式本身的考查。对元小说作者们来说,当代世界像小说作品一样,是一个构成品,一种技术组合,一个相互依存的符号的系统网络。冯内古特小说《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1969)中一个非常显著的元小说特征是:它是一部关于如何写这部小说的小说。这类元小说揭示其自己的虚构,戏仿自己,故意在读者面前暴露其艺术操作的痕迹,从而揭露叙事世界的虚构和虚假。
在构成小说《五号屠场》的十个章节中,冯内古特让一个名叫雍永森的人物出现在第一章和第十章中,以超然而冷漠的语气、不作任何评论地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累斯顿火焰炸弹轰炸。小说第一章一开始的第三句说起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我真正认识的一个人在德累斯顿因为拿了一把不属于他的茶壶而被枪毙了”(Vonnegut 1969:1)。作者没有说那件事是否公平、是否值得。这件事在书中被重复了很多次。在书的结尾,作者又说到这件事:“……那位可怜的老中学教师埃德加·德比因为从废墟中拿了一把茶壶被别人看见了。他被以抢劫罪逮捕。他受到审判,被枪毙了”(Vonnegut 1969:186)。冯内古特重复此事是为了让读者去思考:如果审判并枪毙仅仅在战争废墟中捡了一把茶壶就被认为犯了抢劫罪的德比是公正的话,那么为什么军事法庭不审判并枪毙那些扔下炸弹、杀死十三万五千平民的飞行员、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国空军司令员和策划这场轰炸的同盟国决策者呢?正义何在?他问奥黑尔:“你不认为那真应该是高潮出现之处吗?”(Vonnegut 1969:4)。这个问题不仅是提给奥黑尔的,也是提给读者的。如何表现世界的荒诞、战争的残酷和战争带给人类的死亡是作者再三与读者讨论的问题。传统的历时线性叙事不适合表现德累斯顿事件。作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探索适于表现这一事件的方法。在第一章,冯内古特告诉读者,他想用传统叙事写一部关于德累斯顿事件的书,依照时间顺序,有亚里斯多德式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但传统小说的结构不适合冯内古特想要写的小说,尝试未能成功。失败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像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命一样,小说人物的生命本身也不是朝着一个方向行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记忆在时间上后退就像他们在对未来的预期中前进一样多。因此,在《五号屠场》中,故事的叙述是运用英国小说家《尤利西斯》(1922)的作者乔伊斯和美国小说家《喧嚣与愤怒》(1929)的作者福克纳所开创的意识流技巧进行的,这种技巧追求通过记忆再现过去的共时混合、通过感觉描述现在、通过预期展示未来。
在小说开始处,作者把题材——德累斯顿火焰炸弹轰炸——交代清楚之后,叙述了下列事情:1967年他与奥黑尔重游德累斯顿;23年前他开始写一部关于德累斯顿和二战的书;两年前他与奥黑尔回忆那场战争;战后交换战俘的情形;作者整夜酗酒、打电话;他个人的简短传记;他关于这部书的写作计划;政府对德累斯顿事件保守秘密……;儿童十字军东侵的历史;德累斯顿的历史;他教育儿子们不要参加任何杀人活动。最后,他又回到了他重游德累斯顿的话题。像作者自己评论的那样:这部书的基本特征是“短小、混乱、吵闹”(Vonnegut 1969:17)。第一章的结构预示了整部小说的结构,成为关于如何写这部小说的元小说的第一部分。
在第一章的结尾,冯内古特给读者一个科幻小说的暗示:“有人正在玩弄时钟。……我的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一下,一年就将过去,然后它将再次颤动”(Vonnegut 1969:18)。这成为对后面各章中毕利时间旅行的预示。从第二章到第九章的八个章节构成小说中的小说。在这八章中,主人公是虚构的人物毕利·皮尔格里姆,假定的作者雍永森出现三次,分别在第三章:“我在那里。我的老战友伯纳德·V·奥黑尔也在那里”(Vonnegut 1969:58);第五章:“那就是我。那的确是我。那就是本书的作者”(Vonnegut 1969:109);第六章:“在货车车厢里他身后的那个人说,‘神秘之地。’那就是我。那的确是我”(Vonnegut 1969:129)。雍永森的重复出现表明,这位假定作者在毕利所有战争时期的经历中也都在当场,这一点被开头的两个句子证明:“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都发生了。无论如何,那些部分非常接近真实”(Vonnegut 1969:1)。当然,毕利在幻觉中去541号大众星除外。这八章叙述了毕利在二战前、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的经历。因为毕利自己在连续的、永恒的现在时刻向过去、现在和未来做时间旅行,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事件都被混入了毕利的经历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被共时地表现在这种以表面上混乱的时空进行的叙述中。当读者发现毕利的经历与冯内古特的经历完全相同时,他就会意识到在这些章节中三次出现的雍永森是冯内古特虚构的、用作在作者、主人公和叙述者之间提供距离的面具。
在某种意义上,《五号屠场》是一个幻想,是一个梦,在这种梦幻中作者冯内古特与读者们都认识到,作者受良心驱使,写作这部关于可怕的德累斯顿火焰炸弹轰炸历史事件——一场真正骇人听闻的人类大屠杀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难以忍受的。在第一章里,冯内古特断言:“这部书是一个失败,肯定是,因为它是一根盐柱子写的”(Vonnegut 1969:19),这句话意味着冯内古特宁愿学习《圣经》中罗德妻子的榜样,冒着死亡的危险,回首过去,为未来的几代人讲述人类历史上这一悲惨的部分。冯内古特通过他的小说创作表现了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的关心。在后面构成小说中的小说的八章里,冯内古特用假定叙述者雍永森来继续叙述自己的故事,用毕利·皮尔格里姆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使他与自己有共同的经历。通过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物置入小说中并在战争期间与毕利同时出现的办法,在作者和叙述者之间造成一段距离。这样,他就能远离表现德累斯顿火焰炸弹轰炸的痛苦。作为一个充满同情心的人,毕利感到很难接受541号大众星生物不理睬不快乐时刻的哲学,对他来说回忆他经历的德累斯顿毁灭和人类受难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在德累斯顿遭到火焰炸弹轰炸之后,当他看到两匹马因为受到他的无意伤害而痛苦万状时,“他突然大哭”(Vonnegut 1969:170)。战后,因为他不能忍受看着胖姑娘瓦伦西娅嫁不出去而感到痛苦和孤独,所以他娶了她;他对遭到破坏的德累斯顿的回忆使他希望迅速重建他所居住于其中的埃廉市。可是,在小说《五号屠场》中冯内古特从未明确地指出毕利·皮尔格里姆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这表现出小说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本质特征之一。
在这部元小说的最后一章里,假定作者雍永森本人又来到了前台,告诉读者他将如何在最后几页里结束他的叙述,真诚地劝告读者分担发生在美国生活中的一切所造成的痛苦。在小说的结尾,大屠杀之后的德累斯顿市非常安静,只有“一只鸟儿对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普-提-威特?’”(Vonnegut 1969:186)这只鸟儿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提给读者和所有人的:难道就像说一句“就那么回事”那样说一句“普-提-威特”人们就可以忽视人类大屠杀的悲惨后果吗?小说以一个答案不确定的问题作为结尾,这是一个开放的结尾,小说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其多元的意义等待着读者去创造。
这部元小说的作者与传统小说作者不同,他不是赋予其文本某种单一意义的权威。实际上,他既是一个人物又是一个叙事者,他最多扮演了一个文本解释者的角色。在地位上,他把自己等同于读者,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参与他们的讨论,考查传统小说的基本结构,探索文学虚构文本外面世界可能的虚构性。
2 《冠军早餐》:一部反传统小说
反传统小说是另外一种元小说式小说。它背离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删除了传统小说的构成因素,违反传统文学写作的基本标准,打破传统小说表现手法使读者对作品的猜测。反传统小说不仅在印刷形式上有许多反常的排列,不成直线的字行、空位等,而且运用某些反复出现的印刷字体,例如黑体字、斜体字、大写、镜像、音乐简谱、中文书法、手写体、语言逻辑式等。非小说体裁,例如意象诗、时间表、单子、表格和图表在反传统小说中随处可见。另外,反传统小说也重复引用其它文本,甚至包括非英语文本。通过这些反传统方法,反传统小说作者想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文本,是一个语言创造物;它不是一个对现实的中性的、手写的摹本。一种技巧有其自己的生命,而且能创造生命。它不必要依靠预先存在的内容。反传统小说这一术语也被应用于各种试验性的玩弄语言游戏的作品,这些作品或抛弃情节,或只表现无关的穿插事件,或提供一连串的心理描写,或设法捕捉作者在生活中看到的无目的的、令人沮丧的责任。无论反传统小说以何种形式出现,它的作者都要求读者既是观众又是参与者。(王先霈1999:677-678)
冯内古特的《冠军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1973)具有十分强烈的反传统小说冲动,作者本人竟然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小说中。小说中有这样的场景:作者冯内古特与他虚构的密友、小说中的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在一起谈话,最后释放了他。小说的情节围绕特劳特和有钱的中西部庞蒂亚克汽车经销商德威恩·胡佛展开。对胡佛来说,生活失去了全部意义,所以他希望至少在即将到来的艺术节上会有一位艺术家送给他一把开启生活意义的钥匙。特劳特恰好是受艾略特·罗斯瓦特推荐而得到参加艺术节邀请的一位艺术家。在交替描写特劳特和胡佛的章节中,小说提供了对两人去参加艺术节旅行的描写。在第一章,冯内古特预先告诉读者,胡佛将从特劳特写的一部科幻小说中了解到,他是世界上唯一有自由意志的人,他将暂时患有精神病,使一些人残废,通过诉讼失去所有金钱;另一方面,特劳特将成为名人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小说没有给读者留下关于情节发展的任何悬念。
冯内古特与德威恩·胡佛和基尔戈·特劳特的引人发笑的会面被故意安排在印地安那州米德兰市度假旅馆里,这场会面成为小说的高潮。但第二十三章中突发的打架场面却是故意按突降法来处理的。在度假旅馆,当女招待问冯内古特他戴着墨镜能否在黑暗中看见东西时,他回答说:“那极成功的表演就在我的脑海里”(Vonnegut,Breakfast 1973:201)。恰如冯内古特的这句回答,“小说真正关心的并非是文字上的行为,而是冯内古特评论那种行为的方式,这样就揭示了他对创作本质、美国社会的紧张结构以及对他自己细微的精神状态的关心”(Allen 1991:104)。
《冠军早餐》这部反传统小说是对控制美国小说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亨利·詹姆斯小说理论的彻底颠覆。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冯内古特并不把自己限制在传统的第三人称视角上,而是经常直接对读者说话。他经常开玩笑地发表不同的评论,从对人物可靠性的确定(“这是真实的”)到关于墨西哥甲虫大小和漂浮大陆理论的陈述。冯内古特声明:“让我想一想:我已经解释了德威恩快速阅读的非凡能力。基尔戈·特劳特或许不可能在我给他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他从纽约市赶到这里的旅行,但现在说这话已经是太迟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Vonnegut,Breakfast 1973:249)从而嘲笑亚里斯多德对时间一致性的关注和新批评对小说严密策划的关注。
恰如法国实验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人物的小说完全属于过去,它描写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标志着个人的最远点”(Schatt 1976:98)。因此冯内古特在《冠军早餐》中清楚地表明人物都是傀儡,而他则是傀儡的操纵者。德威恩·胡佛和基尔戈·特劳特都是他的创造物,他们都必须在他的操纵下行动。于是他通过暴露前两章中的情节,破坏了小说可能包含的任何悬念。他在小说中的一处停止人物描写,以放弃的态度说:“我本可以继续详细地描写超级救护车上人们的各种生活,可是更多的信息……挑剔细节的堆积又有什么好处”(Vonnegut,Breakfast 1973:293)。冯内古特要求其读者做的仅仅是全神贯注于他的思想,而不是过于关注人物的命运,因为这不是一部关于人物的传统小说。
在《冠军早餐》中,冯内古特解释了他自己独特的创作理论,既然生活就像一个聚合体,任何关于人的故事的正确结尾都应该是缩写,而且坦白地说正是为了“承认这种聚合体的连续性我才用‘和’与‘因此’来开始很多的句子,用……‘等等’来结束很多段落”(Vonnegut,Breakfast 1973:228)。冯内古特也表示他不喜欢那种不切实际的惩恶扬善的传统情节的固有道德,指出《冠军早餐》“不是那种表现人们在最后终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小说。德威恩仅仅伤害了一个因为邪恶而应受惩罚的人:那就是唐·布里德拉夫”(Vonnegut,Breakfast 1973:274);虽然基尔戈·特劳特是无辜的,但他却遭受了被咬断一根手指之苦;而冯内古特本人过于接近行为现场,他的表被打坏是罪有应得,因为他反复打断故事的流,带着一些表面上不相关的细节闯入故事。在描写年轻女招待帕蒂·基恩迎接德威恩·胡佛的情景时,冯内古特打断叙述,向读者声明他刚刚阅读了关于漂浮大陆的理论,并说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然后,他给出小说中所有男性人物阴茎的精确尺寸和所有女性人物胸部和臀部的大小。虽然这些细节表面上看毫不相关,但它们的确服务于一个目的:揭示一个非常普通的黑色幽默的主题——科学仍然不能解决后现代人类生活的荒诞和无意义问题。
另外,冯内古特在小说中亲笔画了一百二十一幅插图,运用不同的书写体,例如黑体字、斜体字、大写和不同的公式,写了一些具有生动形象的诗歌,展示了一些不同的符号,杜撰了一些常用词的拼写,在段落之间留下双倍行距等。通过所有这些反传统的手法,冯内古特试图强调《冠军早餐》是一个文本,是一个语言构成物,不是一个对现实的中性摹本,证明技巧有自己的生命而且能够创造生命,它们不需要依靠先前存在的内容。作为一位反传统小说作者,冯内古特希望他的读者不仅是一个阅读文本的人而且是一个参与文本写作的人。
3 《神枪手迪克》中元小说式的“戏中戏”
在阅读冯内古特小说《神枪手迪克》(Deadeye Dick,1982)时,我们发现冯内古特的早期小说人物也出现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元小说式戏中戏”(Allen 1991:143)的形式呈现小说中至关紧要的情节,我们的注意力随之被转移到冯内古特话语的人工性上。在小说中,这一技巧被四次运用在主人公鲁迪非常困窘的时刻,鲁迪解释说:“我用这一技巧来处理我最糟糕的回忆。我强调它们是剧本。其中的人物是演员。他们的讲话和动作是程式化的,是嬉戏的”(Vonnegut,Deadeye 1982:83-84)。尽管鲁迪不顾一切地需要把那些令人困窘的情形改变为艺术,从而使他与那些困窘之间有一段距离,而且这种需要表现得非常强烈,使鲁迪这个人物显得更加真实,但是这种戏中戏手法暴露了人物与情景的非真实性,从而产生出一种丰富的自相矛盾的效果。整部小说的一部大戏包含四部小戏,它们不仅表现了小说的重要主题,而且表现了鲁迪充满不幸经历的一生中几个极为重要的时刻。
第一场小戏是鲁迪在乱动父亲收集的各种枪支时意外走火打死了一位孕妇之后,遭到警察的羞辱和虐待。这次痛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影响了他的一生。在主题上,这场小戏暴露了两个社会问题:一个是人的报复激情可能很容易破坏被告公民的自由,另一个是美国有太多平民保管的枪支和难以解决的平民可以持有枪支的问题。在这段情节里,警察让已死孕妇的丈夫动手打鲁迪作为报复,但遭到孕妇丈夫的拒绝,他的理性和道德行为表达了冯内古特反对任何人类暴力的主张,这证明人类有可能抵制加入实施私刑的乌合之众的倾向。这位正派的人只想在他的报纸上写一篇关于他妻子死亡悲剧的社论,他说:“我的妻子被一台永远都不应该落入任何人类之手的机器杀害了……。我们不能很快地消除人类的邪恶愿望。但我们能够很快消除人类邪恶愿望得以实现的机器。我只给你一个神圣的词:放下武器”(Vonnegut,Deadeye 1982:87)。
第二场小戏是关于鲁迪的生活,正好上演在他写的真戏在百老汇灾难性地开幕之前。在这段情节里,鲁迪无意中听到他的哥哥与嫂嫂的争吵,嫂嫂指责鲁迪“可能喜爱当女人”,(Vonnegut,Deadeye 1982:137)说他是“一个马戏团的畸形人”(Vonnegut,Deadeye 1982:139),还说他有可怕的体臭,他需要洗个澡。这一令人灰心丧气的情景预示他真戏的失败将给他带来悲惨的羞辱,为他永久地指明:他永远也不要再与特别令人困窘情形下的人们交往。
第三场小戏是几年后西莉亚·胡佛来访问鲁迪的情形。西莉亚来鲁迪药房的目的是要对鲁迪和鲁迪创作的戏剧《加德满都》表示赞赏,她曾在那出戏的一次地方演出中扮演过角色。自孩童时期以来他们就一直是好朋友,他们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相爱过。鲁迪知道这个曾经美丽的女人现在耽溺于安非他明(解除忧郁、疲劳的药),而且被这种药把身体搞坏了,所以鲁迪把她的称赞误解为她要得到安非他明。结果,鲁迪的误解激怒了西莉亚,她顿时变得疯狂和激烈,砸烂了鲁迪的药房,然后跑出去,消失在夜幕中。鲁迪被西莉亚丢弃在悲惨的情景中。
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小戏上演在西莉亚的葬礼上。出席葬礼的费利克斯对她的丈夫德威恩坦白说,他也曾经爱过西莉亚,而德威恩不仅没有恼怒,反而承认他未能帮助他的妻子,而且诚恳地告诉费利克斯:“本应该是你娶她,而不是我”(Vonnegut,Deadeye 1982:206)。鲁迪只是静静地旁观和听着他们的谈话,对谈话内容无动于衷,因为他在尽力使自己远离作为一个中性的药剂师的痛苦。早已失去爱西莉娅机会的鲁迪,现在致力于关照他无抚养孩子能力的母亲。在一场吞没了米德兰市的大风雪中,她失去了丈夫,如今孤身一人,生活凄惨,因此鲁迪对母亲关怀备至。最后,读者从小说《神枪手迪克》中得到一个冷静的教训:“一些情感的伤疤可能只是太深,难以治愈……。尽管他可能通过艺术和爱的力量来恢复健康,但在社会看来,他将永远是一个有神枪手迪克绰号并令人嘲笑的有病凶手”(Allen 1991:143)。
大戏《神枪手迪克》中四个元小说式的小戏揭示,生活就像虚构的故事,也有主要情节和尾声。在小说的尾声中,作者冯内古特平行于鲁迪的悲惨生活,回到他早先的科学幻想小说中,用一颗中子弹破坏了米德兰市。小说尾声米德兰市被中子弹破坏与小说开始鲁迪玩枪走火打死一位孕妇事件相呼应。美国著名评论家艾伦这样有趣而恰当地评论小说《神枪手迪克》的尾声:“为了给鲁迪的故事提供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冯内古特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这部书——颠倒ToSo艾略特的著名诗行,用砰的一声而不是嘘的一声结束”(Allen 1991:146),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类社会自我毁灭的危险。
冯内古特的元小说创作表明,元小说并未抛弃现实世界,它的目的是找到一种与当代读者紧密关联而且对他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小说形式,并通过自我反省来重新考查传统小说的习惯做法。元小说作者使用反传统的技巧去削弱(不是抛弃)全知全能的作者或叙述者、完整的结局和明确的解释,通过对另外一种语言的模仿使传统的技巧和结构陌生化。元小说揭示了文学作品如何构筑它们想象的世界,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每天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也同样是构筑的,同样是写下来的。元小说把旧的习惯做法的价值转变为潜在的建设性的社会批评的基础。元小说的解构方法不仅帮助小说家和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叙事结构,而且提供一种认识当代人类世界经验的非常清楚的模式(余宝发1987:454-458)。冯内古特的元小说艺术创新不仅考查了小说的叙事结构而且有效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五号屠场》以元小说形式吸引读者参与对现实中战争与死亡的讨论;反传统小说《冠军早餐》揭示了一个非常普通的黑色幽默主题——科学仍然不能解决后现代人类生活的荒诞和无意义问题;《神枪手迪克》中的元小说式的戏中戏暴露了当代人类处于危险的自我毁灭的社会生态环境中。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术语词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余宝发.超小说[A].林骧华等主编.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Allen,William Rodney.Understanding Kurt Vonnegut[M].Columbia,South Carol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1.
Hutcheon,Linda.Narcissistic Narrative: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M].Methuen:New York and London,1980.
Schatt,Stanley.Kurt Vonnegut,Jr.[M].Boston:Twayne Publishers,a Division of G.K.Hall& Co.,1976.
Vincent,William R.Vonnegut,Kurt,Jr.1922 [A].In Scot Peacock,Mark W.Scott,Katherine Wilson,et al.(eds.). Contemporary Authors New Revision Series(Vol.92)[C].Detroit/San Francisco/London/Boston/Woodbridge,CT:Gale Group,Inc.,2001.
Vonnegut,Kurt.Slaughterhouse-Five[M].New York:Delacorte Press,1969.
Vonnegut,Kurt.Breakfast of Champions[M].New York:Delacorte Press,1973.
Vonnegut,Kurt.Deadeye Dick[M].New York:Delacorte Press,1982.
Waugh,Patricia.Metafic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M].NY:Routledge,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