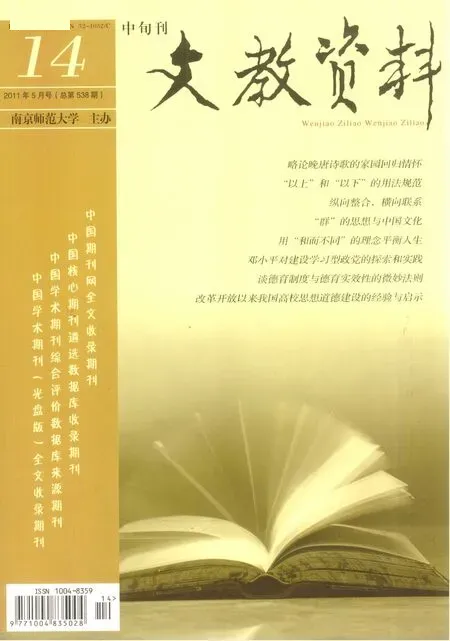凝视与自我建构
2011-03-20陈蓓蓓
陈蓓蓓
(温州医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一、小说《海》概述
《海》是班维尔的第14部小说。这是一部艺术与神话完美交融的小说。故事讲述了艺术史学家马科斯·莫顿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努力去应付所有的混乱并建构失去的自我身份。然而,人生中的新旧缺失却不断地折磨他,过去及现在的伤痕也被证实是难以克服的。他的自我建构之旅在这些交织着的累累伤痕中也因此显得步履维艰。他寻求着各种方式去摆脱迷失重建自我,凝视成了他的选择之一。
二、凝视与自我建构
拉康认为,婴儿最初处于不适应和动作不协调的“原处混乱”之中,对自己形象的认同是破碎的、不完整的,进入镜像阶段后,他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镜像,从此获得了一个认同的完整形象;镜子提供了建构理想自我的媒介,通过凝视自我的镜中像,主体开始进入代表文化与语言的象征界。在象征界,镜子已非物理镜子,而是由他者取而代之,主体为获得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必须去凝视他者。凝视行为将目光的暴力加之于他者身上,凝视者显然处于有利地位并掌握着权力,而被凝视者却被奴役,被迫处于劣势地位。凝视者因而主动地建构自我身份,而被凝视者却被动地接受由于凝视者的凝视而施加与他的形象。然而,凝视所包含不仅仅是主体对他者的凝视,更有拉康所谓的他者凝视;在凝视之下,先前的主体便转化成了一个完全被凝视的他人,而受役于先前的客体,成为了他者的欲望客体,给他者的欲望所俘获。先前的主体受到了他者性的侵入,自我建构的过程也因此极大地受到了他者的影响。个体就在凝视与反凝视的角色转换中逐步建构自我的身份。
三、“那喀索斯”的自我凝视
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为自我的美貌所吸引,将凝视的目光投向清澈的湖泊中的自我影像,童年时的马科斯也喜欢凝视镜中自我:“有段时间我非常喜欢我在镜中的形象”(86),“我年轻的时候,那一双丝绒般的睫毛可是女孩子都羡慕的”(88),而且 “我”很高。这一完美的镜中像成了他信心的来源,尽管他出身卑微;他置身于世界的中心,尽管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人;他从此获得了认同的完整形象,但同时这个形象又是虚假的。
拉康说,除了实体镜子,现实世界还存在着各种各样可以充当镜子的他者。少年时期的马科斯凝视镇上的“医生,律师,还有父亲一直谦恭为之服务的工厂主,还有那些仍住在树丛掩映的大房子里的贵族新教徒的后代”(66),对于马科斯来说,他们都是象征界的镜子,让他看到了自我的未来形象,并努力为此建构。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镜子所映射的理想自我仅仅是理想的自我,而非真实自我。克罗伊是他的另外一面镜子,因为她的存在,“我”也变成了客观实体,“如果她是真的,那么,突然间,我也是了”(115);克罗伊使“我”感受到自己是有意识的主体,她改变了“我”,而“我”也借有这面镜子建构“我”的身份。可惜这面镜子早早地破碎,而“我”身份建构的努力也因此中途夭折。多年后安娜的出现似乎拯救了“我”,或“我”的身份,“她就像一面镜子,在那里我所有的变形都会被拉直”。安娜使“我”重获自我,一个看似理想的自我。
然而,镜中并非只有完美像,从不同的角度完全可能映射出完全相反的形象。现在的“我”不再逗留与镜前,因为“我被里面显现出的那副面容震惊了”:
“一个悲哀蓬乱的人形,像是带着万圣节面具一样,橡胶下垂凹陷,与我脑海中顽固残留的印象毫无相同之处。……最近当我看着自己从镜中望出来,像那样弯着腰,脸上带着惊讶与茫然的表情,嘴巴张开,眉毛像是带着倦怠的惊骇一样供着,我感到我一定有些地方看起来与吊死的人有些相像。”(86)
这一扭曲的形象源于他生命中他者的缺失,包括想象界的母亲和象征界父亲的名字。安娜来了又走了,她是马科斯想象界的母亲亦或是象征界父亲的名字;她曾给他带来希望,然而死神带走了她,留下他独自一人,身心受创,无法自拔,无法忍受。而扭曲的形象是他对自我的否定,是对自我存在合理性的质疑。他无处可逃,却跟随潜意识回到了多年前的海滨小镇,儿时的伤痛席卷重来,与现实相互交织,阻碍了他的身心发展与自我建构。
拉康说,想象世界的自恋式肯定与象征界的他者认同使得主体成功的建构完整的自我身份。然而,马科斯的自我身份是破碎的,因为他的生命中缺少了主要他者,即“父亲的名字”的认同,而“母亲”也从他生命中消失,他所苦心为之建构的理想自我也随着他者认同的消失而濒于溃败。
四、偷窥:承载欲望的凝视
偷窥带有性的色彩,是对欲望客体的凝视,并从中获取快感。弗洛伊德认为偷窥的快感也存在于儿童,尤其是7—12岁之间的青春萌动期少年。处于这一阶段的少年性心理及生理发展都处于潜伏期,此时由于受传统的约束,他们对于性的欲望及表达都是受到压制和禁止的。对于早熟的少年来说,这一压制和禁止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性的异化发展,表现之一就是承载着欲望的偷窥。
男孩时期的马科斯自称是“罪行鉴赏家”,虽然“白点神父”曾向他讲述过偷窥的罪恶,但“我总是留神寻找着裸露的肉体”:
“那些绷紧的颤抖的肉体自由裸露着,只是披着大理石的长袍或是偶尔几片薄纱——偶尔,也许吧,但却像露丝的沙滩毛巾,或者康妮·格雷斯的泳衣一样是令人沮丧的保护——充斥在我青涩但却已经过热的想象中,带着对于爱及爱的犯罪的幻想,追逐着我,俘获了我。 ”(52)
偷窥给马科斯带来了快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他的主体身份。作为凝视的主体,他尽情享受着凝视的权利,目光所到之处,兼成为了他的客体、他的俘虏。在偷窥的世界里,他重获了在现实生活中所缺失的主体身份。
马科斯沉溺于偷窥带来的愉悦,当然这一窥视并非仅限于肉体,所有承载与欲望的客体都成了他窥视的对象。他窥视象征权利与地位的大房子,他不止一次窥视克雷斯一家的生活。他不无期待并充满好奇地透过香杉墅的大门望向里面,“房子背后狭小的花园一览无遗,我甚至能看到对角沿着铁路线栽种的一排树”(8),有一次,他窥到了屋后花园里晒着格雷斯家人衣服的晾衣绳,他还透过卧室的窗户窥到了“窗户后面的阴影,看起来像是裸着的大腿”(54)。在沙滩上,他关注着格雷斯一家的一举一动:体毛茂盛的格雷斯先生头戴帆布帽坐在一张折叠椅上,双手捧着一份报纸;金发碧眼的儿子——麦勒斯正用海上漂来的浮木掘着沙;他们身后几步远,有一个“白得有些不想话”的家庭教师露丝,“眉目灵动,小脸狭长,头发又密又黑”;格雷斯女士身穿黑色泳衣,“每走一步,风撩起裹裙,露出她偏胖却依然匀称的裸着的褐色大腿”;最后出场的女儿克罗伊从沙丘上跳下进入了马科斯的视域,她短发参差不齐,“她的胸像麦勒斯的胸一样平坦,她的屁股不比我的屁股肥。她下着短裤上穿汗衫。她的头发差不多暴晒漂白成了白色”(21)。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这一偷窥者的凝视之下,随之而成为被凝视、被奴役的客体——没有欲望,没有情感,而且被动;与此同时,窥视者却可以随意地塑造或改变被凝视者。马科斯叙述道:“我注意到她张望着,表情愤恨,仿佛张望的是格雷斯爸爸的后脑勺。我还注意到那个男孩麦勒斯斜着眼睛——用意很明显——我们俩同时发现那个女孩的浴巾眼看就要滑落在地。”(20)但女孩的愤恨或是麦勒斯的明显用意都是窥视者马科斯的话语所建构或定义的,而非他们自身的真实表达。马科斯用自己的话语建构了客体世界,而自己就能高高在上,控制着被凝视的客体。他努力去实现自我身份的转换,以成为自我的主体。
老年马科斯依然窥视着周围的一切。住在香杉墅的日子里,他偶尔会注意上校的日常生活安排,他注意到翡妃苏小姐对待上校的讥讽态度,还发现上校是个缺乏自信的人。马科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现在,面对上校,他无需偷偷摸摸地窥视,因为在上校面前,他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因为翡妃苏小姐被 “我”吸引,“我”知道更多关于香杉墅的故事,而且“我”和翡妃苏小姐是老相识,彼此相知。上校暴露在他的凝视之下而不自知,实际上他(上校)是一个局外者,虽然他住在这里的时间比“我”长。对上校的凝视重新给了老年马科斯以建构自我的机会。
窥视是性发泄的出路,也是满足窥视者欲望的途径。在窥视的快感中,凝视者操控着其视域所及之一切事物,行使着主体的权利,在此过程中,凝视者获得了全新的自我身份。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当主体凝视他者的时候,他者也在反凝视。窥视也是如此,窥视者在窥视他者的同时,也有可能在被某个他者所窥。对于马科斯来说,由窥视而得的身份非真实身份,也绝非稳固。
五、结语
镜中凝视或窥视都为自我建构提供了某种方式。马科斯在凝视的世界里试图建构自我,但一切并非一帆风顺。镜中凝视事实上是一种想象的凝视,主体在这一凝视中形成了统一的“理想自我”的原型,塑造了完满的自我,但这以完满自我只是幻觉,而非真实。格雷斯一家,翡妃苏小姐,上校,还有香杉墅,等等,作为客体,一一满足了马科斯的窥视欲望,并建构着他的自我身份,然而这一建构的过程实乃想象性建构,一切其实都只是个陷阱,他掉进去了,身份也破碎了。
[1]Banville,John.The Sea [M].London:Picador,2005.
[2]Foucault,Michel.Power/Know 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 ritings[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
[3]Sartre,Jean-Paul.TheWords[M].Trans.I.Clephans,London:Penguin,1967.
[4]约翰·班维尔著.王睿,夏洛译.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5]张德明.西方文学与现代性的展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吴琼编.凝视的快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