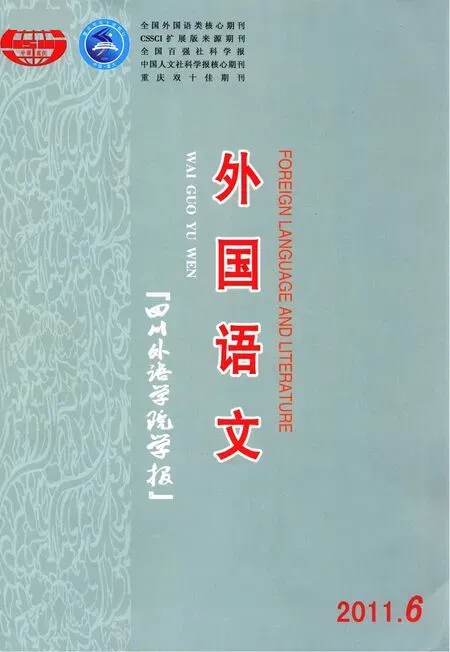不确定性:《喧哗与骚动》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2011-03-20江智利
黎 明 江智利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2168)
一、引言
自从著名意识流作家乔伊斯于1939年发表他那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的苏醒》(Finnegan’s Wake)以后,这部被称为最具有实验精神和革命意识的小说,开启了西方文坛新的里程碑。众多英美文学批评家将这部小说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新纪元的开始。因为他们从这部作品中看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向“以语言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的过渡。[1]关于现代主义,汤学智先生说:“在现代主义那里,‘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他’顽强地按照‘人’的规定的方向奋力自救,苦苦追寻着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生命本质……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则不仅‘上帝’已经不存在,‘人’也放弃了精神意义的‘深度追求’,‘他’似乎已洞穿世事,不愿再背负着孤独、痛苦作为‘自救’,而是以超然冷漠的心态,对荒诞的人生世界作静静的观察、述说、玩味、调侃,或者连这些都不顾及,仅把文学当作个人叙事的智力游戏。”[2]但王岳川先生则认为,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同现代主义相对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主义的反动,但实质上它同现代主义一样,是对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是当代西方“焦虑”、“无言”痛苦的畸形表达。后现代采取了一种比较现代主义更极端的形式,打破一切,进行价值重估,以消解“深度”为由走向“平面”,以自己的无价值的毁灭展示世界的荒诞和无价值……他们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心灵,进而叩问个体的有限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生存价值和意义。[3]40福克纳正是在《喧哗与骚动》这部小说中展示了这种在西方文明下的“世界的毁灭”和“世界的荒诞和无价值”。
福克纳创造性地运用意识流手法,在《喧哗与骚动》中深刻刻画出各个人物层次独立而孤独的失落感。他运用有限的视角,使小说中四个独立人物用他们各自的方式看待现实,因而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现实中。对每个人物来说,过去就是现在,因为他们无法将他们现在的处境和过去的事件衔接起来。时间在这里由一种特殊的形式呈现,过去、现在、将来交织在一起,使小说充满了“不确定性”。读者被毫无心理准备地置身于小说的情节之中,必须自己把小说的一个个事件拼凑起来,才能弄清故事。因此,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不确定性”,在《喧哗与骚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关于“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的定义,伊桑·哈尔在其《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中概括为:“By indeterminacy,or better still,indeterminacies,I mean a complete referent that these diverse concepts help to delineate:ambiguity,discontinuity heterodoxy,pluralism,randomness revalt,perversion,deformation.”[4]126伊桑·哈尔所说的“不确定性”的所有特征都形成了对《喧哗与骚动》的一种强烈解构。
二、主人公的不确定性
对小说人物身份的探索是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与传统小说不一样的是,在《喧哗与骚动》中没有十分清晰特定的主人公。尽管康普生家族本身一部分符合悲剧主人公的经典定义:一个性格上带有使他犯错误走向毁灭的缺陷(康普生家族存在许多种问题)和拥有显赫地位的人(康普生家族曾是美国南方有钱有势的贵族)。然而,典型的悲剧主人公,如Sophocles笔下的Oedipuo,经历了认识错误并承认错误的过程,而康普生家族并没有经历这类过程。因而,有些评论家认为班吉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因为他见证并客观地叙述了小说中最关键的一章,小说题目本身也直指向他。但如果从哪个人物对其他人物影响更大这个角度来说,凯蒂无疑被认为是小说的主人公。福克纳自己曾说:“对我来说,她是美丽,深为我所心爱。这就是我这部书所要表达的……要塑造凯蒂的形象。”[5]6“在独白世界中,作者凭籍自己的外位与超视,可以使主人公失去自主的地位,可以代替他说话,可以给他最终论定,因为主人公已无话可说。但是对话的形象描写,使作者的超现实与外位发生了重大变异,使他不仅从内部即从‘自己眼中之我’、同时也从外部即从他人的角度‘他人眼中之我’,进行双向的艺术思考,使主人公不可替代,使主人公不被物化,从而‘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与未论定性’,成为不可完成的‘自己眼中之我’。”[6]126那么,作为主人公的凯蒂,她是堕落者?这里,福克纳给了凯蒂一个自由的空间。正如巴赫金说:“我们确定主人公的自由,是在构思范围内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自由如同客体性主人公的不自由一样,也是被创造出来的。”[7]218
凯蒂是整个小说注意力和感情的中心,是连接小说各个部分的纽带。她是小说的主人公,但又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主人公。她在小说中,在不同人物的眼中,具有不同的身份,而她的故事,都是通过四个不同的叙述者讲出来,没有一个声音是权威或者压倒一切的。具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个人经历的叙述者通过他们的记忆和想象,塑造了一个充满矛盾和诠释空间的凯蒂形象。
在白痴班吉眼中,凯蒂是一个充满爱心和关爱的母亲形象,而在昆丁的眼中,凯蒂是康普生家族荣誉的象征。作为家庭中的女儿,她代表着康普生家族的荣誉。昆丁无法摆脱家庭的荣誉和南方贵族思想的纠缠,使得他甚至为了保护凯蒂而宣称她的孩子是他的,对于他来说,凯蒂是家族荣誉的象征,他恨凯蒂,连同她的女儿一起恨。因为她只是一个个性强、爱憎分明,敢于同传统的势力和不良倾向作斗争的女孩子,她公开同杰生的恶行对着干,甚至揭露她母亲的虚伪,并敢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8]凯蒂又是一个叛逆和堕落者。她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很强的叛逆精神。即使很小的时候,她就口出狂言:“我要是逃走,我就永远也不会回来。”[9]19她对家庭硬要把她塑造成一个恪守传统南方妇女道德观的大家闺秀非常反感,继而拒绝服从,最后不堪忍受家庭的压抑,终于离家出走,到外面去寻求她渴望的爱。也正是这种叛逆,导致了她的堕落:由于未婚先孕,母亲禁止她回家,丈夫拒绝接受她,经济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痛苦,迫使她一步步堕落。“她的一生从对传统的反抗和对爱的追求开始,竟以悲剧结束,终于从一个具有独立个性和叛逆精神、天真可爱的女孩沦落成为妓女和纳粹将军的情妇。”[8]因此,凯蒂究竟是什么人?我们无法确定。她的形象只是在别人的偏见中存在。
三、情节的不确定性
小说的情节是构成一本小说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运用他那天才作家的艺术手法,抛弃了传统小说连贯、逻辑、封闭的小说情节模式,而让他的叙述者不是从头到尾按时间顺序进行。但这种叙述又不是常人所说的倒叙,因为倒叙就意味着站在现在的位置回顾过去。而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让过去与现在交织在一起,让读者难以分辨。这就是巴赫金论及的小说对话问题:“对话实际上可能在小说的任何组成部分,任何内在和外在的因素,比如不同人物性格、视角、事件、时间、地点等等之间进行。正是这种对话使得小说变得‘不规则’和难以确定,或者用巴赫金的话说,它造成了复调小说本质上的不确定性。”[10]
福克纳把《喧哗与骚动》分为四章:1928年4月7日(班吉部分);1910年6月2日(昆丁部分);1928年4月6日(杰生部分);1928年4月8日(迪尔西部分)。我们从表面上看,小说这四个部分似乎是随意安排的。但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四个部分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在时间上是有序的。第一章是写白痴班吉的意识活动。作为白痴,班吉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做事。他的一切活动都只能靠嗷嗷嚎叫,或呻吟或沉默来表达。他的意识活动既无时间概念,又无先后顺序。他意识里可以把几十年所发生的事情汇聚到一起,变成混乱无序,杂乱无章的意识活动。他所发生的故事情节为小说的另外三个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埋下了十分重要的伏笔。第二章是昆丁的故事,本章的故事情节是以昆丁的意识活动来展开的。昆丁的意识活动跳跃很大,犹如火山爆发。但他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境地中,陷入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在他的意识里,“未来”是看不见的,“现在”则是模糊不清的一片“浑浊”,只有“过去”才是真实清晰的。[11]469第三章是关于杰生的故事,故事情节仍然就是以杰生一天之内的内心独白来展开的。整个情节无外乎是告诉人们:杰生是一个“无知、肤浅、狠毒、自私、猥亵、狡猾、冷酷无情、利欲熏心”的市侩小人。[12]115他一生所想所做都证明他纯粹是恶的代表,是“一个没有道德,最最实利主义和最最邪恶的人。”[13]72第四部分则由作者以全能观点的身份来叙述。小说的四个部分各自独立成章,都有自己的故事情节。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班吉、杰生、昆丁、迪尔西在1928年复活节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康普生整个家庭的故事,故事从1898年延续到1928年凯蒂的女儿小昆丁从康普生家庭中出走。
《喧哗与骚动》中的四个部分的故事情节在后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变得就像一座迷宫,一个个的故事慢慢散落,一点一点的信息渐渐浮出水面,待读者重新拼构组成一幅图画,也奏响出一曲南方家族没落的无尽挽歌。这正如著名评论家康拉德·艾肯所说:“因为福克纳先生倘有某个方面比另一个方面更与众不同的话——的确,有些读者认为,它已经与众不同到了他们永远只好望洋兴叹的地步——那就是他一心一意几乎入迷地拚命要写出一种文体,尤其是最近,要写他坚持的那种非常奇特的文体。”[14]71
四、语言的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作家十分重视打造语言,有的甚至是醉心于玩弄语言游戏,这就造成了后现代主义作品语言的不确定性,使文本语言的风格总是随着时间、空间、人物、情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的文本语言就有典型的不确定性。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班吉部分)中,福克纳的语言风格是简单的,每个单独的句子都相当简单明了,更没有使用什么生僻晦涩的单词。这是因为班吉本身就是白痴,其思维、其语言也应当简单。只要粗略统计,我们可以发现班吉的词汇仅仅使用了500个单词,这些词,几乎绝大多数是动词和名词。这种简单具体的叙述正代表了他的内心世界,从而反射出他智商的低下和词汇的贫乏。福克纳自己常说:“塑造班吉这个人物时,我只能对人类感到悲哀,感到可怜。对班吉那是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的,因为这个人物本身并没有感情。对于这个人物本身,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些担心,不知我把他塑造得是否可信。他不过是一个作开场的演员,好比伊丽莎白时代戏剧里的掘墓人一样,他完成了任务就下场了。班吉谈不上好,也谈不上歹,因为他根本就不懂得好歹。”[14]262然而,福克纳在转向描写昆丁复杂的心理时,他所使用的语言风格又发生了迥异。在昆丁的部分中,我们发现他所使用的是长而复杂、让读者难以理解的句子。要表达昆丁自杀前的意识活动,即他那脑海里涌动而无法说出来的语言不得不让福克纳下一番功夫。昆丁的内心世界总是和复杂的道德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这一部分从文体上看就显得复杂得多。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福克纳用到昆丁身上的很多词汇都是为了表达昆丁大脑中那复杂而抽象的思想和观念。这些都反映了昆丁特有的内心活动,一种让人只能隐约感受到,却又无法完全把握的意识流,这种意识流“使人感到昆丁永远处在一种浑浊的境界,不能自拔,它预示了昆丁自杀的必然性。”[12]而在杰生这一部分,福克纳又使用了既不同于班吉,更不同于昆丁的语言体。他的语言简约而口语化,就像是在与人交流,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而对于迪尔西,福克纳则精心调整了他的语言风格来适应迪尔西这个善良的角色。迪尔西的语言是一种安静而客观的风格。福克纳没有使用任何评论的语言,更没使用他那拿手而复杂的长句,让读者被呈现在四个章节所发生的事件面前。
语言的不确性正是福克纳高超写作技巧的表现。这种不确定性真正艺术地表达了《喧哗与骚动》中不同叙述者的内心世界:白痴的班吉,敏感自杀而死的昆丁,残忍的杰生,充满关爱的黑人仆人迪尔西。正如福克纳自己所说:“我对这本书最有感情。总是撇不开,忘不了,尽管用足了功夫写,总是写不好。我真想重新再来写一遍,恐怕也还是写不好。”[14]262由此,我们可见福克纳对语言的极高要求。
五、主题的不确定性
《喧哗与骚动》是深刻反映时代的传世之作,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的杰作之一,其影响经久不衰!小说的情节更是错综复杂,题材广泛,涉及到历史、政治、宗教、社会伦理、婚姻等等。因而不同的人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和认识,挖掘出不同的主题。这种主题的不确定性,给了读者很大的理解空间,让读者尽量地想像和推理、探索,不得不承认,这正是福克纳的高明之处。
主题一:批判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对“人性美”的毁灭。凯蒂是小说的主人翁之一,她心地善良,富有爱心。在康普生家的亲人中,只有她对哥哥昆丁和弟弟班吉体贴入微,关爱有加。在福克纳的笔下,凯蒂应该说是“人性美”的象征,就像他自己评说的那样:“对我来说,她就是美,是我的心肝宝贝。”[15]6因而,凯蒂的堕落,暗示着“人性美”的毁灭,这种毁灭可以说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果。
主题二:歌颂黑人的精神美。小说中的黑人女佣迪尔西,从小就生活在康普生家,她没有文化,但却能深明世态,她的忠诚、忍耐、毅力与仁爱体现着黑人的美德。她不畏惧主人的仇视与世俗观点的歧视,敢于保护白痴班吉,她身上特有的同情心似乎永不枯竭地从她的身上涌流出来。在她身上,体现了福克纳的“人性的复活”和“人类是有希望的”积极思想。[16]194迪尔西是福克纳最喜爱的人物之一,更是他全部作品中最光辉的形象,因为她代表着历史,也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规律,福克纳通过对迪尔西的赞美,热情地歌颂了黑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精神美。
主题三:南方贵族价值体系的土崩瓦解。美国南方最大的特点就是农业社会、种族问题和清教主义并存,在这种复杂的并存结构中,家庭则是组成这个社会的一个个中心。“家庭在南方社会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的原因无疑就在于南方的农业经济特别是庄园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从本质上讲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它必然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以在南方,家庭观念比在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突出,家庭的价值在南方比在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得到珍惜。”[17]康普生家庭作为南方种植园主阶级以及南方家庭的代表,在内战之中和内战之后的重建过程中,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心理上都毁掉了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家庭。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那个命定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南北战争推倒了腐败的蓄奴制度,商业资本主义的侵蚀,又粉碎了重建旧秩序的梦想。”[18]作为南方家族代表的康普生家族,这种传统南方家族的价值体系的土崩瓦解,标志着美国南方一个制度、一个社会、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由兴盛走向衰亡。如果说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是为康普生家庭唱起的一曲无尽的挽歌,那么它也是为整个南方家族价值体系的瓦解而唱。
主题四:反对奴隶制和种族偏见。反对种族歧视,歌颂普通人的高贵品质,探讨人类相亲相爱的途径是福克纳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早在《去吧,摩西》里,福克纳就从社会、历史、家族的兴衰等多方面探讨了种族问题”[19]213。他在公开谈话和演讲中,都强烈地反对种族歧视,谴责奴隶制度,仗义执言:“谴责第一个黑人被押运到这个国家并被卖籍为奴的日子。”[20]146在福克纳创作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小说里,在他精心设计的四大家庭(沙多里斯、康普生、斯特潘和麦卡士林)衰败的过程中,他都借以塑造典型的黑人形象,描写黑人生活,以此深入探讨种族问题。特别是在《八月之光》中,福克纳描写了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被不合理的社会法则所支配,受到命运的捉弄而悲惨死去。福克纳对种族歧视问题表态十分坚决,就是在他晚年时,他也非常关心这个社会问题,想在“国家的声音中表达一点自己的意见”[21]166。
主题五:对近代文明的深刻批判。福克纳在他的小说中,真实地反映了新旧两种文明形态的撞击带给小说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故而构成悲剧的社会背景。在新旧两种文明形态的撞击中,现代精神文明成为一种扭曲人性、践踏传统美好价值的异己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发达,现代精神文明、现代文明人的道德观念、社会宗教、法律等越来越走向堕落,阻碍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并最终把叛逆者打入死亡和孤独的深渊。福克纳不仅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践踏传统文明、反人性的一面,而且深刻揭露了处于这种文明之下的西方人民的精神世界的分裂和危机:他们的心灵在异教文明和基督,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撕扯中困惑、痛苦、挣扎。[19]102-103
六、结语
“‘文贵独创’,福克纳作为成功的作家,有着自己的风格,这是他艺术独创性的集中表现,也是他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22]通过对《喧哗与骚动》文本的仔细研究,我们对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不确定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如此一部不打算提供任何趋向于结论的小说,无不传达出无处不在的感受,蓄意混淆的效果,要求叙述者与读者共同努力,以求获得文本中不确定的伤感。这也许也是不确定性所具有的文学魅力。福克纳通过小说的种种不确性向我们展示了整个后现代的精神危机和人文困惑。他对传统小说封闭、意义及结构形式的大胆突破与创新,无不体现了一种后现代精神。正如 Patrick O’Donnell所说:“These ripples can be seen as the movement of Faulkner’s text through modern and postmodern culture,through the different molecularities of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23]31因此,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仍然“对现代性有着一种深刻的批判,其作品中隐约地流露出一种解构现代文明,特别是北方商业文明那种主流文化,那种敢于质疑现代文明所确立的绝对性和同一性的后现代精神。”[24]
[1]李维屏.英美后现代小说概述[J].外国语,1998(1).
[2]汤学智.80年代后现代主义寻踪[J].文艺评论,1998(6).
[3]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代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Hassan,Ihab.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M].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5]Gwynn,F.& J.Blotner.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M].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1959.
[6]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C]//巴赫金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2.
[8]肖明翰.试论福克纳笔下的妇女形象[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
[9]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0]肖明翰.《押沙龙,押沙龙》的不可确定性[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1).
[11]李文俊.《喧哗与骚动》译本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12]刘洊波.南方失落的世界[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3]孔耕蕻.《喧哗与骚动》、《高老头》叙事艺术异同论[J].社会科学战线,1991(2).
[14]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5]Gwynn,F.L.& J.L.Biotner.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M].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
[16]董衡巽.美国现代小说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7]肖明翰.福克纳与美国南方[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
[18]张光昂.美国南方的悲剧[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6).
[19]黎明,江智利.另一个角度看福克纳[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20]威廉·福克纳.论文、演讲及公开信集[M].纽约:兰登书屋,1965.
[21]Blanton,J.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n Faulkner[M].New York:Random House,1977.
[22]江智利.福克纳《八月之光》的艺术特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9).
[23]O’Donnell, P. Faulkner and Postmodernism [C] //Weistein,P.M.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lliam Faulkner.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4]黎明.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八月之光》的任务和语言[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