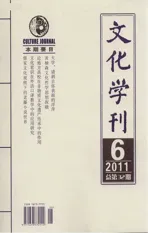南宋佛教水陆画及其商业化进程
2011-03-20申小红郭燕冰
申小红 郭燕冰
(佛山市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广东 佛山 528000)
一、前言
近年学术界有不少关于水陆画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例如,《山西省博物馆.宝宁寺明代水陆画》,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黄河《元明清水陆画浅说》上、中、下,载于《佛教文化》2006 年 2-4 期;姚雅欣《旨一韵殊——京、晋博物馆藏水陆画比较研究初论》,载于《中国博物馆》2010年第一期;白万荣《西来寺明代水陆画‘天龙八部’诠释》,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五期;白万荣《青海乐都西来寺明水陆画析》,载于《文物》1993年第10期;柳建新《泰山岱庙馆藏水陆画初探》,载于《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苏金成《水陆法会与水陆画研究》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叶削坚《水陆画及水陆法会仪式》,载于《丝绸之路》2004年;王国建《水陆画研究的“图像学”意义》,载于《中原文物》2010年第五期;李德仁《山西右玉宝宁寺元代水陆画论略》,载于 《美术观察》,2000第8期;赵庆生《水陆画造型艺木再认识》,载于《文物世界》2007年第2期;李欣苗《毗卢寺壁画引路菩萨与水陆画的关系》载于《美术观案》,2005年第6期;赵燕翼《古浪收藏的水陆画》,载于《丝绸之路》,1994年第3期;谢生保,谢静《敦煌文献与水陆法会》载于《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谢生保《甘肃河西水陆画简介——兼谈水陆法会的起源和发展》,载于《丝绸之路》2004年;谢生保 《河西水陆画与敦煌学——甘肃河西水陆画调查研究简述》,载于《陇右文博》,2004年第2期;徐建中 《怀安昭化寺大雄室殿水陆画》,《文物春秋》,2006年第4期;圣凯《汉传佛教水陆法会大观》,载于《中国宗教》,2003年第 9期;戴晓云《公主寺水陆画新释》,载于 《佛教文化》,2010第3期;戴晓云《北水陆法会修斋仪轨考》载于《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一期;戴晓云 《佛教水陆画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5月版;周雅非《从水陆画看清末四川民间的十王信仰》,载《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等等。
即便研究成果颇丰,但是水陆画的研究一直难以走进深层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有其自身原因的:第一,它属于工匠作品,甚至是流水线商业作品,作者其名不彰,水平参差不齐,历来不受绘画研究者重视,因此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第二,出于其实用性,作品流散各地,损耗时有发生,导致现存水陆画处于散乱状态,无法进行系统研究。
关于水陆法会,在一些论文、论著中已形成共识,“水陆法会曾经是风行中国朝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法事最多,仪式最隆重的一种经忏法事活动。它距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它始于南北朝,历经隋唐、五代,到宋代形成规模,元明时期达到鼎盛,清代晚期逐渐衰落,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已基本上消亡。近年来,港台地区和南方等地的一些寺院又有举办,但已不完全按照古代仪轨。”[1]港台和南方一些寺院的水陆法会仍然举办得相当隆重,而且以皇家礼仪来操办,为整个国家祈求祥和,是佛门盛事。
对于水陆画的历史、内容、功能,已有不少论著进行了研讨,并大有成效。如今国内流传的水陆画大部分为明清制品,李德仁《山西右玉宝宁寺元代水陆画论略》认为山西宝宁寺的水陆画是元代作品,如得到有力实证,这批水陆画已经是现存最早的水陆画实物了,但是早在宋代已有关于水陆画的记载,学者谢生保考据敦煌文献,证明南北朝时期已出现“水陆法会”的字眼。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评价南宋的宗教生活时说:“没有比十三世纪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更多采多姿的了,即使冒过分草率简略的危险,我们亦须首先将这种鼓舞热烈宗教生活的精神加以解释一番。”[2]而王伯敏的研究从侧面印证了宋代民间绘画的热情:“宋代民间绘画的活动,随着农村小农经济的高涨,显得比较活跃。”[3]
在本文,我们将对水陆画在宋代特别是南宋的发展及商业化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水陆画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关于“水陆画”的概念及范围定义。
目前,一些研究者将宗教绘画笼统归入水陆画,其实水陆画与水陆法会一样,是有其科仪的,现行的《水陆仪轨会本》中就有所记载,附录中专辟一章《重订水陆画式引》,文后的落款年代为道光甲申七月,称旧时 “水陆之有画像,由来旧矣……各处道场,随意造作,从无画一……随画师所传,颇不的当,知其泯失,由来已久”[4],于是“依照仪轨中所列名类,每位分为三轴,庠序安列,谱为定式,复各为之说,以申明之,自今以往,画师可以按谱而绘,一改从前混淆之作。”[5]所以后期成熟的水陆画一般成套出现,称一堂,在装帧、尺寸、构图上均有统一样式,但水陆画发展成熟的过程是长期和曲折的,地域跨度较大也导致区域差异的产生,所以统一的形制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有不同的体现。
我们留意到大部分在水陆画研究中没有重视装帧方面,甚至很少提及尺寸。还有一些将壁画归入水陆画中,如《公主寺水陆画新释》、《怀安昭化寺大雄室殿水陆画》等,谢生保曾指出水陆画与壁画有着深厚的渊源:“河西水陆画可以说是敦煌艺术的延续”[6],但并非所有宗教壁画都可以归入水陆画类别,水陆画在功能和场地方面都有所特指,是在举办水陆法会时使用的图像,而非日常装饰庙堂的图像。
关于水陆画的形制,有研究者认为“我国在宋代已盛行在水陆法会上供奉水陆画。水陆画原为轴幅,长方形,以后寺院根据水陆画轴幅粉本绘制为壁画。”[7]壁画和轴幅之间的关系除了同时并存的可能性外,从不可移动的壁画形式向可移动的卷轴发展,于保存及使用两方面来说均有所改进。进而言之,并非所有的卷轴宗教绘画都属于水陆画,仅仅在佛山,与宗教有关的神相、门神、年画、文人画就不胜枚举,都不属于水陆画。因此,我们认为,水陆画是一种用于水陆法会的宗教画像,有其统一的仪轨。
关于水陆法会缘起以及水陆画在水陆法会中的使用方式,研究者已经考察得非常清楚:“水陆画是佛教寺院举行水陆法会(又称水陆道场、水陆斋会)时专门悬挂的宗教画。水陆法会是一种宗教仪式。据佛教经籍载,释迎牟尼弟子阿难夜梦饿鬼面然,佛遂授阿难以经咒,诵以超度。现传佛藏中有《佛说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一卷。中国的水陆法会起于南朝梁武帝时代。“梁武帝制作‘水陆’的年代,各典籍记载不一,《事物纪原》认为是天监七年(508),而《佛祖统纪》认为是天监四年(505)。 ”[8]
《佛祖统记》卷三十三载:“梁武帝梦神僧告之日: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大斋以拔济之。……帝即遣迎《大藏》,积日披览,创立仪文,三年而后成。……天监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仪修设。帝亲临地席,诏(僧)佑律师宣文……此斋流行天下。”水陆法会所请的佛菩萨众神诸鬼无所不包,其中有诸佛、众菩萨、明王、金刚、罗汉及婆罗门仙,还有诸天、地狱、山川、河读神灵以及社会各阶层,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或正寝或屈死的鬼魂,这些都要画在水陆画上。无论是阿难梦面然饿鬼的传说,还是梁武帝梦神僧告以六道四生受苦无量,都说明水陆法会的主要着眼点是抚慰超度那些受无量之苦的饿鬼冤魂。由于封建社会政治腐败,统治残暴,战争频繁,灾祸不断,人民深受苦难,积怨很深,社会矛盾激化,这对于皇朝的统治极为不利。“水陆法会的举行,正是通过对死者的安抚,给生者以慰藉,从而缓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积怨,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因此作为水陆道场重要设施的水陆画的意义,并非一般寺庙雕塑壁画所能替代,这就是水陆画历代一直流行的原因。 ”[9]
水陆法会规模一般较大,通常做7天,有的多至49天。宝宁寺地处边防,故其水陆道场时间较短,定为三天。仪式时将诸佛菩萨神鬼画像按序列悬挂,一卜设灵牌,上书各自名号,焚香并供以精美饮食。设坛诵经,请诸佛神仙饿鬼冤魂到位,每夜放焰口—施食。施食时“诸仙致食于流水,鬼致食于净地”,故称“水陆”。最后夜“送圣”,即将所请诸佛神鬼全部送走,仪式结束。
三、宋代的“水陆法会”
“水陆法会”的最早实施应该在宋代熙宁年间(1068-1077),东川杨锷所撰水陆仪轨(又称为“杨推官仪文”),流行于四川,这是较早的水陆仪轨的完整形态。
元祐八年(1093),苏轼为亡妻宋氏设水陆道场[11],并且撰《水陆法像赞》16 篇。 苏东坡在《水陆法像赞序》中说,水陆道场随后世而增广,惟有四川保存有古法,而且各种画像及设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风格。因为他本是四川眉山人,所以他作的《水陆法像赞》就被称为“眉山水陆”。宋元丰七、八年间(1084-1085),佛印(了元)住金山时,有海贾到寺设水陆法会,佛印亲自主持,蔚为壮观,遂以“金山水陆”驰名,“金山水陆”又称为“北水陆”。
绍圣三年(1096),宗赜删补详定诸家所集,完成《水陆仪文》4卷,普劝四众,依法崇修。现在,《水陆仪文》已经失传,仅从其所撰《水陆缘起》一文,可知其内容之一斑。
南宋乾道九年(1173),四明人史浩曾经经过镇江金山寺,慕水陆斋会的盛况,于是布施田地百亩,在四明东湖月波山专建四时水陆,用来报答四恩,并且亲制疏辞,撰集仪文。宋孝宗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颁赐以“水陆无碍道场”寺额。
月波山附近有尊教寺,师徒道俗3000人,布施财产,购买田地,遵奉月波山四时普度之法。大众又诚心请志磐大师续成《水陆新仪》6卷,大力推广斋法,并且劝十方寺院,重视斋法,大兴普度之道。
水陆法会自从宋代流行以后,很快普及于全国,特别是每次战争后,朝廷上下经常举行超度法会。宗赜《水陆缘起》中说,供养一佛、斋一个僧人,尚且有无限功德,何况普同供养十方三宝、六道万灵,不但能使自己得到利益,而且能够恩沾九族。所以,在江淮、四川、广东、福建,水陆佛事自此十分盛行。
在宋代特别是南宋,如果有人为了祈求保护平安而不施设水陆,那么就会有人认为他不善;如果追悼怀念长辈而不设水陆的话,就有人认为他不孝;如果救度卑微、幼小的众生而不设水陆,那就是不仁慈。所以,在江南地区,富贵有钱人独自举行水陆斋会,贫穷者则共同出钱修设法会,这也就是后世所谓“独姓水陆”和“众姓水陆”的来源。水陆法会仪轨自宋代以来,经过不断的增补,日趋完善。现代水陆法会坛场的布置、念诵经典及其人数,牌轴的规定和进行的程序等,参照《鸡园水陆通论》等典籍。[11]
水陆画随着水陆法会的兴盛而发展,绘制的轴数越来越多。苏东坡为亡妻修设水陆道场,并作《水陆道场法像赞》16篇,当时可能悬挂水陆画16轴。南宋末年,志磐法师所著《水陆新仪》六卷中,规定悬挂水陆画26轴。到了明、清之时基本定型,一堂水陆画一般为120幅,主要依据水陆法会的规模大小来定。私人家庭修设的水陆法会,少者36轴,多者72轴。地方大型寺庙修设的水陆法会,一般为120轴左右,朝廷修设的水陆法会,多达200余轴。“最初水陆画以佛教诸佛、诸菩萨、诸神为主,唐宋之后,随着儒、释、道三教融合,道教诸神、儒家诸神、民间诸神逐步进入水陆画,水陆画中所绘的内容也变得十分庞杂。”[12]
至明清时期,水陆法会已成为一种寺庙文化活动,广泛流行于社会。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全国各地的大型寺院、道观都要举行水陆法会。“今天,人们在七月十五日上坟,给死者烧纸上香,供献食物,半月食斋,以及正月初八拜阎王,也都是水陆法会的遗风。 ”[13]
四、宋代佛教造像
佛教造像最初由印度传来,进入中原后在敦煌莫高窟创造了璀璨的石窟艺术,后沿着河西走廊逐渐南移和东移,在北宋时期来到了四川一带,后东移至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带,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南方佛教造像体系。
宋代开创了继南北朝、唐朝之后中原佛教艺术的又一高峰,宋太祖在建国之初改变了后周的灭佛政策,重修寺庙,广纳僧尼,大造佛像。除徽宗外,历代皇帝对佛教皆持扶植态度,民间也广为呼应。
五代及宋,禅宗独盛,佛教绘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严谨整饬的佛传图、经变故事画衰落了,开始流行罗汉图及禅僧的顶相 (祖传法师肖像)图等。
自南宋,佛教石窟艺术的重心已经转移至南方,敦煌虽然仍在建造,但日益衰减,究其原因,有研究者作出了解释:“敦煌石窟艺术在元代终止的原因:一是宋代之后,南方沿海水上丝绸之路开通,北方内陆丝绸之路衰败。敦煌石窟艺术的营造失去了经济来源。二是明王朝虽然推翻了元王朝,但无力收复河西走廊全境和新疆地区,便以嘉峪关为界,尽迁敦煌、安西、玉门地区的居民入关,致使敦煌成为域外之地。那些创造敦煌艺术的画师、工匠便回到了家乡,或流落到了酒泉、张掖、武威等河西诸县。为了谋生,便为河西诸县寺院绘制壁画和水陆画。”[14]这段话同时解释了河西有大量元、明、清水陆画出现的原因。
南方佛教造像艺术的出现表明中国佛教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汉化时期。
宋代尤其是南宋,绘画崇尚写实,线描艺术达到了成熟期,这时的佛教绘画尤其是水陆画也染上了浓郁的时代风格。即使流传到元、明、清以及日本、朝鲜等地,这些特点仍如影随形地出现在画面上,这方面包括宋代的服饰、场景等。由于追求写实,由印度传来的异域之风一扫而光,人物形象完全依照宋代中原人民的形象来塑造;因为技艺的精湛和成熟,全用本土的技术(线描、赋色)进行描绘,且惟肖惟妙,纤毫毕现,这些作品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随着佛教向东亚的传播,逐渐流传到地区,在该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本土化,但其中的汉化因素,特别是宋代风格,一直延续到今天。
五、南宋佛教水陆画的商业进程
为了佛教传播更加方便和更为深远,宋代佛教造像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卷轴形式,一个是商业化。
出于传播的方便,石窟、壁画等艺术形式逐步向卷轴书画的形式转变。从石窟到壁画再到卷轴这样的发展轨迹,在现存实物中有多方面的体现。从历代佛教艺术的创作时间看,敦煌石窟从南北朝开始开凿直到元代,四川石窟始于唐代而盛于宋,随后元、明、清、民国年间,较大型的宗教艺术多是画轴或木刻印版。从形式上讲,佛教艺术的创作从本来的内向自省型转变为外向传播型,宗教艺术品是表达制作者虔诚皈依的媒介,所以早期的石窟造像都在漆黑、狭小的室内,并不刻意面向观众;后来为了宣扬教义,着重其教化作用,才面向更多的人群。因此石窟、壁画的不可移动性并不利于携带和传播,而纸张的出现、卷轴的形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佛教绘画的大量需求催生了商业化的手工作坊。在南宋时期的宁波就出现了一批这样的画家,最出名的有林庭珪、周季常等。
源自于印度的佛教地狱绘画形式擅变汉化以后,画中的十殿阎王以及各殿的情景,均浸淫了中国传统文化里官僚府衙的权阶色彩。
我们从现藏于海外的南宋时期有关十殿阎王及地狱的绘画中看出,这些出自民间画师笔下,形象生动,颜色艳丽,融释、道于一体的宗教观念的水陆画,在当时已为海外大量接受,主要原因是南宋时期的朝鲜与日本受我国影响,开始流行汉化佛教地狱的信仰,紧接着对于这类水陆画的需求也与日俱增,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南宋对外商埠的贸易大港宁波,因其海运传输之便,成为当时民间画师菌集之地,并成了专门绘制水陆画销往海外的作坊式的中心,所以,“就我们所知道日前许多流失海外的《十殿阎王图》,主要自南宋以来,均先后被日本与南朝鲜公私收藏。由此传播渠道影响了日、高丽有关地狱经变和六道轮回的信仰。 ”[15]
宋朝与日本的商贸比前代显著增多。当时中日两国商品贸易种类凡多,佛教经典亦成为商人贸易品。被派往宋朝的日本僧人,回国时大多携带大批佛经、其它典籍、绘画文物而归,输入日本的不仅有佛教经典及儒家书籍,而且还有书画艺术亦随同佛典。东初法师在《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对此有详细叙述,列举了数位禅师带回的书画经典或高僧写真画像。
南宋时期日本僧侣和幕府将军都非常赏识南宋院体画风的作品,宁波画师所绘制的佛教画像大批量地输入日本,至今仍数以百计地保留在那里,主要藏于寺院中。京都国立博物馆保存了日本各大寺院的珍品,主要有:北宋《十六罗汉像》(京都清凉寺藏);南宋《无准师范像》(京都东福寺藏);南宋《不空三藏像》(京都东福寺藏);南宋陆信忠《十六罗汉图》轴(十六幅,京都相国寺藏);南宋林庭珪、周季常《五百罗汉图》(京都大德寺藏);南宋金处士《阎王图》轴;元代佚名《十王图》(京都大德寺藏)等。金大受和陆信忠等宁波佛教画传到日本后,大都被日本的画师所临摹,其影响不仅发生于日本的佛教绘画,而且波及到以后日本绘画的各个方面。奈良藏《十王图》的组画,原本为十幅一套,现在日本存有十余套。此外,在欧美如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也有收藏。
奈良藏《十王图》署款:“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大都会《十王图》上的朱砂色署款:“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处士家画”。明州即今浙江宁波,当时日本僧人或商人渡海来中国,大多在宁波上岸,宁波是当时中国沿海最重要的口岸,这些商品画的售画对象也主要是日本或朝鲜的僧人、商人。“金处士”画史无传,只知是明州车桥人,当是民间的艺人。他们根据所传粉本(有时略为改动),或者在当地寺院中画壁画或者画了裱成卷轴放在市场出售。林庭珪、周季常的《五百罗汉图》也是如此,画上多题写作者姓名、地名,其性质与《阎王图》同,共有一百幅,原为日本京都大德寺收藏,现有82幅藏原处,少数由美国人购买转赠给波士顿等美术馆。
六、结论
水陆画在宋代出现有明确的记载,是苏东坡为亡妻宋氏修设水陆道场,并作 《水陆道场法像赞》16篇,是历史记载上首次出现“水陆画”,但水陆画及水陆法会仪轨并非横空出世,它们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衍变而来的。
佛山博物馆就藏了近百幅这类作品,这些作品尺寸较大,与谢生保提到的河西水陆画的尺寸相仿:“甘肃河西四县市博物馆所藏的水陆画,最早年代为明代中、晚期,最迟为民国时期。所有水陆画全为卷轴装,绘制装裱有绢绘绢裱、纸绘纸裱、布绘绫裱等形式。画幅不计装裱天地边饰,一般高120~150厘米,宽70~90厘米。若计装裱尺寸,一般高 260 厘米,宽 120 厘米。 ”[16]
十王像每王一幅,罗汉既有独幅的,也有两人一幅的,似乎不单是用于陈列悬挂,是否也用于法会呢?经过实地访查,答案是肯定的。但十王在后期多出现于道教醮会中。如此看来,这些画作仍属于广义上的“水陆画”,但它与后期佛教水陆仪轨中的水陆画相去较远,相信是水陆法会经过历朝历代的修改越加完善,而本来的样式又逐渐流传并发生变化。
佛教图像的实物流传显示了宗教绘画从民间信仰转化为商业绘画的历程,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接触到普通百姓的民俗文化和生存状态,即触及到象征主义中所提的“不在场的中心”。宗教信仰伴随着人们的观念在民间不断衍变,每一个细微的转变均以极其微妙的姿态在宗教绘画上呈现,人类也因这些宗教产物获得了救赎和人文的积累。
为什么我们比较关注南宋水陆画呢?因为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明清以来,作为全国著名的手工业城市之一的佛山,在宗教绘画方面与南宋时期的宁波有许多相似之处:相似的作品,相似的风格,相似的手工业作坊,相似的店铺印章。可以说,明、清、民国时期,佛山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宁波宗教绘画的手工业作坊的技法,这些从侧面印证了宗教特别是佛教造像中心在明清时期继续南移的事实,而这种转移并不是单单是宗教造像的转变,而是顺应了时代局势的大规模的文化中心的南移,因为从宋代开始,中原传统文化的重心南移,[17]明清时期的佛山在宗教绘画方面与南宋的宁波有惊人的相似,是宗教造像艺术的南移的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北方地区如山西、河西发现的水陆画属于皇家形制,而佛山的水陆画则属于南方民间形制,在明清时期通过外销途径传播到东南亚各国。
[1] [6] [14] 谢生保.河西水陆画与敦煌学——甘肃河西水陆画调查研究简述[J] .陇右文博,2004,(2):54.
[2] [法] 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M] .台北:中华文化大学出版部,中华民国七十一年三月.160.
[3]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M] .上海:三联书店,2000.366.
[4] [5] 水陆仪轨会本:据明代高僧云棲订本重刻[M] .上海佛学书,2002.145,146.
[7] 徐建中.怀安昭化寺大雄室殿水陆画[J] .文物春秋,2006,(4):59.
[8] 圣凯.汉传佛教水陆法会大观[J] .中国宗教,2003,(9):56.
[9] 李德仁.山西右玉宝宁寺元代水陆画论略[J] .美术观察,2000,(8):62.
[10] 苏轼.东坡后集:卷十九[A] .东坡七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36.
[11] 宗凯.汉传佛教水陆法会大观[J] .中国宗教,2003,(9):56.
[12] [16] 谢生保.甘肃河西水陆画简介——兼谈水陆法会的起源和发展[J] .丝绸之路,2004,(1):10.
[13] 周雅非.从水陆画看清末四川民间的十王信仰[J] .中华文化论坛,2009,(1):104.
[15] 张纵,赵澄.流失海外的〈十王图〉之考释[J] .艺术百家,2003,(4):140.
[17] 张全明.试析宋代中国传统文化重心的南移[J] .江汉论坛,2002,(2):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