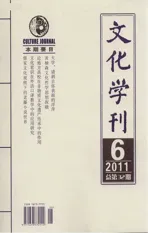凯尔纳文化批判理论的借鉴意义
2011-03-20何美子
何美子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道格拉斯·凯尔纳(1943-),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被西方理论界誉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分析者”,也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也有学者称其为“第三代批判理论家”。他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科学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育哲学首席教授,主攻方向有三个:文化研究、哲学与教育、后现代理论与批判理论。主要著作有《卡尔·科尔施:革命的理论》、《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让·鲍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更远》、《电视与民主危机》、《波斯湾的电视战》、《摄像机里的政治:当代好莱坞电影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后现代理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历险》、《媒体奇观》、《媒体文化》等。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问题日益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文化批判更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理论课题,凯尔纳的文化批判理论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站在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在避免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理论某些极端结论的前提下,对当前时代表现出的新的时代特征与现象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应,其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时代界说、对多元差异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的追求等都赋予其文化批判理论以客观、辩证的学术向度,从而开创了当前文化研究的新局面。无疑,这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理解处于世纪之交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深层文化危机,并且对于正处在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过渡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可以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一、当今时代的文化定位
给当今时代以文化定位成为各派文化研究之起点。凯尔纳的文化批判理论从广义的文化涵盖出发,首先对当今时代进行了文化定位——正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广袤地带,由此表现出现代与后现代性征兼而有之的时代特点,现代与后现代的视角对解读当前时代均有意义,因此需要发展出新的综合与跨学科的文化批判理论,凯尔纳批判地介入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理论,进而指明了当前文化的突出特征——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在理论、艺术和科学方面出现了一种后现代转向,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要范式的改变,有些人据此认为是从现代世界到后现代世界的划时代转型,声称西方社会正进入一种 “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丹尼尔贝尔语),也有人称作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消费社会、高度发达社会,在文化形态上称为“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时代”。但凯尔纳反对诸如此类的提法,他指出:以“后”字为定语的思潮谱系低估了过去和现代之间的延续性,并且也未能很好地解释传统工业和制造业为什么仍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等称谓仅仅突出了社会某一方面的特征,在本质上是一种决定论。
既有别于那些后现代激进分子所鼓吹的历史断裂论调,也有别于一心返回现代的悲观论调,凯尔纳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路——一条思想之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一条中间道路。凯尔纳一方面肯定西方社会当前正经受着一种范式的转变,后现代转向已经开始;另一方面,他强调当前后现代转向虽然已经出现,但作为一种新兴事物,还没有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仍有待于充分地展开、成长和成熟,后现代转向正值突显,不能轻易地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仍然主导着世界。当前我们正同时体验着现代与后现代的诸多性征。凯尔纳一直“把后现代看作是现代的一种激进化,它使一些现代现象如商品化、大众化、技术、传媒得到不断强化,以至与现代世界产生真正的中断和产生真正新的事物。”[1]这个立场的长处在于提供了避免过于夸大非连续性和断裂,并强调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连续性的重要线索。
正如凯尔纳所说:历史时代不会以纯粹形态或以精确的年代顺序时间产生或结束。也许我们当前时代在某些方面与文艺复兴平行,而文艺复兴构成了前现代社会结束和现代社会诞生之间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这样的时期具有多层面的变化和发展不平衡以及一个新时代喷薄欲出所伴随的分娩阵痛之特点。[2]正如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层铁幕或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因为历史是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中。 ”[3]
显而易见,凯尔纳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时代界说为我们审视当前的中国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考。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后现代性虽然并非中国的“主流”,但这股“支流”能够反照“主流”,能够让我们更清醒地评估现代化事业。在如何看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转向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无法对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后现代现实充耳不闻,对自己身边的后现代现实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正视它、研究它。我们必须研究、探讨后现代的范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割断历史,将后现代视为孤立的文化事件,我们不同意断裂论。在此,凯尔纳对当前的文化定位——现代与后现代并存,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们正在共时性地体验着传统、现代、后现代,因此,我们更有理由在强调现代价值理念的同时,警示后现代对现代某些方面的反思,同时也要注重吸收传统中的现代因素。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思路都是有益的视角,凯尔纳批判地介入现代与后现代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二、解读“媒体文化”
(一)“媒体奇观”的解读
当前是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世界,在媒体制造的种种奇观面前,人们被动地、潜移默化地失去了分辨的能力。凯尔纳的文化批判理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媒体奇观”世界的门。
凯尔纳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从法国理论家盖·德堡那里获得灵感,将“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定义为“媒体奇观”,并指出:这些奇观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和政治事件等”,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被称为“奇观”的现象正渗透在电影、音乐、建筑、时装、商业等各种领域。麦当劳的金色拱门神话、乔丹和耐克公司联手制作的体育文化奇观、好莱坞化的美国政治奇观等等无不将受众带进了一个由信息、娱乐和消费组成的奇观世界。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的受众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奇观时代的气息。“超级女声”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下走进了中国大众的视野,并迅速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南方周末》曾用著名的“蝴蝶理论”来描述“超级女声”在国内掀起的娱乐风潮:“超级女声”是一场10万人的游戏,共吸引了15万人参加,在全国范围内收看年度总决选的观众总量约有2亿左右,形成了2005年风靡中国的“超女现象”。在“超级女声”长达49天的7场决赛中,吸引了超过2000万观众每周热切关注;收视率突破10%,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的第一名;报道媒体超百家;Google相关网页达1160000条……“超级女声”成为2005年盛夏众人狂欢的盛大节日,缔造了一个全民娱乐的神话。[4]无疑,在中国“媒体奇观”也正在蓬勃出现,并形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2004年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哈尔滨宝马车撞人”事件也正是政治和新闻“内爆”导致的“奇观”,其中的关键词主要有三个“哈尔滨”、“领导亲属”、“宝马”。凯尔纳的分析提供的正是研究此类媒体现象的普遍模板,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框架,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世界,也为立足本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总的说来,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更深刻的方式来解读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以“超级女声”为例,运用凯尔纳的理论,我们要透过“超女”奇观的表面现象,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文化解读。“超级女声”的复制性、消费性编织起了一条密织的“文化产业链”。首先体现在节目形态的模仿与克隆——对英美“流行偶像”和“美国偶像”的复制。《超级女声》实现了一次飞跃,一次由电视栏目向媒体娱乐奇观的飞跃。当无数电视观众为它零门槛的选秀风格、想唱就唱的节目形式和大众参与狂欢的平民精神而叫好的时候,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场绚丽而盛大的媒体奇观背后,在它主张的快乐中国、平民娱乐的外衣之下,隐藏的是一个巨大的商业运作奇观。《超级女声》演绎出了一场精彩的商业奇观。“刚刚结束的年度总决赛的广告报价为15秒11.2万元,超过央视11万元的报价;每场比赛数百万元的短信费收入;为购买节目冠名权,蒙牛集团投入了2800万元,在竞得冠名权后,该公司又追加了将近8000万元的投资……收视率第一,广告价位第一,赞助商产品销售量第一”[5],《超级女声》全然成了一场商业奇观的发动机。无疑,庞大的受众关注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媒介将这些具有公民特性的受众变成消费者。
当前中国正步入奇观社会,媒体塑造出一个个奇观,人们的认识通过这些奇观被规定、被控制,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人们没有选择地知道、相信从而听从,个人在这种商品的包装、展示和消费以及媒体文化面前失去了自主能力。”当真实世界化为简单视象时,后者就变成了一种真实的存在,其催眠和麻痹的作用十分有效。”在”奇观”文化中,商业和经济结合,共同产生了“娱乐经济”,经济背后的寡头,最终控制了人们的注意力、想象以及思考能力,人们在娱乐中逐渐爱上了麻醉和催眠,因此,和波兹曼一样,凯尔纳也认为这是一场“永恒的鸦片战争”。目前,国内媒体刚刚迈上娱乐化的大道,各电视台平民选秀节目仍旧热火朝天地进行,人们还在欣喜着它们的变化,愈来愈陶醉于娱乐之中。而凯尔纳的忧虑,倒为我们敲响警钟——“不要那么快乐,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感到痛苦——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凯尔纳的分析深刻而精辟,正可以作为我们解读当下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的奇观文化的参考。
(二)“文化霸权”问题的阐释
葛兰西关于“文化”与“领导权”的阐释可谓开创了文化霸权理论的先河,而凯尔纳以大量翔实的资料、事件与多角度的症候式分析为我们警惕与分析西方文化霸权、发展自身文化产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思路。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也已然成为他们的支柱产业。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叶郎教授在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文化产业?》一文中指出:文化霸权是美国霸权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的文化霸权也在扩张。凯尔纳以“麦当劳”为例作了深刻而客观的分析,他认为“它既是快餐生产和消费的具有代表性的形式,又是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霸权的重要表现形式”。[6]
据统计,美国生产全世界75%的电视节目,60%的广告节目。发展中国家75%以上的文化产品来自美国,而美国市场上的外来文化产品只占l%至2%。美国电影的生产量只占世界的5%至6%,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总放映时间的80%,这种强大的文化实力是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意识形态的扩张,还有美国霸权的扩张,布什就曾明确宣告要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以美国为主导的媒体文化以其商品、服务以及神话般的影视作品、媒体形象等形式,潜移默化地打造和美化本国形象,并以此诱使全球公众融入到其文化中,为其赢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可和羡慕。
具体到中国,从电影、服装、饮食等传统的文化载体,到电脑软件、网络、卫星等高科技的文化载体,甚至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无不让人感到美国文化肆无忌惮的充斥、蔓延,对此,凯尔纳一针见血的分析:警惕全球化背后的黑手——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推行着的问文化霸权,例如,对于SARS曾经肆虐中华大地这一事件,作为文化研究者需要警醒各国媒体在这场危机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从《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叠印的两片带有阴影的肺叶的五星红旗到 《远东经济评论》封面带着大口罩的毛泽东画像,从CNN推出的《北京:被遗弃的鬼城》的系列报道到福克斯电视台 “SARS国家”(但似乎没有人称美国为“AIDS国家”)的主题词,我们看到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媒体又在不遗余力地制造新一轮的“媒体奇观”。[7]无疑,凯尔纳号召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从地方、民族、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进行批判式的“诊断式文化研究”,对中国的学者和普通受众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将文化产业列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加以推动,明确了发展文化产业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提升综合国力的紧迫需要。可见,凯尔纳的关于文化霸权的阐释思想对于像我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巩固与发展文化领导权仍然有启发意义。
(三)批判的媒体解读能力
在中国,由于正处在现代化媒体的普及过程中,大多数的中国受众面对的是媒介(即媒体呈现的介质)接触时间不够的问题,甚至是能否接触到媒介的问题。但媒介接触过量问题的苗头在许多地方,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甚至十分明显。在众多问题中,因为媒介数量的快速膨胀和传播内容的无限量增加而导致的受众不适应、无所适从,已表现出严重的问题。由此,如何引导或创造条件使公众掌握接触和使用媒介的能力,是保证媒介正常发挥社会作用的基本前提。而这一点,也正是凯尔纳文化批判理论的最终指向,其借鉴价值可见一斑。
正如凯尔纳所说:“批判性的媒体解读能力的获得乃是个人与国民在学习如何应对具有诱惑力的文化环境时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学会如何读解、批判和抵制社会文化方面的操纵,可以帮助人们在涉及主流的媒体和文化形式时获得力量。它可以提升个人在面对媒体文化时的独立性,同时赋予人们以更多的权利管理自身的文化环境。”而这种批判性解读能力的获得并不是在自然状态下完成的,需要一种外界力量的介入,凯尔纳进一步指出:“学生以及其他人都不是生来就懂媒体的,或生来就能批判自身的文化,因而要为他们提供批判的方法和工具,使他们获得力量以抵制现存社会和文化中的操纵性的势力。”通过这种努力,使得受众 “得以辨析出深藏在媒体文化文本中的讯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凯尔纳称这一方法为“批判性的媒体教育学”。[8]其目的就在于将广大的普通受众从长期以来被媒体控制的被动状态中解放出来,还原受众以原初状态。通过这种努力,健康而理性的受众得以培养,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重要依托。
三、文化研究思路的构建
20世纪50年代文化研究在英国兴起,在经历了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文化研究的美国化之后,如今的文化研究已成为欧美学界的新宠。近年来,文化研究在中国也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学派的问题,仍亟待解决。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分析当下中国复杂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也正是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许多被条块分割的传统学科排除在外的文化形式得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恰恰正是这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现象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支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借助于文化研究思想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和更深邃地思考问题的能力,从而准确地把握我们身边正在急剧变动中的生活世界。然而,文化研究并不是纯实证的,而是批判式的研究。只有从中国语境而不是从某理论入手,才能达到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深切体认和合法批判。
中国的文化研究像它的现代化一样属于 “后发型”,因而势必带有横向移植的诸多特点,所以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研究思路时,更应该警惕对西方理论(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还是后现代主义)的照搬,应避免制造新的“理论马赛克”。要呈现文化研究的中国图景,我们必须在警惕北美文化研究的流弊 (这种北美化的文化研究已经蜕化为资本主义学术体制内部的知识生产活动)的同时,继承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努力把政治经济、文本分析和接受研究三者结合起来。
对此,凯尔纳的文化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有益思路,他一贯倡导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接位,从而产生新的视角来推动一种更加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事实上,部分中国文化研究者(主要以自称“批判知识分子”的新左翼为主)已经实践了凯尔纳的“理想”,他们同时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视作自己的重要资源,吸取其中的理论精髓,并且认为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从而呈现出整合两个学派观点的趋势。比如与凯尔纳文化研究思路甚为相似的中国学者南帆就用“双重视域”来考察传播媒介的意义,他说:“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带来了一种控制;既预示着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双重视域的意义在于,人们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的子弟,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9]总体说来,中国的媒体文化研究思路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上,用文化研究学派的方法对媒体文化现象进行反思。显而易见,这种思路对中国当代的媒体文化构建具有警示性和建设性的意义。
然而,文化批判的悖论和困境却在于:它不能超越自身的文化、历史语境,又必须批判产生它的历史文化条件,这就要求它不仅要批判对象而且也要时时审视自己的立足点,承认它的局限性,允许它的可变性;还要求它不是给事实以合法性的说明和认同,而是不断地探索新的可能性。可能性既是对事实的批判,又是新的经验的起点。因此,批判的延伸应该是建设。文化批判也是一个建设性的事业。
[1] [2]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芬·贝斯特.后现代转向 [M] .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38.
[3] 伊·哈桑.后现代主义初探[A] .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18.
[4] [5] 超级女声:一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动[N] . 新 京 报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2005-08-20.
[6] [7]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M] .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40.译者的话.
[8] 道格拉斯·凯尔纳[M] .丁宁,译.媒体文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
[9] 南帆.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