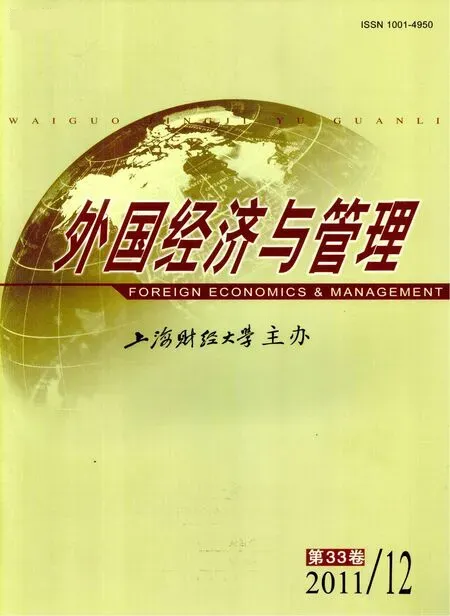控股股东、投资者法律保护和公司价值研究综述:基于不对称股权结构视角
2011-03-20周方召潘鹏杰
周方召,潘鹏杰
(哈尔滨商业大学 经济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150028)
一、引 言
控股股东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法与金融分析为代表的针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公司治理文献(如Holdness和Sheehan,1998;Villalonga和Amit,2008)认为,全球股权集中趋势非常明显,各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在不对称股权结构①下会产生监督效应和侵占效应,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而影响公司价值。
对控股股东而言,股权集中是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一,它可以使控股股东有能力监督经理人,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从而提高公司价值。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发现在股权趋于集中的同时,控股股东往往会利用不对称股权结构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控股股东利用少量的现金流权就可以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并且采取诸如扭曲投资、利用隧道效应和在职消费之类有损公司价值的行为。近年来,全球频发的公司丑闻②又为侵占效应研究提供了丰富又生动的现实背景和证据支持。正是上述现象和相关研究使得不对称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问题逐渐成为公司治理、法与金融以及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焦点集中在不对称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投资者法律保护和公司价值的关系上,兼论不对称股权结构和法律制度的交互作用问题。具体来讲,本文以不对称股权结构为主线梳理了近年来有关控股股东、投资者法律保护和公司价值关系的文献,并对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述评,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借鉴。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主要对近些年来此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文献进行整理,并非因为研究质量的好坏,而是因为直到本世纪一些大样本数据和跨国比较研究才开始兴起。
二、不对称股权结构:定义、分类与决定因素
公司治理本质上就是一种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免受公司内部人剥夺的机制,投票权是股东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契约权利。股东通过行使投票权来影响公司决策,进而获取公司控制权。“一股一票”制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表决原则,其遵循公司股东的投票权应该与其所持有的现金流权保持一致的原则,认为均衡的股权结构可以保障所有股东的权益免受侵害。然而,现实中却存在许多不对称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往往利用复式投票权、交叉持股、金字塔形层级控股、股权质押等形式使得其拥有的投票权远远大于现金流权。
“一股一票”制把股东的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结合在一起,中间不存在分离的层级结构,而不对称股权结构是一种背离了“投票权和现金流权均衡”原则(即背离了“一股一票”制)的股权结构。从形式上看,不对称股权结构是采用了复式投票权、交叉持股、杠杆投票权、金字塔形层级控股结构等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相分离的层级控制型股权结构。根据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不对称股权结构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其中,直接形式是指能够较为清晰地计算和衡量控股股东投票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股权结构,如从金字塔形层级控股结构就可以直接看出最终控股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和现金流权,而且这种结构使得控股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远远大于其所需要付出的现金流权;而间接形式则是指不能明确测量控股股东投票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股权结构,如接管防御、股权质押等形式的股权结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得,大多数研究倾向于考察直接形式的不对称股权结构问题,往往忽略了间接形式的不对称股权结构问题。其实,间接形式的不对称股权结构问题同样重要,因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产生不对称股权结构的原因以及控股股东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相分离所造成的结果,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间接形式的不对称股权结构。
既然不对称股权结构像一枚硬币具有两面,那么,控股股东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结构,也就是说哪些因素致使控股股东要把投票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开来?令人惊讶的是,有关不对称股权结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为数甚少③。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不对称股权结构的理论研究结论存在矛盾(Khanna和Yafeh,2007);二是难以获得大样本数据,因而无法进行比较研究。不过,Villalonga和Amit(2006)以及Gompers、Ishii和Metrick(2010)还是以美国公司为样本就不对称股权结构的成因进行了实证研究。Villalonga和Amit(2006)采用美国《财富》500强公司1994~2000年的数据进行Probit回归分析发现:第一代家族控股公司很少采用不对称股权结构,而且公司的托宾Q值越高,采用不对称股权结构的概率反而越低。而Gompers、Ishii和Metrick(2010)则利用美国采用单一股权结构和二元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1995~2002年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大量有限投票权股由那些并不想转让或交易的股东持有,他们持有这些股票实际上是为了获得和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采用二元股权结构公司的控股股东平均拥有60%的投票权和40%的现金流权。另外,Gompers、Ishii和Metrick(2010)还研究发现,股权结构不对称的公司大股东的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并不高。这说明控股股东并不能利用少量的现金流权获取大量的控制权。他们还通过Probit回归分析发现,采用不对称股权结构的原因可能是要更好地保护控股股东的利益和获取公司控制权。
三、不对称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监督效应和侵占效应
众所周知,中小股东对公司决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有效监督经理人行为,而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中,控股股东则能够利用自己手中的投票权对经理人实施监督;如果公司不是完全归控股股东所有的话,那么,控股股东也就会有自己的私利目标。因此,对有关不对称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即监督效应观和侵占效应观。下面,我们分别从监督效应和侵占效应两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
1.不对称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监督效应。中小股东在投资股票时更加关心股票的价差,他们既没有能力监督经理人的行为,也不会投入太多的精力去关心公司决策。与中小股东不同,控股股东持有大量股票,因而有能力也有动力影响公司决策,并利用手中的投票权来监督经理人(Burkart和Panunzi,2006)。
实际上,控股股东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力和对经理人的监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投票权和现金流权。例如,控股股东的提议需要足够多的投票支持,否则提议就无法通过,他们就不能对公司施加任何影响。因此,如果控股股东自身仅拥有少量的投票权,那么就必须获取额外的投票支持(Bennedsen和Nielsen,2006)。同样地,在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不起任何作用的条件下,控股股东掌握较多的投票权能够实现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和监督作用(Rydqvist,1992)。控股股东利用不对称股权结构所产生的投票权杠杆效应是有利的,因为对厌恶风险的投资者来说持有大量的现金流权是有成本的;同时,直接持有更多的股票也会降低股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股东如果需要更多现金的时候,变现股票也是需要成本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对称股权结构使得控股股东的投票权大于现金流权,使得他们可以较少的成本监督经理人。
2.不对称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侵占效应。早期就有学者(如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控股股东等内部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控股股东承担了所有的监督成本,而中小股东则搭便车分享了控股股东通过实施监督增加的公司价值;同时,控股股东通过监督获得的收益又是边际递减的,而他们通过利益侵占获得的收益却是边际递增的(Bennedsen和 Wolfenzon,2000;Venky、Kathy和Daniel,2008)。因此,控股股东有动机转移公司资源或采取自利行为来影响公司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控股股东持有的现金流权越多,控股股东利用“隧道”行为转移或侵占的收益就越少,因此他们不会投入过多的现金流;如果控股股东拥有较少的投票权时,那么就得争取其他股东的支持,为了尽可能多地侵占收益,控股股东就必须拥有较多的投票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对称的股权结构安排把投票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开来,这实际上是控股股东通过权衡利弊来选择是监督经理人还是侵占其他中小股东利益。不对称股权结构放大了投票权的杠杆效应,使得控股股东可以较低的成本监督经理人,但也加剧了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Bennedsen和Nielsen,2006)。但是,实行“一股一票”制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不受控股股东侵占的同时,也会留给经理人更多的权力和攫取私有收益的空间(Burkart和Lee,2007)。因此,有必要仔细考量不对称股权结构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以明确不对称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的总体影响,这正是今后相关实证研究应该关注的一个方向。
四、不对称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与投资者法律保护
控股股东作为主要的监督者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能否在不对称股权结构下获得更多的控制权收益呢?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制度环境、投资者法律保护结合在一起,下文将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和投资者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展开述评,进一步明晰法律保护变量对控股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影响。
1.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学者们在研究不对称股权结构时总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不对称股权结构能给控股股东带来控制权私有收益吗?很多学者对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普遍认为,控股股东的优先投票权股能够获得正的溢价收益(Cox和Roden,2002),但是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因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样本和方法而异。
有学者从控股股东的大宗股权交易入手分析了控制权私有收益情况。早在1989年,Barclay和Holderness以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1978~1982年63起大宗股票交易为样本,分析了成交溢价与大宗股权交易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宗股权交易总是以很高的溢价成交,平均收益高达20%,这就说明拥有控制权的公司大股东可以在大宗交易中获得私有收益。而Megginson(1990)针对英国市场股票交易的分析表明,控股股东持有的优先投票权股的平均溢价比有限投票权股高13.3%。还有学者采用跨国数据来研究控制权私有收益问题。Dyck和Zingales(2004)利用1990~2000年39个国家393起控股股东大宗股权交易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控制权平均收益为14%。
1.秋季深翻土地。在秋季耙茬可将冬蛹露出翻出地表,在冬季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成虫的羽化率被极大降低。
另外还有学者对转型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情况进行了研究,但是相关研究不是很多。例如,Trojanowski(2003)以1996~2000年波兰证券市场发生的53起大宗股权交易为样本分析了控制权私有收益问题。Nenova(2003)采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18个国家1997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公司控制权平均收益相差很大,溢价收益从-3%到48%不等。蔡志杰、杜巨澜和芮萌(2008)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研究表明,我国存在正的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控制股份的交易价格要比非控制股份的交易价格平均高出14%。
2.控制权私有收益和投资者法律保护。控股股东利用不对称股权结构获得的私有收益比中小股东多,那么,这种控制权私有收益是否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呢?进一步地,这种利用不对称股权结构所获得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是否侵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呢?法律、政治和规制体系在约束经理人的挥霍行为方面并不是十分有效,而各种公司治理机制也不同程度地依赖法律做出规定或付诸实施(Jensen,1993)。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投资者法律保护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影响。一般来说,在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治理结构较为完善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较低,这可能就是法律制度因素限制了控制权私有收益幅度。如果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能产生较大的私有收益,那么就会增强控股股东的侵占动机,而执法效率较低、投资者保护机制缺失,则会进一步放大这种私有收益和侵占动机(Bebchuk、Kraakman和Triantis,2000)。Nenova(2003)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控股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相异,法律执行情况较好和投资者法律保护指数得分较高的国家控股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较低。而Dyck和Zingales(2004)针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国际比较研究也表明,较高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较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较高的执法效率均与控制权私有收益负相关。既然法律对中小股东的高水平保护有助于减少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那么在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就能够获得较多的私有收益;同时在不对称股权结构下的投票权与公司价值负相关的条件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有一部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是通过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获得的。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控股股东、投资者法律保护和证券市场发展的关系。Shleifer和Wolfenzon(2002)研究发现,在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上市公司市场价值较高,股东得到的股利分配较多,控股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较低,因此它们证券市场的总体发展状况良好。他们俩的这项研究从宏观层面揭示了投资者法律保护、公司治理与证券市场发展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相关研究大多认同投资者法律保护在制约控股股东侵占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没有哪一种单一的内部治理机制可以有效解决控股股东侵占问题,因此,较为合理可行的方案是整合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尤其是通过有效整合外部法律保护和公司内部治理,利用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互动产生的合力来限制不对称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侵占行为,并且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不同法律保护水平下的不对称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已有的股权集中效应研究主要探讨了股权集中引致的控股股东监督效应和侵占效应问题。自Claessens等(2002)利用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控股股东的投票权和现金流权及两者的分离程度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以来,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实证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和观点。由于不同国家在法律渊源、法律体系以及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学者利用跨国数据来研究不对称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基于此,下文将对跨国层面的不对称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进行述评。这种安排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领域实证研究的总体情况,并且能够从技术方法和经济逻辑两个方面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为今后研究找到方向。下文将根据相关实证研究的先后次序和逐步完善过程这一线索展开讨论,从而厘清实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法。
Claessens等(2002)率先实证分析了不对称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他们采用托宾Q值来衡量公司价值,以投票权、现金流权以及两者的分离程度为解释变量,并且还设置了公司特征等一些控制变量,然后采用OLS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和公司价值正相关,而不对称股权结构所产生的投票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与公司价值负相关。Claessens等(2002)认为上述两个结论正好可分别用于解释控股股东的监督效应和侵占效应。但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Claessens等(2002)采用东亚及东南亚八个国家或地区(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和法律体系大相径庭,因此,他们的研究可能存在变量遗漏问题,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法律保护可能会对不对称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La Porta等(2002)利用27个国家的371家公司1995~1997年的数据,以托宾Q值来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公司价值,并引入投资者法律保护变量,进一步考察了投票权、现金流权和法律保护等解释变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投资者法律保护指数和公司价值正相关,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对公司价值产生正向影响,从而进一步佐证了Claessens等(2002)的研究结论。随后,Lins(2003)利用18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④1 433家公司的数据,分别以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和公司价值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然后采用OLS和2SLS检验了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投票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其对公司价值产生的负向影响就越显著。但是与以往相关研究不同,Lins(2003)没有发现现金流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正相关性。此外,Lins(2003)还研究发现法律制度因素能够减弱投票权以及两权分离程度对公司价值的负向影响。
Cronqvist和Nilsson(2003)利用瑞典上市公司1991~1997年的面板数据,以公司价值为被解释变量,以投票权和现金流权为解释变量,并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行业特征等因素之后,检验了控股股东投票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他们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了因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偏误,结果发现,虽然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与公司价值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控股股东的投票权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引入现金流权作为解释变量以后,投票权和现金流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都变得不显著了。就整体而言,家族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加倾向于采用不对称股权结构来获取私有收益(Cronqvist和Nilsson,2003)。有些学者没有使用公司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不对称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Maury和Pajuste(2004)采用136家芬兰公司1993~2000年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控股股东的投票权与现金流权比率与公司价值负相关,但现金流权对公司价值没有显著的影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美国公司为样本,针对二元股权结构、金字塔形层级控股结构等不同的分离机制,用虚拟变量表示不对称股权结构的研究,采用投票权和现金流权之差来衡量两者的分离程度,得出了“二元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负相关,金字塔形层级控股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不显著”的结论;而采用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比率来衡量两者的分离程度,则得出了金字塔形层级控股结构会提高公司价值的结论(Villalonga和Amit,2006)。Bennedsen和Nielsen(2006)采用西欧14个国家的大样本数据分析了不对称股权结构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公司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现金流权、投票权、法律保护指数为解释变量来构建模型,并在所有的OLS回归中设置了行业和国家虚拟变量,最后得出了以下结论:不对称股权结构的虚拟变量和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而最大股东的投票权和现金流权之差对公司价值产生较弱的负向影响;在投资者受法律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其对公司价值所造成的损失就越大。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若干问题,从中不难总结出以下几条有益的经验。首先,计量模型的估计对不对称股权结构的变量选择是非常敏感的。例如,有些学者采用虚拟变量来表示不对称股权结构,有些学者则采用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差或者比率来表示不对称股权结构,而利用不同代理变量所得到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次,控制变量的选择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在部分文献中,国家这个虚拟变量和投资者受法律保护水平这个解释变量会对模型的估计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再者,就是没有充分重视股权结构的内生性问题。实际上,股权结构和公司价值相互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的设计也会受到公司价值的影响,因此,股权结构并不一定是外生的,股权结构和公司价值之间可能存在逆向的因果关系。部分学者尝试利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股权结构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在第一阶段的回归中,公司价值随现金流权增加而递增,随投票权增加而递减;然后运用工具变量法得到了与OLS回归结果相同的结论,但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Gompers等,2010),这表明投票权集中对公司价值没有显著的影响。最后,现有研究大多没有做稳健性检验。Cronqvist等(2003)用资产收益率代替公司价值进行稳健性估计,结果表明不对称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显著相关;但是Maury和Pajustel(2004)以及Bennedsen和Nielsen(2006)的稳健性检验显示,不对称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并不显著相关。由此可见,稳健性检验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但迄今没有分析其中的原因。针对稳健性检验缺失或结论截然相反的问题,未来研究应该对股权结构的内生性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六、总结与研究展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控股股东造成的不对称股权结构使得控股股东能够利用少量的现金流实现对公司的控制,通过行使投票权降低中小股东搭便车造成的成本从而获得监督收益,又能够有效防范敌意收购等威胁。同时,不对称股权结构也会提升控股股东的侵占动机,从而可能对公司价值产生负向影响。投资者法律保护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有效抑制控股股东的侵占动机,并协调股东之间的利益,但其作用也要受股权结构和股东—经理人关系的制约。
实际上,相关实证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尽管部分研究表明,不对称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具有负向影响,但是却能够显著增加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即二元股权结构或金字塔形层级控股结构公司的大宗股权交易往往存在溢价现象,而且平均来说远高于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未来需要关注不对称股权结构影响的比较研究,即不对称股权结构为控股股东创造的价值和对中小股东减少的价值哪一个更大;两相比较之后,公司长期价值是否会增加或减少,如果控股股东获得的价值大于中小股东减少的价值,但公司长期价值为正的话,那么,不对称股权结构就并不一定是一种无效的安排,而可能是一种次优安排。而且,如果控股股东只是采用了不对称股权结构的治理方式,并没有采取其他的违法“隧道”行为的话,就不能说控股股东所获得的私有收益就是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
其次,由于受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影响,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矛盾和差异,如有的研究显示不对称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产生负向影响,但也有研究表明不对称股权结构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有些实证研究把投资者法律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但又遗漏另外一些影响因素。大部分跨国实证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样本,忽略了法律制度、政府规制等外部环境变量的影响,从而导致回归估计有偏和不一。而且,相关研究大多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背景下进行的,由于不同国家在制度、文化等方面相异,即使是一些跨国层面的分析也很难对特定国家的改革提供有效的参考。因此,既有研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澄清,尤其是将研究视角更多地向一国的长期实践情况集中,利用一个国家内部时间序列的证据来研究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对称股权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它们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影响。
最后,既有研究往往忽视了所有者兼任经理的情况。在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民营上市公司往往都是由控股股东直接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等管理职位,即所谓的所有者—经理人的管理控制方式。针对这种控股股东直接担任经理的情况,不对称股权结构、法律保护作用以及和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仍较为缺乏;不但实证研究缺少此方面的分析,理论研究也忽视了控股股东直接管理上市公司的情况。在所有者兼任经理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在实施利益侵占的时候就不需要与经理人合谋或分配收益;同时,既然经理人和控股股东是同一个人的话,也就不存在控股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道德风险问题,那么这种背景下不对称股权结构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投资者法律保护是否产生有效地制约侵占效用呢?未来研究须关注此类问题,以厘清不对称股权结构的作用和经济影响。
注释:
①不对称股权结构(disproportional ownership structure)是指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相分离的股权结构。详情参见本文参考文献[3]。
②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的公司丑闻,例如美国的Enron和WorldCom、日本的Sumitomo、韩国的Lernout&Hauspie、俄罗斯的Gazprom、意大利的帕拉马特、澳大利亚的HIH等等,在中国则有银广厦、闽福发、猴王股份、古井贡、五粮液等。
③有关不对称股权结构决定因素的文献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我们将简单做一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Smart S B and Zutter C J.Control as a motivation for underpricing:A comparison of dual and single-class IPO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9(1):85-110。
④这18个国家或地区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捷克、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以色列、马来西亚、秘鲁、菲律宾、葡萄牙、新加坡、南非、韩国、斯里兰卡、中国台湾、泰国和土耳其。
[1]Adams R and Ferreira D.One share,one vote:The empirical evidence[J].Review of Finance,2008,12(1):51-91.
[2]Burkart M,et al.Why higher takeover premia protect minority shareholder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6(1):172-204.
[3]Burkart M and Lee S.The one share,one vote debate: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R].ECGI-Finance Working Paper No.176,2007.
[4]Burkart M and Panunzi F.Agency conflicts,ownership concentration,and legal shareholder protec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06,15(1):1-31.
[5]Claessens S,et al.Disentangling the incentive and entrenchment effects of large shareholdings[J].Journal of Finance,2002,57(6):2 741-2 771.
[6]Easterbrook F H and Fischel D R.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7]Gompers P A,et al.Extreme governance:An analysis of dual class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0,23(3):1 051-1 088.
[8]Holderness C G.The myth of diffuse owne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9,22(4):1 377-1 408.
[9]Kyle A S.Continuous auctions and insider trading[J].Econometrica,1985,53(6):1 315-1 335.
[10]La Porta R,et al.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1999,54(2):471-517.
[11]La Porta R,et al.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J].Journal of Finance,2002,58(3):1 147-1 170.
[12]Lins K V.Equity ownership and firm value in emerging markets[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3,38(1):159-184.
[13]Marianne B and Sendhil M.Enjoying the quiet life?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rial preferenc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111(5):1 043-1 075.
[14]McConnell J J and Servaes H.Equity ownership and the two faces of debt[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5,9(1):131-157.
[15]Niclas H,et al.Family ownership,dual-class shares,and risk management[J].Global Finance Journal,2006,16(3):283-301.
[16]Shleifer A and Vishny R B.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3):461-488.
[17]Villalonga B and Amit R.Benefits and costs of control-enhancing mechanisms in U.S.family firms[R].Working paper,HBS and The Wharton School,2006.
[18]Yermack D.Flights of fancy:Corporate jets,CEO perquisites,and inferior shareholder retur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0(1):21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