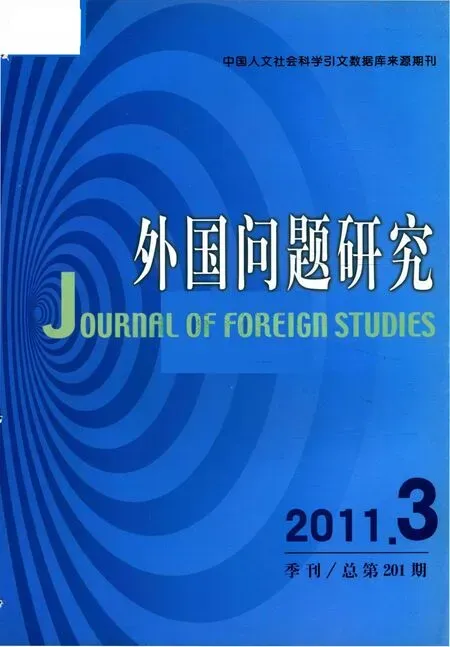《国性爷合战》的创作依据与主题思想
2011-03-20张博
张博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天津300071)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是江户中前期首屈一指的净琉璃与歌舞伎的剧作家,论他对日本近世文学乃至日本国民精神的影响则绝不亚于威廉·莎士比亚对于英国的影响。时代净琉璃《国性爷合战》是近松晚年艺术成熟期的作品,取材于明末清初中国的历史,虚构了郑成功渡海回国光复明朝的故事。1715年11月它在大坂的竹本座初演,直到1717年2月为止,连演了17个月(含闰月),是近松时代物中最受欢迎的作品。近松其后又推出了两部续作,《国性爷后日合战》和《唐船话今国性爷》即《国性爷三部曲》。在整个江户时代,《国性爷合战》作为净琉璃上演过70多回,作为歌舞伎演出过60余次。可以说《国性爷合战》中宣传的“中国观”对“锁国”期日本人之影响是巨大的。
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对《国性爷三部曲》的探讨仅局限于第一部的《国性爷合战》,并未将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分析近松的创作过程,这样对《国性爷合战》主题思想的把握就可能有所欠缺。而且《国性爷合战》译介至我国时,正值上世纪60年代非常时期,极“左”思潮泛滥也影响到了对《国性爷合战》主题思想的评价。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王燕的回忆:“60年代后期,在中学读书时曾被组织学习过一篇批判《国姓爷大战南京城》的文章,对文章中以犀利的文革式语言指证剧作美化侵略战争,并且早在二百多年以前就开始为本世纪四十年代制造南京大屠杀进行舆论准备的说法至今仍有较深的印象。”[1]改革开放之后,近松研究基本上也承袭了以上的批判基调,大抵认为《国性爷合战》中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侵华思想。
一、学界对《国性爷合战》的批判
我国学界对《国性爷合战》主题的批判,总结起来有三个要点:第一,近松的剧作是对历史的歪曲,剧中一些我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史实都遭到了180度的逆转。这不但会给观众很大的心理冲击,也伤害了研究者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这部历史剧虽然取材于我国的史实,但是一开始就把史实抛在九霄云外,把你带到一个虚构的传奇世界。多么像《天方夜谭》中出现的故事情节呀!……这个剧在人物的塑造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吴三桂、郑芝龙之流卖国投敌的佞臣贼子,说成是抗清扶明的最大忠臣。”[2]54-55“近松门左卫门却把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写成了日本武士。”[3]
第二,先学们的研究都引用了《国性爷合战》中“千里竹之场”的情节作为证明该剧中包含“侵华意识”的证据。尤其吸引批判者眼光的是和藤内(国性爷)用从伊势神宫请来的神符,在中国制服猛虎,又招降李蹈天(李自成)的士兵给他们改换日本服装,起日本名字的描述。据此证明和藤内的战争名为光复明朝,实际上却是侵略中国。
第三,以往的观点基本上都认为“历史的歪曲”与“侵华意识”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即近松是基于鼓动“大陆侵略”的想法创作《国性爷合战》并歪曲史实的。“在丰臣秀吉的军队侵略中国的迷梦破灭100多年后,许多日本人——当然包括在野的文化人及受其影响的庶民百姓,对于中国仍暗怀觊觎之心,祸华之心不死,有时还变得炽热如火,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侵华难以付诸行动,于是就以文艺的形式加以表达和发泄。”[4]
本文通过考察近松门左卫门在“锁国”条件下,是如何获得海外情报,进行再加工创作的情况,结合日本江户时代中前期的社会背景,对《国性爷三部曲》的主题思想进行再探讨。
二、《国性爷合战》的创作依据
《国性爷合战》本来应写作《国姓爷合战》,以“性”代“姓”的近松究竟是笔误还是另有考虑今已无稽可考。故事的主角和藤内(即郑成功,和藤内意为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国人之意)是明臣郑芝龙(剧中称一官)与日妇人所生之子。剧中思宗烈皇帝是崇祯帝,李蹈天即李自成,鞑靼代指的是后金,和藤内母为田川氏(中国文献称翁氏),甘辉是郑成功手下的将领历史中确有其人,吴三桂也是本名登场。
本剧初段中李蹈天逼思宗烈皇帝自尽的故事,大抵符合1644年北京动乱的情况。而和藤内的母亲在狮子城自杀,大概取材于田川氏在清军破福建安平镇时自缢身亡的故事。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三记顺治四年(1647)二月,清将“韩代奉贝勒世子命,统满、汉骑步突至安平”,郑成功母翁氏手持剑不肯去,“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剑割肚而死”①郑成功母去世时间是有争议的。郑克塽著《郑氏附葬祖父墓志》云:“翁曾祖母生于壬寅年八月十八日未时,卒于丙戌年(1646)十一月三十日巳时,享年四十有五。”与江日升的记录有三个月的差距。。和藤内、吴三桂、甘辉攻入南京城也与1659年郑成功与张煌言联军北伐,包围南京的史实相合。
综上所述,纵观《国性爷合战》,历史大脉络还是正确的。而“悖谬”的集中之处还是吴三桂、郑芝龙二人的忠奸问题。能解释的理由无外两个,一是近松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不够准确;二是近松出于某种目的故意美化了吴三桂和郑芝龙。
那么身处“锁国”的日本的庶民近松是如何获得国姓爷故事的历史材料的呢?其实在《国性爷合战》以前,以“国姓爷”为主角的净琉璃已经有了锦文流(?-1720)的《国仙野手柄日记》。该剧于元禄十四年(1701)春,由山本飞騨掾座上演。有很多迹象表明,近松的《国性爷合战》的创作借鉴了《国仙野手柄日记》。比如明皇女从日本搬救兵回国讨贼,这样的虚构情节两剧中均有,《国性爷合战》第五段中吴三桂用的竹筒计在《国仙野手柄日记》也出现过。然而仅依靠从《国仙野手柄日记》中获取的资料,是无法完成《国性爷合战》的,因为前者中并无崇祯帝、郑芝龙、吴三桂等人的情况。
根据野间光辰的论文《关于〈国姓爷御前军谈〉与〈国性爷合战〉的原据》[5]和《〈明清斗记〉与近松的国姓爷物》[6]中的研究,宽文元年(1661)成书的通俗史传小说《明清斗记》应该是《国仙野手柄日记》之外的另一创作资料来源。《明清斗记》叙述了明末清初的历史,集中描绘了郑成功在中国南部的反清战争。但是《明清斗记》中既有吴三桂在山海关一役中投降了后金,又有郑芝龙被高官厚禄收买的记录。
那么依据以上的分析是不是就可以证实近松是故意美化了郑芝龙和吴三桂的呢?郑芝龙我们先放在一边,《明清斗记》只记叙到郑成功退守台湾,在那之后还有一个关于吴三桂的重要史实:历史上的吴三桂声称自己蒙周、田二皇亲的托孤,一直隐忍不发等待崇祯遗子长大成人。1673年他因受康熙撤藩政策打击,带头掀起“三藩之乱”。吴为了使反叛战争正当化,就标榜自己是明朝的忠臣,在其广为传布的《讨清檄文》中曾为当初的投降辩解说:“本镇刺心呕血,追悔莫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忍隐,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警惕者,盖三十年矣!”[7]52而这个情况与《国性爷合战》的故事却是吻合的。
吴三桂起兵不久,台湾的郑经也与吴相互配合。1674年3月郑经命陈永华留守,自率侍卫冯锡范、兵官陈绳武、吏官洪磊等西渡,进驻厦门,开始举兵北伐。郑经亦发檄文,大书吴三桂所不敢深谈的华夷之辨:“中国之视夷狄,犹峨冠之视残履,故资冠于履,则莫不腕(惋)忿,沦夏于夷,则孰不感媿。”[7]53一方面郑经起兵的故事同样进入了《国性爷合战》的续集《国性爷后日合战》中。另一方面,有唐船传闻集《华夷变态》中的风说书为证,至迟在延宝二年(1674)吴郑檄文以及他们起兵的消息就已传入日本。
近松如果能知悉吴郑二檄以及吴郑反清战事,那么他即便通过《明清斗记》知道吴在山海关的投降,所谓“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材需待七年期”,近松转变态度认为吴三桂是与郑成功一样的明朝不二忠臣,也是极有可能的。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延宝二年幕府官僚上层才能看到的公文资料,当时年仅21岁的庶民近松是否有机会了解其内容呢?
三、近松海外消息的获取
首先近松大概无法看到作为最后上报幕府的唐船传闻,其次我们知道在长崎的外国商人与日本人的交往受到严格限制,那么近松有没有可能从传闻报告的制作者和经手人处得知其内容呢?
前文已略提到过的《华夷变态》是一本长崎外商所带来的海外消息的汇编集。江户幕府于庆长八年(1603),任命旗本小笠原一庵(生没年不详)为初代长崎奉行,全权负责长崎的外交、通商、司法事务。长崎奉行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情报收集工作,为此小笠原聘当时留居长崎的明人冯六为唐通事役,搜集来往客商带来的消息。以后历代长崎奉行皆照此惯例办理,逢有中国来的,或荷兰来的商船入港,则必登船听取海外的消息,记录誊清,上呈幕府。
当时外国人入港先要上报国籍、船员名单,核对信牌,然后再由风说役①负责听取船员讲述海外传闻的幕府下层官员。听取海外新闻。用二、三天的时间将听取到的内容整理成报告(风说书),派飞脚把它从长崎送到江户。到江户的风说书,经过驻留江户的长崎奉行之手,上呈幕府中掌握实权的老中、若年寄、侧用人等,如有必要甚至会给将军过目。在这中间充当秘书工作,负责实际阅读、翻译的人即林春胜(1618-1680)这类儒学家。《明清斗记》的作者虽未必见过这些“风说书”,但按该书序文中的说法,他当时对海洋彼岸的情势是有所耳闻的,所谓“闻唐土国姓爷战事,不堪义愤。”[8]那么近松是不是也和《明清斗记》的作者一样是听到了长崎商人的海外传闻才以此为据创作了《国性爷三部曲》的呢?
《华夷变态》共三十五卷,书中收入了正保元年(1644)到享保二年(1717)74年间商船带来的传闻。细查该书就能发现有关李自成、吴三桂、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的记录都甚为详细。如《国性爷合战》和《明清斗记》均提到过的,李自成起兵、崇祯自杀、郑芝龙化名一官等事,在《华夷变态》卷一中均有记录。
郑经的反清活动是《国性爷后日合战》的主要内容,但在《明清斗记》中是没有涉及的,而在《华夷变态》中却记载得很清楚。早在吴郑二檄传至日本以前,万治元年(1658)就有一则风闻记录提到郑经:“朱成功三十八岁②郑成功死时应为三十九岁。病死,其子名郑经,字锦舍,继父业居东宁。”③东守应为东都之误。[7]46《国性爷后日合战》中也以“郑锦舍”来称呼和藤内之子,这个信息不可能从《明清斗记》中得到。
同年七月郑经遣使蔡政向长崎奉行讨还郑泰在日本寄存的货银,蔡政所携郑经来书亦编入《华夷变态》。郑经在该信中叙述自己继承父志,反清复明,追回郑泰银为的是“资恢勦逆虏之资”[7]46。这些都和《国性爷后日合战》的情节有所对应:在第三段中曾描述国性爷军资匮乏,而第四段中郑锦舍梦中在伊势神宫得到了能流出金银的宝瓶,这宝瓶暗指的应该就是郑泰的存银。
经过以上的推理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近松起码是知道一部分《华夷变态》中传闻书所载的内容的。那么这些情报是如何泄露给近松的呢?
我们知道,因为政令限制,能直接见到中国船员,亲耳听到中国故事的人,大抵仅限于第一手风说书的制作相关人。查《华夷变态》现所收的风说书上记载的经办官员姓名,多见如“唐姓林”、“唐姓欧阳”、“唐姓陈”者大概是明遗民的后裔;又见如“柳屋治郎左卫门”、“阳三郎又卫门”者明显是没有姓氏的庶民。后者可能本是日人,因长期从事与中国的贸易,通晓了汉语。至此可以间接证实,至少有一小部分长崎的商贾市民是有可能知道郑经反清战争和郑泰存银纠纷的。如果近松能获得他们所掌握的消息,那么就解释了在看不到构成了《华夷变态》的风说书的条件下,近松是如何创作完成《国性爷后日合战》的了。
为了进一步证实以上之假说,我们可以再分析第三部国性爷剧《唐船话今国性爷》的资料来源。享保七年(1722)近松推出了“国性爷”系列的又一部续作《唐船话今国性爷》,一月由大坂竹本座上演。研究界一般认为这部作品是取材于1721年4月19日台湾爆发的农民起义“朱一贵起义”。近松剧中的“今国性爷”即农民起义领袖朱一贵。
关于朱一贵起义,日本史料最早见于享保八年(1723)四月出版的《台湾军谈》。中国方面按蓝鼎元的《平台纪略》自序中说,应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二月的《靖台实录》[9]。近松作品在二史料之前,不可能是参考以上书籍进行的创作。
无独有偶,尾张藩士天野信景(1663-1733)也在官方史料出版之前就获知了朱一贵起义。天野信景从元禄十年(1697)到享保十八年(1733)所写的随笔《盐尻》中,于1722年提到朱一贵的起义。《盐尻》的原稿相当散漫并不成书,搜集、校订、出版时已经是天明二年(1782)。近松与天野素不相识,所以读《盐尻》的草稿或是听天野提及台湾起义事都不太可能。
然而《唐船话今国性爷》与《盐尻》的内容却有许多类似之处:第一,两书都提到了朱一贵身边105岁的老军师吴二用。第二,《唐船话今国性爷》中从南京领三万援军赶来福建的将领叫苗景龙,其人其事在《盐尻》中也出现了。第三,朱一贵称顺成王,均见于二书。第四,近松以朱一贵为洪武皇帝的子孙,这与《盐尻》的说法也一致。
《唐船话今国性爷》与《盐尻》诸多关联说明两作之前一定还有一个共同的消息源。而且这个消息经过总结,写成风说书编入了《华夷变态》的后续《崎港商说》卷三,享保六年(1721)有关朱一贵起义传闻的记录。近松、天野二人虽然不可能直接看到幕府的公文报告,但他们却可以获得从担任风说役一类官职的人处泄露而在长崎部分庶民中流传的海外新闻,至此可以基本确认了。
在弄清了近松是如何获得海外情报之后,我们不妨回到郑芝龙、吴三桂由叛臣变忠臣的问题上来。郑芝龙投降清廷以及郑成功被赐朱姓(国姓),郑成功母自杀之事,均收录于《华夷变态》卷一正保三年(1646)收到的一则风说书。这份材料是十月十七日到的江户,十月四日由长崎发出,叙述的是当年八月下旬清人入闽之事。近松在《国性爷合战》中安排一官(郑芝龙)奋战不敌被鞑靼王掳为人质,又以他逼迫和藤内投降,在《国性爷后日合战》中让一官假意皈依鞑靼人的邪教为儿子筹措军资。可见参考了《明清斗记》的近松并非不知郑芝龙降清和清政府以郑芝龙为质迫郑成功投降等事实,他也的确改动了郑芝龙的汉奸属性,对他进行了美化。
至于吴三桂,《华夷变态》中关于吴三桂的记录一直是十分正面的。江户时期长崎的对华贸易大致以康熙二十三年(1684)“展海令”分为两个阶段。17世纪前半到18世纪前半,通航至长崎的中国船遍布大陆沿海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广阔区域,其中的主流乃是台湾郑氏控制的“五商”。在清廷忙于大陆内部征服时,郑氏已掌握了中国大半的海上贸易,除了郑氏本身拥有的东、西洋船队之外,其他商船亦需获得郑氏政权的许可才得以通行。所以这段时间到长崎的中国商船,其背后或多或少都有郑氏政权的影子。因此三藩之乱时期,在长崎进行贸易的客商论及吴三桂等人的起兵一律以“义军”、“义举”称之。谈及清朝和三藩的胜负情势则都是对恢复大明充满信心,比如说“大清过半已复大明”[7]69,“盖广东之推量,吴三桂之胜利可得之也”[7]75等等。正因为近松整个《国性爷三部曲》的创作都有长崎传闻的素材影响,吴三桂才被塑造为忠臣。在吴三桂的人物塑造上,倒很难说近松是为了某种目的故意对他进行了美化。
四、《国性爷合战》创作目的与主题
近松为了维持竹本座的经营,决心写作一部叫座的剧本,这就是《国性爷合战》。净琉璃因其大众文艺的性质,决定了作者在写作时一般会把预设的消费者(庶民)的趣味与好恶,置于本人审美、思想之上。我们在评论通俗文学的主题时,也应该意识到其与文人文学、历史著作的区别,避免对文学意象的夸大解读。和二战中为侵略需要,写作“大陆开拓文学”的御用文人不同,近松的文学创作是自由的、商业的。他的文学姿态,与其说是宣传性的,毋宁讲是迎合性的。
《国性爷合战》搬上舞台的正德初年,江户时代的日本正处于其庶民文化的巅峰期——元禄时代的余韵中。锁国温室内的日本此时“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充盈着太平气象。”[10]一个有日本血统的“国性爷”回归大海彼岸的祖国,光复中华王朝正统的战争故事,对于此时的观众来说,应该是既新奇又刺激的。为了博取更多观众,近松还参考了当时的畅销读物、前代受欢迎的净琉璃之内容,设计出《国性爷三部曲》中的种种奇妙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情节。例如《国性爷合战》第一段用宫女们的花战来反映明皇昏庸,根据日本学者的考证,这其实是借用了当时歌舞伎评判书《野郎虫》的内容[11]232。《国性爷后日合战》第二段中甘辉保护永历帝逃命,途中宿于叔父陈芝豹家,叔母等人商量杀羊准备接风宴的声音让甘辉误会叔母一家对自己不利,结果把叔母等人误杀了,这是化用了当时已传入日本的《三国演义》中曹操杀吕伯奢的情节[11]236。
在先行研究中引起许多批判的《国性爷合战》“千里竹之场”,和藤内拿出伊势神符来降服猛虎,设计这个情节的原因,大概与当时正风行的伊势参宫热和“天降神符”的流言有关。《国性爷三部曲》还在上演的享保三年(1718),伊势山田奉行向幕府汇报伊势神宫参宫求符的人数,这一年从正月到四月五日就有427 500人[12]。而当时全日本的人口也不过1 800万左右,可见去伊势神宫参宫求符的流行程度。而且自庆安三年(1650)开始,60年左右日本就会爆发因“天降神符”传说而引起的伊势神宫参宫潮[12],《国性爷三部曲》创作时期和第二次参宫潮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这样看来和藤内用伊势神符降服猛虎,象征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个论断还是有待商榷的。至于和藤内收复李蹈天的士兵,给他们改服易名,又嬉笑嘲弄了一番,虽然不免有国粹主义的气味,但这些滑稽表演的确是化用了古净琉璃《箱根山合战》的情节。而且这种荒唐不羁又性格倔强、武艺超群的英雄形象,正是当时江户最后欢迎的歌舞伎,市川団十郎(1660-1704)之荒事艺中主人公的典型特征①歌舞伎演技形式之一。以《暂》、《矢の恨》的主人公,《曽我の対面》中的五郎,《菅原伝授手習鑑》中的梅王为代表,是充满天真稚气,又力大无穷,武艺精湛的人物。江户时代前期流行的金平净琉璃中,主人公坂田金平,就是歌舞伎荒事艺与净琉璃的结合。近松在塑造国性爷的英雄形象时,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我们不能否认《国性爷合战》乃至整个《国性爷三部曲》中均有一些国粹主义的成分,其“国家意识强烈,不时地礼赞日本。在刺激观众对唐土未知世界的好奇心的同时,又将日本置于高于诸国的位置。”[13]13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就此断言《国性爷合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先声”,“近松精心设计的这部历史剧是想通过和藤内在我国施展日本的神威,把我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2]57上述思想成分的确迎合了庶民们庸俗、浅薄的“国粹心”,但是就此断言其中必有侵华野心,则略显得武断。
如果说《国性爷合战》体现了近松所代表的一部分日本人的“华夷意识”,倒可以说是恰当的。由于“锁国”体制的制约,日本人对海外的了解途径是单一的,情报是匮乏的。比如《华夷变态》中的海外传闻报告,康熙攻取台湾之前的风说无不是拥明反清,以明为中华正统,以清为夷狄的。这种观点在日本国内的流布,也许就是近松的“日本优越”的理论来源。但是从另一面看来,作品也表现了以中华(大明)为正统,以恢复中华的战争为义战这种文化上的“中华认同”。
这正如林春胜在《华夷变态》序文中所表达的感情:“顷间(闻)吴郑檄各省,有恢复之举。其胜败不可知焉。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7]1又如安东省庵给朱舜水的赠诗:“鹏程好去图恢复,舟楫今乘万里风。”[14]近松在《国性爷合战》末尾写道:“祝永历皇帝御代万岁。祝大日本君之代的国土安全。凭赖神德、武德、圣德。此三德遍及全国,必使国家繁昌,人民富足,五谷丰登。祈祷年年如是。”[13]291这难道不是表达了向往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愿望吗?和藤内虽然穿着日本衣冠,讲着日本语,怀中揣着从伊势神宫请来的神符,他的战斗却是为了光复大明的“中华正统”。在批判《国姓爷合战》的狭隘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同时,我们也不宜忽略这一点。
[1]王燕.不该发生的失误——解读《国姓爷合战》[J].铁道师院学报,1988(12):55.
[2]李树果.对日本古典历史剧《国姓爷大战南京城》的评价——评近松门左卫门对历史的歪曲[J].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1).
[3]王向远.江户时代日本民间人文学者的侵华迷梦——以近松门左卫门、佐藤信渊、吉田松阴为例[J].重庆大学学报,2008(4):121.
[4]李群.武士道与文化侵略——探析近松门左卫门文学中的侵华意识[J].东疆学刊,2005(10):29.
[5]野间光辰.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会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C].东京: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会,1934:73-89.
[6]野间光辰.『明清闘記』と近松の国性爺物[J].国语国文,1940(3):23-42.
[7]林春胜,林信笃.华夷变态[M].东京:东方书店,1981.
[8]鵜飼信之.明清闘記[M].京都:田中庄兵衛刊,1661:2.
[9]蓝鼎元.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M].台湾:大通书局,1988:82.
[10]諏訪春雄,日野竜夫.江戸文学と中国[M].东京:毎日新聞社,1977.
[11]神崎宣武.江戸の旅文化[M].东京:岩波書店,2004:5-6.
[12]藤谷俊雄.おかげまいりとええじゃないか[M].东京:岩波書店,1968:35.
[13]德富蘇峰,平泉澄.近世日本国民史元禄時代世相篇[M].东京:講談社,1982.
[14]安东省庵.省庵先生遗集[M].福岡:安東省庵顕彰会.1971:7.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