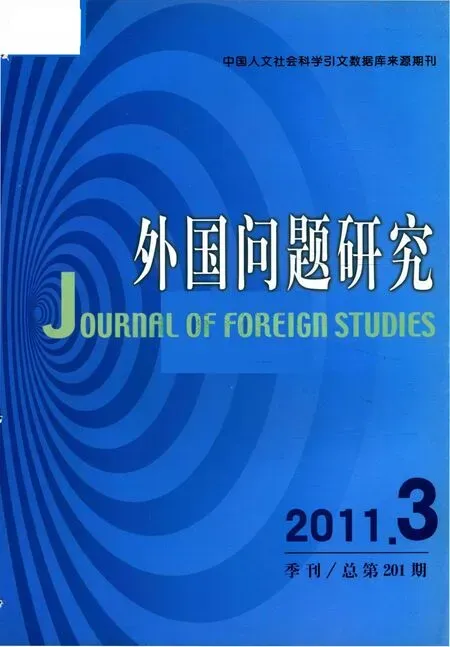《安逊环球航海记》与英国人的中国观
2011-03-20赵欣
赵欣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高句丽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38)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英国社会普遍流行着一股“中国热”。这股热潮的掀起一方面源于当时英国与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贸易关系,茶叶、瓷器、丝绸等中国商品被直接运抵英国海岸;另一方面是受近邻法国的影响。法国社会先期流行的“中国热”波及了英国。随着对中国物质文化实际接触频率的增加以及法国入华传教士汉学在英国的传播,英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和仰慕之情变得越来越强烈。中国文化和商品在英国受到了众人的追捧,“中国热”在英国日渐流行。英国王公贵族以拥有中国货为荣;文人学者以谈论中国、赞美中国为主调;平民百姓则挖空心思收集或仿制中国商品。这种风尚至18世纪中期达到了高潮,中国形象被定位成完美富庶的“乌托邦”。
1748年,根据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逊(George Anson)勋爵①乔治·安逊(1697-1762),英国海军上将,出生于斯特福德郡(Staffordshire)。父亲是威廉姆·安逊(William Anson)。安逊于1712年入伍后迅速升迁,1724年即被任命为小军舰的舰长。1737年任“百夫长”号(中方文献称其为“百总号”)舰长,开赴与西班牙海战的前线。1740年受命进攻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但后来却因风漂泊成环球航行。日记整理而成的《安逊环球航海记》(George Anson:A Vo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1740to1744.London)出版。负责整理此书者是随安逊出航的“百夫长”号(Centurion)的牧师瓦尔特(Richard Walter)。该著记述了“百夫长”号1740年从英国出发向西航行,绕地球一周后于1744年回到英国的整个过程。安逊一行于1742年冬到达中国沿海,并与中国官方就补给一事多次交涉。书中有关中国的记述占了较大篇幅,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左右。《安逊环球航海记》在“中国热”高潮时期出版,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当年就再版了6次,受到了欧洲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对《安逊环球航海记》中安逊等人的传奇经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执,导致此著长盛不衰,从1748年到1796年间共计再版了27次②据《18世纪作品在线》(According to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数据库统计。。再版频率之高在英国图书史上极其罕见。
《安逊环球航海记》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轰动,主要是因为安逊在此著中抨击和否定了中国文明,传递回了一个与英国原有的“乌托邦”式中国所完全不同的形象。安逊作为具有高级爵位和军衔的英国人,其身份和地位决定了该著的权威性;安逊此次航行又不同于商人、海盗式的单纯的急功近利的冒险行为,而是与中国官方和民间都进行了一年多的密切接触,这些客观情况增加了该著的可信度;此外,该著不是以传统的回忆录的方式记述,而是由实地考察时的日记整理而成的,因此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具体说来,安逊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抨击了中国文化:
一、否定中国科技的进步性。安逊记载说“无数事实表明,中国人在机械制造方面根本无法与欧洲人的灵巧性相提并论。事实上,他们主要的长处还是模仿。”[1]345他接着说中国人在精细、精确度等方面要求严格的制造业,例如钟表及火器等物,尽管能够模仿这些机器的外形却无法模仿其精细的制动部分;
二、否认中国艺术和文学的杰出性。“在绘画方面,尽管中国有许多有名望的画匠,却很少能成功地绘出人体的色彩或是大作品的组图。即使他们在花鸟方面的技法令人称道,但也归因于所绘的花鸟颜色的明艳而不是画匠的技能。而欧洲画家却能正确地使用光和影,绘画手法自如流畅。总之,多数中国作品都是生硬呆板和微不足道的,令人极其不悦。他们在艺术上的缺陷是由于中国人特殊的性情所致,在那里找不到伟大而有思想的人。”[1]345他随后又说中国人的迟钝和荒谬在文学作品中尽显无遗;
三、贬低汉字,否定中国历史的古老和实用性。安逊记载:“尽管几个朝代以来,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在使用字母,中国人对字母业已很熟悉,但他们迄今为止却仍然不使用字母,继续用那种粗俗而笨拙的武断的标记来表达词汇;他们的文字数量太多了,超出了人类的记忆范畴,他们就采用一种方法,使文字的书写变成一种艺术,需要大量的练习,所有人都是粗通一二。然则阅读其所写文字时,也是极其模糊和混乱的,因为这些所表意的标记和其所要表达的词汇之间的联系在书本上根本找不到,而只能靠代代之间口口相传。表意的繁复和不确定性在所难免。因此其过去的历史和发明是靠这些错综复杂的象征符号来记录的,已经屡次证实乃不明智之举,无数事实证明,这个国家的知识和所吹嘘的古老性是极其有问题的。”[1]345-346
四、否定中国政府管理的优越性,贬低中国军事防御体系。安逊开门见山地说,据传教士所载,中国政府规章制度完善,国内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但安逊与中国人的交往经历却完全推翻了这些记载,“因为我们见识到了地方官都腐败不堪,人们偷盗成性,他们的法庭也是诡计多端和贪污成风,这个国家的宪法也不例外。这种形式的政府首先没有为公众提供安全的防御外侮的保证,当然是一个最具缺陷的组织。至于这个人口众多、富有和广阔的国度,以其讲究的智慧和政策而徒有虚名,却被一小撮鞑靼人征服了一个时期。即使是现在,居民的懦弱,适合的军规的缺乏,不仅暴露在任何觊觎它的强国面前,也暴露在每个微不足道的入侵者的蹂躏之中。”[1]348瓦特还详细地将中国船只进行了分类描述,最后预言“百夫长”号一舰即可摧毁广东所有的海军设施[1]348。
回顾一下安逊航行中国的过程,可以发现安逊等人贬低中国的动因。据英方史料记载,1740年9月,身为上校的安逊奉命率领“百夫长”号进攻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出发时间正值英国与西班牙海战正酣之际。安逊途中因飓风和敌军的追击被迫绕行好望角,一行由7艘船组成的舰队被迫改成环球航行。船上条件极差,拥挤不堪,7艘船上载着一个团的海军,259名海军中以老、病、伤残者居多。吊床紧绑在大炮之间,食物短缺[2]476-477。船队经过好望角后只剩下3艘船,近2/3的船员死去,侥幸逃过了西班牙战舰的追捕[2]477。1741年4月只有安逊的“百夫长”号到达了菲律宾,船员死伤大半。由于船体漏水,英军选择了澳门作为补给地,于11月13日“百夫长”号开进了澳门港口。
可见,安逊到达中国沿海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而他选择停泊在中国沿海却是必然的,当时英国“中国热”的流行使英国人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怀疑,安逊自然会利用偶然的机遇来创造必然的结局。安逊也表达了他想到中国的意愿:“据一些传教士所言,虽然中国人在科学方面的技能逊于欧洲,然而他们的道德和公正性却是最模范的。依据这些神父们善意的描述,诱使我们相信,整个中华帝国是一个管理规范的热情的大家庭,唯一的竞争是谁会发扬最人性和最善良的美德。但是我们在广东与那些地方官员、商人和商民的接触却驳斥了那些传教士缔造的神话。”[1]346
安逊等最初希望能在澳门得到补给和修整,但澳门政府官员不敢擅自答应,告知安逊须获得两广总督的批文[1]297。安逊租船欲赴广东求总督批文,但澳门海关官员却不给其船颁发通行证。经过一番周折后,安逊到达广州询问东印度公司获批文的途径,告知只能由中国商会头脑进行调停[1]298。安逊等待一个多月也没有结果,后来只得亲笔写信上呈总督,该信被译成汉语后辗转送达,始有中国地方官员来验船。安逊向该官员提出补给的要求,并投诉了澳门海关官员的勒索和重税行为,官员答应立即在其职权范围内予以改正。安逊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官员见识到了‘百夫长’号的实力,也必然确信单凭‘百夫长’号一艘船就能摧毁广东整个海港,或任何中国的港口”[1]302-303。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英国舰队船员到目前为止都以极其谦逊和克制的态度行事,他们的需求与日俱增,饥饿再也扛不住了。”[1]303澳门给予“百夫长”号以初步的修整,于次年4月末离开澳门,在五月初曾到过台湾。但安逊一行并未回航,原因有二:其一,安逊在6月20日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劫获了一艘西班牙大船,缴获了大量财宝,并虏获了500余人[1]309;其二,想到中国沿海进行考察求证,同时再求大量补给以供回航。于是安逊等将虏获的船和人员一并拖到了广州港口。英船一进广州,中国官兵即登舰检查,并提出征税之要求。安逊以“百夫长”号并非商船为由予以拒绝,中英双方相持不下。安逊等人不谙就里,以为中国官员拖沓和刁难是其一贯作风。安逊无法忍受中方的刁难,只得再次求见。广东政府官员首先要求释放英舰所捕获的西班牙人,理由是不能看着本国的化外商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制于人,安逊正苦于无法处置西班牙人,正好顺水推舟,但因广东政府先提出,他亦故意刁难了一下,以便为谈判加码[1]328。双方协商后,广东政府答应提供补给,于1742年7月28日派船接走了全部西班牙俘虏,送往澳门。但广东政府官员所答应的补给又过了3个多月还迟迟不兑现。安逊忍无可忍,大骂中国官员诡计多端,唯利是图[1]329,再次上书求见总督。信送出后两天,恰巧广州城郊发生大火。安逊与船员立即赶去救火[1]339-341。因灭火之功,安逊得见两广总督,准其所求。“百夫长”号修整后于1742年12月10日离开广州到达澳门,把缴获的西班牙大船卖给了澳门的中国商人后于12月15日离开澳门回驶英国[1]349。
以下再从中方史料的相关记载来印证安逊航行中国的过程。《清史稿》载“乾隆七年冬十一月,英巡船遭风,飘至广东澳门,总督策楞令地方官给资粮,修船舶遣之。”[3]《海国四说·粤道贡国说卷五》“乾隆七年十一月,■咭唎巡船遭风,飘至澳门海面,遣夷目至省城求济。两广总督策楞,令地方官优给赀粮,修整船只,俟风便归国。”[4]中方史料中用的是“英巡船”,来华的时间比英方记载少一年,月份大体与英方一致,离去时间语焉不详,对英船在华的经过皆轻描淡写。束世澂《中英外交史》对此有载:东印度公司乃于1742年遣安孙提督率百总号军舰来广东,是为英国军舰至中国之始。安孙排除一切障碍,与广东总督会晤。又当百总号入港时,广州城大火灾,水兵尽力消防,得华官之感谢,故当时华官之诛求大减。七年英国巡船在大洋遭风飘至澳门,其首领至省城求济,总督策楞亦令地方官给赀粮修船只以遣之[5]。
束世澂用的是二手资料,记载有误:一、英舰“百总”号不是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二、乾隆七年的英巡船(显然是据《清史稿》的记载)就是安逊的军舰,并非一年来了两艘英巡船。束世澂的记载只有灭火之事与英方相合①束世澂用的是日本田中萃一郎《东邦近世史》和道格拉斯(R.K.Douglass)《欧洲与远东》(Europe and the Far East)中的史料。。实际上,英舰入港,中方官员一时不知如何处置:视其为商船征税,英船不允;“百夫长”号是战舰,但来华又非挑衅。因以前凡进入中国内海的外国武装船只都冠以进贡之名,而英方既无礼物,对朝贡之俗亦毫不知情。对此,两广总督策楞主战,广东布政使托庸则力主不要起衅。于是派东莞县令印光任前去打探消息。印光任见英舰之窘境,回来提议断绝英舰一切供给以迫其就范,中方因此故意拖延英舰。后来因一些中国官员可能收受了英方的贿赂,再加上英军救火有功,才准其补给。
广东官员对英舰在广东内海停留之事既不上报,也不下令防范,对英军舰态度十分暧昧,由此推测收受英舰贿赂的可能性较大。此外,直至英舰返航后,策楞为推卸英军舰私自侵入中国内海的失察之罪,副将王璋参奏,把英舰入内港之事的时间晚写一年,对交涉过程含糊其辞,并以同情英舰的笔调上奏,显然是为自己开脱以减轻责难之故。即便如此,乾隆闻知亦怒而下谕斥责:
谕:据署广东总督策楞等奏,“上年(乾隆七年)十一月内,英吉利国巡哨船只遭风坏船,飘到澳门海面,并遣夷目撑驾三板小船,经至省城,恳求接济水米。沿途水塘汛弁,绝无盘诘稽查,后经督抚准令湾泊内海,接济口粮,采买木料,修理船只,俟风信便时,饬令出口。策楞随将海口毫无查察之副将王璋,并不早为揭报之总兵焦景竑题参”[6]。
遭到乾隆的申斥后,粤省官员为保住乌纱,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管理,特别是澳门海外事务,对外国船只,特别是英商船的限制也更加严格。两广总督策楞与左都御使广东巡抚王安国,在乾隆八年(1743)联名上书,请求设立广州海防军民同知,以便加强对广州沿海日益增多的外国船只的管理。乾隆准奏,令曾参与安逊交涉的东莞县令印光任为第一任广州海防同知[7]。
经过中英双方史料的对比,证实《安逊环球航海记》所载之事并未与中国史料有太多冲突,人物、地点、时间、事件等基本能够相互印证。唯中方史料太过笼统,为减轻通英之责而故意将英舰在华时间少写了一年,而英方史料则较详细地记述了事件的详细过程。
《安逊环球航海记》还记录了一些英军与中国官民交往的细节,记录了给他们留下深刻的不良印象的见闻,对于改变英国人的中国观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中国人排外思想强烈,官员蛮横无理。英舰初到澳门时,一名英军官因病想上岸活动一下以期恢复。但上岸后遭到了当地人的殴打和抢劫。安逊就此上诉当地官员,却遭到了他们本不应该擅自上岸的训斥[1]330-333;二、中国官员受贿成风,安逊曾贿赂了翻译,并托他交给清政府官员一些钱[1]333;三、中国百姓贪图小利,欺诈行为时有发生。“百夫长”号在未得允准之前,零星地从沿海商民处购买生活必需品,经常是短斤少两地被欺诈。一次从当地村民处买了一些鸡鸭,到船上一看大部分都死了,检查发现这些家禽内脏里全被塞进了石头以增加分量[1]333-334;四、中国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一艘英国商船(Hastingfield)在广东内河抛锚,船上货物及财产被中国人付之一炬,一箱财宝不知去向[1]343。五、中国人不讲卫生。安逊说中国人从不忌讳吃自然死亡的动物尸体,很多中国船跟着“百夫长”号就是为了捡食他们扔掉的死猪肉[1]334。因此,安逊极力贬低中国人,认定他们虚伪、狡诈、贪婪、肮脏。安逊所说的现象早在葡萄牙人的中国游记中也有相似记载,因而存在可能性,但他以澳门、广州两港的部分商民作为评价整个中国人的窗口显然是片面的。
《安逊环球航海记》不仅在本国流传极广,而且很快就有了法文本、德文本等其他语种的译本①“百夫长”号上共有4人留下了此次航海记录。除瓦特外,还帕斯科·托玛斯(Thomas,Pascoe)的《百夫长号的一个真实而公正的南海航行和环球行纪》(A true and impartial journal of a voyage to the South-Seas,and round the globe,in His Majesty’s ship the Centurion,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George Anson....By Pascoe Thomas,....London,1745);约翰·菲利浦斯(John Philips)写的一种版本,还有一位未署名。。该著对中国沿海社会现实的揭露和对中国文化的贬低给英国人心中的“乌托邦”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从而引发了对中国观问题的广泛讨论。1750年3月,《安逊环球航海记》的一些英国评论者首先表示赞同安逊对中国的贬低,坚持认为中国人不仅在智力上逊于欧洲人,而且其美德不过就是一种“假装的礼节”。甚至休谟和高德温(Godwin)所倡导的中国人值得称道的“庄重且认真的举止”也被蔑视为一种“胆怯、异化和欺骗”的伪装[8]。但也有很多人对安逊的中国之行表示怀疑,认为“安逊除了描绘他曾宴请一位非常讨厌牛肉的中国官员外,在其游记中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色彩”[8]。沃尔波尔于1751年7月5日写给斯特拉福伯爵(Earl Stratford)的信中,也把《安逊环球航海记》视为一本想象中的浪漫史[8]。法国学者对《安逊环球航海记》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卢梭(J.J.Rousseau)和孟德斯鸠等反中国文化的学者对安逊的记载表示赞同,因为他们一向就认为中国的科学和艺术历来只有消极作用,安逊的评论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证据。而伏尔泰则义正词严地在《风俗论》中反驳安逊等人的记述,再次指出中国人既非无神论者也非偶像崇拜者,知识界、王孙贵族等与孔子之道结合在一起便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人的宗教[9]。伏尔泰的书风行一时,在英国也受到了同样的欢迎,这对抑制笛福和安逊等人对中国的诋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成为维持“中国热”的中坚力量。必须要指出的是,安逊著作中流露出的这种强烈的文化反差和精神叛逆为大众所认可并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何况《安逊环球航海记》中对中国的评论和描述也有很多地方是属于中性的,甚至还有少量的赞美成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该著对中国的诋毁之论。作者曾以中肯的口气说,“中国人虽然通常负有粗俗的污名,并非没有忠诚、善良、果断和许多其他值得称道的品质。”[1]347“中国人在处理问题时的冷静和耐心是所有其他民族所不及的。”[1]347此外,安逊一行并非是由英国官方派往中国沿海进行科学考察或进行正式外交的团队,尽管安逊的职位很高,但作为一种逃兵性质的漂流记,其立场和观点本身就颇具争议性,基于此,安逊等对中国的贬斥虽然产生了不良影响,但还不足以完全逆转“中国热”。
[1]Richard Walter,George Anson.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1740to1744[M].London,1748.
[2]John Hemming.Review:New Light on a Famous Circumnavigation[J].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74(10).
[3]清史稿卷一五四[M].
[4]海国四说·粤道贡国说卷五[M].
[5]束世澂.中英外交史[M].商务印书馆,1931:8.
[6]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八[M].
[7]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三[M].
[8]Chien Chung-shu.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J].China Quarterly,1949(2).
[9][法]伏尔泰.风俗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