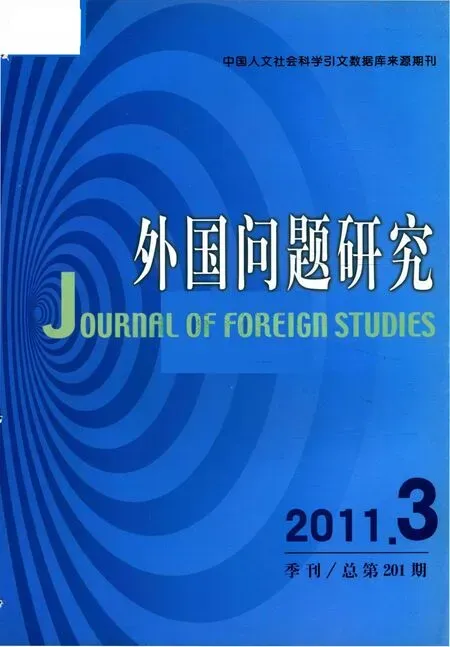江户时代日本史学中的早期民族主义
2011-03-20瞿亮
瞿亮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天津300071)
民族主义强调认同自民族共同的语言、文化以及价值取向,并对其产生归属感。在欧洲,直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早期民族主义逐渐形成。它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朕即国家”,国王的权力就是国家的权力。第二,君权神授,君主的权力来源于上帝。第三,强调民族优位,并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戏剧等产生归属感,在对比其他民族时对本民族产生自我认同。
日本战后思想家丸山真男认为:日本的早期民族主义与人们对于乡土的热爱不同,它需要外部刺激,即外来的压力使其自觉转换,进而凝聚成一种政治意识,要求在民族认同感基础下建立国家共同体[1]。基于此种考量,他将日本的早期民族主义源头归为日本的开国,把反抗外来殖民危机作为早期民族主义起源的契机。但笔者通过江户时代的史著资料发现,日本在未开国之前,自身的思想体系之中已经孕育出了早期民族主义。
日本的早期民族主义包括三种形态,即为:华夷观变化滋生民族主体意识、神国思想、尊皇意识。对比西欧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华夷观变化滋生的民族主体意识类似于西欧早期的民族认同,尊皇意识类似于绝对王权,神国思想也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君权神授理论,但由于其自身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又独具特色。本文试通过分析开国之前史学中所存在的早期民族主义形态,来论证日本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其内部,外来殖民危机只是促使其成长变化的催化剂。
一、华夷思想转换下滋生的民族主体意识
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同参照物“他者”——中国比照之中,自我民族认同以及民族优位思想逐渐形成,这主要体现在华夷思想的转换上。
华夷思想萌生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汉民族由于文明发达程度高于其他族群而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从而萌发了“华夷”分野的观念。随着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华夷”概念也自中国南朝时代传入日本,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形成了它自己的“华夷思想”[2]。在江户时代之前,尊慕中华礼义、以中华文明为效仿学习的对象,是日本思想界的主流。然而,江户时代初期,明清易代这一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成为华夷思想转化的契机①近年来,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著述有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崇明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书城》2004年第9期;韩东育:《明清鼎革之际东亚“华夷观”的演变》,《思想史研究》(日本)、《“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受到儒家华夷思想影响的日本思想界认为明清易代乃是华夷位置颠覆的重要转折,此种定位促成了民族优位思想的滥觞。
江户时代初期,幕府儒官林春斋为了搜集关于中国国情和通商的情报,专门编纂资料史籍,命名为《华夷变态》。在其《序》中就明确指出:明清易代乃是“华变于夷”。“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3]《华夷变态》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若干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对传统的华夷观进行否定,汉人自称的“华”自此被“夷”所代替。在《华夷变态》卷一附载的史料、日本翻译文或注解中,一律对“满洲”人称为鞑靼、虏等。自《华夷变态》之后,曾经作为效仿和尊崇的对象的他者中国,逐渐被平等意识甚至是轻蔑意识的形象所代替,而曾经作为文明滞后者的自身,地位开始受到尊崇。
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史学家将“华夷”的概念进行重新诠释,抬高了本民族的文明位置。浅见炯斋在他的史论著作《中国辩》中,从文化立场上对“华夷”的意义进行了转换,他指出“中华”并非只是一个地域观念,而是文化观念,他贬斥了盲目尊崇中国学问的为学之人,“吾国自儒书盛行以来,凡读之者,皆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以生夷狄之地为耻,虽读儒书,却失大义名分之实,无知至极,可悲之极。”[4]417他进一步指出:用圣人之道,则日本亦可成为圣人之国,“儒者所倡道者,天地之道也,吾之所学,亦天地之道也……孔子若亦生日本,从日本以立春秋之旨也,是则所谓善学《春秋》者也。”[4]418在此基础之上,他进而指出日本不应凡事都遵奉效仿中国,当尊崇本国的传统,把儒家的正统名分思想发扬光大。“若悉从唐国之制,废吾国帝王之号,不用年号,每年取唐人草履,冠名以大义,此乃视吾亲为奴仆,与乱贼同罪……各国皆遵其制,亲其亲,是天地大义并行之举。”[4]418-419
粟山潜峰编写《保建大记》,对华夷思想进行了总结,贬斥了日本的学人称明、清为中华,称本邦为东夷的做法。“华用夷礼,则夷也,夷而进于华,则华之……呼元、明为中华,自称为东夷,殆几乎外视万世父母之邦,而无蔑百王宪令之著矣……”[5]358
到了山鹿素行那里,“华夷”的位置则发生了颠覆。山鹿素行在其史著《中朝事实》中指出,日本卓尔万邦,人物精秀,才是真正的“中国”。“夫中国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紘,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焕乎文物,赫乎武德,以可比天壤也。”[6]2-3他批判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们崇尚中国的学风,将日本同中国、朝鲜进行比较,列出了日本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中国”的缘由。他指出中国虽然地大人多,但多次遭受少数民族侵犯,导致易姓失国,“凡外朝,其封疆太广,连续四夷,无封域之要……故人物亦异其俗,如啖牛羊,衣毳裘,坐榻床,可以见之也,况朝鲜蕞尔乎。”[6]2-3
山鹿素行进而指出:日本人杰地灵,不仅没有太多的劳役之苦,也很少受到外族入侵,优于中国和朝鲜。“独本朝,中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国,正南面之位,背北因之险,上西下东,前拥数洲而利河海,后据绝峭而望大洋,每州悉有运漕之用,故四海之广,犹一家之约,万国之华育,同天地之正位,竟无长城之劳,无戎狄之膺……”[6]2-3最终他得出结论,称百年不遭受易姓革命乃是日本优于外国,称为“中国”的重要原因。“故皇统一立,而亿万世袭之,天下皆受正朔而不贰,万国禀王命而不异其俗,三纲终不沉沦,德化不陷涂炭,异域之外国,岂可企望焉乎。”[6]11-13
以华夷观的转变为契机,激起了江户时代从整体角度重新认识本国史地的热潮。到了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主政的元禄时代,太宰春台、谷泰山等知识人吸取明清易代的教训,倡导重修本国地志。《元禄国绘图》、《会津风土记》、《五畿内志》等地理志的编修,打破了中世和近世初期的史地认识按照各个大名诸侯领地来划分行政单位的藩篱,而是从整体的“日本”的角度,对本国史地进行再认识,这体现了早期的“国家”概念[7]。
二史学所体现的神国思想
神国思想是自古以来兴起于日本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它强调日本的皇室、国土、国民由诸神护佑,优于其他民族,也渗透到神道教、古代神话传说以及早期的史书之中。在忽必烈率兵伐日失败之后,日本的神国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北畠亲房在《神皇正统记》中,提出“大日本乃神国”的主张,对之后的思想界影响深远。进入近世之后,神国思想为儒学、国学所提倡,强调日本万世一系的神国观念也逐渐凸显于近世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认识之中。
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中,将万世一系的优越性同神授皇统的思想结合起来。“皇统之初,天神以授之,天孙以受之,然其知德不愧天地,而后可谓神器之与授,凡天不言,人代言之,天下之人仰归,则天命之也,天下所归仰,更不他,唯在天祖眷眷之命而已。”[6]34-35
粟山潜峰在《保建大记》中,则把象征皇室的神器同日本万室一系的神国优越思想统一起来,使抽象的神国意识同具体的器物联系起来,让皇统有了载体。“护身之灵器,镇宇之神物。万世公议,终不容伪主乱真,闰位蔑正,则世道虽夷,王风虽降,而三玺之尊自若矣……故至以躬拥三器为我真主,则臣要质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其人而不惑。”[5]373他认为只要神器存在,即便是历经乱世,皇统也不会因此而断绝。
江户时代中后期,一些史学家开始把神国观念运用到具体的史学辩伪和考证之中,这也达到了明皇统、确立日本优位的目的,松下见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松下见林编撰的《异称日本传》将自《山海经》到元明时代中国、朝鲜有关日本的所有史料收录,并对其进行辨伪、整理,意在让本国知识分子对本国的国史重新认识。著者将神国思想运用到考证之中,对中国史中所记关于日本的记录究误、辩伪。在序言中就明确的表明了这一态度。“大日本国者,神灵所扶,开辟神圣出而尚其道,明其位,拓土贻统,杰于百派千流朝宗之中,中华以为礼义之国,质有雅风。吴败,姬来奔,秦暴,徐福逃入,至任那斯卢屈膝,鲁侯赤帝之后,莫不依归,此岂得非神道文明有仁民爱物之政哉。”[8]1-2
对《晋书》以后中国诸史书称日本为吴太伯之后的记载,著者从神代皇统和中日史籍考证两方面,加以否定,认为当时吴太伯后,日本乃姬氏国等史料记载乃是失实,认为中国史书记载因为距地遥远,所载事实不足以信。体现出著者浓厚的民族优越感以及欲与中华并驾齐驱的情绪。“晋书说我国事,其问与前史有异同,宜参考,诸史皆仿此,谓太伯之后者,此为首出。夫一犬吠虛千犬吠,声从晋书出,后史多同然一辞,何其不详乎?听者不察,引以为口实,何其惑乎?自天地开辟之初,有我国,而号曰大日本丰秋津洲,我君之子,世世传续,所谓天照大神之神孙也。吴始自太伯,世之相后数千万岁,日本何为太伯之后哉……”[8]20
随着新兴的国学兴起,突出神国史观的国学派史学逐渐与儒学派史学分庭抗礼。其代表的人物就是本居宣长,他的代表史著《古事记传》,力图排除中国思想对日本历史的影响,从解释《古事记》出发,揣度其意,考证其事,并将其同《日本书纪》等汉文史籍进行比照,从诸多方面论证《古事记》是最佳的史著。
本居宣长认为《古事记》排除了“汉意”,以日本自身的思想来叙述历史,从而达到究明皇统的目的,因此史学价值高于其他史书。“《书纪》以汉文之意著史,不达皇国古语者甚多,此失真也。然《记》遵照古言,如实记载,所书上古之言文甚美……昔日汉学盛行,天下制度皆仿汉而定,故书物亦以相似汉之书物为喜,此种风气亦成主流,而上古真实之事则沦为旁流……自此之后,世人当取《古事记》而观国史,国史之正体乃成。”[9]24
他批判了《日本书纪》借鉴中国阴阳学说诠释日本国土生成的记述方法,认为《古事记》中的相关记述才是真实属实的。“以乾坤之道诠释吾国神灵之生成,此乃大谬也。吾国之神灵,乃高御产巢日神、神御产巢日神所生也……《书纪》虽书伊邪那歧命、伊邪那美命之事,但引汉典《易经》阴阳之说,以此释神代之事,真实之道难立。”[9]27本居宣长试图排除日本史学中的中国思想成分,以《古事记》中所体现的神国思想为主旨,重新建立新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评论体系。
综上所述,江户时代的史学所体现的神国观念,强调了神授的皇统是日本整个民族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同外来思想的比照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体现日本民族精神的理念,对思想界影响深远。
三、史学中涌现的尊皇思想
尊皇思想也是早期日本民族主义的主要形态,它最初来自儒家学说,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儒家提倡行德政,以王道来统治,反对诸侯以武力霸道夺取天下。自江户时代中后期起,随着幕藩体制的瓦解,儒家的尊皇观同神国思想糅杂在一起,渗透进江户时代的国学、儒学等学问之中,为树立天皇的权威打下了思想根基。在近世日本的史学中,尊皇思想也逐渐确立并且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这主要集中体现在《大日本史》、《日本外史》的编修上。
《大日本史》是江户时代最有价值的史书之一,其创始者德川光圀编修史书的重要动机便在于以正皇统。在他的墓志碑文中就强调:“正闰皇统,是非人臣,辑成一家之言。”[10]
在围绕正统问题方面,《大日本史》不再局限于朝代更替而引起的正统纷争,强调“皇朝一姓相传”、“南北两宗均之天祖之胤”。原本在撰写的最初阶段,《大日本史》尊崇南朝,将北朝君主列于本纪之外。安积觉入史馆之后,建言诸位史臣,“窃谓设如异邦(中国)革命之世,修前代之史,其书法或然。今皇朝一姓相承,嚮之所谓南北两宗,均天祖之胤,而所谓北朝五主,即今天子之祖宗也。岂可降为列传乎……侃侃建言,遂得带书诸后小松纪首。”[11]其意见得到采纳之后,史书的结构再一次被调整。由上论述可知,《大日本史》的南朝正统观既遵循了儒家的名分思想,又顾及日本的实情,将尊皇和大义名分统一起来。
宝永八年(1711)迹部良显的《三种神器传来考》中,力图证明水户藩修史正统观的渊源。“是水户光圀卿,尊三种神器,奉南朝天子为正统,除北朝之主朝臣之字,此古今独步之笔法,显我神国之志。自始至终仰皇朝之正统,又解后世之惑,其器量超群,能考见之。”[12]到文化七年(1810),水户藩主德川治纪作《进大日本史表》,提及神器与皇统的关系,表明水户藩史学的立场。“日域皇化所被,环海咸仰,天朝帝王授受,三器徵神圣之谟训,宝祚之隆兴与天壤无穷……遗腹西东之争南北之乱,皇统唯视神器之在否。”[13]“神器正统论”最终渗入到《大日本史》之中,与儒学的君臣名分之道一起,推进了尊皇思想的发展。
在对待幕府的态度方面,《大日本史》与以往的史籍不同,它没有全力去褒扬幕府和武家的功绩,而是将其作为朝臣,并依据孟子学说,认为幕府政治是霸业而非王道。安积觉在《将军传序》中,就鲜明表现了这一立场,并且强烈的斥责足利尊为奸诈之辈。“然尊氏之谲诈权谋,功罪不相掩,可以笼络一世,而不可欺天下后世。”[14]这反映了整个彰考馆及水户藩诸士对幕府的态度,从儒学大义名分的角度,坚持尊奉天皇朝廷,主张君臣有序。在幕末,这种史观同尊王攘夷思想契合,成为倒幕维新的一大依据。
尊皇思想也反映在删除论赞上,江户时代后期的水户藩臣们,认为不得对日本历代之君肆意评论,掀起了关于论赞存废的论争。享和三年(1803),江户史馆总裁高桥广备致书水户史馆众史臣,首倡削除论赞,主张一姓相承的日本不同于易姓革命的中国,论赞随意评判历代君主、朝臣的是非,有失体统。“吾天朝百王一姓,方今之世,虽至尊垂拱,委政关东,然君臣之名分,严乎不乱,四海之内,莫不皆奉正朔,上世虽远,均为今之祖宗,论其失得,无所忌惮,事体已非所宜,安知不负先公之意哉……盖史之分纪传,其体创自司马子长氏,而其末各系以论赞是非其失得善恶,是盖一家之私议,固非天下之公论也。”[15]最终,藤田幽谷、高桥广备、川口长孺议定,德川纲纪应允,削除论赞便成为定局。从此之后的《大日本史》,纪传之后不再附有史论,正文和论赞分立,成为两部的史著。纵观论赞存留的始末,体现了传统朱子学在思想界的解体,早期民族主义逐渐成为统合思想的新理论。
直至幕末,幕府无力应付商品经济对封建领主经济的冲击,也难以抵御西方殖民危机,有识之士为寻求改变国内外危机的精神动力,尊皇思想备受推崇,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便是顺应这一潮流的产物。
赖山阳在《日本外史》中,把名分的中心偏向了皇室,认为君臣秩序的名分与君子有德无德、政治上有无实权并没有关系,君臣关系是恒久不变的。《日本外史》用大量的笔墨描述楠木正成勤王事迹,在外史氏曰中,明确表述了对勤王的认识:“勤王之功,余以楠氏为第一……自公卿,自将士各执弓箭以勤王事,概皆闻楠氏之风而谓不愧武士之名矣。”[16]《日本外史》中这种强烈的勤王意识,受到倒幕维新志士的推崇,对近代日本的重要人物也有深刻的影响。
江户时代中后期兴起的尊皇意识,打破了松散的幕藩制结构下各自孤立的状态,开始构建以天皇为中心的信仰体系,具体到史学上则表现在皇国观念开始影响历史叙述和认识,为近代日本的皇国史观产生了影响。
结语
江户时代日本史学中所体现的早期民族主义,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表征,不仅促进了对本国历史的再认识,而且萌生出对君主、国家、民族的一体认识,这对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身份认同起了积极作用。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也影响了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华夷观转化下的自我民族意识在幕末变为攘夷的动力,也成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理论依据,对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有一定影响。万世一系的神国观成为“王政复古”的一大重要思想依据,也为近代日本的“国体”观念埋下了伏笔。尊皇意识克服了近世后期幕藩体制的松散局面,将整个国民、国家集合于皇权之下,而成为倒幕维新的重要旗帜,也是近代天皇制的一大思想根基。
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它仅仅是当时知识界少数精英的思想,并没有像西欧的早期民族主义那样,通过启蒙运动发展成为国民对国家和民族进行自我认同,而是在列强开国的刺激之下,才逐渐同反抗外侵的思想相结合,向近代民族主义发展转变。而日本早期民族主义形态中,除了强调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之外,其专制色彩和失去理性的民族优越论影响了日本思想的进步,在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给日本和周边民族国家带来了伤害。
[1]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M].三联出版社,1999:268-269.
[2]川本芳昭.倭国における対外交渉の変遷について——中華意識の形成と大宰府の成立から見た[J].九州大学史淵,2006(3):27-65.
[3]林春斋,等.華夷変態(第1卷)[M].东洋文库,1958:1.
[4]浅见炯斋.中国辩[A].日本思想大系——山崎闇斋学派[M].岩波书店,1982.
[5]粟山潜峰.保建大记[A].日本思想大系——近世史论文集[M].岩波书店,1974.
[6]山鹿素行.中朝事实(上卷)[M].尚古堂,1908.
[7]日本近世地志编纂史研究(思文阁史学研究丛书)[M].思文阁,2004.
[8]西川见林.异称日本传[A].改定史籍集览第廿册——新加通记类[M].临川书店,1984.
[9]本居宣长.古事记传[A].本居宣长全集(第9卷)[M].筑摩书房,1968.
[10]德川光圀.梅里先生碑文[A].赖山阳抄.大日本史论赞集[M].大正书院,1917:1.
[11]藤田幽谷.修史始末(上卷)[A].义公三百年纪念会编.大日本史后附及其索引[M].大日本雄辩会,1931:4.
[12]迹部良显.三种神器传来考[A].日本学会协会编.水户学集成5—大日本史的研究[M].国书刊行会,1957:269.
[13]德川治纪.进大日本史表[A].德川光圀.大日本史[M].吉川弘文馆,1911:5-7.
[14]安积觉.将军传序[A].安积觉著.赖山阳抄.大日本史论赞[M].大正书院,1917:273-274.
[15]冈崎正忠.修史复古纪略[A].义公三百年纪念会编.大日本史后附及其索引[M].大日本雄辩会.1931:74-75.
[16]赖山阳著.久保天随订.重订日本外史(卷5)[M].博文馆,1909:14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