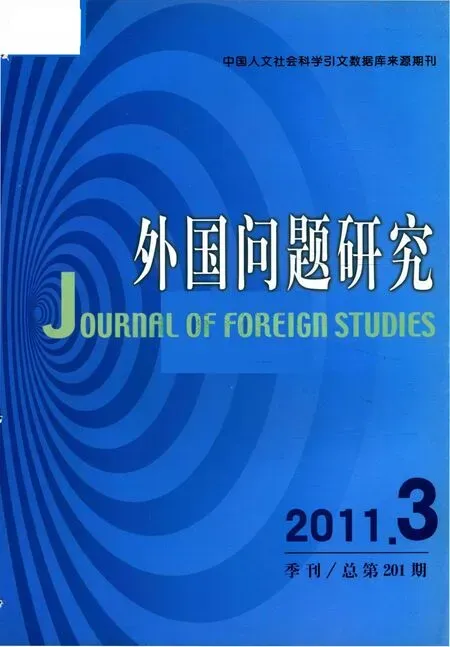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与外交取向
2011-03-20安善花
安善花
(大连大学历史学院,辽宁大连116622)
近代日本国际秩序观的构建,除与日本历代思想家的理论思辨工作有着深厚的关联外,还在西势东渐的大环境下,在国际秩序的理念构造中吸纳了欧洲近代国际秩序思想的二重原理认识,并在明治维新后迅速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最终确立起近代日本的双重外交路线。
一、明治初期维新政府的对外观
1868年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封建统治,为日本建立近代国家和新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维新后日本的民族危机和国力衰弱的现实并无改观。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正是明治新政府苦苦探索的一个课题。从旧幕府手中接过外交权的新政府于1868年2月在太政官内设外国事务挂。在官职表中明确写道:“外国官掌总判外国交际,监督贸易,开拓疆土。”[1]并向各外国通知通过王政复古进行政权更迭的事情,同时向国内阐明开国和亲的外交方针。布告文中明文规定:“外国之事,先帝多年宸忧。由于幕府以往之失错,以致因循至今。然事态一变,大势诚不得已。此次朝议断然同意缔结和亲条约之事,当上下一致,不胜疑惑,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以对答祖宗先帝之神灵。天下列藩以至士民,当奉戴此旨,尽心力而勉之”。同时又称:“以往幕府所缔结之条约,弊害有之,当在公议种种利害之后进行改革。再者外国交际,应以宇内公法待之……”[2]即承诺将依“世界公法”处理“对外交际事宜”。1868年4月6日,以天皇名义发布施政纲领,即《五条誓文》。第四条为“破旧有之陋习,循天地之正义。”表明日本放弃攘夷口号,要与外国交往。第五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即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以振兴国基。同一天又发表《天皇御笔信》,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3]维新政府的上述方针除了表明了它的开国精神,同时也为日后对外侵略的方针政策指明了基本方向,尤其是对待欧洲国际体系的态度。
在新政府的权力中枢中,很多人都认识到要改变相对于欧美列强的国力不足和文明程度之低的现实,提倡遵循基于国际法“条理”和“信义”的外交。即使像议定岩仓具视这种强调“海外万国皆为我皇国之公敌”这一权力政治理论的人,也认为“恪守条约,不失信义,互通有无,乃当今宇内惯例,唯独我国固守锁国之旧法”,“要谋求富强,必须拓展与海外万国的交通。”最终,依据国际法行事的外交论成为新政府的主流意识。1869年5月,天皇亲自向知藩事发布关于外交的策问,再次提倡“遵守信义,追循条理,确立独立自主的局面”[4]。从而显示出明治政府将以迎合条约体系为前提建设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基本姿态。
同年7月外务省成立时,全面负责外交事务的寺岛宗则在很早的时候就作为兰学者而出名,作为有着两次旅欧经历的具备国际认知能力的官僚,他对弱肉强食的国际权力政治现实非常清楚。1865年12月,在伦敦滞留的寺岛宗则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所谓弱肉强食……由是观之,看将来的形势,为使我国与万国并立,要让国家的最高君主大开眼界,舍弃固顽,向海外三、四个大国遣使,……其中的道理非这封简短的书信所能言尽。……希腊、葡萄牙、荷兰、丹麦是欧洲的弱小国家,但互相帮助,维护了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土耳其没能被俄国吞并,正是因为在其所处的国际关系中,互惠对等原则运作的结果。”[4]在这里,寺岛宗则通过明示在主权国家享有独立平等权利的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规则,想要说明对当前日本民族危机的解决办法,并提出了驻外使臣制度的理论。另外他还认为“为了实际适用国际法规,就必须调整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对立及协作的关系,而且需要外交这一用来进行国家间交涉乃至一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技术。”[4]
1871年11月开始任外务卿的副岛种臣是明治初期《政体书》的主要起草人。他强调,中国春秋时代虽是弱肉强食,但注重信义和名分,副岛外交因此也被称为“春秋外交”[5]。他认为,各国间的主权问题也有可能在“信义”中得到解决,如果采取有悖于信义的行动,那么这个国家不仅失去作为主权国家的资格,而且作为讨伐的对象也是正当的。这在他对待台湾和朝鲜的问题上具体反映出来。1873年6月9日,当驻清英国公使威妥玛向副岛问及对台湾、朝鲜两问题的处理方案时,他回答说:清国没有向“台湾生番之地”派遣官吏,清国的版图中也没有这个地名。以前美国人和番人争斗时,生番就随便与美国换约,而清政府却不知道这件事,还称之为属领,真是可笑。因此断言,清政府之权力未及生番之地[6]171。从而认为,清把生番说成“属下”,而生番“和战结约由其自主不通知政府”,就是有悖信义的行为,而代替清国征伐生番是正义的。后来,副岛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就是以这种说法说服清国政府,并成功地得到个别清政府官员关于生番之地为“化外之地”的口头约定[4]。
在这样的国际认知下,副岛已急欲践行对欧美屈从,对亚洲邻国侵略的强硬外交路线。1872年,副岛与俄国就库页岛边界进行谈判时,曾打算与俄缔结密约,放弃库页岛,而以日本武装入侵朝鲜时俄国不加干涉作为补偿之一[7]。而在对待朝鲜问题上,他却有着明确的征韩意图:“我皇帝政一新以来,屡次遣使,可对方却有失敬意,如今唯有谆谆教诲之,如若对方仍顽守固愚,则终将使用实力。”[6]171认为日本是基于信义与之交际,可对方却顽固地拒绝时,不得不把对方作为征伐的对象。因此,可以对朝鲜使用武力。
总之,在维新政府的对外观以及外交实践中,一方面显露出取代旧幕府外交的新政府对外通好的态度和遵循基于国际法的“条理”、“信义”外交的姿态;另一方面,也表明新政府承继了自幕末以来对亚洲邻国强硬的外交路线。
二、岩仓使团出使欧美及明治政府中枢的国际秩序观
明治初期,过去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严重威胁日本民族独立和工商业发展。因此,收回丧失的民族权益,与外国缔结平等新约,成为新政府外交的新课题。但是,由于对弱肉强食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认识不足,新政府认为能够轻松地修改幕末列强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把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的主要目标。
1871年10月8日,新政府派出了由48人组成的使节团(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赴欧美访问。其目的一是向缔约国致“聘问之礼”,并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学习欧美各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为日本实现近代化作参考[8]161-162。1872年2月15日,考察团抵达出访第一站华盛顿。使节团就不平等条约问题在华盛顿与美国展开谈判。岩仓、木户向美国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建议。美国则提出关税自主权的归还应以开放日本内地、允许美国人在日本的自由行动为先决条件。双方见解相差甚远,交涉不得不终止。美国赤裸裸的欺凌使考察团特别沮丧,木户在日记中写道:“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经营,竟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9]
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普法战争,1870年9月法兰西帝国在战争中失败,拿破仑三世被俘,同月意大利完成了统一。在普法战争中获胜的普鲁士于1871年统一了德意志,建立了帝国。欧洲正面临新的国际关系的到来。在欧洲,英国不仅强硬拒绝日本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并提出更为苛刻的修约方案。其他列强也企图利用改约机会,进一步在日本谋取更大的殖民利益。于是,使节团改变了原定的方针,以考察欧美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军事制度、社会文化等为主要内容。这些人“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燦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10]大久保在考察中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必须富国强兵;而要富强,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下手,并切实谋求进步发达。”[11]1873年3月15日,使节团会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1815-1898)。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于己不利,则幡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12]他讲了19世纪国际社会中强权政治的活生生的现实,给使节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在统一德国时使用的铁血政策大加赞赏。大久保认为“重新经营不可不如彼”[13]。要以实力对抗强权,首先要着眼于“内治”。这是使节团在新的自我认识和世界认识的基础上对日本的重新定位,也是他们归国后主张“内治优先”的思想基础之一。使节团在考察中感到,要想富国强兵必须建立法制,决心效仿普鲁士,在日本实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使节团带着把英国作为“富国”的标本,德国作为“强国”的榜样的印象,结束了对欧美各国的访问。大久保、木户、岩仓从1873年5月到9月间先后回国。1873年岩仓使节团归国后起草的《任务书》中指出:“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们尽善尽美。欧洲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开明之风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8]189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使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前,在1869年4月9日,议定岩仓具视向议定兼辅相三条实美提出关于《外交、财政及开拓虾夷地区》的长篇意见书。强调:“海外万国皆我皇国之公敌”,主张必须保持日本的独立,“允许外国军队在我港口登陆”或“侨居洋人违犯我国法令,也要由外国官员处理”等是皇国之耻辱,所以应该修改条约[14]。后来成为殖产兴业主要推动者的大久保利通在下关战争时还是个攘夷论者,但通过到欧美的考察使他完全摒弃了旧时的世界认识,他深有感触地说:“到西洋一看,深感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15]通过考察,看到欧美之富强皆因工商业发达,回国后于1874年6月,他正式向明治政府提出《殖产兴业建议书》,殖产兴业成为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指导方针。使节团认识到日本与欧美列强的差距,对他们的自我认识、对欧洲的认识以及如何处理与欧美列强的关系及日本对未来的选择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为此,维新政府在政治方面吸收欧美的宪政思想。明治政府成立之初虽然在所颁布的《五条誓文》中就提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在《政体书》中规定了“太政官”制度,其中枢为“太政官”,下设议政(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初具类似欧美资产阶级国家政体三权分立的雏形,但与近代议会制度还有很大差距。如《五条誓文》的拟制者木户孝允在旅美的日记中写道:“维新之岁,草率之际进言,使天下诸侯华族有司成五条誓约,稍定亿兆之方向。而至今日,则不可不定确乎之根本律法。故此行欲追究作为各国所根本之律法及政府组织。”[16]并要求随员认真研究各国宪法政治的得失,考察各国的议会制度。
岩仓使团出使欧美廓清了日本的国际秩序构想。在使团回国后形成的正式报告书《美欧回览实记》中,他们首先将日本与欧美先进国家做了比较,认为大概相差30年。然后又将日本与亚洲的后进国相比,进而寻求在东亚建立日本文明的可能性。在该报告书中,提到东亚邻国朝鲜的地方仅2、3处,主要是把中国和日本作为论述的中心。这样,“藩阀势力从明治初年开始就认为自己在将来有可能实现欧美式的近代化,从而对清朝抱有优越感,而朝鲜则在其视野之外,把朝鲜当作远不如自己的下位国家。”[17]总之,这次出访的根本意义在于:使明治政府中枢更深刻地了解到日本所置身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形势,认识到只有使国力充实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加深了对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重要性的理解,归国后确立了全力发展经济的体制,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政府从1873年起重新调整国际秩序认识,确立近代日本“脱亚入欧”的未来走向。
三、近代日本国际秩序观的构造
在19世纪后半期围绕东亚的复杂国际环境中,综合国力远不如欧美国家的日本如何与西方列强共处?这一问题在明治政府的对外考量中挥之不去。
在日本迈向近代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被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境地。意欲登上国际舞台的日本,急于消除不平等条约的威胁。为此,日本所持的态度是:承认列强的强大,并尽一切可能学习西方强国,实现本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实现自然融入西方强国的目标。
开国以来,被纳入欧洲条约体系一环的日本,可以说仍然独立于“华夷秩序”的外缘。围绕日本的国际环境可以描绘成是环形的同心圆,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日本眺望世界的时候有两个眼睛。一个是向外圆眺望欧洲世界的眼睛,另一个则是向内圆眺望亚洲世界的眼睛。从根本上支撑这个“复眼”似的世界观的支柱,就是“力”的理论和所谓“国家间平等”这样的西欧型的国际秩序理念[4]。最终,维新政府决意在东亚世界彻底贯彻西欧型的国际秩序理念。
近代欧洲国际秩序是以“势力均衡”为生存原则的国际秩序,国家主权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和实力上各国间不平等关系同时并存,是一个形式上平等和强国吞食弱国同时并存的世界[7]36。即根据力量均衡原则来谋求本国生存,而且国际关系的平等原则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得到尊重。它包含适用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内部原理”和适用于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外部原理”两部分,是一个二重原理体系。所谓“内部原理”即只在西方国家范围内相互承认各国的主权存在,并以国际法的原则处理相互关系。而所谓“外部原理”则是指西方诸国不承认非西方国家享有主权,国际法也不适用[18]99-100,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也被视为野蛮或半野蛮之地。
日本的国际秩序思想与欧洲近代国际秩序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既从横向也从纵向上看待国际秩序。欧洲强国以横向秩序看待欧洲范围,以纵向秩序看待欧洲以外的世界。“脱亚入欧”的日本近代国际秩序观既有纵向性也有横向性。日本的横向秩序是指与西方的关系,而纵向秩序直接所指就是与朝鲜等东亚小国的关系,另外还潜藏着基于“华夷之辨”世界观而愈加蔑视的清朝中国。
福泽谕吉国际秩序思想中的上下秩序认识与欧洲近代国际秩序思想如出一辙,也与明治政府的国际秩序观不谋而合。福泽谕吉在早期著作中表现的国际秩序观既具有“国家平等意识”,又兼具对中国等被西方奴役国家的蔑视及对强权的渴望。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他那仅有的“国家平等意识”再也没有出现。取而代之,他逐渐强调欧美国际秩序中的“上下秩序”。1875年,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阐明了“文明”的特征和近代工业文明精神的合理主义实质,对日本旧文明进行了剖析批判,揭示其不适应近代工业的非合理性,提出汲取新知识,创立“新道德”的文明转型史观。但福泽将欧美各国的西方文明形态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视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路为日本唯一的出路。他说:“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19]11而且据此他站在西方国家体系的立场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的国家序列。中国先是被划入半开化,后来则被列入野蛮国家之列,朝鲜也被列入野蛮国之列。并认为曾经滋养了日本的大陆文化是日本人在同西洋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根源。这使得日本在如何看待亚洲、如何处理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上,从日本率先达到“文明”的立场出发,以西方看待亚洲的图式提出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都是文明对野蛮之战的谬论。
欧洲条约体系原理中虽标榜国家平等的观念和国家平等秩序,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却形成了“统治—被统治”这样的上下秩序即双重构造。具有“两副面孔”和“开化的现实认识”[20]的福泽谕吉看破了这样的二重构造,并采取了认同的态度。认同这一构造原理的日本在加入欧洲条约体系并与欧美国家享有同等国家权利即国家平等秩序意识的同时,把其他剩下的国家编入上下秩序中的二重构造中。他把弱肉强食的原则视为文明国家的权力,而且渴望日本也能拥有,这是直接照搬欧美列强的方式。随着明治日本的近代化的进展,他的以上下秩序为前提的国权扩张论也逐步升级。
他非常清楚在欧美强权政治下国际法的适用范围。他在遗稿中吐露:“哪儿有什么万国公法,耶稣教有什么用,公法是欧美各国的公法,在东洋一点用都没有。”[21]这就意味着他否定了国家平等观念,而肯定了权力政治。在《文明论概略》第10章中他说:“自从外国人到我国通商以来,虽然在条约上明文规定彼此平等,但实际上绝对不然。”[19]180
他对主权国家之间的认识是这样的:“本来,与外国交际乃相互主张权利,而不是以情相让。总之,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仍成立于同等相待者之间”。他对欧洲近代国际秩序中势力均衡政策的理解是:“或偶尔有欲使其同类中之小国蒙受祸害者出,而又有助之者出。以此权衡得名,称权利均衡”。同时,他又深知这一政策仅适用于欧洲诸国之间。他说:“最终,正得同种人类尚有相怜之情,此权力均衡说方能得以实际实施。舍西欧就东洋诸国而言,西洋人无论怎样逞暴,皆傍观之,动口职责者全无。”[18]101-102这些都表露出他越来越重视弱肉强食的权力政治的现实姿态。
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国家主权、武力扩张和势力均衡为生存原则的国际秩序,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在那里,国家主权形式上的平等和实力上各国的不平等关系同时并存,这是一个形式上的平等和强国吞食弱国同时并存的世界。福泽谕吉对欧洲国际体系的二重原理有了充分的认识,才在后来提倡“脱亚论”。正因为福泽谕吉国际秩序思想中的上下秩序认识与明治政府的国际政治理念不谋而合,因而使得其国际秩序思想中区别对待欧美国家和亚洲近邻的双层原理构造迅速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方面,明治政府最终确立对欧美屈从,对东亚邻国强硬的双重外交路线也恰好表明思想界的主张与政府决策之间的高度契合。
四、近代日本双重外交路线的确立
国际秩序观终究是要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有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观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这是国际秩序观与外交取向的一般关联。基于近代日本国际秩序观的双层构造原理,在外交取向上也表现出双重性格。而这种双重性与晚清外交的近代转型的双重性又完全不同。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欧美国家的外交是中国传统的朝贡外交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延续,未能脱离传统“华夷之辨”的世界观。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万国公法》的传入,清政府意识到不平等条约的危害,进行着适应全新国际关系的现实努力。另一方面,在对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却仍保持传统的朝贡关系,在对朝关系上尤其突出。晚清外交“不仅在事实上确曾存在着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体制外交关系共存的客观现象,而且在制度层面负责处理对西方国家近代条约关系之新型机构与主管对周边朝贡国家关系事务的传统对外关系机构,也曾至少共存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22]这既延误了自身外交近代化的进程,也严重地影响了朝鲜近代外交的开展。
对比中国,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和近代意识相对成熟,在国门洞开之后,经过相对短暂的磨合后,迅速调整自己的国际秩序观,对自己未来发展方向作出了自主性的选择,确立新的外交坐标,在明治初期就确立起对欧美屈从,对东亚邻国强硬的外交路线。
如何面对东亚邻国以及欧美列强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所面临两个外交课题,从日本处理与上述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就充分显现出日本外交路线的双重性。在对朝鲜问题上,1870年5月,外务省请求太政官就三种方案进行裁决,其中第一条方案“在国力充实之前,停止同朝鲜进行谈判。”第二条方案“视朝鲜态度如何,必要时逼以军舰之兵威,或进而不辞武力。”[7]132都是援引欧美列强曾强加于日本开国的方案,可见日本在近代对朝关系的出发点上一开始就是以本国国家实力为后盾的炮舰外交来考量的。由于当时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阻碍了日本与朝鲜的直接接触,因此,中朝宗藩关系和清政府对朝鲜问题的态度成为日本对朝鲜施行外交政策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中,清朝中国被定位于日本角逐朝鲜的对手和向朝鲜扩张的最大障碍。因此,对日本而言,朝鲜问题,不是对朝问题,而是对华问题。朝鲜问题的解决,最终要在中日角逐中得到实现。因此,为了在未来与朝鲜交涉时处于上位,日本采取对华强硬立场,使日清交涉先行。1870年,伊达宗诚全权代表到达天津与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就清日缔结条约反复谈判,日本方面执意要以《中德条约》为蓝本作为谈判的基础,目的是想从清政府得到与欧美列强同等的特权,表现出强硬的外交立场。
修改与欧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明治日本外交的另一个课题。根据《安政条约》的规定,到1872年7月,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修改条约。在如何改变与西方的不平等关系问题上,井上馨分析说:“一靠兵力,二靠和平谈判。”而当时日本的国力尚未达到可以依靠兵力解决而只能靠谈判时,就应致力于使“泰西各国对我国抱有应该撤销治外法权之感情。”[7]214为此,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为了在交涉中占尽主动,首先从搜集、整理、分析、比较研究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与其他各国所订立外交文件入手,找到了英国之所以能在外交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原因,从而强调今后日本在对外交涉中保护本国贸易的必要性。表现出遵从欧洲近代国际体系原理的对欧洲列强协调的外交姿态,并找到了未来日本应该规避的问题。在国内,为了创造能为列强认同的氛围,可谓煞费苦心,主张全面欧化的文明开化之风特别是“鹿鸣馆外交”都是为了迎合欧洲列强的努力和尝试。可见,日本之于欧洲近代国际体系的强权政治逻辑,不是去颠覆之,而是首先掌握其内部原理并小心翼翼地加以规避。在加入这个体系后,最终以对条约体系早慧者的姿态反过来将曾经束缚过自己的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东方近邻。因此,修改不平等条约“其目的不单是修改不平等条约本身,恢复日本独立,而是要创造条件,以应付正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政治局势。”[7]214
1876年1月6日,黑田清隆一行赴朝鲜进行正式谈判。谈判中,日本运用了近代国际法。黑田清隆对朝鲜方面的大臣说:“这个条约是基于天地之公道、万国普遍之惯例。”[23]这里的“普通”即普遍通用的意思,日本要求仍坚持锁国攘夷政策的朝鲜开国,就是希望自己也能与欧美诸国一样。处于内外交困的朝鲜政府终于在1876年2月27日与日本签订了《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规》,史称《江华条约》,日本实现了朝鲜的开国。
《江华条约》共计12条,不平等条款主要有:准许日本自由贸易,日本货物免纳关税。日本人可自由往来,租借地方,修盖房屋。准许“日本国航海者随时测量海岸”以及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等[24]。日本一方面与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又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邻国。
随着日本出兵台湾,迫使朝鲜开国等强权政治逻辑的演绎,美俄两国开始单独对日外交,1973年美国在对治外法权的解释上表示应该服从日本国内法律,并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观点[7]170-171。这对日本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有着特殊的意义。至此,应该说日本对欧美协调、对亚洲近邻强硬的双重外交路线达到了日本预期的目的。此后,日本与亚洲邻国愈行愈远,终于在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颠覆了几千年来的中日强弱态势。日本在东亚的异军突起,引起在东亚拥有巨大利益的列强的注目。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政府充分考量围绕中国的复杂国际形势,也因为日本当时的国力尚未达到能与欧美列强一决雌雄的程度,决定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前提对三国干涉采取忍让的态度。时任外相陆奥宗光表示:“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25]日本已经完全站到了列强的阵营。
[1]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5:52.
[2]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M].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36:227-328.
[3]吉野作造编.明治文化全集(2卷)[M].东京:日本评论社,1928:33-34.
[4]犬塚孝明.明治初期外交领导人的对外认识[J].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102号.1993(2).
[5]木村毅监修.大隈重信说谈[M].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186.
[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6卷)[M].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38.
[7][日]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大久保利谦.岩仓使团研究[M].东京:宗高书房,1976.
[9]木户孝允日记[M].(明治5年2月18日)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1980.
[10]小西四郎,远山茂树编.明治国家的权力和思想[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9:158-159.
[11]土屋乔雄.明治前期经济史研究(第1卷)[M].东京:日本评论社,1944:3.
[12]久米邦武.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M].东京:宗高书房,1975:329.
[13]田中彰.岩仓使节团[M].东京:讲谈社,1977:133.
[1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M].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38:367-377.
[15]吴廷璆主编.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407.
[16]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393.
[17]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M].东京:绿荫书店,1996:108-109.
[18]山本吉宣编.王志安译.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3:99-100.
[19]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20]片岡啓治.幕末精神日本近代史的异说[M].东京:日本评论社,1979:203-211.
[21]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再版第十九卷)[M].东京:岩波书店,1970:225.
[22]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4).
[23]安岡昭男.幕末维新的领土和外交[M].东京:清文堂,2002:18-19.
[24]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0:135-136.
[25]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