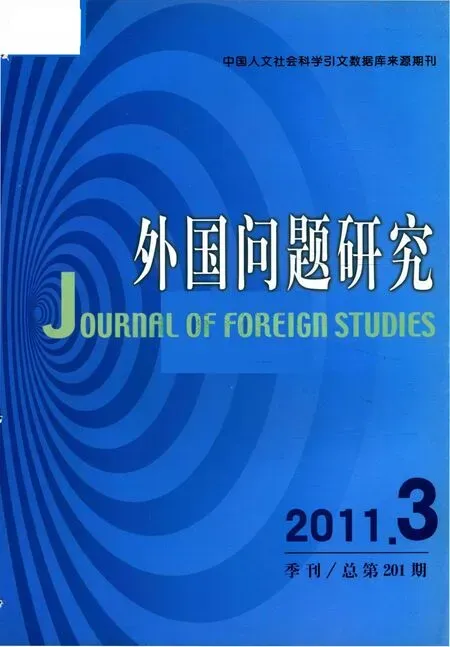《棉被》中的“新女性”形象
2011-03-20肖霞
肖霞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田山花袋(1872-1930)作为日本近代自然主义作家,其小说《棉被》(1907)被誉为是日本自然主义、私小说的代表作,在当时的文坛、评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也作了深入的探讨,或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的建构、特征出发,运用文本细读和比较的方法探讨《棉被》的价值与意义;或从叙事学角度对此进行研究[1]。本文试图从《棉被》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以女性主义视角来阐述《棉被》对“新女性”描写和塑造的社会意义。
一、《棉被》创作的社会背景
《棉被》创作于明治40年代,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对外侵略扩张、大力吸收欧美科技和社会思想文化的时期。日本人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他们能够更加自由、能动地关注自我的欲求,于是,“为自我”、“为个人”的主张开始成为时髦的话语。日本人学习西方、赶超欧美不再只局限于科学技术的国力增强,而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文化领域,他们感到日本与西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文化时差”。在“世纪末”思潮影响下的作家、诗人以及他们的文化活动,使日本与欧洲同步前行,第一次实现了日本与欧洲的“同时代”性。其中,积极介绍西欧文化,一直致力于启蒙活动的森鸥外、上田敏等人最敏感于这种“文化时差”,以焦虑的心态急切号召人们力争赶超,并将英法文学中的代表作家及时地介绍到日本。于是,以“新诗社”为中心,在由作家、诗人、画家和新闻撰稿人构成的文化界,形成了一股“世纪末”艺术思潮。同时,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信奉个我”、拥有“反社会生活类型”的“高等游民”,即“世纪末”人物形象。他们在《金与蓝的愁夜曲》(北原白秋)中过着“美酒加咖啡”的倦怠生活,将日本社会彻底导向一个追求享乐、唯美的消费社会。
从社会生活层面上看,明治30~40年代正值日本近代消费社会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迎来了百货商店的初创期,“三越”百货商店作为消费社会的象征,在经历了改制、重组后,按照美国模式以“股份公司”的形式重新登场。新创立的近代“百货商店”从和服、西装、家具、美术品以及儿童玩具到食堂、照相、剧场等文化生活应有尽有,可以说是一个将生活艺术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名副其实”的“巨大娱乐设施”。为了提高销售额,初创期的百货商店利用各种文化创意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以“流行”概念的普及勾起人们购物的“欲望”,刺激人们的消费,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在众多举措当中,“陈列贩卖方式”的采用取得了巨大的收效。它最初的意图只是为满足顾客的愿望,让顾客随意自由地“观看”商品,结果却使顾客不能只满足于“观看”的“欲望”。除此之外,百货商店一改过去的经营方针,从人们的心理欲求出发采用文化主攻战略,引导人们的消费。它们尝试创办刊物,利用有奖征文的形式提高商品销售的品位,吸引人们注意。利用各种传媒手段刊登广告,介绍应季的流行花色、有关服饰的知识以及穿着时的身体感受,并面对女性展开专门攻势。“明治30~40年代也可以说是百货商店PR杂志的创刊高峰”[2]31。方便的购物环境和周到的服务培养了一批能够“自由购物”的“中产阶层”。杂志广告的推广和通信贩卖的便捷很快使城乡融为一体,刺激着人们的购物想象,很快使“流行”一词在全国普及开来,有力地推动了消费文化的发展。
在这新旧交替、价值转换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面对现实而迷惘,因欲望不得满足而“焦虑”,因理想追求无果而“败北”,尤其是那些处于青春骚动、满怀理想的青年男女的内心因社会的浮躁而无法得到安宁。他们乘时代新风而不停地探求,寻找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途径,结果个个碰得“遍体鳞伤”,收到的是内心无法治愈的“伤痛”。田山花袋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实,在小说《棉被》中很好地展现了这一时期日本青年男女的形象。其中有“世纪末”思潮的影响,有自然主义文学的心理描写与告白,除此之外,作品涉及作为新事物的“新女性”(女学生、女教师),比较典型地描写了女学生的“堕落”过程。从小说女主人公来看,作为时代表征的“新女性”,即《棉被》中所描写的新女性代表人物芳子,依然摆脱不了日本传统社会强加于她的社会规范,她在受惠于消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成为落寞男性排遣自身焦虑和不安的消费对象。总之,小说展现了明治社会过度时期都市人的欲望与心理追求,再现了那个时代典型人物的窘境和心理纠结,是一部如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不朽之作。
二、男性视野中的“新女性”形象
在《棉被》中,男主人公“竹中时雄”原名“竹中古城”,从他的名字来看,本身就是个新旧矛盾的统一体。作者使其作为文学家、艺术家登场,可谓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作为“观看”的男性主体,由女教师到芳子,可以说是由远到近、由外及内地“观察”、描写了“新女性”的精神面貌。从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男性欲知女性的内面世界,以及不知是将其“作为新的主体,还是看作性的对象”的矛盾与苦恼。他对“新女性”的“观察”,主要体现在对女教师及芳子的外部描写上,借助与其妻子的比较,展示了近代女性的“新”,揭示了她们不论是作为行动主体,还是作为性的对象,都足以勾起“我”(时雄)的“欲望”。而对芳子的近距离观察与描写,旨在揭示“新女性”的内面世界以及“我”(时雄)欲知其内面世界的渴望之心。
《棉被》重点描写了当时的男性与女性对“新女性”的不同看法。起初,时雄作为芳子的文学教师,衷心希望芳子成为时代“新女性”,屡次对芳子说教:“女子也必须觉醒。像过去的女子那样具有依赖心是不行的。正如兹代尔曼的玛古达所言,从父亲手中立即转到丈夫手中那样无能实在没有办法,作为日本的新女性,必须独立思考、独立行动。”[3]75他列举了易卜生作品中娜拉的言辞、屠格涅夫作品主人公艾莱乃的话语,谈到俄罗斯、德国等国的妇女所具有的强烈意志与感情,转而指出:“所谓自觉,也包含自省之意,胡乱地卖弄意志与自我就不得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必须做好承担所有责任的准备。”[3]75-76在他看来,所谓“新女性”首先必须是“觉醒”的女性,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而对“觉醒”的理解,他认为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简而言之,觉醒的女性就要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负责,言外之意与别人毫无关系。他的理论使芳子感到“最有意义”,除了陡增“仰慕之情”外,还让她感到老师的教训更加“自由”和“富有权威”,她对老师充满感激之情。
小说中,时雄作为老师,要冠冕堂皇地坚守“道义之力”和“习俗之力”;而作为男性,面对年轻美貌的女弟子,他常常为身处“恋爱”和“并非恋爱”的处境而“痛心”。他认为自己与芳子之间“有无尽的缘分”,如果没有妻子的话,自己一定会娶芳子,芳子也会乐而从之。他甚至在内心深处把两人的未来都做了规划,即过着理想浪漫而又颇具文学性的生活。在二人诗意的栖居中,她会为他“寂寞的生活增添美丽的色彩和无穷的力量”,也会为他“消除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创作上的烦闷”,安慰他那颗“荒凉的心”[3]100-101。因此,他衷心希望这个多情而又漂亮的文学女弟子成为自己的妻子。因为按照传统观念,作为女性的芳子一旦离开父母,应该尽快找到另一个归宿,从属于某一个人。这反映了当时男性所普遍具有的既进步而又传统的女性观。
从表面看,男性与时俱进地号召女性尽快“觉醒”,追求自我意志的实现,但在内心深处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即希望女性或是尽快嫁人,或是独立行动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仅如此,时雄的封建意识还表现在“处女”崇拜上。在他看来,女子一旦以身相许便会完全失去自由,女子保持“贞操”甚为重要。他作为师长,引用当时甚为流行的近代恋爱观的话语,多次“殷切而又真挚地”就“灵的恋爱、肉的恋爱、恋爱与人生的关系、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应当坚守的东西等”进行说教,指出“灵肉一致”的恋爱至关重要,“日本的新女性”、“特别是新派女子”“一定要二者兼有”[3]88。但当芳子真正与田中恋爱时,他又陷入嫉妒并百般阻挠,由此可见,当时男性对待“新女性”的矛盾心态。
三、消费的“新女性”成为被消费的对象
从明治30年代开始,日本快速步入消费社会,百货商店销售战略的主攻对象首先瞄准女性。这种由男性“预谋”引导的消费文化,在不知不觉间轻而易举地对女性实行了“整编”。
日本学者小平麻衣子在对女性与消费的关系的研究中指出:“这样,自动购物的消费者就是被动性的了。而且,这种被动性才将消费者与女性性差结合在一起。因为在男权统治的社会里,所谓被动性就是被女性所允许的行动规范。在消费被公众所允许的形象渗透的时候,才会出现将消费者与女性结合起来的契机。”[2]36百货商店进入引导消费的新时代。在它们制定的销售战略中,首先将时装流行、色彩搭配与女性的肤色结合起来,培育新时代的美感及美人形象,在不停激发人的欲望的基础上培养人们树立新的消费观。当然,其话语言说的重点在于培养女性“被看”的欲望,使她们个个都想变成“比我更加美丽的‘我’”。在这里,消费无疑成为女性自我赌注的价值砝码,西方的时装模特儿被改装为日本的风俗偶人,陈设在商店的橱窗内。而后,由于玻璃制品的大量进口,镜子的普及使人们能够亲眼目睹自己的风采,女性的自我管理便成为可能。这样,不管是橱窗内摆设的女性,还是广告中出镜的女性,她们个个美丽动人、跃跃欲试,犹如“商品”一样展现在男人的面前,成为男性“观看”、“欣赏”的对象。与此同时,男女两性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女性作为商品的代言人,如同所代言的商品一起成为“诱惑”人的工具;男性作为欣赏者,他们有“观看”、“欣赏”和“买卖”的权利,更有“不买”的权力。也就是说,在日本近代步入消费社会的过程中,百货商店的销售战略直接利用女性,间接地将女性改编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被看”对象,再次明确地划分了男女之间的界线,规定了各自所属的文化范畴。更为直接地说,百货商店先是利用女性展开新的销售战略,后又将女性差别化,重新将其置于“被看”、“被欣赏”,即被男性“消费”的境地,女性的地位没有任何变化。
在这一时期刊登的小说中,那些具有旺盛购物欲的女性往往被描写成具有强烈性欲的人。她们疯狂购物的目的在于充分展示自己,而展示自己就意味着引起男性的注意,以唤起男人的性欲,表现了艺术与现实相结合的时代风俗。这一时期出现的代表性小说,如夏目漱石的《三四郎》(1908)、森田草平的《煤烟》(1909)、有岛武郎的《一个女人》(1911)等作品,而田山花袋的《棉被》则是这些同题材小说中的典型。他们都集中描写了明治40年代被“新女性”所唤起的男人“欲望”。这种“欲望”不是指男人的自我奋斗与理想追求,而是指男人想要“阅读”女性的内面世界,了解那些令他们无法琢磨的“女性之谜”的欲望。这是因为在消费社会成立的过程中,女性首先成为他们利用的对象,其后又被当做新的社会成员编入其中,使其成为近代社会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日本近代国家成立的过程中,女性首先被当做“性”的对象所利用,而后才被作为新的人类主体使其参与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而男性则一直徘徊于传统与变革之间,对女性身份的变更感到不可理解。他们一如既往地欣赏女性的美貌、才智,在女性纷纷接受近代教育、要求平等与自立的社会风潮中感受到社会的蒸蒸日上。然而,他们的内心也非常迷惘,不知道自己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该作何种选择,正如日本学者藤森清所言:“是将她们看作为新的主体,还是看作为性的对象呢?他们摇摆于二者之间”[4]195。其实在消费社会里,男性需要女性二者兼而有之。田山花袋及时地捕捉到这一社会现实,在小说《棉被》中塑造了男主人公时雄的形象,集中展现了过渡时期男性知识分子的苦恼。另一方面,借助女主人公芳子的形象,集中展现了在新的性差意识结构中的女性处境,即作为性与行动主体的女性追求以及她们欲望败北后的痛苦与绝望。作者以当时普遍具有的男性思维描述了自己对“新女性”的看法,以及“新女性”最后的下场。
四、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命运
在小说中,芳子作为“新女性”,不管从其思想愿望、文学追求,还是从其穿着打扮、交友方式来看,都超前、时尚。她自由、开放,纯真无邪;追求志同道合的爱情,甘愿为爱牺牲自己的一切。她与田中的恋爱属于自由恋爱,完全符合灵肉一致的近代恋爱观,这种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说明她完全可以承担所有的责任。她不折不扣地践行了老师的说教,本来应得到老师的褒奖与保护,然而,老师却以“温情保护者”的身份出来作梗,强烈的嫉妒心促使他要拆散他们。在“温情”拆散的过程中,他最为关心的仍然是芳子的“贞操”问题,即芳子是否已经属于田中了。当得知芳子与田中已经有了肉体关系时,他不是力求成全,使之早结良缘,而是坚定不移地予以拆散。为了保住自己作为“温情保护者”的面子,他写信将芳子的父亲——一个“旧式顽固的”、丝毫“不懂年轻人内心世界的老头”——叫来,巧借传统的势力给偷食“禁果”的年轻人施压。不仅如此,他还援引基督教的观点,强调人世间如同耶和华所思,罪恶深重的人只有等待神那强有力的审判,让偷吃“禁果”的年轻人在罪责中忏悔,从而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可以说,时雄“恰到好处”地将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砸”得稀烂,满足了一个男人的报复之情,充分暴露了他自私的灵魂。
芳子作为消费社会形成过程中典型的女性代表,无疑兼具新的社会主体与性对象两种特性,既是消费主体,又是被消费的对象。作为女性之一,她在无意识之中被巧妙地诱导至消费的大潮中,不管是在外貌特征、行为方式还是从知性方面,都是男性“观看”、“欣赏”的对象,然后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而被日趋内面化。“从女性方面来说,这种消费结构的内面化使女性的自我实现变得更加困难。女性总是在自己之外发现自己应该实现的自己,既然自己认识到还并非自己本人,她就会对现在的自己不抱有自信,因为她们只会一直抱有一个理想,即什么时候会成为真正的自己。而且,女性并非只是客体的存在,如果被分配为与男性性质不同的主体性,这样的自我认识就可归纳为欲摆脱只作为客体的存在而觉醒的女性。女性虽是女性之身,但越是抱有欲成就何事的真挚愿望,自己就会为不具有可称为自己的坚固的轮廓而焦虑、绝望。这一时期多出现女性的烦闷,除了不具备接受觉醒女性的环境这一理由之外,还可看作为与这样的自我认识有关。”[2]51-52
在小说中,田山花袋将芳子塑造成为当时的“新女性”形象,即她所追求的恋爱是发自内心的纯爱,灵肉一致不掺杂任何杂质。她既没有金钱的欲望,也没有门第观念,爱情是神圣的。为此,她可以中断学业,甚至靠打工去养活自己;更不怕断绝父女关系。总之,为了实现自我、成就爱情,她甘愿牺牲一切、抛弃一切。然而,在老师的精心安排与“操作”下,芳子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不得不改变态度,乖乖地顺从“师长”的安排,被父亲悄悄地带了回去。最后,她不是为了自我、为了爱情坚决抗争,而是以“我是女人”为理由选择了回归故乡,“埋没”自己的发展道路。对此,尽管她内心深处充满“不服”、“不平”和“悲哀”,不得不以“悲惨”、“暗淡”的心情“悲哀”地迎接返回乡下的“命运”,表现了当时“新女性”的无力、无助。面对不可改变的现实,芳子只有在内疚中埋怨自己,还要按照传统的方式维护老师的体面。如她在第三封信中写道:“承蒙老师教诲的、作为新的明治女子的事业,我没有去做。我仍旧是一个旧派的女性,没有勇气去践行新的思想。……请老师一定要可怜一下我这个可怜的女子。除了依靠老师之外,我无路可走。”[3]98可以看出,这段“告白”是芳子针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的表面归顺,也可看做是返乡后出于“礼貌”对曾经照顾过自己的老师的感谢。因为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尽管事情不顺,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但是,在推进过程中自己着实得到过他人的帮助,事后就要特意表达自己的谢意。否则,就会被别人说成是“没有常识”而后不与交往。这样,芳子在信中表现出深深的自责和对老师的“依赖”之情就可以理解了。其做法与信中对自己的定位、批判都让时雄感到十分满意,他高度评价道:“相信我的态度作为新日本的女性不为之羞愧”。从小说的结尾和对芳子的命运安排来看,田山花袋对社会上出现的“新女性”是持批判态度的。
从时雄关于“新女性”的说教与芳子的言词行为来看,当时社会上的知识男性所理解的“新女性”与真正“新女性”的思想追求完全不同。时雄代表了当时社会尤其是男性话语的普遍形态,面对日益增多的“女学生”和女性旺盛的求知欲,感到日益改变的新型男女关系无形之间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不知道自己应该支持还是反对,便以“羡慕”、“嫉妒”的心态追求,表现了男性的与时俱进。然而,作为生长于明治社会的当代人,他的身上同时残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希望芳子能按约定俗成的传统思路行事,当然不会允许芳子真正追求自我、成就恋爱。最后,在他眼里看到的尽是如同芳子那样“收拾好行李、被父亲领着返回故乡的女学生”。因为偏远的故乡正是落后、传统的空间象征,其传统的封建性足以“挽救”那些在都市直线“堕落”的“女学生”。面对当时喧嚣一时的女学生“堕落记”,他认为教育家争论的女子问题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从芳子来看,在男性引导主流价值观与消费的社会里,女子虽然接受教育,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觉醒与追求,但是,面对强大的男权中心的社会压力,女性仍然是软弱无力的。她们虽有愿望,但难以实现;虽有追求但总是败北;最后不得不被人当做“堕落的女学生”接受残酷的命运安排,从而丧失话语权,回归原来的出发点。
《棉被》与森鸥外、夏目漱石等作家的作品相比,作家跳出个人的视域局限,着眼于社会现实,及时捕捉到明治40年代的社会突出问题,力争在近代社会剧变及转型期、男女“欲望”的追求中展示社会的新生事物,揭示社会性差下的女性命运,为我们解读日本近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本。
[1]王梅.男性欲望与叙事——试比较田山花袋《棉被》与郁达夫《沉沦》[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3).
[2][日]小平麻衣子.女が女を演じる[M].新曜社,2008.
[3][日]田山花袋.蒲団[A].田山花袋集(明治文学全集67)[M].筑摩書房,昭和43.
[4][日]藤森清.『或る女』表象の政治学[A].総力討論ジェンダーで読む『或る女』[M].幹林書房,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