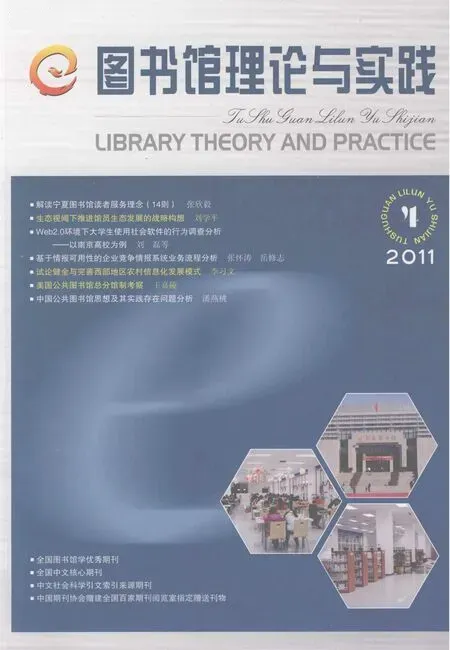简论元代易学典籍在辑佚方面的价值
2011-03-18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北京100875
●谢 辉(北京师范大学 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875)
元代时期的易学,可以说是一门获得了重大发展的学术。元代学者上承宋代重视易学的传统,积极地对《周易》进行研究和注释,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易学著作。据今人考证,元代的易学著作数量为“可知者共240种,确有流传者57种”,[1]在元代文献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些著作在易学史上的价值,可谓不言而喻;但若从文献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审视,则可发现其中还蕴藏着丰富的辑佚价值。具体而言之,其辑佚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宋元时期散佚的易学著作的辑佚,二是对《宋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的辑佚。
1 对宋元时期易学佚著的辑佚
在对宋元时期散佚的易学著作的辑佚方面,其价值体现在元代的集解体易学著作上。元代集解体易学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5部,包括李简《学易记》、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以及董真卿《周易会通》,①这些著作都引用了大量散佚的宋元易学典籍。如李简《学易记》卷首著录引用卜子夏等64家之说,自陈抟以下的60家,都是宋元时期的著作,其中已散佚或残缺者约37家。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目前仅存于日本,但据陆心源《仪顾堂题跋》记载,其书前列出的所集各家之说为63家,同时还有“引其说而姓氏未列者”[2]9家,其中宋元时期散佚或残缺者约42家。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卷首引84家,其中散佚或残缺者约46家。董真卿《周易会通》所引者最多,据学者统计,其“总共引用了三百一十五人的《易》说”,[3]其中两宋时期253家,元代22家,散佚或残缺者约105家。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所引各家之说,在元代集解体易学著作中算是最少的,经统计约为32家,其中散佚或残缺者也有16家。这些所引的各家之说,情况又不尽相同:有些是所引的易学著作与作者都明确可考者;有些是仅列作者姓氏而无名字,其著作亦不可考者;有些所引的人物本无易学著作,其说可能是出自其论述易理的文章或语录中。
因此,元代集解体易学著作中所引的宋元易学佚著,可能在100种左右。此前亦有学者已注意到了这一价值,如华中师范大学廖颖在其硕士论文《元人诸经纂疏研究》中,仅从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和董真卿《周易会通》中,就辑出了明确可考的宋人易学佚著110多家,尚未及元代,数量远多于本文所统计者。但其统计实际上存在着很多问题:一方面,其所列出的113家中,有50余家在《易本义附录纂疏》与《周易会通》中并无引文,仅存目于胡一桂的另一部著作《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中。胡氏在《翼传》中所列出的先儒著述,多达300余家,但实际采入《易本义附录纂疏》的,只有30多家。廖氏可能未及细考,遂将这些存目之著作一概收入,而不知其并无佚文可辑。另一方面,其征引还有着不少错误,如易芾《周易总义》、魏了翁《周易集义》、游广平(即游酢)《易说》、赵虚舟(即赵以夫)《易通》,现在都还存世,并未亡佚;徐古为与徐直方、李觏与李遇,实际都为一人,而廖氏误分为二;蔡攸《七易》则并无其书,实际情况是蔡攸曾于宋徽宗朝进上7种前代易学著作,包括干宝《易传》、东乡助《周易物象释疑》等,且撰有进表,故董真卿云“宋徽宗朝进七易”,[4]179廖氏却误以“七易”为蔡氏书名,等等。由于存在着这些问题,因此其统计恐难以为据。
除了以上所引的易学佚著之外,从元代的5部集解体易学著作中,还可以辑出一些目前存世的易学著作的阙文,这方面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张栻的《南轩易说》与耿南仲的《周易新讲义》。张氏之书,目前传世的四库本与《枕碧楼丛书》本,均只存《系辞上》“天一地二”章以下部分,但据董真卿记载,其所见者为“乾坤阙”[4]179之本,比今本完整很多,其所援引而可补今本之缺者约有30节。在董氏之前,宋代冯椅《厚斋易学》也对张氏之书有颇多引用,但其引文亦没有乾坤二卦的内容,所据之本可能与董氏相同,并不见得具有版本上的优势;其所引的文字与董氏也互有出入,正可彼此补足。耿南仲《周易新讲义》,今所存四库本缺第六至第十卷,而董真卿下至《系辞》部分对耿氏都有引用,可见其所用的应该是全本。冯椅《厚斋易学》同样大量引用耿氏之说,但也有数条是冯氏书无而董氏书有者。此外,在元代其余非集解体的易学著作中,也同样保存着不少宋元易学佚著的文字。如吴澄《易纂言》中,引用了数条范大性之说,据吴氏《王安定公墓碑》曰:“蜀人范先生大性,数十年寄隐……锓其所著《易辑略》以传。”[5]可知范氏乃蜀人,曾著《易辑略》,其书早佚。吴氏约与之同时,故能引用之。又如新安王埜翁,曾“撰《玩易彙编》,又有图说象数甚详”,[6]但其著作今亦不存,赖俞氏《周易集说》保存其数条佚文。其余如王申子《大易缉说》中保存玉井阳氏之易说,丁易东《大衍索隐》中引杨忠辅、申孝友、陈高、罗泌、徐侨、潘植、刘泽、冯大受、储泳、何万、古杭袁氏等人之说,许衡《揲蓍说》中记载了耶律履《揲蓍说》的内容等。由此可见,元代易学著作中存在着大量宋元人易著佚文,在辑佚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前杨倩描辑录王安石《荆公易解》,即从李简《学易记》、俞琰《周易集说》、董真卿《周易会通》中,辑出了数条不见于他书的重要佚文,①杨氏所辑《荆公易解钩沉》,载《王安石易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104页。元代易学典籍在辑录宋元易学佚著中的价值,也由此可见一斑。
2 对《宋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的辑佚
《宋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是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史馆为《中兴四朝国史》所编制的一部史志目录,其材料来源是《中兴馆阁书目》《续中兴馆阁书目》以及理宗时期搜访所得的“嘉定以前书”。与主要记载北宋时期典籍的《三朝志》《两朝志》《四朝志》相比,《中兴志》收书数量较为丰富,②《中兴志》的具体收书数量虽未有统计,但据其序言,其所采的《中兴馆阁书目》数量为44000余卷,《续中兴馆阁书目》为14000余卷,合之接近60000卷,《中兴志》的数量当还在其上。相比之下,《宋史艺文志》记载《三朝志》39000余卷,《两朝志》8400余卷,《四朝志》24000余卷,数量都要少于《中兴志》。是宋代官修史志目录的重要代表著作。此书在元代时期尚有流传,如马端临曾引用过该书的内容,元代末年官方修撰《宋史》时,也将该书作为修《艺文志》的主要依据之一,但元代以后便散佚无存。民国时期赵士炜曾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主,辑得一卷,仅46条,较原书差距很大。③赵氏《宋中兴国史艺文志辑佚》,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4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621—4644页。但在元代胡一桂的易学著作《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与董真卿的《周易会通》中,却还能发现不少该书的佚文。
胡氏的《周易启蒙翼传》分上、中、下、外4篇,在中篇的“传注”部分,胡一桂采集多种前代目录,再加以自己搜访所得者,共得宋代之前的易学著述300余家。而其所采用的各家目录中,就有“宋艺文志”一种。董真卿《周易会通》书前所列的先儒之说,多达300多家,其中也有一些是标明出自“宋志”。据胡氏与董氏自序,《周易启蒙翼传》约成书于元皇庆二年(1313年),《周易会通》约成书于天历元年(1328年),此时元代官修的《宋史》还远未开始纂修,因此二人所采的,绝不可能是《宋史艺文志》,而只能是宋代的4种《国史艺文志》中的一种。再从二人所引出自所谓“宋艺文志”的易学典籍来看,有不少是南宋人的著作,如冯椅即是如此,如果二人所引的是北宋3种《国史艺文志》,那么南宋人的著作就不应该出现在其中。所以真正为二人所采用的,应该是南宋时期的《宋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以下简称《中兴志》)。此前《四库全书总目》已对此有所发觉,在冯椅《厚斋易学》提要中,即引胡氏之说,而称之为“胡氏《启蒙翼传》引《宋中兴艺文志》”,[7]可见亦是认为胡氏所引的“宋志”当为《中兴志》。
经统计,《周易启蒙翼传》中标明出自《中兴志》的易学著作,共有44家,《周易会通》中有4家。
将所辑得的《中兴志》的内容与赵士炜辑本进行比较,便可看出:赵氏辑本于易类仅辑得两家,于《中兴志》原来收录的140家的数量差距巨大;而上面从胡、董二书中辑得者则多达48家,其中只有冯椅《厚斋易辑》一家与赵氏辑本重复,其余均为其所无。据马端临记载,《中兴志》易类部分收录著作的数量为“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六卷”,[8]而从胡氏与董氏之书中辑得48家,即占了原本大约1/3的内容,这对《中兴志》的辑佚工作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除了以上的44家著作外,《周易启蒙翼传》中还保存了《中兴志》经部易类小序的一部分内容。宋代的4部《国史艺文志》,每类均有小序,可算是宋代官修史志目录的一大特色。但这些小序现在基本全佚,民国时期赵士炜遍辑4种《国史艺文志》,却连一段小序也未辑到,因此,保存在《周易启蒙翼传》中的这一部分《中兴志》易类小序,就显得弥足珍贵。就目前所见而言,胡氏书中标明出自“宋艺文志序”的共有4段,现将其分别采录于下:
汉以来,言《易》者局于象数,王弼始据理义为言,李鼎祚宗郑玄,排王弼。国朝邵雍亦言象数,及程颐传出,理义彰明,而弼学浅矣。张载、游酢、杨时,郭忠孝、雍,皆祖颐。髙宗时,朱震为《集传》,其学以颐为宗,和会雍、载之论,合郑王之说为一,兼取动爻、卦变、互体、五行、纳甲。至郑刚中为《窥余》兼象义。(以上第一段,见朱震《集传》一节,《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中篇《传注》部分,第二、四段同)
该本《春秋左氏传》占法论爻变。(以上第二段,见沈该《易小传》一节)
孝宗时,程迥所作《易考》十二篇,别为章句,不与经相乱。(以上第三段,见程迥《古易考》一节,《周易启蒙翼传》中篇《古易之复》部分)
宁宗时,冯椅为《辑注》、《辑传》外,犹以迥、熹未及尽正孔传名义,乃改“彖曰”、“象曰”为“赞曰”,以繋卦之辞即为《彖》,繋爻之辞即为《象》。王弼“彖曰”、“象曰”,乃孔子释《彖》、《象》,与商飞卿说同。又改《繋辞》上下为《说卦》上中,以《隋经籍志》有《说卦》三篇云。(以上第四段,见冯椅《厚斋易辑》一节。此段文字赵氏辑本亦有采录,但却据《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其为冯氏书之提要,而不知其实际出自小序)
以上所辑得的4段序文中,第一段与第二段大致是概述宋代易学发展的情况,句法也有前后衔接之处,应该可以归为一类;第三段和第四段则是专论程迥、冯椅对古《易》面貌的讨论,亦可归为一类;两类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估计中间会有一定阙文。但仅从这4段文字中,已可窥见《中兴志》小序梳理学术源流、总论各家学术特色的基本特点,可以说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资料。而胡氏书保存了这些小序的片段以供后人辑录,同样也是功不可没。
元代易学典籍在辑佚方面的价值,大致即如上所述。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元代易学著作既多,其所征引的各种典籍的数量亦很丰富。这些被征引的典籍,有一大部分现在已不存于世,或者虽存而残缺,因此,元代易学著作理应成为辑佚的重要来源,其在辑佚学上的价值应该引起学界的注意。
[1]黄沛荣.元代易学平议[C]//元代易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162.
[2](清) 陆心源.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Z].北京:中华书局.2009:23.
[3]许维萍.董真卿《周易会通》在“复古《易》运动”中的意义[C]//元代易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318.
[4](元) 董真卿.周易会通[M]//通志堂经解 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5](元) 吴澄.吴文正公集[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560.
[6](元) 俞琰.读易举要:卷4[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清)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2003:15.
[8](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Z].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