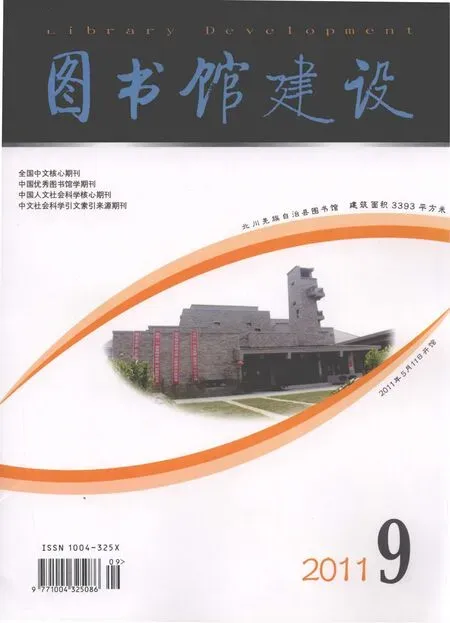数字时代海外中华古籍的回归
2011-03-18苏州大学图书馆江苏苏州215123
张 敏 (苏州大学图书馆 江苏 苏州 215123)
董 强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古籍是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海外中华古籍的回归历来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面启动,加快了海外中华古籍回归的进程。一方面,传统的古籍回归形式(如实物回归、出版形式回归、影性式回归等)在新时期有了新的进展;另一方面,古籍数字化的范围拓展至海外,嘉惠中外读者,影响深远。这不仅成为国际图书馆间文献资源共享的典范,而且使以数字化方式解决古籍保护与利用矛盾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达成共识。
1 传统回归方式与传承
1.1 出版形式的回归
1.1.1 海外中华古籍书目的出版
探究海外到底存有多少中华古籍是开展古籍回归之路的敲门砖。20世纪90年代是海外中文善本书目出版的分水岭。90年代之前,国内学者对海外中文古籍的关注仅限于零星的个别海外图书馆,成果亦相对较少,影响有限。如裘开明先生于1938—1940年编撰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共3册),台北艺文印书馆于1975年出版了屈万里先生校订补充的《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等。90年代之后,海外中文古籍整理面貌为之一新。先后有《东洋文库所藏中国古籍目录》、沈津著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李国庆编著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录》、陈先行主编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严绍璗编著的《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录》、乔晓勤编撰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达西安娜和吴云编著的《西班牙图书馆中国古籍书志》等较有影响的善本书目及书志问世。这些著作不仅使国人进一步了解了国外馆藏的中文善本,而且其本身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例如,《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一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版本考订,理清了各古籍版本的异同及相互间的联系,对各书所涉及的源流与异同、原刻与翻刻、初印与后印等问题[1],也尽可能作出了充分的揭示。1.1.2 海外中华古籍全文出版
在原件不能回归的情况下,海外古籍以出版形式回归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如流失于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的出版。其代表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纂的《英藏敦煌文献》(15册)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17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2005年启动整理、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前正由法、英两国的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西北民族大学专家加紧整理,按计划万件流失于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献将于2012年前在中国影印出版。至此,除日本所藏敦煌文献外,流失于海外的敦煌文献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出版[2]。
近年在日本所藏中文古籍的全文出版中较有影响的是由线装书局影印出版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1辑、第2辑),共21部,其中不少是海内外孤本,如第2辑中的《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一书刻工精良,首尾完具,惟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有藏,在学术界影响较大。该书的第1辑在出版后两个月即销售一空,并在读者和专家的建议下,重印时增加了函数和册数。
1.2 实物形式的回归
1.2.1 以拍卖竞价回收为主要形式的实物回归
中国政府和民间团体一直致力于古籍回归工作,建立了健康、有序的回流机制。2002年,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启动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同年,由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与文博界专家、社会知名人士等在北京共同创设了“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20世纪末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分别以800万元购得《孔子弟子像》(手绘善本)、990万元购得《钱境塘藏历代名人书札》,1997年上海市政府斥资450万美元将“翁氏藏书”整体从美国迎归[3]。海外华人基于爱国之情也不断将获得的古籍捐赠给祖国,2008年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行拍得战国时期竹简2 100枚,全部捐赠给了清华大学[4]。
1.2.2 外国政府主动归还及依据相关国际公约追索
《永乐大典》 的流散与回归是近代以来中国流失海外古籍命运的缩影。《永乐大典》现存只有380册左右,不到原书的4%,而且分散在十几个国家的30多个机构,其中英、美、德、日等国家收藏的数量较多[5]。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之所以会流失海外,进行野蛮侵略的帝国主义列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世纪50年代,苏联曾归还过一批《永乐大典》。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国,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向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移赠1册[5]。当时的东德也赠还我国3册[5]。我国是《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的主要起草国之一,根据两个《公约》的条款,我国政府应在法律的范围内积极展开流失海外古籍的追索工作。
1.3 影性式回归——学术调查与追踪
对海外中华古籍的摸底调查和追踪是开展其他回归方式的前提。日本是除中国大陆地区之外收藏中华古籍最多的国家,就日本目前所藏的中华历代文集而言,元人文集以静嘉堂所藏为多,其次是内阁文库和宫内厅的书陵部;而明人文集则以内阁文库最为丰富,其次是尊经阁文库。日本学者山根幸夫的《日本现存元人文集目录》和《增订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对日本现藏元明文集作了全面的著录。国内学者严绍澷先生从1985年起开始对日本所藏汉籍进行系统的调查与著录,足迹遍布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金泽文库等重要汉籍收储机构,在汉籍东传的轨迹与形式、日本汉籍目录学、日本刊印汉籍、甲骨文与敦煌文献东传日本以及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的劫掠等方面都有突破性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
2 数字化回归——典型数据库介绍
2.1 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
1991年,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 ( Research Libraries Group,简称RLG ) 建立了“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该项目主要由普林斯顿大学负责,后发展为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中外共30余家图书馆参加了此项目[6]。这是第一批以数字化形式回归我国的海外中华古籍,数据涵盖了北美图书馆的几乎全部藏书及中国图书馆的部分藏书,共计2万多条[6]。该系统自2010年5月20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开通以来,公布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约3 000条中文古籍善本数据[6]。
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收录了清乾隆六十年(1796年)以前在中国印刷或抄写的中文古籍,但是,日本、朝鲜等非中国境内印制的中文古籍及满文、蒙文、藏文等非中文古籍(包括中文与其他语言合璧的文献)不在收录范围之内[6]。该书目系统的著录内容包含题名、责任者、版本信息、行款版式、存卷及补配情况、题跋钤印等14项,几乎每部书都配置了首页书影,相较目前国内许多古籍书目数据库只作简目的著录现状,堪称完备。这种较为详细的著录方式方便读者窥知书之全貌,如通过看钤印便可知前人递藏源流,借以考见古籍之真伪。再如详细的题跋之文对于帮助了解该书的学术价值、版本源流等意义非凡。该系统免费开放,提供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3种界面,用户可以自由检索、浏览、打印、下载书目数据及书影。
2.2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影像数据库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创办于1941年,当时为东京帝国大学的附属研究所,创办至今已近70年。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古籍包括原东方文化学院、大木文库、仓石文库等机构的藏书,这些藏书绝大部分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购买的,共计10万本[7],且其中包含相当多的孤本、善本,不管是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称得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汉籍收藏。20世纪90年代,该研究所开始建立古籍目录数据库,从2002年开始建立古籍全文影像数据库,并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开放性服务。
进入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影像数据库,读者可按照经、史、子、集进行分类浏览。这批数据包括收藏在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一些专藏文库中的珍贵的宋、元、明、清善本和民国时期抄本,其中以小说、戏曲为大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截至2009年3月,该数据库展示了包括A类(不设限)、B类(限特定机构才可浏览全部的影像)古籍在内的共4 630种古籍[7]。2009年11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将所藏的4 000余种中华古籍以数字化方式无偿提供给中国国家图书馆[7],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面向读者提供服务,这是海外中华古籍数字化回归的又一重要成果。
2.3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所辖哈佛学院图书馆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受到哈佛燕京学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在图书购置经费上的支持。其馆藏中华善本古籍特藏以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大著称,如各地的方志、丛书及宋元明清善本、钞本、拓本、法帖等,甚至有不少孤本,为西方大学图书馆之冠。
为方便海内外学人便捷地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同时以数字化形式保存这些中华古籍精品,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哈佛大学图书馆计划用6年时间(2010年1月—2015年12月)合作完成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所有馆藏中文善本和齐如山专藏(以戏曲、小说为主,内有不少传本较少、版本价值较高的善本)的数字化,即中文善本古籍4 210种、51 889卷的数字化拍照[8]。
目前,读者可以查到首批发布的中华古籍善本(包含齐如山专藏共204种),并可按照书名、著者、出版信息、分类等进行检索和分类浏览,书目信息为中英文对照,同时可以在线阅览全部书影,均为免费[8]。这一项目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历史上与国外图书馆合作开展的规模最大的文献数字化项目,项目成果分别发布于各自网站,供其他学术研究及文献保存之用。
2.4 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
日本收藏有大量的中文古籍,且十分重视中文古籍的整理和编目。2001年3月,由日本国立信息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研究信息中心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原汉字信息研究中心)等诸多机构共同参与,正式成立了全国汉籍数据库协商会,并由此开发了“全国汉籍——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全国汉籍デ一タベ一ス)”系统。该数据库分两期建设,每期5年,一期项目首先集合日本所有入藏汉籍机构的目录,目前已有67所公(私)收藏机构所藏中文古籍书目记录约80万条,读者在网上可直接登录“全国汉籍——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输入繁体中文查询,有书名、作者、刊期、出版者、子目及关键词6项检索方式[9]。第二期项目则主要开发重要古籍的提要和重要版本的全文影像信息。
该数据库虽没有中国图书馆参加合作,但用户可以在网上自由查询,所以可以直接了解某种古籍在日本的收藏情况。目前它是日本参与机构最多、搜索范围最广的汉籍数据库,通过查询目录便可知在日本收藏有中华古籍的各大公(私)立图书馆的大致馆藏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该数据库具有联合目录性质,是一个动态的网络数据库,数据内容不断更新、增加,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目前推荐和使用频率较高的海外中文古籍数据库之一。
3 海外中华古籍回归之路的思考
海外中华古籍的发掘、利用有利于国内学术研究和国际汉籍研究以及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历史上中华古籍流失与散佚海外渠道众多,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回归了一部分,但仍有大部分珍贵古籍保存在异国他乡的图书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对于承载着厚重中华文明的古籍,我们有责任保护与传承,用多种方式让其早日回归祖国。
3.1 传统与数字化两种方式回归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国际合作开发海外中华古籍数字化资源,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有开拓前景的领域,这一点在业界已达成共识,但不可以忽略传统方式下的回归,两者相辅相成、殊途同归。
首先,海外中华古籍回归尤其是善本回归,其本身就是中华文物的回归,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努力使中华古籍以实物形式回归。其次,以出版书目和全文为主的回归模式已有多年的经验可循,同时也是进行海外中华古籍数字化回归的学术基础。再次,大量的海外中华古籍流布状况仍需中外学者孜孜不倦的摸底调查,否则海外中华古籍回归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最后,海外中华古籍的数字化回归将是今后工作的重点。目前,国内古籍数字化工作正有序展开,大批古籍文献走出公(私)藏书之家,化身千万。国外的中华古籍资源虽已有一部分进行了数字化,并且有的数据库已相当完备,堪称典范,但从数量上来说,仍是沧海一粟,任重而道远。对于浩如烟海的海外中华古籍,无论是提供精善的版本著录信息的数据库,还是以提供全文影像为特色的数据库,在网络共享的基础上,都将大大改变国内对传存于海外的中华古籍利用不够的现状。
3.2 海外中华古籍的回归需要中外合作主体更为广博的胸襟
近年来,我国学者赴海外留学或访问的机会逐渐增多,许多国外图书馆和学术机构也主动邀请国内学者帮助他们编辑中文文献目录和合作完成古籍数字化项目,如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西班牙图书馆邀请国内学者共同参与本馆善本书志的撰写工作。国内以北京大学古文献所为代表的多家高校图书馆都已根据项目研究的需要从海外引进了相当数量的珍本古籍,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与海外多家图书馆合作,建设了规模庞大的中华古籍特藏资源库。
这些世界文化交流的新动态使国内对国外的相关收藏逐渐有所了解,亦加快了海外中华古籍回归的进程。但目前的合作仍属于初级阶段,海外中华古籍的发掘与利用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古文献特别是善本的开放程度,让更多的国内外专家合作交流,仍是今后海外中华古籍回归的重点与难点。
3.3 国内古籍人才的培养是海外中华古籍回归的前提与保障
海外中华古籍的回归需要一代又一代古籍工作者的努力,古籍专门人才的能力直接决定了未来古籍事业的兴衰。图书馆在人才引进和管理理念、管理机制上要有意识地加强古籍数字化人才的培养。首先,要意识到古籍整理人才是复合型人才,其除了要掌握中国古籍文献的分类、版本鉴定、编目知识外,还需懂得数字化处理的相关技术。其次,古籍人才的培养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良好的学习环境。最后,古籍整理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古籍工作者多实践、多做笔记、多查书、多请教专家[10],才能练好基本功,从而才有可能在古籍专业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国内不少古籍收藏丰富的图书馆拟撰写本馆的善本书目,借此机会可以安排年轻的馆员在老馆员的指导下“练兵”,为以后写善本书志和古籍数字化工作打下基础。以前受邀到国外做中华古籍整理工作的学者多为老专家,将来需创造机会让中青年学者去国外锻炼,发扬海外中华古籍资源的传世功能。
[1]陈先行. 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后记.
[2]府宪展. 寻找敦煌的海外游子:流失海外敦煌西域文献文物的编纂出版[J]. 敦煌研究, 2006(6):194-195.
[3]潘德利. 流散海外中国古籍的回归与思考[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147-149.
[4]清华简:发现中国最早史书[EB/OL]. [2010-01-10].http://scitech.people.com.cn/GB/8278027.html.
[5]安平秋谈海外流失古籍[EB/OL]. [2010-01-10].http://chinese.pku.edu.cn/cnpkuen/artDetail.jspx?channelArtId=382.
[6]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EB/OL].[2010-01-10].http://res4.nlc.gov.cn/home/index.trs?channelid=630.
[7]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影像数据库.资源介绍[EB/OL].[2010-01-12].http://res4.nlc.gov.cn/home/index.trs?channelid=629.
[8]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简介[EB/OL].[2010-01-14].http://res4.nlc.gov.cn/home/index.trs?channelid=724.
[9]全国汉籍デ一タベ一ス: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EB/OL].[2010-01-16].http://www.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10]钟稚鸥. 如何培养古籍专业人才:与沈津先生座谈纪要[J].图书馆论坛,200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