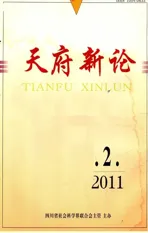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接受新论
2011-03-18冯利华
冯利华
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接受新论
冯利华
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维护忠义伦理,广受读者喜爱。学术界对其思想倾向多持贬抑态度。社会主流文化、价值标准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有明显的影响和制约。审视社会主流道德与小说的接受效应,公案侠义小说思想主题的形成,纯属自然,是民间道德价值取向的“集体无意识”,其良好的接受效应,反映平民阶层对社会道德本体的认知自觉,展示出儒学的道德感召力与民间影响力。
公案侠义小说;接受效应;儒学伦理;道德本体;认知自觉
清代中后期,公案侠义小说维护忠义伦理,获得了极好的接受效应。精英与平民皆喜阅之。然而,学者对其思想倾向多持贬抑态度。一些学者无视其接受影响,将此类小说视为文学发展中的一股“逆浪”。作为文学文本的现实消费者与传播者,读者在文学接受中有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再现或表现的功能,而且在于它的影响之中。”〔1〕读者接受决定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作用不容忽视。本文拟通过《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等小说的民间接受效应,探讨其主题自然形成所传达出的平民阶层的道德价值取向及其对正统伦理的自觉认知。
(一)
《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等公案侠义小说,皆以正邪、忠奸、善恶之斗争为基本情节冲突。施仕伦、包拯、彭朋等清官,率领黄天霸、展昭等侠士,上忠于国君、下恤于黎民,激情昂扬地主持社会公正,维护忠义伦理。清官与侠客之间,不再是前代侠士、门客与贵公子之间的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的低层次物质满足,而是爱国忠君、维护大道,为共同政治目标奋斗。吴士余指出,小说是展示生活、历史和自然因果的载体,“小说叙述的美学意义,不是摹写生活、复述故事,或者释放自我意识,而是通过情节的叙述来显示一种价值”〔2〕。综观公案侠义小说,我们必须承认,其基本价值取向是维护儒学伦理,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云:“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必不背于忠义。”〔3〕
其主题思想源自儒学伦理。在人生价值方面,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忠孝统一的最高境界就是朝廷为官,显亲扬名。《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4〕“孝之终”,即最大的孝道。富贵功名便是人生价值之最高体现。公案侠义小说中,侠客们的人生状态已不再是任侠放纵、快意恩仇、浪迹江湖,而是为国为民,以建功立业、光宗耀祖。黄天霸毫不隐讳对功名、正道的热衷:“小的为老爷,只为图名上进。”〔5〕他因保全对施公尽忠的大义,竟杀兄逼嫂。展昭追随包公,官封四品,即回乡祭祖。丁兆兰以报效国家为男儿本色:“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6〕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俱愿为朝廷效力,以遂功名。在社会礼教方面,儒家认为,“礼”既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守则,也是实现理想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孝经》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7〕《礼记·曲礼上》强调礼制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至关重要性,“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8〕,“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9〕。儒学之男女伦理,要求 “发乎情,止乎礼”,必须遵守“男女授受不亲”之原则。宋明理学甚至将其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塑造的正面人物皆是道德楷模。展昭路遇妇女痛哭,欲行侠相助,“又恐男女嫌疑。偶见那边有一张烧纸,连忙捡起作为因由”〔10〕。徐胜被淫邪美妇九花娘百般挑逗而心如止水,坚守社会礼教,不越雷池一步。反之,小说对纵欲淫邪、贪恋酒色等有伤风化等违反礼制之行则深恶痛绝,严厉批判。白莲花、尹亮等采花淫贼,被清官、侠客联手惩治。九黄、七珠、飞云僧等恶徒,拐骗、诱奸良家妇女,终受严厉惩罚。
社会共同道德价值标准对小说的思想倾向有明显的影响作用。无疑,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思想倾向于倡导儒学价值。谢桃坊认为,文学创作力图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它必然受到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观念影响,表现出一种思想和艺术的倾向。这种创作倾向如果体现了时代的审美理想,即体现了人们关于至善至美的生活的追求和至善至美的人的观念,则其价值的等级总是与精神生活的等级相一致的。精神生活等级里自然包含了道德价值”〔11〕。显然,其主题本无可厚非。遗憾的是,学者对其多持贬抑态度。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此类小说宣扬封建思想糟粕,腐朽、反动,是文学发展中的一股“逆浪”。我们姑且将此类含贬抑之意的观点统称为“逆浪说”。
在此类观点中,胡士莹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其《话本小说概论》明确指出:“影响最坏的是清代的所谓公案侠义小说。话本小说发展到清代,短篇话本逐渐衰歇,而长篇话本却在公案侠义小说这一门上畸形发展,成为长篇话本发展过程中最后一个浪头,也是影响最坏的一个逆浪。”〔12〕胡氏认为,此类小说宣扬忠君思想,用侠义来腐蚀人民,“不是宋、元、明市民欣赏肯定的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市民文学”〔13〕。曲家源强烈批判《三侠五义》的思想倾向,“歌颂的是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膝、为维护封建统治奔走效劳的奴才性格和奴才人物”〔14〕。我们应该看到,无论社会思想、人生追求与科学水平,古代专制社会都与今天存在巨大差异。如果在文学研究中,不知人论世,而以今非古,那么其结论的合理性就颇应商榷。齐裕焜亦持逆浪说:“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来考察,公案侠义小说就其总体来说,并不代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前进潮流,表现了逆转的趋势”,“从公案侠义小说内部来看,发展的趋势是逐渐走下坡路”。〔15〕曹正文虽未明言 “逆浪”,但其《中国侠文化史》对此类小说的贬抑之意溢于言表。他指出,“《施公案》与《彭公案》的作者是站在封建意识的立场上,把奴才歌颂为英雄,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16〕,总的倾向是反人民的。古今教授的批判态度亦十分强烈。他认为,《施公案》这类作品,“侠客不再反抗官府,而是归顺大清王朝,帮助统治阶级去捉拿、剿灭所谓 ‘强人’、 ‘恶霸’”〔17〕,其基本思想倾向是反动的,读者最好远离它们。言下之意,侠士就应该浪迹江湖、对抗官府,而一旦效忠朝廷,由叛逆转向建功立业,反而是错误的。对公案侠义小说的思想倾向持批判意见的学者,还有刘世德、邓绍基、王俊年、罗嘉慧等,可谓不乏其人。罗嘉慧甚至称其是文化上的倒退:“这样一种文化追求在清代已完全变质,以塑造‘为一大僚隶卒’的鹰犬式侠客的侠义小说,标志着这一时代的大众的文化境界并没有随着时代进入近代,而是在倒退,退回到中世纪,与急剧变化的近代历史进程有明显的落差。”〔18〕。
公案侠义小说果真如此不堪吗?恐怕未必。事实表明,其接受效应极为良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施公案》“久已海内风行;南北书肆,各有翻刻”〔19〕,“能使天下无数平民听了不肯放下,看了不肯放下”〔20〕,以至于“无人不知有黄天霸者,即无不知有《施公案》也”〔21〕。《三侠五义》成书,“令社会嗜好为之一变”〔22〕,“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23〕。《彭公案》则“人喜阅之”〔24〕,不仅平民喜好,而且精英阶层亦大力提倡。石庵称,此类小说被统治阶级认可,甚至“上等社会中巍巍执政诸公,亦若深受此书之魔力”〔25〕。它们极为畅销,续书亦大量涌现,甚至被一续再续,“构成了古代小说史最后一个热点”〔26〕。
我们探讨作品的现实意义,必须结合其社会接受效应。读者通过既有的期待视野能动地选择适合其审美需求的作品,如接受美学所云:“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27〕如果真的是反动、倒退,那么公案侠义小说何以风行社会?如果宣扬儒学伦理就是逆浪,那么我们又当如何审视其如此良好的接受效应?毫无疑问,胡士莹、曲家源、古今、齐裕焜等学者在其研究领域都有很大的建树,对我国古代小说的整理、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逆浪说”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带有阶级批判的色彩,忽视了公案侠义小说在民间的广泛影响。我们应结合儒学伦理的社会影响,客观地探讨公案侠义小说思想主题与接受效应之关联,评判其文学接受意义。
(二)
在对人性及个体行为的规范上,社会道德至关重要。就现实生活而言,人的道德意识源于其实际所处的经济关系。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28〕儒家伦理源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代宗法社会和专制集团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社会发展的道德需求。郭英德指出:“政治伦理和道德规范的信持就至关重要,关系着社会政治的安危治乱。”〔29〕对社会政治的发展,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漫长的专制社会里,在精英阶层的倡导与统治者的推行下,儒学逐渐成为社会文化主流与道德价值体系核心。其伦理作为本位道德,展示出在维护社会秩序、整肃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
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文化、价值判断。其主题内涵必然受主流文化与道德价值标准的制约与影响。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指出,“中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伦理道德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以及各种观念,如认知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出发点与归宿”〔30〕,而小说是寓理性思维于感性形象的艺术,“通过情节展现人生命运的描写来表述一种人生观念,倡导一种理想的社会伦理道德”〔31〕,儒家文化对中国小说创作有重要影响,“使小说家在不同生活层面的审美中表现了一种对政治教化和道德本体化的思维认知自觉”〔32〕。所谓创作者的道德本体认知自觉,指在小说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中自觉融入主流道德观。从这个角度看,儒学对文学作品的渗透是何等自然,“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思想行为的准则,长期渗透,并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要素,自然也渗透到作家的审美意识和文学观念之中”〔33〕。在其影响下,中华文化历来重视道德伦理教化。公案侠义小说亦如是。其成书,不可能割裂与时代文化、现实人生的联系。公案侠义小说大多是根据民间艺人的说唱,经多人加工创造而成,体现民间集体价值判断。其创作者与接受者不可截然分开。李惠芳指出:“民间作者可能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在进行艺术创造,但他却能自觉地意识到,他的讲述是直接为对象而发的,或是进行道德教育,或是进行道德评价,或是进行道德审判。”〔34〕
就文学对于接受者的情感影响而言,它以语言的形式传达价值观念,调节人的情感张力。人类普遍期望社会公正,向往真、善、美。关爱和指出,人性的底蕴包括“对恶的憎恨,对善的赞美,对美的追求,对英雄之性的敬仰”〔35〕等原则和情感流向。小说作品既要让读者获得审美愉悦,又要唤起其道德感悟。接受者的道德本体认知自觉,表现为对作品道德价值取向的积极认同。大众化的小说作品必然是在反映一定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传达普遍的理想观念,才能产生广泛的接受效应。公案侠义小说的流传与接受,受普通民众的道德意识的影响与制约。李惠芳认为:“民众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这一积层,深厚而复杂:既有古代原始信仰的遗留和传承,也有后世关于伦理关系、人生态度、善恶是非、生死观念、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历史认同。”〔36〕经统治阶级长期推行、潜移默化,平民阶层自然将儒学伦理作为普遍认可并自觉遵守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判断标准,以此实现自我认同及社会群体认同。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历经民间众口相传而成书。《三侠五义》源于《龙图公案》。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云:“少时即闻乡里父老,言施世纶为清官。入都后,则闻院曲盲词,有演唱其政绩者。盖由小说中刻有《施公案》一书,比公为宋之包孝肃,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传,至今不冺也。”〔37〕《彭公案》的成书,亦是杂采民间传说。它们凝聚着民间的智慧、情感,体现民众的思想观念。鲁迅认为:“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38〕他并不否认通俗小说的正统道德教育意义。《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维护正道,鞭挞假、丑、恶,肯定真、善、美,体现民间接受者的道德价值取向。他们既从惊险新奇的故事中获得乐趣、遣散郁闷,又受到道德教益。关爱和指出,阅读审美与道德认同之间有必然联系,“在审美与教化的和谐中,求得生命个体对社会伦理政治的心悦诚服”〔39〕。因此,公案侠义小说对儒家伦理的激情演绎,易于唤起普通阶层的道德情感共鸣,诚如连阔如所云:“不论是袍带书、公案书,凡是听书的人,都是一样的心理:喜爱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侠义英雄,都恨奸臣佞党、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绿林的采花淫贼。”〔40〕赵景深对公案侠义小说的评价十分中肯:“它具有人民性,表现了人民喜爱正义、痛恨邪恶的愿望。”〔41〕反之,若小说褒扬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大众的反映是热烈追逐,还是深恶痛绝?结论不言而喻。
马克思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42〕创作与接受相互影响。综观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在其故事的传承中,既有民间艺人依据受众心理的不断改造,又有接受者的口耳相传,谈论渲染。因而,其忠义主题的形成,纯属自然,是民间道德价值取向的“集体无意识”。其良好的接受效应,反映出创造者与接受者对儒家伦理的积极心理认同。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经千年而不衰,“并不单纯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和历代政治制度的附属品,它更积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包含着中华民族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智慧结晶,是一种具有社会行为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具有跨时代的生命力和超历史的恒常价值”〔43〕,在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激情演绎中展示出它在民间的巨大道德感召力和生命力。社会各阶层对《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的广泛喜爱证明,儒学作为主导文化,被精英阶层认可、推行,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逐渐在民间得到广泛地认同。
综上,公案侠义小说把主流道德融入平民喜闻乐见的日常故事中,获得读者的普遍认同。其民间接受效应,传达出平民在不同生活层面的接受审美中对社会道德本体的认知自觉。我们应科学地审视其思想价值和文学接受意义。
〔1〕姚斯.走向接受美学 〔A〕.李泽厚主编.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9.
〔2〕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 〔M〕.上海三联书店,2000.87.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95.
〔4〕孝经注疏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
〔5〕施公案 〔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7.
〔6〕石玉昆.三侠五义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38.
〔7〕孝经注疏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2.
〔8〕礼记正义 〔A〕.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
〔9〕礼记正义 〔A〕.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
〔10〕石玉昆.三侠五义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3.
〔11〕谢桃坊.评新儒学派“文以载道”观念 〔J〕.社会科学研究,1995,(5).
〔1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 〔M〕.中华书局,1980.664.
〔13〕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 〔M〕.中华书局,1980.674.
〔14〕曲家源.论《三侠五义》的思想倾向及其广泛流传的原因 〔J〕.四平师院学报,1983,(2).
〔15〕齐裕焜.公案侠义小说简论 〔J〕.明清小说研究,1991,(1).
〔16〕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 〔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66.
〔17〕古今.《施公案》的思想倾向 〔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18〕罗嘉慧.“侠义”的蜕变及历史定位——谈清代公案侠义小说 〔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6).
〔19〕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 〔Z〕.齐鲁书社,1990,425.
〔20〕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A〕.施公案 (附录)〔Z〕.宝文堂书店,1982.1388.
〔21〕郑振铎.文学大纲 〔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1.
〔22〕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 〔Z〕.齐鲁书社,1990.417.
〔23〕问竹主人.忠烈侠义传序 〔A〕.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 〔Z〕.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542.
〔24〕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 〔Z〕.齐鲁书社,1990.428.
〔25〕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 〔Z〕.齐鲁书社,1990.423.
〔26〕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05.
〔27〕姚斯.走向接受美学 〔A〕李泽厚主编.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
〔28〕恩格斯.反杜林论 〔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152.
〔29〕郭英德.明清传奇史 〔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659.
〔30〕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 〔M〕.上海三联书店,2000.5.
〔31〕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 〔M〕.上海三联书店,2000.22.
〔32〕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 〔M〕.上海三联书店,2000.5.
〔33〕佘德馀.《水浒传》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思 〔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5,(2).
〔34〕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 〔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51-52.
〔35〕关爱和.19世纪侠妓小说流行的成因与主题模式 〔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2,(5).
〔36〕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 〔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39.
〔37〕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11.
〔3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1.
〔39〕关爱和.稗官争说侠与妓——19世纪中国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主旨与主题模式 〔J〕.文艺研究,1998,(2).
〔40〕连阔如.江湖丛谈 〔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371.
〔41〕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 〔M〕.齐鲁书社,1980.472.
〔4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95.
〔43〕唐明燕,宋志明.论儒学社会影响的多元性 〔J〕.天府新论,2009,(4).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
I207.41
A
1004—0633(2011)02—144—04
2010—10—28
冯利华,文学博士,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四川内江 64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