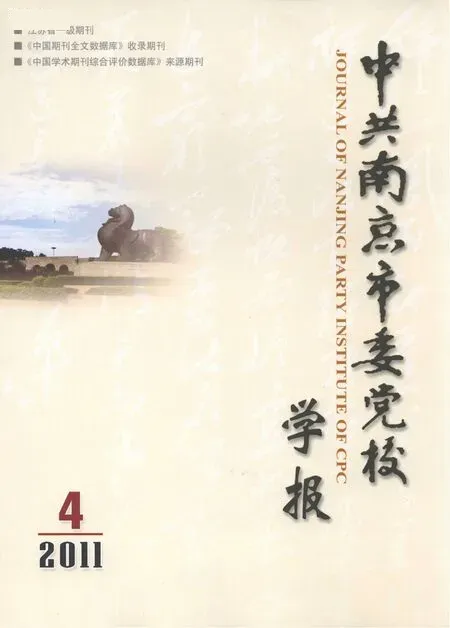“外压模式”下政策议程设置的触发机制分析*——一种对公共事件催生解决机制的解读
2011-03-04龚雪
龚 雪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引言
托马斯·戴伊在《理解公共政策》中,介绍了一种“过程模型”,并指出它通常按如下顺序展开:问题的确定、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贯彻。其中,议程设置是指,媒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些具体的公共问题,以解决决策问题。[1]事实上,政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议程设置是连接问题确定和政策形成的关键环节,由于政府能力资源、财政资源等各种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可能任何问题的确定都能如愿以偿地进入政府决策议程。诚如柯比和艾德所说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性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2]因此,研究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对于深刻理解公共政策的实质有着重要意义。
王绍光认为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3]这就是议程设置,它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4]王绍光将政策议程划分为媒体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三种政策议程,其中,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5]因此,政策议程设置对理解真正的民主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将建立议程称为“看门”。伊斯顿用一个关于政治的“系统模型”来界定在一些更广泛的“环境”内的输入、通过量、输出及反馈机制的运作情况。输入或要求经过政治系统而通过由一些“看门人”看守的检查站,政策议程就是由这些“看门人”的行动所决定的。[6]伊斯顿的模型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政府过程的宏观框架,但是输入与输出之间的“黑匣子”内部却无法知晓。理解“问题如何首先成为问题”对于我们深刻分析公共政策过程有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从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出发,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分析我国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主要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外压模式”下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触发机制,希望通过对政策过程的各方参与者及其在政策议程设立和备选方案的阐明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和所利用的资源等的详细分析,使我们对政策过程的“黑箱”有清晰的了解。
二、“外压模式”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
有关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观点是不断完善的。柯比和罗斯将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与政治体制联系起来,提出三种类型的议程设置模式,分别是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中盛行的外部推动模式、集权主义社会中流行的动员模式和法团主义社会中的内部推动模式(Cobb&Ross1976:127-136)。约翰·金登提出,议程设置的方式不仅与政治体制有关,更由问题本身的性质决定(Kingdon1995:20-21)。梅将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根据问题的提出者是公众还是政府和公众支持程度的高低,将议程设置的模式分为外部推动、内部推动、加强民意、动员四种类型(May,1991:187-206)。王绍光则从民众参与程度和议程提出者的身份这两个维度,将中国改革变迁中的议程设置模式分为六种类型,如下图:

议程设置的模式
结合现实公共政策实例,其对六种政策议程设置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指出,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7]所以,本文重点阐述“外压模式”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
王绍光指出,“外压模式”与“上书模式”一样,议程变化的动力都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政策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此事件中媒体的持续报道、公众的网络民意、学者的积极上书无疑对政策系统内的政府构成强大的外部压力,从而迫使政府废除20余年的《收容遣送办法》,颁行《救助管理办法》。再有“躲猫猫”事件,同样是“外压模式”政策议程设置的例证。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利益的多元化、矛盾的复杂化以及流动机制的僵化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强大的结构性张力。潜在的压力往往因为某些突发的危机事件而一触即发。因此,在此背景下,“外压模式”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更加多见和频繁。诚如王绍光指出的,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8]
三、“外压模式”下政策议程设置触发机制分析
美国学者拉雷·N格斯顿认为,一个问题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考虑,必须符合三个标准:一是该问题必须是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二是相当大量的公众必须有采取行动的要求,三是该问题必须是一个适当的政府单位所重视的。[9]他对政策触发机制做过详细分析。他认为,“在政治过程的背景中,一种触发机制就是一个重要事件(或者整个事件),该事件把例行的日常问题转化为一种普遍共有的、消极的公众反应”;“如果一种进步或一种行动引起公众的明显关注和公众对变革的普遍要求,那么就被认为是一种触发机制。而一种过程未引起显著反应,则不是触发机制。”[10]笔者认为,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触发机制,就是促使“问题成为首要问题”并进入决策者视线,被列入政府决策议事日程,使政府决定采取政策行动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它对政策议程的设置起到催化剂、加速器的作用,实现从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向政府议程的跨越。在“外压模式”下,政策议程设置的潜在压力转化为现实压力主要有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11]
因此,“外压模式”的政策议程模式下,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是多元化的。其中,焦点事件充当“导火索”,媒体起到“扩音器”的作用,利益集团博弈则起到“政策平衡”的作用,最后,政府决策者是“关键主角”。
(一)焦点事件
一般认为问题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因此,焦点事件在政策议程设置中起到“导火索”的作用,这里的焦点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并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同时,焦点事件的影响范围、作用强度和持续时间必须突破一定范围,才能发挥“导火索”的作用。[12]它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直接暴露出来,引起公众关注。近些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社会群体性危机事件就是一些典型的焦点事件。政策确立的利益分配格局不能适应环境变迁,造成既得利益群体和利益受损群体之间的冲突,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金登关于“问题流”的分析,则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回答。金登认为,焦点事件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常常是因为焦点事件与其他因素相融合,形成综合的政策影响力,从而造成制度的变革或政策的调整。金登归纳了焦点事件与社会因素的三种融合可能:“一是焦点事件与已经存在的问题相结合,从而加深并强化了对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二是焦点事件与潜在威胁相结合,诱发人们对社会潜在的、巨大危险的关注,从而产生政策预警,促进政策变革;三是焦点事件与其他类似事件相融合,产生对问题的新的解读和界定。”[13]2009年的“胡斌飙车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事件的危害性是有目共睹的,不仅给受害者家庭带来极大的伤痛,更引发了社会上人们对“富二代”的强烈反感和猛烈抨击。媒体爆炸式的报道、家属朋友的申诉抗议,使得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备受公众关注。此后一段时间又不断曝光一系列“宝马撞人事件”,酒后驾驶已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各方压力的不断加大,治理酒后驾驶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迅速进入政府的决策议程。据公安部网站消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于2011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定》中加大了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并放宽了对残疾人驾车限制。
另一典型案例是2009年上海“钓鱼事件”。刚刚到上海工作两天的河南小伙孙中界好心搭载一位乘客,反被诬陷为黑车运营,被上海区交管部门扣押并处以罚款。孙中界自感冤枉却又无能为力,于是,挥刀断指用鲜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一事件一经媒体报道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此前,上海像这样的司机“被钓”事件是早已有之的。此前这一问题,也许因为影响力不够大而被“去问题化”,此次孙中界“断指”却引发了巨大的波及力和影响力。在如此强大的外部压力下,相关政府部门成立专门调查组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公开向孙中界道歉、赔偿。
由此来看,焦点事件往往与戏剧性要素和情感的张力结合在一起,并带来广泛的关注。因此,焦点事件在政策议程设置中发挥着将潜在政策问题显性化,争夺“注意力资源”的重要作用。
(二)媒体和公众
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Bernard C.Cohen)。
媒体作为服务平台,是渠道提供商。是大众与政府之间交流的桥梁,大众和政府才是真正的内容提供商,但是媒体对内容有过滤和审核作用。
我国的媒体传统上只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内容发布平台,是所谓的“党和政府的喉舌”,单调而呆板,且方向旗帜一致,主要是动员和教育作用。近年来,政府的政治理念改变,媒体的开放度提高,自由度也有所提高,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功能有些许淡化,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伴随政治体制改革,媒体主要功能开始向信息功能转变,向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用转变。公众通过媒体了解外界、表达观点、反映生活、干预生活,媒体的社会公器色彩加重。
三十年改革,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碎片化的潜在危机。城乡矛盾、就业矛盾、教育差别、阶层差别等各种矛盾、冲突开始凸现。社会转型时期,国民心态呈现出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躁动化、虚假化倾向。[14]尤其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在中国的泛滥,人们在真实的生活和想象的世界之间迷茫,在幸福的追求和生存的压力之间阵痛,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忘却和个体的关注之间困惑,在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多元文化的浸淫中彷徨。“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权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力量作用下,多元化成为社会各领域的、各层面发展变化的普遍特征和价值观图腾,中国社会随之带上了碎片化特征”。[15]生活富裕了,不必为温饱发愁了,对社会对人类的关注必然增多,转型期的矛盾丛生又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关注点。在类型化自己的时候,人们经常感到很多问题都极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样的心态和环境中,对公共事件的关注渐趋明朗。对体制改革、社会发展以及与自身紧密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关注自然也多了起来。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的公开化程度越来越高、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媒体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传统的大众传媒还是蓬勃发展的网络媒体,在新闻发布、事件报道、提升问题可见度等方面越来越来越重要。马库姆斯提出,媒体没有权力告诉人们如何想问题,但是有权利告诉人们想什么问题(McCombs,2004)。因此,媒体为公众提供了讨论的话题和关心的议题,提供了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并越来越引导着舆论的方向。媒体的关注提升了焦点事件的影响范围、强度和影响的持续时间,对政策议程设置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媒体越是把问题界定得严重、危险、新奇,接近政策制定者的利益,与此同时,问题影响的范围广泛,产生的原因简单,解决方案可行,问题越能引起政府的注意(Rochefort&Cobb,1993)。
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对传统的媒体提出了挑战。以博客和论坛为主的个人信息发布系统使得民众的话语权开始有分量,突破传统的信息渠道有限的瓶颈。理论上说,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来源,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至少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某些论坛和名人的博客浏览量可以和主流媒体相媲美,如天涯、猫扑等论坛和徐静蕾、郎咸平等人的博客,事件和观点的及时且传播面广量大。这也逼迫传统媒体改变自己以迎接挑战,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与合作方兴未艾。
媒体议程设置功能表明,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新闻报道有效地影响公众和政府对公共事务的轻重缓急的考虑。一部分社会问题在传媒的报道和渲染之下,获得了进入政府决策议程的机会,而另外一些则被排除在外。当然,并不是媒体设置的所有议程问题都能最终变成政策问题,但是媒体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可能性变大。有些社会问题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就被放大了,这样就使得原来在政策过程中可能会被忽略的问题获得了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的机会。
比如“王帅案”。2009年3月,网民王帅以“河南老农的抗旱绝招”为题发布博文,揭露家乡灵宝县政府农民耕地征地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上引发网民的热议,搜狐等网站将该帖放置在网站首页。王帅个人因此被当地政府以诽谤罪拘留8天。4月初,《中国青年报》记者以此网络事件为线索进行采访,经过深入调查,对王帅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公开报道,引发网络和社会舆论热烈反应,之后又有多家新闻媒体跟进报道,众多媒体纷纷转载和发表评论。社会舆论的持续关注,对当地政府形成压力,河南省公安厅长致歉,王帅获得国家赔偿。在“王帅帖案”中,网络、中国青年报等传播媒介都扮演了积极角色。
此外,媒体与公众常常是互动的过程,媒体的报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则借助网络等媒介发表言论,对政府形成强大的压力,网络民意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影响力量,虚拟压力转化为现实压力会一触即发。
“躲猫猫事件”中,媒体报道之后不少网民对这一事件广泛关注,不断跟帖发表看法,从而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迫于此,相关政府部门主动组织部分网民成立调查小组,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虽然其公正性受到质疑,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已充分意识到了网络民意的压力和重要性,并开始正面回应,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三)利益团体
托马斯·戴伊在《理解公共政策》一书中指出,团体之间的互动是政治的核心内容。只有当人们的行动是作为团体利益的一部分或者代表团体利益的行动时,个人在政治中才是重要的。[16]在团体理论者看来,特定时间内的公共政策是团体斗争所形成的平衡,这种平衡由所有利益集团的相应影响力所决定。这种利益集团相对影响力的变化会导致公共政策的变化;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会符合那些获得影响力的团体的希望。[17]事实上,利益团体的博弈贯穿于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在政策议程设置方面,利益团体的博弈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哪些问题首先作为政策议题进入政府议程则取决于与议题相关的利益团体的博弈。
比如武汉“麻木事件”。“麻木”是武汉市对三轮车及车夫们的特称,在武汉已有很久的历史,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一段辉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需求,整治“麻木”成为武汉交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议题。一边是“麻木们”挤占道路、危及安全、影响秩序、污染环境、损害市容;一边是弱势群体的生存与既得利益者对现有利益格局的维护。显然,政府已经将这一问题视为重要的政策议题,然而却困难重重。作为“麻木”群体中有一定活动能力和威信的“麻头”,他们组织“麻木”到政府上访、静坐、游行、堵塞交通。由于这一利益团体的抗争,之前的多项整治措施都以“麻木”的胜利宣告结束。直到2003年年初,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妥善解决麻木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将“依法整治、有情操作、回收车辆、帮助择业”作为指导方针,通过“赎买”方式有效地解决了“麻木”问题。
(四)政府
政府掌握着丰富的决策资源,因此在政策议程设置中处于决定性的位置。在焦点事件及其他外部压力的作用下,政府感知、成本收益分析、预算约束、自身利益(政府形象)等因素都影响政府接下来的行为。只有问题被政府积极关注并且政策建议是可行的情况下,政府议程才会真正建立。2003年农民熊得明面对面向温家宝总理反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由于直接进入最高决策层从而掀起一股“追薪”浪潮,并促进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机制形成。相反,有些重要议题如果迟迟不能进入决策者的视线,即使满足上面提到的三个因素也无法推动政策议程的顺利设置。诚如金登在“多源流分析框架”中指出的,政策议程的设置存在三条溪流——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这些分离的溪流只有在关键的时刻汇集在一起,才能完成决策。[18]三条溪流相互独立但又不完全独立,问题、政策、政治是贯穿政府议程建立的三个过程。只有政府决策者感受到政策问题并且积极的回应,才能够真正打开金登所说的“政策之窗”。
四、结语
综上所述,焦点事件、媒体和公众、利益团体以及政府都是“外压模式”下政策议程设置的触发机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压模式”显然为我们把握当前我国政策议程设置提供较好的指导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外压模式”下,处于决策地位的政府是被动的,在客观环境的不可预知性以及政府能力的有限性现实面前,此种议程设置模式显然使得政府在决策中处于风险和挑战之中。诚如托马斯·戴伊对公共政策模型的评价:“每一种政策模型都有各自关注的公共政策焦点,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公共政策中的不同内容。因此,我们不能判断哪一个最好。”[19]同样,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只是为我们理解政策议程设置提供了一种规范或者为理解公共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1][16][17][19]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华夏出版社,2004.13、18、18、11.
[2][12]胡杰容.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一个逼迫型政策变迁过程研究[A].杨团,彭希哲主编.当代社会政策研究IV[C].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340、341.
[3][4[5]][7][8][11]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6][13][美]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
[9][10]拉雷·N格斯顿.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原理[M].朱子文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71.
[14]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
[15]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3.
[18]陈建国.金登“多源流分析框架”述评[J].理论探讨,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