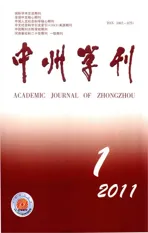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探析
2011-02-21张兴成
张兴成
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探析
张兴成
两晋宗室制度发展异趋,各自形成特点,其形成原因有四:两晋政治格局不同、地方势力状况不同;两晋最高统治者资质各个有别、在位年龄大小不同、政治素质高低不等、在位时间长短不一;两晋宗室成员总量多少不一、爵位高低不等、与最高统治者血缘关系亲疏不一,行政素质、文化素质、社会声望各不相同;两晋时期政治文化观念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两晋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
两晋;宗室;制度差异
一、两晋宗室制度差异举要
两晋时期,宗室①是一特殊社会阶层,这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
其一,在经济制度上,宗室享有一定特权。《晋书》卷廿六《食货志》载:“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宗室这种荫其亲属的特权在国家经济法令中予以特别指出,这还是第一次,说明宗室在当时经济制度上被当作一个独立阶层来看待。此外,宗室成员还可得到国家供给②,这也是其在经济上拥有特权的一种表现。其二,在司法制度上,自曹魏始,八议作为一项法令固定下来③。宗室成员犯罪后,根据“议亲”的法律规定,可以减免罪行。《晋书》卷五九《司马伦传》:“有司奏伦爵重属亲,不可坐。谏议大夫刘毅驳曰:‘当以亲贵议减,不得阙而不论。’”可知,议亲之典的确实施。其三,在国家机构设置上,专门设置宗正机构以掌管皇族谱谍④。在西晋武帝时,又设置宗师一职以训导宗室⑤。这是宗室阶层特殊性在职官制度上的反映。另外,宗室地位的特殊性在当时的天文天象中也有反映,宗室有相对应的星宿。《晋书》卷十一《天文志上》:“宗星二,在候星东,宗室之象,帝室血脉之臣也。客星守之,宗支不和。”天文观念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可知当时人观念中宗室是一特殊阶层。
两晋宗室阶层的特殊性根本上是由当时君主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宗室与实行这种政治体制的统治政权相伴而生。因此,皇权政治是宗室阶层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宗室也是保证这种政治体制稳定和延续的政权基础。宗室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和政治阶层在两晋未有变化,然而,考之传世文献,参以时贤论述,⑥可知两晋宗室制度在发展和演变中却呈现出显著差异⑦,具体差异如下:
其一,西晋宗室管理机构相对完备,专职机构及有关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宗师一职均由位望显赫、戚属尊重的宗室成员担任。朝廷对宗室成员的管理比较宽松,限制较少。东晋时宗室管理机构或并或省,其官员人选位望较轻。朝廷对宗室成员限制较多,宗室成员在东晋大部分时间内遭到压制、打击。其二,西晋宗室大都担任职事官,或管司朝政,或总御兵马,在政治生活中作用显著,表现为在中央参与政治决策、在地方执行最高管理。惠帝元康以后,宗室诸王直接左右政局,宗室对皇权政治的影响达到极致。此外,宗室成员任职者迁转较快,其僚佐、属吏多选任清望之士,加崇者往往多置佐官、属吏,他们大多仕至高位,死后多赠高官。东晋时,宗室担任职事官者较少,担任散职官者增多。除个别时期外,宗室成员基本不担任地方都督、重要禁卫长官、录尚书事等重要军事、行政长官,即使有任职者,受当时政治形势制约,也不能对朝政有显著影响。其相关僚佐、属吏人数不多,其佐吏对政治影响不大,他们能达到的最高官位品秩降低,相应赠官官品也不高。其三,西晋宗室封王众多,王国林立,曾经推行诸王就国的统治政策,王国官地位和声望都还不错,西晋末期,王国官政治影响显著。东晋诸王不就国,受封人数少且王国规模小,王国官人数亦少,对政治影响微弱。
二、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形成原因
两晋时期,重用宗室以为藩辅的统治政策相同⑧,但两晋宗室制度上存在的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试论如下:
1.两晋政治格局不同、地方势力不同状况导致了两晋宗室制度之间的差异
西晋时期,皇权比较强大,地方势力暂时不能抗衡中央。巴蜀政治势力在平蜀之后被分化瓦解,原蜀国文武官吏被以各种方式徙出,西晋又通过鼓励蜀人内迁方式削弱巴蜀旧有地方政治势力。因而西晋时蜀地在流人政治势力入蜀之前地方势力活动很少,这从晋武帝策问华谭诏文中可以看出。⑨当时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势力虽然屡次称兵,但经过马隆、孟观打击之后,基本归于平静。与此同时,晋武帝又制定许多相关政策以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如刺史只负责监察,不理民事。地方行政重心转移到郡国守相,郡国守相不负责军事事务。都督、刺史各自用人,不相兼领,都督负责军事,不掌民事。⑩此外,晋武帝又于咸宁三年(277)实施诸王就国的政策,藉此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凡此制度都保证了西晋皇权的强大。而皇权强大又保证了西晋重用宗室的政策得以彻底推行,许多具体宗室制度如“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得到严格执行。故此,西晋强大的皇权使这一时期的宗室制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东晋时期,皇权衰落、高级士族轮流当政。皇权衰落与当时地方势力强盛大有关系。当时,原吴国地区地方势力并未在平吴之役中遭到沉重打击,其对东晋王朝中央兵源和赋税分割相当严重,同时拥有潜在的武装势力。周玘三定江南,沈充起兵响应王敦称兵犯阙,虞潭起义师于会稽以讨王敦,说明原来吴地地方势力向背在当时政治军事斗争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晋元帝初镇扬州时,虽然对当时异己势力进行了打击,如讨伐周馥、华轶等,但多是西晋朝廷所任命的征镇牧守,并未对原来吴地地方势力有太大触动。这些地方势力一直伴随东晋王朝相始终。另外,由于各种制度原因,东晋中兴后又形成新的地方势力。东晋都督并兼领统府所在州刺史,都督权力很大,既统管军事,又兼理民政。并设州府和军府,自行辟除属吏,这些属吏多是本地人。都督同时可以表请任命参佐和统内地方官长[11],统府僚佐大都兼领统内郡国守相。这往往使出任都督者形成强大地方势力,从而与中央相抗衡,甚至以此专断朝政。许多侨姓高门南渡后,并无吴地旧姓那样的经济势力和武装势力,他们正是通过担任地方都督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如庾氏家族、桓氏家族等,桓玄还以此转移晋阼,可见此种政治势力影响之大。
吴地旧有地方势力和东晋中兴后形成的地方势力力量强大,造成了严重后果。前者招诱大量隐户,造成国家户口大量流失,如太元年间,“略计户口,但咸安以来,十分去三”[12]。户口流失严重,造成国家赋税和兵役供给出现困难,中央朝廷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这使得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无法统一协调、管理国家军事、民政。后者主要在政治上对中央朝廷造成威胁。如王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遂欲专制朝廷”。庾亮坐镇荆州时,虽在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趋向者多归之”。354年桓温废殷浩后,“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又《晋书》卷六四《司马元显传》载张法顺对元显所说:“桓玄承籍门资……既并殷、杨,专有荆楚……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吴耳。”地方势力强大使得中央政令无法在地方上得到执行,从根本上导致了皇权衰落。皇权衰落使重用宗室的统治政策无法推行,宗室阶层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随之低落。表现在宗室管理制度上便是对宗室政治活动加以限制,宗室犯法动加裁制,无复优容。表现在宗室任官制度上便是宗室成员出任重要军政长官的机会有限,其能达到的最高官位、死后赠官官品相较西晋降低。表现在王国制度上便是王国封户寡少,国秩微薄,王国官数量减少,王国官对政治影响十分微弱。
2.两晋最高统治者的个体差别,导致了两晋宗室制度的歧异
这种个体差别主要体现在继位年龄、在位时间和政治素质上。如西晋武帝即位时已30岁,在位26年。他“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13]。惠帝即位时32岁,在位16年。虽然“厥体斯昧,其情则昏”,但他为太子20多年,民望素定。怀帝即位时24岁,在位7年,“天姿清劭,少著英猷”。愍帝即位时14岁,在位5年。西晋51年当中,除愍帝继位时不到弱冠之年,其余诸帝都是年长即位,按照制度,他们均能躬亲政事,临朝听言。从在位时间看,除怀帝、愍帝因政治动荡,在位时间较短以外,武帝、惠帝在位时间都较长,共计42年,皇位更代较慢,稳定政局,利于长期推行行之有效的统治政策。西晋重用宗室政策一以贯之,这对宗室制度发展影响很大,表现在宗室管理制度上便是相关机构完善,表现在仕进制度上便是起家年龄小、起家官品高,表现在任官制度上便是宗室出任重要行政和军事长官,表现在王国职官制度上便是王国官发展渐次完备,王国官人选严格,王国官地位和声望都还不错。
东晋诸帝情况则稍有不同。元帝43岁即皇帝位,在位6年。元帝“沉敏有度量”,能够“详刑简化,抑扬前轨,光启中兴”,但“失驭强臣,自亡齐斧”。明帝24岁即位,在位3年。他“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远近属心焉”。成帝5岁即位,15岁加元服,继位10年后亲政,在位17年,他“少而聪敏,有成人之量……雄武之度,虽有愧于前王,恭俭之德,足追踪于往烈矣”。康帝21岁即位,在位2年。康帝“亦克俭于躬,庶能激扬流弊者也”。穆帝2岁即位,15岁加元服,继位13年后亲政,在位17年。哀帝21岁即位,在位4年。即位第四年因服食中毒,不识万机,由崇德太后临朝摄政。废帝24岁即位,在位5年。简文帝52岁即位,在位2年。简文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矣”。孝武帝11岁即位[14],15岁加元服后临朝听政,在位24年,孝武帝“既威权己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安帝15岁即位,16岁加元服开始亲政,[15]在位22年,安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恭帝33岁即位,在位2年。[16]东晋首尾102年,共有11位皇帝,长年即位者7位,未加元服而即位者4人。诸帝亲政时间总共76年,有26年时间是由母后执掌朝权。亲政时间超过20年者只有2人,其余诸帝亲政时间都不超过8年,皇权迭代很快。中央政局变化过快,这就使得主臣之间未能恩信素布、共济患难。东晋最高统治者的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有关宗室制度。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由于享国日浅,有关统治政策未能长期贯彻执行。《晋书》卷六《明帝纪》:“帝崎岖遵养……廓清大祲。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强本弱枝。”明帝在消灭王敦之后,皇权复振。他实行强本弱枝的统治政策,改任方镇是其措施之一。重用宗室,任命南顿王司马宗为左卫将军、司马祐为领军将军以掌握禁卫军权。但明帝很快死去,任用宗室以加强皇权的政策未能继续贯彻下去。明帝死后,庾亮先以明升暗降方式夺取司马宗、司马祐兵权,继以谋反罪名杀死司马宗,废黜司马羕,宗室势力遭到沉重打击,门阀政治却得到巩固和发展。此后,成帝、康帝时期,宗室势力政治影响都很微弱,穆帝即位之后这种状况方有所改变。从中可以看到最高统治者对于宗室制度发展影响之大。
另一方面,如果最高统治者未能亲政,大权下移,庶姓高级士族秉政,宗室会遭到排斥。另外,政权更代过于频繁,政治矛盾不易得到及时化解,而幼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与宗室矛盾往往容易激化,从而引发政争,甚至引起政治暴乱。如成帝即位后庾亮打算诛除司马宗,司马宗也密谋废黜执政,外戚与宗室争夺辅政权。最后庾亮杀司马宗,废黜司马羕,庾亮取得政争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此事又引发了苏峻之乱。这种政争后果在宗室制度上的影响便是相关宗室管理制度更加严格,宗室任官受到限制,其最高官位、赠官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
3.两晋宗室成员的个体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晋宗室制度的差异
两晋宗室成员的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其总量多少不一、爵位高低不等、与最高统治者血缘关系亲疏不一,行政素质、文化素质、社会声望各不相同等方面。西晋伊始,宗室成员众多。武帝26男,除惠帝、怀帝继体为君外,早卒有封国及追谥者9人,早夭无封国及追谥者8人。其余7人,均受封高爵,任寄特隆。文帝9男,除武帝外,早卒有封国及追谥者3人,早夭无封国及追谥者2人。其余4人皆受封高爵,担当重任。宣帝9男,除景帝、文帝外,司马京年24岁卒,其余6人都受封王爵,荷受荣宠。宣帝兄弟8人,除司马敏官爵无闻外,其余兄弟均后嗣兴盛,官爵显赫,尤其以司马孚一支最为突出,一门三世,同时10人封王,2世子,公族之宠,中代少有。他们与开基之主武帝族属不远,属同一曾祖后代,血缘亲近,戚属尊重。宗室官员迁转相对较快,久滞不迁者少。宗室官员犯法,多蒙优贷,黜落者少。纵有坐事免官者,通常很快起复,少有禁锢偃蹇者。在任官方面,宗室官大都职任崇重,充任散职者少。宗室诸王,官俸优给,国秩丰厚。在王国职官制度上,宗室诸王国官任职者大都是清望之士,宗室诸王甚至一度可选任国官。
东晋则不然,永嘉之乱中,宗室成员死亡较多,南渡过江者很少。当时宗室诸王只有五人得以南渡,他们是元帝司马睿、司马羕、司马宗、司马祐、司马雄。[17]其中,司马祐是宣帝子司马亮之孙,司马羕、司马宗是司马亮之子。元帝司马睿是宣帝子司马伷之孙。司马雄是宣帝弟司马馗四世孙。元帝与司马祐是再从兄弟,司马羕、司马宗是元帝从叔父,属于同一曾祖后代,族属较近。元帝与司马雄则已非五服之亲。司马羕在永嘉初担任过镇军将军,领后军将军,南渡五马中,除元帝外,他是在西晋时任职最为崇重者。司马宗在西晋担任过征虏将军,司马祐担任过扬武将军,司马雄则在西晋官爵无闻。另外,谯王司马承在西晋担任过广威将军、安夷护军(五品),官职不高。当时政治体制下,虽然宗室可以凭借血缘关系在任官上享有一定特权,但必须是较近血亲,血缘关系过于疏远,其所享有特权也就有限。另外,纵是血缘较近宗室,他们任官也必须是渐进的。虽然皇帝母弟等至亲可以辄居大位,但属于少数。大多宗室成员进入仕途后也需逐步积累资历,并不能暴得大位,从而示天下以私。[18]司马雄在东晋寂然无闻,正因他与元帝服属转远,在西晋又无任官经历,资望不够,纵然受封王爵,仍然不能加以显擢。南渡宗室诸王中,只有司马羕官位显贵,东晋中兴后,元帝任命司马羕为太保、录尚书事,与王导、荀组分管朝政。此外,元帝任命司马宗、司马祐为禁卫军长官,典领禁兵,职任机要。同样这两人与元帝戚属较近,为五服之亲,在西晋且担任过四品将军。总之,当时南渡宗室成员人数很少,力量寡弱。他们与元帝血缘转远,在西晋位望崇重者少,仕途不显者多。除上述南渡宗室诸王及一些宗室疏属外,元帝6男,明帝及简文帝次第继承皇位。司马焕早夭。司马裒在317年即去世,其子司马安国即位未逾年即薨,后嗣无人。司马冲卒于咸康七年(341),无子。只有司马晞子孙稍多,但毕竟只有一门,总数不多。简文帝有7子,孝武帝继体为君。早夭者3人。长子司马道卒年24岁,无后。司马郁卒年17岁,无后。只有司马道子与孝武帝同产,血缘最为亲近。东晋其他在位皇帝如明帝只有2子,相继位登大宝。成帝2子亦然。康帝子只有穆帝1人,居位称尊。孝武帝2子亦相继即皇帝位。综合上述可知,东晋时期,帝室近亲只有司马晞一门,司马道子一支,其余宗室多非五服之亲,他们在东晋官位不显,与此不无关系。谯王子孙在东晋宦位通显,特因司马承死难王室,并不因其子孙与当时在位皇帝血缘关系亲近之故。
值得注意的是:西晋时期,许多宗室成员学术修养较好,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较高。如司马模“少好学,与元帝及范阳王虓俱有称于宗室”。其子司马保“少有文义,好述作”。而范阳王虓也是“少好学驰誉,研考经记,清辩能言论”。又如司马繇“有威望,博学多才”。司马骏“少好学,能著论,与荀顗论仁孝先后,文有可称”。齐王司马攸则“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与之相对,东晋许多宗室成员或善玄言,或信浮屠道,或长武略。司马昱“尤善玄言”,“(哀)帝雅好黄老”,司马德文“深信浮屠道”。司马道子“崇信浮屠之事”。司马勋“以勇闻”。司马晞“无学术而有武干”。[19]由于儒家经籍往往是古代统治经验的荟萃,学习典籍有助于增长统治才干,西晋宗室服膺儒学者多,其政治素质相对来说较高。这与司马氏家族本来就是儒学世族,儒家经籍的传习成为其门风有关。东晋宗室接受儒学者相对较少,统治经验因而有所欠缺。这与江左玄风独劲、儒学式微有关。
4.两晋时期政治文化观念不同也潜在制约着两晋宗室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司马氏家族是汉魏以来儒学大族,儒学主张采用由近及远、先亲后疏统治政策缉和万邦。故此晋武帝采用尊宗茂亲的统治方略,以求统治稳定。不仅如此,晋武帝的佐命功臣及其辅政大臣也大多服膺儒教,而当时的舆论也是倾向于重用宗室,如刘颂、段灼、陆机等人均主张恢复封建,建立磐石之宗。正是在各种力量的驱动之下,西晋重用宗室便成为大势所趋,宗室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也就很自然了。
东晋时期则有所不同。当时玄风炽盛,东晋高门士族大都由儒入玄[20],玄学被门阀士族用来为自己所享有的特权作合法性论证[21],当时最高统治者也是濡染玄风。如东晋元帝、明帝、简文帝和孝武帝[22]。这种统治术(玄学)要求君主在政事处理上委任群下,并不总揽权力,政由己出,在政治上提倡玄学的后果便是门阀专断朝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皇权衰微,与皇权政治命运相系的宗室阶层在政治上也因此不能有所作为。
三、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对两晋政治的影响
西晋宗室制度积极影响表现在:通过宗室制度,宗室成员充分获得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起到了巩固、稳定和加强皇权的作用。魏晋禅代能够顺利实现,正是司马氏任用宗室所收到的实效之一。此外,司马骏镇守关中时遗爱西土,司马伷任青徐州都督时在平吴之役中立下大功,赵王伦篡位时三王起义兴复皇祚,均是西晋实行一系列宗室制度而收到的宗室藩辅王室统治效果的积极方面。
西晋宗室制度对于当时政治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西晋对于宗室法禁宽驰,威刑不肃,当时宗室在政治生活中肆行不法,完全不顾宪章法制。这往往会导致政治生活中法令紊乱,西晋的灭亡与宗室制度的消极影响有很大关系。对于东晋宗室制度对政治发展的不利影响,前此论著已有涉论,不烦置言,其积极影响则从晋宋之际宗室政治活动延缓晋宋禅代进程上反映最为显著。[23]
综括上述,在皇统世袭制、帝王终身制的政治体制下,任用宗室担任国家军政长官是有必要的,有助于政权交接、巩固、稳定和发展。但在官僚政治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古社会中,选贤与能也是时代要求,同样有利于政治统治。况且,任用宗室参与中央政务管理和地方统治,有时会产生很严重的弊端,甚至危及王朝统治。因此,任用庶姓贤良之士参与统治以纠偏除弊也是必要的。两晋宗室制度正是在总结历史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在王朝的统治实践中得到发展,经过历次残酷的政治斗争的考验和洗礼之后,其成败得失又成为南朝王朝统治者的龟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改造和发展,成为他们巩固统治的重要制度。
注释
①本文使用宗室特指皇族,也称“公族”,与非皇族即“庶族”相对。②《晋书》卷九《孝武帝纪》,“九亲供给,众官廪俸,权可减半”,中华书局,1974年。③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④⑤[11][12][13]《晋书》,卷廿四《职官志》、卷五九《司马亮传》、卷六九《刘隗传》、卷六九《刘波传》、卷三《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⑥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鲁力博士论文《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相关章节。⑦《西晋的宗室仕进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略探》,《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2001年第6期;《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晋宋宗室与地方政治》,《中国古代史论丛——黎虎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⑧《晋书》卷三七《司马望传》泰始三年诏及《晋书》卷三七《司马承传》“帝欲树藩屏”条。⑨《晋书》卷五二《华谭传》,中华书局,1974年。⑩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4]《晋书》卷九《孝武帝纪》:“简文之崩也,时年十岁。”据其生年推算其年孝武帝应11岁。[15]安帝本应于396年加元服,是年孝武帝驾崩,推迟至次年正月始加元服,属于特殊情况。[16]以上均见《晋书》各篇帝纪。[17]鲁力:《东晋的“五马”与谯王》,《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18]《晋书》卷六四《司马元显传》:“元显自以少年顿居权重,虑有讥议。”[19]以上所引材料分见《晋书》诸帝纪、诸人本传。[20]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21]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338页。[22]《世说新语笺疏》中卷上《方正第五》注引《高逸沙门传》,余嘉锡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晋书》卷九《简文帝纪》和《晋书》卷九《孝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23]张兴成:《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略探》,《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何参
K235
A
1003—0751(2011)01—0171—05
2010—10—05
张兴成,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