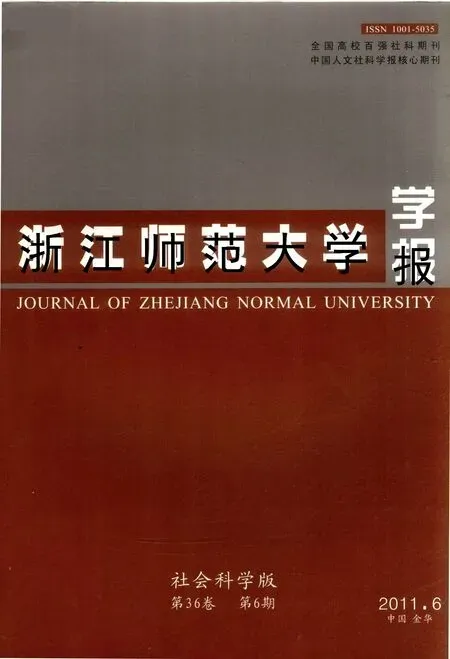艺术“突围”与文化“暴动”
——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和“五四”文化启蒙关系再梳理*
2011-02-20邵向阳杨荷泉
邵向阳, 杨荷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两次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变革,第一次是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古老而传统的思想文化史上,这场狂飙突进的思想“哗变”无疑是一场惨烈的文化“暴动”。第二次是世纪末期的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因政治解禁而引发的艺术“突围”,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艺术的模仿和创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一道永远亮丽的风景线。
关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与“五四”文化启蒙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学术界一个业已形成广泛共识的话题。大多论者往往认为,以“伤痕文学”为起点的新时期文学就是“重回五四起跑线”。不可否认,20世纪80年代文学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走上“五四”文学的道路,诸如重拾“五四”的启蒙理想、重现“五四”的“文学复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由于社会背景、思想氛围等条件大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不可能完全重复“五四”时期的道路。随着艺术“突围”的激情冷却,它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解构成一场艺术模仿表演秀。
一、80年代:第二个“五四”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文学压抑多年的能量与激情似乎也在一夜间爆发,呈现出多元共存的局面。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崭新现象。无论是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伤痕文学”,还是寻找失落人性的“反思文学”,抑或是探索开拓的“改革文学”等等,无不包含了破旧立新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的人文理想,“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这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五四时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六十年之后的惨痛复归”。[1]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然而,有着类似时代背景的不同时代,也可产生相通的文学主题。作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开端的“伤痕文学”发轫之作,《班主任》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充满了强烈的启蒙精神,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我们听到了和五四文学相同的呐喊声。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那个新旧思潮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融会撞击的“五四”时代,“五四”先贤先哲们将解放“自我”、张扬“个性”作为人性解放的一种手段,高扬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直接投身到文学启蒙的伟大实践中。以反封建、人性解放的启蒙理想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五四”文学,自诞生之时,就将通过启蒙手段达到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将人从长期的封建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作为一己的道德使命,充满着人道主义关怀的“五四”启蒙精神。遗憾的是,“十七年文学”所要着力表现的是集体主义的“大我”“英雄”,人道主义被放逐,“文革文学”里稍有一点人情人性的作品,就有被打成“毒草”的危险。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达近三十年的政治运动,使得“五四”启蒙被迫中断,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核心精神的“五四”精神渐行消退,甚至消失殆尽,以致酿出一场反科学反民主的闹剧和悲剧,致使整个国家遭殃、思想文化隔绝封闭、亿万民众落难、人身人格备受摧残和侮辱,也使得“五四”启蒙精神蒙受奇耻大辱。
在结束“文革文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文学之际,人们要告别一种旧话语而创造一种新话语,必然要借助一些思想资源。由于“文化大革命”被广泛看作是一场丧失人道主义的封建文化专制运动,是一股建立在反启蒙基础上的文化思潮,因此,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他们选择了“五四”,并且特别青睐于“五四”的启蒙思想,他们高喊着“回归五四”、“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重新发现了“五四”的启蒙理想,接续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期间中断已久的启蒙运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五四”精神才终于回归它的发祥地,并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迎来了“五四”启蒙精神的全面复苏和回归。而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发展也被视为类似于“五四”文学那样的“复兴”。“‘复兴’的提出,又通常与‘五四’启蒙文学相联系,看成是对‘五四’的‘复归’。在八十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的,是他们心目中‘五四’文学的那种自由的、‘多元共生’局面”。[2]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中心问题来看,所要“复兴”的,主要是“五四”文学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的启蒙精神,和以“五四”为旗帜、在20世纪50-70年代被视为“异端”和“毒草”而遭到否定乃至批判的文学思潮。20世纪80年代文学和五四文学在“启蒙”这一点上产生了共鸣,这就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文学接通了“五四”以来被阻断隔绝了30年的启蒙思潮,也实现了当代文学与“五四”文学的链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新的思想启蒙。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被看作是“第二个‘五四’时期”,开启了以“五四”启蒙思想为主导的“新启蒙”运动阶段。
二、“五四”启蒙:“启蒙”的悲哀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3]与之相伴而生的“五四”文学革命,也因此具有浓郁的启蒙色彩。“五四”文学先驱们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意识,他们以启蒙为己任,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启蒙精神,鲜明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启蒙思想,并试图以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实践唤醒人们关于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等意识的思考。从整体上来看,“五四”启蒙运动的根本动因和任务,就是侧重于“人”的彻底解放和觉醒。因此,“人”的发现可以看作是“五四”启蒙的最大收获。
作为“人的自然的呼声”的“五四”文学,将“表现自我”、“个性解放”作为自觉的文学追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的“人的文学”,可以作为“五四”启蒙文学的基本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感召下,个人独立、个性解放成为“五四”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出现了一大批抒写个人生活和情绪的个人化色彩极为浓厚的文学作品,此外,家庭、爱情婚姻等问题在“五四”文学中也或多或少都有所反映。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先驱者以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精神为参照,试图运用思想启蒙的手段,来改造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积淀而成的国民劣根性,从而推动“五四”启蒙的历史进程。鲁迅在30年代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出发,鲁迅的作品往往热衷于表现一系列的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在鲁迅的影响下,以鲁彦、彭家煌、蹇先艾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家群则深刻地描绘了封建宗法社会中落后、愚昧、野蛮的农村生活图景。在“五四”时期的特定环境下,“五四”文学先驱者坚信自己人道主义的精神立场,进行深刻的思想启蒙,做出了种种艰苦卓绝的努力。无论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为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工具,还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呼吁、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郭沫若的“凤凰”的吟唱等等,都是时代的最强音、启蒙的最强音。
“五四”启蒙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为激进的一股反封建思潮,具有极其乐观的主观设想:回顾过去的历史,为辛亥革命之前远未完成的“人”的解放与觉醒,进行了历史的补课;瞻望未来前景,“是从这种人性的得到解放,以及民主主义秩序的得到确立,向着社会主义民主理想,以及人类全面和彻底的解放过渡,由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主义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5]然而,无论是回顾过去历史的补课,或是瞻望未来前景的发展,这两个方面都还远远没有完成。就前者而言,当时的国民并没有从那种激进的“启蒙”思潮中清醒过来,在愚昧麻木的“被启蒙者”眼里看来,“启蒙者”的一切启蒙理想全都是毫无意义的“表演”,甚至将“启蒙者”当作了闲聊的“谈资”。这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不可避免的隔膜,是启蒙的悲哀。实际上,“五四”启蒙陷入一种“启而尚蒙”的尴尬局面。此外,“在‘五四’前期,现实急需的是直接服务于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启蒙文学’,而不是对文学自身进行启蒙的‘文学启蒙’”,[6]也就是说,“五四”启蒙走上了政治启蒙先行的道路,五四文学沦为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20年代末启蒙高潮的自动衰减,成了启蒙运动失败的明显标记,在启蒙意识被不断涌来的革命文学、救亡运动遮没覆盖、瓦解的同时,胡适走向了学术,陈独秀走向了革命,周作人走向了闲适,只剩下鲁迅孤独地、始终不懈地坚持自己怀疑的启蒙精神”。[7]然而,全国解放以后的文学发展趋势并不是向“人性的解放”迈进,“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批判和禁锢人性的趋势推向了极端。总之,由于“五四”启蒙所要试图解决的艰巨任务并未能得到完成,所以“五四”启蒙并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然而,历史是绝不会跳跃前进的,历史在哪里断裂,历史就会在哪里重演。任何一个可能会产生重大历史作用的文学命题,只要在前一个时代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它就会在后面一个崭新的时代中被再度提出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的解放和觉醒、独立和自主、价值和尊严等问题被重新提出来,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新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继续未竟的“五四”启蒙的任务。既然“五四”所开启的反封建任务没有完成,那么80年代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同“五四”时期打破封建传统那样,将深受“现代迷信”毒害的人们从“文革”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三、“新启蒙”:“五四”的回归与偏离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篇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文章中提出的著名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李泽厚以“启蒙”与“救亡”两大性质不相同的思想史主题来建构中国现代史,认为在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迫使知识分子放弃启蒙理想而走向民族救亡,“反封建”的“五四”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而且被封建主义传统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悄悄地改头换面,最终造成了封建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泛滥成灾。李泽厚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封建传统”的全面复活,其原因是“五四”提出的反封建任务没有完成。李泽厚不仅解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过程,而且把它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回到“五四”的根本动因,“这种对‘文革’产生原因的解释成为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广泛共识,以致有学者称它为80年代知识界的‘元话语’”。[8]作为对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发生原因的一种阐释,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无疑成为了新时期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在“新时期”文学史叙事中,“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常常被理解为“五四”启蒙精神在此期间中断的两个文学史阶段,这就是影响至深的“断裂论”。“‘断裂论’之所以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述,不能不说和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有着直接的关系”,[9]既然“五四”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那么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使命,就是继续被中断的“启蒙”精神,“救亡压倒启蒙”作为“元话语”,促使“启蒙”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的主导声音。
以1985年前后为界,20世纪80年代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由于“文革”被普遍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全面复辟”,因此在纷杂的思想文化“输入”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人道主义的启蒙精神成为反叛“文革”模式的话语资源。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对“文革”批判、反思的具有启蒙精神的文学创作。就小说而言,出现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以“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班主任》为开端,作品所传达出来的那声原始的现代性呐喊,振聋发聩地撼动、唤醒并复苏了人们内心深处反封建的现代人性欲望。事实上,“伤痕小说”就是人的心灵拷问的文学表达过程,“伤痕小说”发轫的初衷,就是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启蒙过程。随后,“反思文学”继承了“伤痕文学”的衣钵,从建国以来的历史事实中寻找反人道、封建专制的根源,试图寻找失落的人性基点。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体现在青年一代的“朦胧诗”创作和“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舒婷、北岛、顾城等青年一代朦胧诗人以思想启蒙为创作的基点,以表现“自我”和张扬“个性”为时髦和责任;艾青、公刘等“归来”的诗人用他们非凡的勇气与胆量,对十年浩劫进行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写出了一系列引人共鸣的优秀诗篇,成为启蒙的利器。此外,这一时期的戏剧也承接了“当代”的传统,以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为主。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歌”、“归来的歌”等文学思潮都属于广义范畴的启蒙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积聚的革新力量开始得到释放,迎来了文学创新的“高潮”,涌现出了一大批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艺术形态不同的作品:《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古船》(张炜)、《透明的红萝卜》(莫言)、《爸爸爸》(韩少功)、《你别无选择》(刘索拉)等等,此后便有“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的提出。到了80年代中后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成了热门话题。在这一文学命题的感召下,对文学“形式”问题的关注、对文学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清理、对文学只关注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反省等问题,引起了当代作家的重视。他们开始探索语言和叙述的可能性,开始尝试远离社会政治问题的“日常生活”写作、“个人写作”,诸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等,此后又有“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的提出。纵观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中后期的文学创作,“文学启蒙”的口号已经成为疑问:“寻根文学”表现出的“复古”倾向,会导向对批判反思的“传统文化”的回归;“现代派文学”所引起的“现代派问题”之辩与“伪现代派”之辩,“实际上就是堵死了一个人文启蒙的探索通道”;[10]“先锋”作家们只注重追求诸如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一系列西方现代派大师的形式表现,却忽略了他们作品中深层次的人文思想内涵;“新写实小说”所谓“还原”生活的“零度叙事”模式使得文字中人文价值的判断显得模糊难辨,最终与现代启蒙的精神渐行渐远。
纵观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前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在努力继续“五四”时期未竟的“启蒙”任务,然而,启蒙主义思潮的内涵在80年代中期和中后期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思想内核由启蒙主义向着存在主义的蜕变”。[11]无论是 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还是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启蒙思想的含量显得愈加稀薄:“寻根文学”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挖掘,清晰可见地透露出对文化保守主义观念的坚守;“现代派文学”将西方现代文学资源作为获取灵感的渠道,潜隐地对启蒙已经构成了某种有力的威胁;“先锋小说”在吸纳西方现代主义观念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对现实的消解,将文学导向了虚无主义的道路;“新写实小说”看似褒扬“日常生活”的背后,隐藏的是对启蒙精英意识的颠覆。不可否认,单单从文学本位的角度来看,80年代中期以及中后期的“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的文学价值远远超过了80年代前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等文学思潮,然而前者在启蒙上的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样,不可避免地,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同“五四”启蒙一样,最终陷入了“式微”的悲剧宿命。
关于“启蒙”,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2]在康德看来,启蒙遭遇的最大问题不是理性、理智的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是大量“懒惰和怯懦”之人对于安逸的“不成熟状态”的一味沉溺。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以那些“人道主义”、“自由”、“尊严”等抽象的启蒙理念作为评判的准则,就果断地把“五四”时期和80年代统称为“启蒙的时代”,无疑是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启蒙的标准。从严格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的启蒙和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都远未能真正实现。
20世纪80年代试图延续“五四”时期未完成的启蒙任务,这一出发点固然充满着积极的乐观主义理想,但随着“新启蒙运动”在80年代末期的戛然而止,又把一场演化为“动乱”的激进运动掩埋在我们历史的记忆里。因此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出了“启蒙已经终结”的断言。同时,“启蒙尚未终结”的呼声也此起彼伏,发生于1993年至1995年间“关于‘人文精神’的那场大讨论就是在滤去了‘革命’激情之后的‘再启蒙’”。[13]尽管五四文学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缺陷,并没有完成它应有的“启蒙”使命,但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光荣与辉煌,值得文学史永远纪念。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的“新启蒙”运动也很快销声匿迹了,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作为一个弥足珍贵的人文思想武器,“启蒙”仍然是一个绕不开、永远也不会过时的话题,启蒙的路仍要走,即使是在艰难曲折中负重前行。
[1]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M]//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51.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1.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
[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
[5]林非.对“五四”启蒙与“文学革命”的反思[J].中州学刊,1989(3):3-9.
[6]洪峻峰.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意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61-68.
[7]尚水英.五四启蒙文学的理想与现实效应[J].甘肃农业,2006(2):198-198.
[8]赵黎波.1980年代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现代化特征[J].文艺争鸣,2010(12):114-119.
[9]赵黎波.“重返八十年代”与“十七年文学”研究[J].理论与创作,2010(2):42-46.
[10]丁帆.八十年代:文学思潮中启蒙与反启蒙的再思考[J].当代作家评论,2010(1):4-18.
[11]张清华.“80年代文学”论略:一个文学史的考察[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7):34-43.
[12]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C]//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2.
[13]樊星.从“新启蒙”到“再启蒙”——纪念“五四”九十周年[J]. 文艺争鸣,2009(2):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