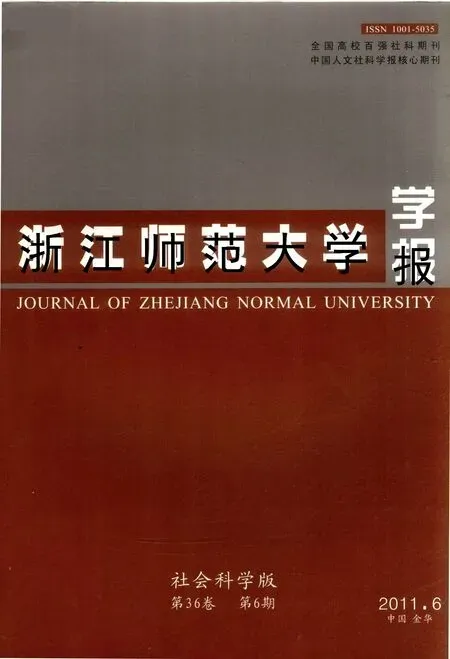2010年度儿童艺术学研究述评
2011-02-20常立
常 立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2010年度,中国生产电视剧的总时长为世界之首,更早一些,2008年度,中国动画片全年总产量为131042分钟,超过日本、欧洲和美国,也为世界之首。学术论文的发表篇数,近年来同样也是世界之首。
然而,诚如盘剑在《中国动漫产业目前存在的四大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在这些令人欣喜的数字后面,中国动漫产业还存在着一些让人堪忧的问题”(盘剑《中国动漫产业目前存在的四大问题》,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在令人欣慰的论文发表篇数之后,2010年度儿童艺术研究领域也还存在着一些让人堪忧的问题。
第一,论文数量可观,而整体质量欠佳,内容相似度、重复度较高。2010年度的儿童艺术研究覆盖了儿童音乐、影视动漫各个领域,既有对历史的考证,又有对现状的考察,既有基础研究的理论热情,又有策略研究的现实关怀,还有对热点问题的积极探索,看似形势喜人。如果穿透繁荣的表象,却会发现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或者点到为止,或者彼此相似,或者新瓶旧酒,而较为缺乏创意、深度、效果和质量。尤其是在问题与策略研究方面,仅动漫产业的问题与策略研究论文在全年就有31篇之多,但提出的问题虽角度略有不同,但彼此间相似度乃至重复度甚高,很多问题其实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报纸上就已被屡屡提出,诸如《国产片真的绝望了吗?》、《目前中国电影的生路问题》(李舰《不一样的白日梦——中西电影艺术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只需把“国产片”更替成“国产动画片”,把“中国电影”改换成“中国儿童电影”,这些问题的答案至今仍然在寻求解答中。更令人担忧的是,解答也是彼此相似的,这就使得成果的实用价值成为疑问。
第二,应用研究比重远超基础研究,但成果缺乏实用价值。2010年度儿童艺术学领域的应用研究所占比重较高,研究者大多比较关注选题的现实意义,注重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问题。例如:袁靖华的《我国幼儿电视节目的发展现状与品牌建设研究》指出了目前洋品牌占据幼儿收视市场的现状,并提出了我国幼儿电视节目品牌发展策略;又如戴与瑶的《中国儿童剧:路在何方?》和陆文喜、陈琰辉的《我国儿童电视节目现状和发展路径探索》指出儿童剧和儿童电视节目在数量不断增加品种日益丰富的情况下仍存在着“成人化倾向严重”等各种问题。研究者都试图针对问题给出解决的策略和方法,袁靖华倡议“一方面要抓住幼儿认知心理,制作品牌娱教节目;另一方面要拓展幼儿节目品牌价值链,建立长效赢利模式”;戴与瑶诊断“国产儿童电视剧欠缺的不是市场,而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开拓的精神”;陆文喜、陈琰辉主张“以儿童为本位”、“深入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等发展策略——一如上个世纪初的研究者所给出的策略。而在动画研究方面,遇到的问题和提出的策略与此相仿,比如:杨利民的《立足本土文化的中国动画产业化发展之路》,朱利民的《文化的另一种发现与输出——传统文化的动漫转化与动漫产业民族品性的培育》,韩波、洪京的《中国传统地域文化在动漫产业的影响》,都不约而同地把显微镜和手术刀对准了产业化方面的“百年陈疾”而给出了“本土化”、“民族化”的“祖传药方”。然而,我们不禁要问:问题还是老问题吗?即便是老问题,解决的方法还是老方法吗?
第三,研究方法较为多样,但理论创新较少,理论深度不足。2010年度儿童艺术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可谓丰富多样,有历史考据的方法,有现状调查的方法,有借鉴自西方各类文艺理论的方法,仅以对电影《小公主》的研究为例,就有《从后殖民主义看〈小公主〉所蕴涵的民族平等与融合》、《从面子论角度浅析影片〈小公主〉中的矛盾激化》、《从接受美学看新版电影〈小公主〉》、《从精神分析批评的视角解读电影〈小公主〉》、《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解读影片〈小公主〉》、《后殖民视阈下的〈小公主〉》、《〈小公主〉神话原型之叙事线条解读》、《从身份认同角度看〈小公主〉中人物命运变化》、《从关联理论看〈小公主〉字幕翻译策略》9种不同的理论阐释。但细究起来,此种丰富存在疑点,上述9篇(还有另两篇研究《小公主》的论文,共计11篇)均发表于《电影文学》2010年第4期和第5期,此外全年其他刊物并无关于《小公主》的研究,由此可猜测此一研究热点并非自然生成,刊物的导向作用至关重要,与其说学者们自主自发对《小公主》进行多元研究,不如说学者们把《小公主》的电影文本当作演练各类文艺理论的操作地和实验场。相似的情况也见于对《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等热点影片的研究,大多止于对西方文艺理论的一般性借鉴和运用,而缺乏理论上的深入分析和创新。这一类研究在重视理论借鉴和运用的同时,较为忽视艺术中的客体,无论采用何种理论、何种观点,批评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与所批评对象的联系。
第四,理论运用过程中对研究对象本体较为忽视。在上面的例子中,把《小公主》替换成其他影片,研究结论很可能并无不同,如是,批评就容易成为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趋向空洞性的纯粹辩证的空谈,而这种批评对象的“蒸发”,正是当下人文学科中重要作品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罗伯特·福格林指出:“如果我们打算从事方法论,它的基本问题必定是:是什么约束使一个特定的学科不至于成为纯粹的辩证?如果答案是不存在这种约束,那么,这就表明该学科已失去了与其主题的系统联系,并且作为一种学科,其实不过是一种幻觉。”(罗伯特·福格林《行走于理性的钢丝上——理性动物的不确定生活》,新星出版社,2007年)这对在日益繁多的批评理论兴起的学术环境下每一种人文学科的研究者都具有警示意义:理论不该脱离非理论的东西(具体作品)的限制。不止是2010年度,包括2007-2009年度,儿童艺术学领域本体研究方面的论文都较为匮乏,学者们或者被关注现实的激情所引导而投入策略研究,或者被理论形而上的冲动所吸引而投入纯粹的辩证。
忧虑之后,必须指出,2010年度的儿童艺术学研究成果绝非乏善可陈,较之于前几年,有几个明显的亮点值得肯定。
第一,历史考据的研究方法,以今知古,以古知今。孙继南的《中国第一部官方统编音乐教材——〈乐歌教科书〉的现身与考索》(载《音乐研究》,2010年第3期),考察了目前所见最早以官方名义统编、出版的音乐教科书《初等小学乐歌教科书》,作者以颇似年鉴派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和治学方法,对该书编纂背景及部分内容进行探索、考析,对“乐歌”的词源进行考辨,并对一些历史事实提出疑点以供进一步查证。论文以珍贵的史料为文本依据,运用历史考据方法加以分析,以今知古,从儿童音乐教育的现实问题出发,从已知推向未知,以马克·布洛赫所称的“倒溯”历史研究法,寻求历史重构,再现“中国由封建社会即将向共和政体过渡的历史背景下”清末政府对待新生的音乐文化品种持何态度及其音乐教育理念。同时由古知今,从清末政府的教育方针、文化政策以及具体的教育举措和教科书中所彰显的意识形态这一维度观照当下的儿童音乐教育现状及其问题。为了正确把握当今社会的儿童教育问题,我们从晚清民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延安讲话等历史事件中应能获得有益的启迪——历史考据的研究方法,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在于此。此外,杨和平、宋莉的《近代化历程中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材建设问题》(载《人民音乐》,2010年第9期)研究了近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中国音乐教材的特点,为当今的音乐教材编撰工作、音乐教育事业提供经验与教训。
第二,现状考察课题,彰显出现实关怀。夏小玲的《论音乐教育中的公平问题——以鄂南地区部分中小学为例》(载《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关注音乐教育不公平的现象,指出鄂南地区音乐教育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城乡、区域、校际间音乐教育发展不平衡,提出应建立健全音乐教育援助制度、强化农村学校音乐教学管理、加大对音乐教育资金和设备的投入、加快农村音乐教师队伍培养、建立健全音乐教学考核机制、完善农村音乐教育监督机制,以落实音乐教育的公平。邓琪瑛在《一个被激活了创继潜能的新典范——论“婺娃娃”的培育与“校园儿童婺剧”发展的可能性》(载《民族艺术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中关注学校的戏曲艺术教育。作者分别针对培育工作者的“境教智慧”和儿童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作了实地的考察和论证,总结出“婺娃娃”在“境教智慧”下得到了很好的艺术传承;在扎实的传承基础下,“婺娃娃”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让“校园儿童婺剧”得到应有的发展,并以此来丰富婺剧的生命内涵。
第三,符号学、叙事学的研究更趋深入。李涛的《商业动画电影的符号学解读:改编与意义再生产》(载《当代电影》,2010年第8期),以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及其美国改编动画电影《小美人鱼》和日本改编动画电影《悬崖上的金鱼姬》系列文本为例,运用符号学理论解读美国迪斯尼和日本吉卜力商业动画电影的叙事符号和意义生产,指出“成功改编的商业动画电影是观照文化规范的产业符号编码,造就的是‘符号真实’和‘审美体验’,动画电影内容生产的实质是符号生产”。此一论点颇具启发性,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和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的方法也可移植到对中国商业动画电影的研究中去。论文进而指出:“在动画文化生产的流程中,第一步骤是选择动画文化内容,对即将开发的文化资源进行研究,附之以内容符号。下一步骤才是根据动画电影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设计符号内容生产和销售,形成在出版物、演艺、互联网、室内外游乐、食品、广告代言、文具、玩具、工艺品等相关市场中,层层回收的价值产业链”——此一策略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当下中国动画电影的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状况如何?更大的潜意识的心理结构为何?适应其心理的符号如何设计?在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如何选择动画的文化内容?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更深入的研究探讨。陈晓云的《动画电影:叙事与意识形态》,对动画电影《功夫熊猫》、《麦兜响当当》和《宝葫芦的秘密》的叙事进行比较研究,以探讨动画电影叙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指出:“动画电影的想象力更接近于儿童的非逻辑、非常规、非线性思维,或者也可以说是反成人常态逻辑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动画电影的外在形态与叙事特征。动画电影在意识形态诉求上显然更着意于人类共性的文化内涵,因为作为动画电影主体观众的孩子,与成人世界相比,其意识形态呈现出更少的差异性和更多的普泛性特点。动画电影比起常规的以成年人为基本受众对象的故事电影,更需要‘寓教于乐’,更需要通过影像和叙事形象来有效地完成意识形态的传达,而不是借助简单的说教。”(陈晓云《动画电影:叙事与意识形态》,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而具体如何通过影像和叙事形象来有效完成意识形态的传达,则仍需进一步地思考、分析。周涌、冯欣的《在想象与现实之间飞行:中国青春偶像剧研究》(载《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通过对中国青春偶像剧这一“亚类型”的分析,归纳出与中国青少年青春期接受心理相适应的叙事主题模式、演员配置模式和视听语言模式,指出“青春偶像剧中的世界是带有很强虚幻色彩的想象性现实,它映射了这一代人面对现实时的内在需求,物质化地再现了他们想要在现实社会里实现的东西”。因而其叙事主题模式体现为青年人最关注的励志、爱情和时尚,演员配置模式体现为消费时代具有大众亲和力的偶像明星,视听语言模式体现为时尚的画面结合流行的音乐。
第四,问题及策略研究更具深度。此处主要是指盘剑的《中国动漫产业目前存在的四大问题》一文(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动漫产业存在的问题有:“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将动漫作为产业发展在具体操作层面出现了矛盾;动漫产业“产量”高而“产值”低;动漫教育与动漫产业的实际要求、需求脱节,导致动漫行业“人员”过剩、“人才”奇缺,某些环节的专业人才过剩,而另一些环节的专业人员却奇缺;理论研究滞后且缺乏足够的重视,已严重影响动漫产业的发展。尤其问题一和问题四的提出和分析,是近年来问题及策略研究方面颇具深度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动漫的受众并不限于儿童,从中国的相关政策来看,动漫的受众也包含各个年龄段。儿童本位还是兼顾成人?分级制是否应当实施并且怎样实施?……以及儿童影视动漫的本体研究如何才能有所进展?儿童艺术教育的瓶颈问题如何解决?所有这些新老问题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会日益醒目,是研究者不该回避也无法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