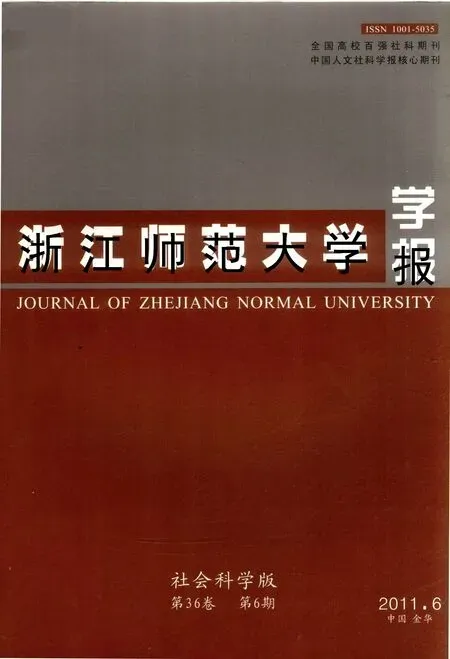汉末士人政治困境中的突围
——从《中论》、《昌言》中作者的“介入”谈起
2011-02-20杨霞
杨 霞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部,安徽 合肥 230022)
中国古代士人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而“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1]政论散文即是士人参与政治的有效途径与表达方式。对政论散文作深入研究,可对其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士人的立场、观点乃至情感都有深刻认识。末世政论文尤其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深味此期文章之运词结句,更易窥探动荡时局下士人的心理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士人群体的分化与重组。汉末士人徐干的《中论》与仲长统的《昌言》即有这样的考察价值:两部文集同属政论名作,《中论》“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2]669《昌言》“切中利弊”、[3]“笔力风裁俱称”;[4]两位作者皆为汉末名士,徐干入选“建安七子”,仲长统位列“后汉三贤”。二者可视作汉末士人群体的代表人物,但两部作品侧重不一、文风相异、情绪有别,留于后人的启示亦有不同。本文尝试从语言学研究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评价系统”的“介入”理论,对《中论》、《昌言》中作者的“介入”信息作一微观考察,并由此铺延至对汉末士人突围政治困境的宏观把握。
一、“君子”与“我”——写作主体的介入方式
“介入包括表明语篇和作者的声音来源的语言资源,它关注的是言语进行人际或概念意义的协商的方式”,[5]主要表现为作者对“借言”或“自言”表述方式的使用。借言带有或显或隐的对话性质,是作者抽离于所评价事物,“客观介入”并表达观点的方式,“意味着语言使用者的客观取向”;[6]自言是作者直接介入事态,感同身受,进行“主观介入”,它“意味着语言使用者的主观取向”。[6]作品中人称、词语、句式的运用是判断作者介入方式与介入程度的重要质素,其中人称的使用是作者介入的最直观表达。
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应采用信息化技术,创建电子商务平台,对外公开财务信息,人们可随时查询所需数据。电子商务平台有利于会计人员掌握财务处理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使得农村财务管理更加规范化与高效化。
总的来说,这时期体育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以职业化、市场化为核心的体育改革发展符合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是符合现代世界体育发展潮流和规律的。改革中逐步形成以体育法制化发展为根基、政府实施全民健身计划、集中力量兴办奥运战略、体育社会组织协助政府推进社区体育发展、企业投资和兴办职业体育的混合型政府体育管理体制。
落实于《中论》、《昌言》两部政论著作,前者多表现为以“君子”、“圣人”发声,而后者多以“我”来直陈。《中论》中,“我”有45次,“吾”20次;“君子”、“圣人”分别出现了 105次与 45次——“君子”数量最多;《昌言》中,“我”出现了47次,“吾”5次;“君子”、“圣人”使用较少,分别是13次和5次——“我”次数最多。
《中论》多直接以“君子”谋篇立论,“作者介入最少,拿别人的话为自己服务,以达到说服别人的目的”。[6]这里的“别人”集中表现为君子、圣人。以《治学》为例,作者开篇即表达观点:“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指出学习是成就德行的有效途径,也是“圣人之上务”,又以子夏“日习则学不忘”之语来论证学之不懈的重要性。[7]254-255再如《贵言》一篇,首句即言“君子必贵其言”,“君子非其人则弗能与之言”,又以《易》之“艮其辅,言有序”来论证“与之言,必以其方”的观点。在谈到君子之言“弗过其任而强牵制”时,以孔子“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加以佐证。[7]273综观全书各篇的写作思路,大多是先作价值判断,即标明“君子”的理想范式,然后对社会现实作事实判断,并随时以先哲圣贤为例加以辅证。“君子”的典范作用贯穿了整部文集。
(一)《中论》以“君子”为重,全书弥漫儒者之风
不同人称的使用在《中论》、《昌言》中存在着数量、主次、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作品呈现出如下特色:
从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论新药创制与仿制药产业的共同发展…………………………… 邵 蓉,董心月,蒋 蓉(3·161)
类似的细节遍布于文学史。6月8日,百岁刘以鬯在香港去世。对大部分读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名字。他去世后,众多媒体围绕着他和王家卫、和《花样年华》才能做起文章,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之于现代文学、香港文学的重要性。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是他从上海到重庆编辑《扫荡报》副刊时,专门约稿、编发的。包括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姚雪垠,创作起步的主要支持者正是在上海开办怀正文化社的刘以鬯。
相对而言,《中论》中“我”、“吾”多出自经典之文,多用来证明“君子”之道,而非作者情绪的率性抒发。如以《诗经》之《大雅·棫朴》“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句来说明“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7]261的重要性;以《小雅·小宛》“相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句来强调“君子服过”、“迁善不懈”[7]271之举;以《小雅·鹿鸣》“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句来说明“礼乐之所贵”而“欲为夫君子,必兼之”[7]277的道理;以《小雅·节南山》“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句描述“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时世之不遇”[7]284的心境。此外,“我”之出处尚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7]284取自《周易》、“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7]280出自《论语·先进》、“此天亡我,非战之罪”[7]310出自《史记·项羽本纪》等。
可以说,上文中的“君子”即是“我”所推崇之人,而“圣人”则是更高层次的“君子”,是“君子”、“贤者”之师。
(二)《昌言》以“我”见长,全书充满浓厚的“自我”意识
《昌言》中“我”时时出现,并具有多重身份。首先,“我”是不同于“彼后嗣之愚主”的“人主”:“我”有“公心”、“平心”、“俭心”,则士民不敢“念其私”、“行其险”、“放其奢”,“政平民安,各得其所”,以致“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皆归心于我矣”;[8]948-949其次,“我”是与“豪杰战争者”对立的正义之师:“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图,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8]948再次,“我”又是普通人,以“士民”之心去看世间百态:“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8]956“我之欲尽孝顺于慈母,无所择事矣。我之欲效恩情于爱妻妾,亦无所择力矣”;[8]952“人之交士也,仁爱笃恕,谦逊敬让……有负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8]954“我”虽随着情境的不同变换着身份,但都显示出个体的独特性,都介入事态,表明了自己的鲜明立场与观点。
空间计量方法最早应用于截面数据分析,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相关性。随着计量方法和大数据的发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学者们将空间计量运用到面板数据中,提出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s Model,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
与“我”相对应的“君子”一词在《昌言》中使用较少,且其神圣性远不及《中论》之“君子”。这里的“君子”易陷入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锔高天,蹐厚地,犹恐有镇厌之祸也”,[8]949而“禄不足以供养”的局面使得君子“营私门”,正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8]951至于“囊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的权责倒置更是对君子的刁难,犹如“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8]951
可见,《昌言》中的“君子”与《中论》中为帝王师、为众生师、为万世师的“君子”有别,它只是“我”的一个考察对象;而“我”的多重身份则表明了作者开阔的思维方式及更深层次的作者个体意识的日益觉醒。
二、《中论》“君子之风”与《昌言》“自我意识”的成因
《中论》、《昌言》两部政论文集既反映了汉末士人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乱世中澄澈天下的愿望,又体现了士人在精神领域内自我救赎的努力。前者处处以“君子”立意,表现出趋于上的道德领域的升华;后者时时突显“我”之风采,表现出趋于内的自我意识的深化。就徐干、仲长统而言,两人所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非常相似,皆处在黄巾军大起义至献帝禅位、魏国建立的动荡时期,同样才华横溢、声名远播,也都曾侧身于曹魏集团,但他们的文章却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品貌与风范,这与他们各自的气质、学术思想和政治环境有关。
在这种新型的雇佣关系下,对于劳动者和企业而言都是有利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可以很大程度上自由利用,并且可以为多个企业、机构或者个人提供劳动;而企业则可以节约长期用工成本,同时还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
(一)个体气质有别
与“君子”之道的理论化阐述相对应的是作者对汉末乱世道德沦丧、学风败坏现象的有力抨击。在《谴交》篇中,徐干指出士人背井离乡、四处交友、夸夸其谈,皆意在“欺人主、惑宰相、窃选举、盗荣宠”;[8]291而针对其时“冠盖填门,儒服塞道”的尊学尚贤之假象,徐干指出了其“为师无以教训,弟子亦不受业”的虚伪实质。[8]292
仲长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友者多异之”,且“谓之狂生”。[10]1644据《后汉书》记载,仲长统游学时曾面刺其时并州刺史高干“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的性格缺陷,《昌言》中也明确提出“三代不足摹,圣人未可师也”[8]950的观点。对高干的直言无忌和对圣人学说有选择地接受,体现了仲长统的狂狷之气,反映在作品中亦是鲜明的自我意识的张扬。
(二)学术思想差异
徐干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是儒家正统思想的忠实信奉者和传承者,反映于《中论》一书的是“士志于道”的儒家大义、“哀而不伤”的儒学诗教观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儒者气质。同时,两汉以来儒学的尊贵地位带来儒生的济世天下的使命感与优越感使得徐干不可避免地居于高处,俯瞰世间百态,并以君子、圣人发声。作者多采用全知全能视角著述文章,从此处亦可窥知一二。
仲长统的思想较为复杂,儒道互补、由儒入道是仲长统思想的主流。法家观点在其作品中也有反映。对诸家学说的学习与内化,正是仲长统发挥个体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可以说,兼蓄众学说之长的治学能力与学术素养使仲长统对个体价值、自我意识有了更深刻、更清晰的认知。
(三)政治环境不同
徐干与仲长统都曾一度进入曹魏权力核心:徐干事曹“历载五六”,[8]1360先后任“司空军师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11]599以诗文出彩,得到喜爱文学的曹氏父子的垂青;仲长统以政治判断力发迹,受尚书令荀彧器重任尚书郎一职,成为曹魏核心军事层中出谋划策的政治幕僚。两人又皆有隐逸之志:徐干被曹操征用前“闭户自守,不与之群,以六籍娱心而已”,托病辞官后更是“潜身穷巷,颐志保真,淡泊无为”;[8]1360仲长统弱冠之年游历四方,失望于黑暗现实,“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10]1644有超拔尘俗、遗世独立之想,并写下了“岂羡夫入帝王之门”的名篇《乐志论》。
反映到各自的作品中,《中论》像一本规范社会与人心的教科书,这与徐干或高居庙堂或避世不出的生活方式有关,这种生活方式导致其未曾深刻、全面地考察百姓疾苦、民生凋敝以及王朝倾覆的本源;《昌言》则更像是个人情绪的厚积薄发,游学民间的观与感、权力中心的浮与沉使仲长统“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10]1646在论理乱损益之时,蕴藏着对自身价值的深刻思考。
三、“君子”与“我”——士人政治困境的突围
(一)汉末士人突围政治困境的方式
多以“君子”借言的论述方式使《中论》的说教意味浓厚,以“我”自言的方式使《昌言》的抒情色彩凸显。两种介入方式的运用也隐约昭示着汉末士人在复杂时局中的政治走向。
1.《中论》描述了汉末士人趋于上的道德精英路线,亦有对道统的回归
“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8]1360是徐干写作《中论》的初衷;“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12]并以儒学圣贤之道重建有序社会是作者的意旨;建立一套“君子”标准以垂范当世乃至后世则是作者心中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不二之法。
有别于传统士人“富贵于我如浮云”的价值观,仲长统提出了“高薪养士”的主张。他认为君子居高位,本应“重肉累帛,朱轮四马”,而现实却是以“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8]950如此“得拘洁而失才能”,是“开虚伪之名”,[8]951亦是对人才的废弃。在《乐志论》中,作者更直抒对“居有良田广宅”、“舟车足以代步涉之难,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8]956的悠闲富裕生活的向往。此种观点彻底背弃了“君子固穷”、“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传统儒家理念,更多的是对个人幸福的向往及个体价值的认同。
徐干出身庶族,“其先业以清亮臧否为家世”,[8]1360少有才气,长成后“擅名于青土”,性格“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2]669不喜交游,曾拒绝州郡的征召,一度“绝迹山谷,幽居研几”;[2]2又以诗文获得曹氏集团青睐,与曹氏兄弟及王粲等邺下文人交游酬唱数年后,托病辞职。其一生大致平稳,心态平和,有彬彬君子气质,作品也熏染上“雍容静穆,霭然儒者之度”[9]的文风。
仲长统还进一步提出了“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主张,并按照对人事和天道的利用程度,将帝王分成“审我已善,而不复恃乎天”的一等、“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济者”的二等和“不求诸己,而求诸天者”的末流三个层次。[8]955主张求诸于己,注重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这同样体现了作者对个体价值的思考和崇尚。
2.《昌言》描述了汉末士人趋于内的自然名士路线,亦是对个体价值的审视
与对个体价值的认可旋踵而来的是作者自我意识的张扬,这种意识尤其反映在仲长统不守章句、不随流俗的治学态度上。汉代经学重承袭,强调传授先师之言。至于东汉则变本加厉,士人思想禁锢、墨守成规。关于此,仲长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方面他认为“规矩可模者,师传之德也”,[8]957指出尊师重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三代不足摹,圣人未可师也”的观点,称不应盲目遵从书本和老师。在与侍中邓义就“社所祭者何神”的争论中,仲长统进一步以“先儒未能正,不可称是。钩校典籍,论本考始,矫前易故,不从常说,不可谓非”的言论推翻了邓义“唯书本”的论战方法。[8]946
在《中论》开篇《治学》一文中,徐干指出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的根本原因在于“学也”,认为通过学习可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这是成为“君子”的先决条件,亦是“圣人之上务”。继之,徐干提出了“君子”尚需必备的其他条件,如“君子必贵其言”、“君子必立其志”、“君子必择师”、“法象立,所以为君子”、“君子敬孤独而慎幽微”等等。
这种趋于更高精神领域的道德精英路线也标志着士人向道统的回归。中国古代士人一直在道统(道德标准与精神价值)与政统(世俗政治权势)的复杂互动中寻找平衡和突破点,之于大道不行、政局动荡的汉末乱世,徐干探寻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即以道统规范或重建政统,具体反映于道德标准的构建、世俗人心的净化和彬彬君子的塑造。这是自汉初独尊儒术而使道统沦于政统权威之下的几百年后士人对道统的挺立,是对先秦“道尊于势”理念的继承,也是陷于政治困境中的汉末士人对政治权势的突破与超越。
《昌言》是针对时局的直言、当言之作。该书直陈戚宦政治、豪强经济、动荡军事等各领域的危机,“闿陈善道,指斥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磨灭者”。[8]948与对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深刻洞悉和细致考察相一致的,是作者对个体价值的考量,这是一种趋于内在的自我审视。
对数学任务的分析主要借助“QUSA课题”[9]中所使用的课堂教学中任务展开的分析框架,主要分析教师在同一课题的教学设计、第一次教学和第二次教学时的数学任务数量、内容以及探究水平三个方面的内容.
在《乐志论》中,仲长统抒发了“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8]956的寻求自身超越的心绪,个中对理想人生的描述,体现了儒学精神的逊色及道家气度的渗透,也体现了士人与政权的疏离、国家意识的淡薄和个人意识的强化。在《乐志诗》中,仲长统又表示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这是对“委曲如琐”的政治生涯的绝望,也是对世俗生活的回归。这种“翱翔太清,纵意容冶”[10]1645的生活主张于其时恰如星光一点,但却与其后魏晋名士的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相契合。正如元人吴师道所评价:仲长统“得罪于名教甚矣。盖已开魏晋旷达之习,玄虚之风”。[13]在他身上折射出的两汉儒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光与影,使他成为了魏晋名士的先驱,汉末士人由任“道”变为任“自然”的名士轨迹亦由此得以呈现。
(二)汉末士人突围政治困境的方式的广泛性及意义
无论是标榜君子,以道统重建政统,还是张扬自我,从社会的良心走向个体的内心,都可总结为汉末士人与皇权的疏离。这种疏离以东汉建国光武帝“虽置三公,事归台阁”[8]951疏远士人为伊始,以东汉中后期清流士人“匹夫抗愤、处世横议”[10]2185与政治相博弈为高潮,发展到政治衰颓、山河板荡的汉魏易代之际,终于形成了士人主动疏离皇权、突围政治困境的局面。
通过安装在育明轮上的船舶能效监控系统测出船舶在不同吃水差下主机每海里的油耗,为了更明显的反应不同吃水差下主机每海里的燃油消耗量的变化,用燃油消耗量增减比来表示,即:
对于Nt ≤ Nr的系统,分别进行搜索星座符号的实部和虚部,如果i>Nt,则开始搜索虚部。根据表1,搜索一个虚部的计算量包括以下两部分:①2Nt ≤ i ≤2Nr时,计算需要(2Nr-2Nt)次实数乘法;②Nt≤i≤2Nt时,计算需要2Nt次实数乘法。由于R1是上三角矩阵,因而②中包含了(Nt-l)个无效的操作,因此总共需要(2Nr-Nt+l )次实数乘法.一旦i=Nt +1,发现一个可能的虚部就开始搜索相应的实部.由于计算需要3Nt次实数乘法,其中包含(Nt-l)个无效操作,因此搜索一个实部需要(2Nt+l )次实数乘法运算.
执著于儒学大义与君子之道的汉末士人是东汉政权长期“倾而未颠,决而未溃”[10]2043的砥柱。孔融任北海相期间,“立学校,表显儒术”;[10]2263郑玄“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10]1212刘桢著《毛诗义问》10卷;刘劭著《乐论》14篇;即使是标榜“唯才是举”的曹操,也在其散文名篇《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提到对乐毅不背燕、蒙恬不背秦的激赏,并说“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8]1063以示对君子重义轻生的推崇。可以说,虽然“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11]420但正是汉末士人对儒学的坚守、对道统的推崇使得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领域自汉以后就未动摇过其主导地位”。[14]
转向内心世界,张扬自我个性的汉末士人为陈腐的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马融“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10]1972崔寔发出“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治哉”[8]722的质疑,又有群臣“奉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必然导致“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生”[8]726的言论,与仲长统观点如出一辙。“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15]
上述这两种趋于上、趋于内的路线并非矛盾对立的,在某种程度上,两种路线可以合二为一,即外名士、内君子。就其本质而言,这两种路线又是儒、道思想作用的结果,即以儒治世、以道存身。汉末士人多同时具有这两种特质。如徐干,言论上虽以儒学为重,但其行为却染有道家思想中出世、归隐的特质;再如仲长统,虽张扬个性,却也秉持着“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8]953的正统思想与“肃礼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义,敬天地,恪宗庙,此吉祥之术也”[8]952的儒家礼学主张。
总之,以关怀天下、济世苍生为出发点,以“指切时要,言辩而确”[10]1725为特征的政论文流露出作者对政治的疏离态度,表明了汉末士人政治突围的广泛性。这种突围与士人在末世中“咸复思中兴之救”[8]722的理念并不矛盾,它更多的是对于世俗皇权的摆脱,表现了士人欲以更高姿态、更独立精神激浊扬清、匡扶衰弊的思考与实践。正如徐干所言:“贤人之道者,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或见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遐举,或被髪而狂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辞聘而山栖,或忍辱而俯就,岂得责以圣人也哉!”[7]298-299更进一步言之,此期士人“大抵能同气相求、殊途同归地保持一致”,“依然程度不同地在完成着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16]即面对乱世说出真相,面对强权说出真理。
[1]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王弼,注.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3.
[2]陈宏天,赵福海,陈复兴.昭明文选译注:卷四[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3]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儒家类[M]//续修四库全书:第12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31.
[4]归有光.诸子汇函[M].明天启六年(1626年)序刊本.
[5]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26-327.
[6]王振华.杂文中作者的介入[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2(1):58-64.
[7]俞绍初.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9]徐湘霖.中论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0:327.
[1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773.
[13]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584.
[14]郝虹.汉末魏晋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J].孔子研究,2006(2):67-74.
[1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62.
[16]汪国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5):8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