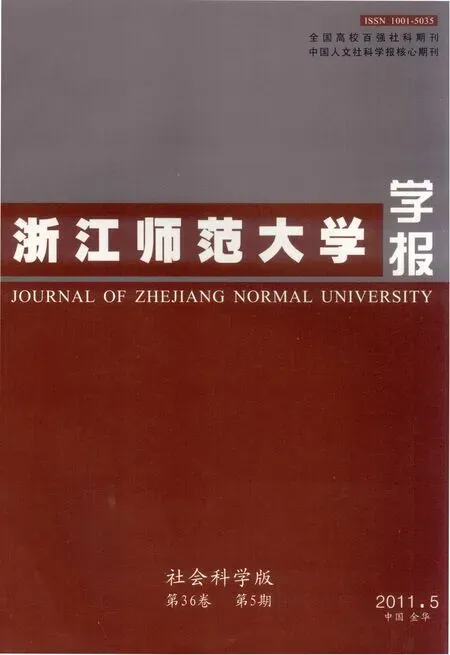西方国家中央政府部际协调机制研究及启示
2011-02-20曹丽媛
曹丽媛
(北京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6)*
大部制作为对西方改革实践的借鉴已经在我国正式拉开帷幕。通过对西方大部制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央政府部门间高效、合理的协调机制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大部制与部际协调机制是加大政府机构整合力度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研究西方国家中央政府建立部际协调机制的主要做法与基本经验,对我国成功实施大部制改革并进一步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国家中央政府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背景
1.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改革兴起于西方国家,通过引入企业管理的先进做法提高了政府效率。但与此同时,新公共管理中分权、建立“单一目标组织”(single-purpose organization)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加深了政府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程度。政府各部门只关注于本部门的目标,忽视政府整体目标的实现,各自为营甚至出现地盘之争(turf-war)。1997年,布莱尔政府上台伊始就提出了旨在应对中央政府的碎片化和空心化(hollow out)的协同政府概念。它是作为“部门主义”(departmentalism)、“管窥之见”(tunnel vision)和“垂直仓”(vertical silos)截然相反的措施提出来的。[1]协同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与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连接政府(connected government)、横向政府(horizontal government)等已成为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导着西方政府对新公共管理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修正。
2.解决社会“棘手问题”的需要
棘手问题(wicked issues)已经成为当代公共行政和管理的组成部分。它们具有的不稳定性、社会复杂性、目标模糊性等特点,使得棘手问题不可能由单一的部门独自解决。因此,处理棘手问题需要全面而非线性的思维,这种思维可以把握住大局,包括造成问题产生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政策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2]具体到政府管理方面,解决棘手问题需要跨越部门界限进行合作,不仅需要垂直层级上的合作,也需要水平方向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例如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生物安全或者大范围的流行疾病等,使得政府与外部、政府内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对政府协调包括部际协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虽然西方国家中央政府进行的部际协调活动已经有很长历史,但是传统的集中化结构(例如内阁协调)和集中化协调程序(例如预算管理)已经不能完全解决现在的“棘手问题”了。
此外,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减少了横向沟通与协调的成本,公众期望与消费者主义的影响使公民希望获得满足他们需求的公共服务,学界的关注点已经从原子化的模式转向整体的分析。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协调需求的增加,有助于采取更全面的方法制定公共政策,“在一个全球化和欧洲化的世界,政府不得不用一个声音说话,并在治理模式上更加协调一致而不是相反”。[3]4
二、西方国家中央政府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主要做法
机制一词首先用于机械专业,后引入社会科学领域,是指使各种体制得以进入运行状态并发挥特定功能的方式、方法、工具、技术的总称。虽然没有大家一致认可的关于协调的定义存在,但结合机制的含义,我们可以将政府部际协调机制视为在合作的管理理念引导下,在特定的政策领域范围内,使处在水平方向的政府各部门协调配合并进入协调状态的方式、方法、工具和技术的总称。
1.中央政府部际协调的结构技术
德国学者Thurid Hustedt和Jan Tiessen将中央政府的协调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结构技术,另一种是程序技术。结构协调技术是指中央政府为了制定协调一致的政府政策而建立某种组织结构的方法。[4]9这种技术的使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立新的组织并赋予其资源、权威和一定程度上永久性的地位进行协调。如丹麦在二战后建立了内阁委员会,承担了丹麦中央政府大部分的部际协调职能,“不夸张地说,作为丹麦中央政府协调的结构技术,内阁委员会已经制度化了”。[4]19或者设立超级部(superministry),也就是大部制改革,将职能有重叠的部门进行合并,将部门间冲突转换到合并后的部门内部进行解决,以此减少部门间冲突,实现部际协调。二是成立专门的部际委员会或者类似组织。如挪威在加入欧盟后,对中央政府横向协调与一致的要求提高,为此挪威成立了包含中央所有部委和各种相关政策部门的特别委员会。但作为部际协调的方法,委员会也有其局限性。[5]委员会的优点是在没有中央权威的干预下,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与协调,它在促进部门间对话和信息交换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在某一艰难决策上僵持不下时,也会形成零和博弈,导致资源的浪费。
英国布莱尔政府则在1997年创立了第一个跨部门组织——社会排斥小组。此后,绩效与创新小组、妇女与平等小组、区域协调小组等相继成立,这种跨部门组织既涉及到政策制定领域,也存在于执行领域,是结构协调技术的另一种组织形式。他们的任务就是针对某一个特定问题打破组织壁垒,将不同的部门资源整合起来,实现跨部门的合作。
2.中央政府部际协调的程序技术
部际协调的程序技术是指中央政府为了制定协调一致的政府政策,对协调的各种方法和手段进行安排的技术。程序协调技术首先将协调视为一种过程,把中央政府各部门职权的配置视为这个过程的开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组织边界的划分。此外,在按照职能对部委进行权限划分时发现,相较于其他部门,一些部门本身就具有协调的任务。例如首相办公室(Prime Ministry Office)、内阁办公室(Office of the Cabinet)、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和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等等。丹麦的财政部就因其日益提高的协调能力被称为“伟大的协调者”(the Great Coordinator)。因此,中央政府在权限划分的基础上应扩大这些部门的协调权限。
其次,程序协调技术将中央政府部际协调分为三个阶段,行政协调、政治—行政协调和政治协调。每个阶段的参与者不同,协调的方法也不同。在行政协调阶段,所有活动由一般公务员(rankand-file civil servant)参与,对他们进行协调的方法往往是制定法律、签订合作契约等。德国政府为了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制定了联邦各部委间的联合程序法(The Joint Procedural Code),为公务员在横向协调的活动中提供了行为规范;英国则将公共服务协议(Public Service Agreements,简称PSA)作为中央政府核心部门控制和协调公共活动的具有创新性和发展潜力的工具。而行政—政治阶段作为中间过渡阶段,由于高层公务员(top civil servants)的参与,对政治因素的考量逐渐增多。到了协调的最后阶段,政治协调阶段则涉及政府各部委和其他政府领导。例如,丹麦的经济事务委员会和协调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两个最重要的委员会,前者由经济部领导,后者则由首相领导,协调委员会甚至被称为“内阁中的内阁”(inner cabinet),[4]18因为政党领导(和高级内阁部长)一般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3.培养具有协调技能的高级公务员
经合组织在2001年的报告中将公共部门的领导扮演的角色分为以下几种:变革推动者、提高效率的促进者、政府政策的协调者和公共服务价值的守护者,并认为高级公务员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加强政府内部的凝聚力、实现政府的协调与整合。政府内部的合作需要这样一个协调“企业家”,[3]7他们可以通过创新等方式发现和重新定义问题,提高政府内部组织合作的能力并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战略途径,促使政府以整体的形式运作,而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部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丹麦中央政府19个部门的常任秘书(the permanent secretaries)参加每月一次的午餐会和半年一次的研讨会就已经成为传统。[6]20这些会议为加强常任秘书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并提高其协调能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而里根政府班子中与其他部门的联系率比卡特政府高出55个百分点,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里根政府增加了4位进行信息协调的高级助理,他们介于总统与白宫各部门之间,其任务就是接受大量信息并经常互通信息,以加强总统与政府其他部门的联系,实现政府的协调。[7]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实现协调的方法和技术是可以混合使用的,而高级公务员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反过来,这也会促进高级公务员的协调能力。“如果高层公务员可以引入一套混合协调战略,实现中央政府部门间冲突和协调的平衡,高层公务员进行部际协调的能力也会加强。”[6]31
三、西方国家中央政府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经验及启示
通过对西方国家中央政府构建部际协调机制主要做法的分析,我们发现不管是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例如英国、澳大利亚等),还是欧洲的莱茵国家(例如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例如瑞典)的中央政府,“协调和‘水平状态’都是政府从业者永远追求的行政圣杯”。[8]虽然在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具体做法上有国别的差异,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部际协调机制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而国家面积的大小(常住人口数量,地理区域)、国家结构形式(联邦制与单一制)、宪政体制(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政权组织形式(集权制与分权制)以及中央政府体制(总统制、内阁制与委员会制)等对中央政府部际协调机制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丹麦在行政阶段的协调方式很大程度上都是非正式的方法,而德国采用的是正式的协调规则,瑞士则选择了以上两种方式的混合类型。这种差异是由国家不同的宪法传统造成的:德国宪法甚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开始为联邦政府制定明细的程序法规,而丹麦和瑞士则没有这种宪法传统。因此,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在进行部门间冲突的解决和协调时都结合本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构建有本国特色的政府部际协调机制。例如,最早实行内阁制的英国在其内阁中有个特殊的职位,称为“不管部长”(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一般按照传统由枢密院长、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或掌玺大臣来承担这个角色。“不管部长”常被任命为内阁委员会的主席,因为他们超脱各部,有利于部际间的协调。[9]而现在,“不管部长”或类似的角色作为一种协调机制已经被烙上英国特色,飞越英吉利海峡推广至其他内阁制国家甚至实行不同政府体制的国家。因此,建立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部际协调机制是我国构建完善的中央政府部际协调机制的首要原则。
2.网络协调模式逐渐兴起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对跨部门协调、无缝隙和更具创新性的服务供给模式的需求逐渐增多,以等级制和法定权威为基础的传统的官僚协调模式已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许多国家的中央政府开始引进以主动创新为基础的网络协调模式来实现“协同”,并在不同的方案和项目中实现服务产出的最大化。“将当代政府结构视为‘多元化组织’网络或者‘松散耦合式’的组织体系,而不是命令和控制的等级结构的看法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这个背景下的协调涉及对差异性的管理和多样性的包容。”[10]例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①的政府服务供给项目(The Government Service Development Project,以下简称GSD)就是中央机构通过网络协调模式完善政府服务的一个尝试。GSD项目设置了共同的价值观并对网络中的关系进行梳理,以此形成一个覆盖现有的和即将出现的政策及服务的治理网络,将政府服务整合进入一个更有凝聚力的、协调和全面的服务供给体系之中。正如福山所说:“高度分权组织内部的协调问题的另一种解决办法就是网络。它并非是由中央集权的权威创造的,而是由分权后各部门间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自发秩序。”[11]而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以领导权威和层级为基础的官僚协调方式在我国各级政府中占据主导优势,虽然这种模式具有快速整合各种资源的优势,但是对于政府最高领导协调能力的过度依赖,会使领导陷入无止境的协调活动中不堪重负,同时也抑制了其他参与者的积极性与创新性。因此,引入以参与者的主动性、平等协商和协调对象的综合性等为内容的网络协调模式,并与官僚协调模式相结合是我国政府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必然选择。
3.培养相互信任的文化是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关键
新公共管理改革不仅使结构上的碎片化程度加深,文化上的分裂也同样如此。所以,文化因素在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中越来越凸显,包括创造一个更“全面”的文化的努力,其中信任文化和合作文化的发展被视为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和部门主义的一种平衡。在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中,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促使公共组织在文化上重新结合起来。文化不仅涉及垂直方向的深度,也与水平方向的宽度相关,它意味着同一机构不同组成部分中的人员(这里指的是中央机构的公务员),必须在文化上彼此相连并且身处同样的文化氛围之中。而相互信任的文化似乎包含了以上所有方面,培养相互信任的文化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共识。澳大利亚政府的“价值管理”(value-based management)就是这样一种努力,通过制定公务员和领导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和价值观,培养有助于实现协调的信任文化。在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各部委及其成员之间培养相互信任的文化对于我国部际协调机制的建设也非常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和”思想(“和为贵”、“地利不如人和”等)与信任文化就存在着一定的契合之处。因此,我国政府在培养有利于部际协调的信任文化时应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拉长政府人员的信任半径,扩展其信任范围。
4.政治权威的支持是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前提条件
传统公共行政中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一直饱受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质疑。到了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实践再次证明绝对的政治与行政分开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中央政府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过程中,政治因素始终贯穿其中。
强调内部横向协调的“协同政府”之所以最早出现在英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台伊始的首相布莱尔,除了修正撒切尔时期新公共管理改革加剧的碎片化,最重要的是向选民展示本届政府要走一条不同于老左派(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右派(撒切尔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而在协同政府或者整体政府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例如,昆士兰的GSD项目虽然得到了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和认可,但是最终被废除。该项目政府执行小组的大部分成员认为缺乏来自高层的政治支持是项目难以继续运行的首要原因,[12]主要体现在项目运行所需要的资金预算得不到议会的批准。同时,随着后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政治官员对行政事务的干预也越来越多,期望通过积极参与政府的协调活动加强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活动的控制,以重树其因为新公共管理的分权化和去中心化等改革削弱的政治权威。可见,政治因素在启动、运行甚至终结部际协调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政治权威的支持是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前提条件。
与西方政党制度不同,我国宪法规定了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政府领域的各项改革不仅不会影响党的权威,反而会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党的领导并维护党的权威。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不仅拥有绝对领导地位,党的领导包括其提供的政治支持是中国政府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也是中国政府相较于西方政府开展各项改革并促进政府机构协调配合的优势所在。
如上所述,大部制只是政府实现部际协调、促进机构整合的主要方法之一,甚至可以说通过在一定范围内消灭部门间权限分工的大部制是解决部门间协调配合问题的一种极端方法。更何况,部门再大也要有边界,除非成立一个“国务部”,部门之间注定会出现协调问题。因此,大部制并不是解决部门间协调问题的“万灵药”,在实行大部制的领域,应当在权衡各种协调配合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使部际协调作为一种机制在整体上发挥作用。尤其是随着“协同政府”、“整体政府”等在西方政府改革理论和实践中的兴起,为政府进行部际协调提供了除大部制之外的其他方法和技术。但相较于西方,我国理论和实践界热炒大部制而忽视“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13]为了弥补这种遗憾,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界应该加强对政府部际协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为构建政府部际协调机制、实现政府机构的整合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注释:
①澳大利亚实行联邦制,州政府不是由中央政府建立的,每一个州都拥有独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因此,州政府构建协调机制的实践经验也可以应用到中央政府对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考量中。
[1]Tom Christensen,Per Legreid.The Challenge of Coordination in Centr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M].Oslo:Tein Rokkan Centre for Social Studies,2007:10.
[2]Briggs L.Tackling Wicked Problems:A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R].Barton ACT: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2007:11.
[3]Peters Guy B.The Search for Coordination and Coherence in Public Policy:Return to the Center?[M].Berlin:Frei University Press,2005.
[4]Thurid Hustedt,Jan Tiessen.Central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in Denmark,Germany and Sweden—An Institutional Policy Perspective[M].Potsdam:Universita tsverlag Press,2006.
[5]Herman Bakvis,Luc Juillet.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Horizontal Issues:Lessons in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in the Canadian Government[M].Columbia:University of British,2004:14.
[6]Morten Balle Hansen,Trui Steen.Top Civil Servant and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in State Administratio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Prais:ECPR Conference,2010.
[7]多丽斯·A·格拉伯著.沟通的力量——公共组织信息管理[M].张熹珂,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38.
[8]B.Guy.Peters.Managing Horizontal Government:The Politics of Coordination[J].Public Administration,1998,76:295.
[9]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11.
[10]Martin Painter.Steering the Modem Slate:Changes in Central Coordination in Three Australian Slate Governments[M].Sydney:University of Sydney Press,1987:9.
[11]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03.
[12]Keast Robyn,Brown Kerry.The Government Service Delivery Project:A Case Study of Push and Pull of Central Government Coordination[J].PublicManagement Review,2002,4(4):23.
[13]周志忍.“大部制”:难以承受之重[J].中国报道,2008(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