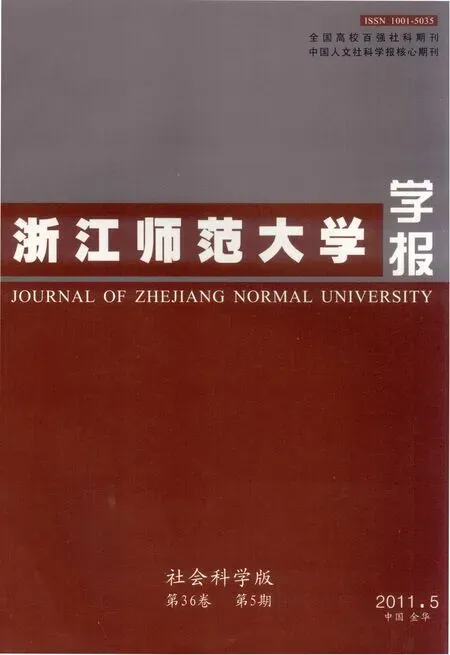空间殖民、景观社会与国家装置*
2011-02-20支运波
支运波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中国处于全球资本机制之中,城市化、机械化、电子技术化彻底地变革了民众的现实生活。作为空间殖民和空间生产的城市化分离且掌控了主体,作为技术结果和物质发展的机械化安置了身体却截除了身体与世界的多重生动关系,而电子技术营造的赛博空间则麻痹了主体,让其在展示、观看、消费的快感中忘却或丧失了斗争性、对世界的感知性以及对有意义生活的追求。因此,思考助推和统治这一景观的背后主谋——国家资本主义装置,可以澄清时代的文化境遇理解。
一、作为生产和政治的空间殖民
科技理性和资本机制是当今的全球语境,所有国家和地区无一不被纳入到这一政治机器的运作之中。科技理性或者说技术理性的进步,必然带来城市化进程,而资本机制又加剧和助推了这一进程。城市化俨然成为各个国家无法逃离的空间殖民,尤其是那些欠发达国家。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勒菲弗断言未来社会是“都市社会”。都市社会以“空间”对社会群体进行重新区隔和分离,人与大地的天然联系被切断,取而代之的是坚硬的冷冰冰的钢筋混凝土构造的“格子”,即使是像广场、剧院、集市等长久以来作为人们交流思想、评议世事的政治性场所,也失去了它作为公共领域的功能。空间就像一个楔子一样硬生生地楔入进社会,打碎了人类的群居性,人被赶进客厅、卧室、地铁、汽车、商场、办公室等各式各样的私人化布局里。人不再是居住在地方(place)的动物,而是寄寓空间(space)里的生物。空间的殖民往往带来身体的延伸,但当身体延伸到居所、商场、地铁、办公室这些都市空间时,我们却开启了电视机、随身听、手机、游戏机、电脑等等机械装置,此时,感觉和精神不知不觉地溜到了另外一种新的空间形式——赛博空间或者媒介空间中。媒介空间及其装置可视为一种本体论机器,它将所触及的任何事物都从空间和时间组构上加以解构和重构,即“开始了对世界和人类的殖民化”。[1]33空间的殖民还体现在它以多维的形式展开,它可以是具体的位置、空隙,可以是一种可能性,可以是康德所谓的某种先天之物,甚至还可以时间来指涉。故此,莱布尼茨主张空间存在与事物是同在的。
倘若坚持人是空间的动物,即以空间人类学的观点看,处于现代空间的身体感受性如何呢?我们认为感官也是有空间性的,“每种感官都在对人们进行空间定位、感受他们与空间的关系,以及鉴赏他们对特定微观和宏观环境的性质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2]然而,都市空间里身体的“具身意识”被屏蔽,其所携带的环境记忆也始终处于漂浮和“撒播”的“延异”状态,知觉与体验成为无关涉的幻觉,那种我们“看似栖身其间的环境并不存在于惯常的物质感觉之中,而是一个计算机生成的世界”,莱茵戈德将此描述为“脱离身体的体验”。人居于此在世界的“亲在”成了媒介空间的“仿像”。
此外,空间也具有政治意识性。“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3]空间的殖民包含着政治权力机制,它将个人再一次抛向无援的境地。如哈维所言:“城市囚禁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并把它们推向广阔的社会边缘。”[4]以占有空间的方式,实现权力和社会再生产,“地区在实质上,就是一台增长机器”,[5]于是,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为经济增长而不遗余力。“都市是一种空间的生产过程”,以消费为导向打造的空间清除了地方的多样性和生动性。勒菲弗在《空间与政治》中认为“空间中的物品生产”开始过渡到对“空间的直接生产”。权力“像一切生产关系一样,是在空间的生产中得以具体体现的”。[6]都市生活——在齐美尔看来——个体之间的活动使其获得了内在的完整性,各种要素相互依赖,并因此在个体之间造成了以空间界限为象征的东西,通过意识到权力和权利不得扩展到另一个活动范围去,来补充自己的活动范围的正面权力和权利规模(空间)。按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的观点,由于现代社会中,国家掌握了媒介话语就掌控了媒介空间,民众言说的媒介语言因失去了对象和“所指”而成为一种“独白式”的自指性游戏话语。民众的不自由不是解放了而是被强化了。
城市阻隔了温情,步入一个生人社会;都市切断了记忆,带入一个没有大地感的冰冷空间,政府借此中断了永久性物权和所有权,进入有期限的产权和使用权社会。身体与环境的“具身”意识被冻结,人类成了空间的寄生物。
二、没有知觉和具身的景观社会
德波声称:“现代社会就是景观的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7]空间殖民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景观社会。鲍德里亚也主张景观社会到处是空间的殖民,在这里“不再以真实和真理为经纬的空间,所有的指涉物都被清除了”。[8]而且,符号与拟象比真实还真实。人生活在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缔造的虚拟景观中,“仿真”(simulation)和“拟像”遮蔽了原始的真实,人在这样一种超现实中,迷失了真实的感性,被切断了与大地的联系,人的主体意识被技术理性所取代,而技术理性却是一种充满暴力的非理性。哈拉维认为赛博(cyborg)是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也是一种测绘我们的社会与身体现实的虚构和一种暗示某些非常有成效的耦合的想象的源泉。毫无疑问,网络和景观已经实际地“改变了当代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特别是我们对于身体以及它与身份、处所的关系的思考方式”。[9]
其实,大众传媒成为景观社会的原动力。在媒介时代,麦克卢汉认为它是“身体的延伸”,并带来器官、感官的“强化和放大”,但对于“这样的延伸,中枢神经系统似乎都要在受到影响的区域施行自我保护的麻醉机制,把它隔绝起来,使它麻醉”,即他所说的“自恋性麻木”(Narcisusnarcosis)。按照穆尔对于赛博空间中身体的体验和感受的看法,我们“仍然依赖于我们的生物学身体”。[1]198鲍德里亚和波斯特则在景观社会中发现了“复杂的色情部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所谓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知觉到的世界”,是“在我们肉身之中”的世界,与大地、环境、世界充满“具身意识”的身体被电子空间中“非身体的感官与心理体验”的“无器官身体”①所取代。因为技术城邦中,“人们都近似于液态般的不稳定,人既是物质又是隐晦难懂的物体。”[10]“无器官身体”是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千高原》中提出的一个美学概念,其字面意是剥去身体全部器官之后所遗留的空躯壳,是纯粹的赤裸裸的表面,可刻录的表面,残酷戏剧的场景。它是“欲望的内在领域,欲望的一致性平台”,流动着“纯强度的、自由的、前无知的、前有机的单一性”。[11]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网络具有根茎性(the rhizome),因为根茎可以联系到任何一点和其他的任何点,景观社会中的身体是无器官的身体,是一台欲望机器,不断生成与消费就是身体的本质。知觉被屏蔽了、麻木了、自恋了,进入世界的通道则是机械性装置。景观社会中身体不再直接与自然世界接触,身体的感知和体验的功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具有“我思”、“意识”的“主体性”身体,都统统转变为幻觉,并在无数次的幻觉后变得麻木,“自我截除不容许自我认识”,[12]只要通过“意向性“观念就可以达到自然世界中身体所做的几乎全部工作。作为身体意向性的语言和意义的结合在景观社会中大行其道。
社会学的观点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身体习惯和身体技术。“无器官身体”是可以刻录的躯壳,是生成性的,主体和意义是分离的身体。电子文化又促成了个体的不稳定身份、促成了个体多重身份形成的连续过程,而“景观话语没有给回应留下任何余地”,进行社会性建构的方式和渠道丧失了,价值次序传递变成同向传递。生活中人们开始完全顺从景观的统治,逐步远离一切可能的切身体验,并由此越来越难以找到个人的喜好,个性的抹杀无可避免。此种生存状态要求的不是某种不断变换的忠实态度,拟像、娱乐、消费、展示以及低俗、侵权、暴露隐私以及网络民粹主义等种种非理性就孕育而生。景观社会犹如一场把“满足等同于生存的鸦片战争”,[13]15人们“不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14]不是交流判断,而是诉说事件。甚至,事件的真实性反而没有拟像、传播与关注重要,不再有什么现实的公共领域可供人们谈论那些与他们自己切肤相关之事。
“哪里有独立的表象,景观就会在哪里重建自己的法则。”[13]19鲍德里亚说:“对政治经济制度来说,身体的理想类型是机器人。机器人是作为劳动力的身体得以‘功能’解放的圆满模式,是绝对的、无性别的理性生产的外推。”[15]景观社会中,身体成为性和政治的中介。为了视觉景观而去塑造身体、身体维护以及展示。通过对身体的诱导和控制,景观实现资本生产。景观的逻辑的背后是资本和机制的殖民逻辑。景观对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控制、景观的无意识形态性质是新的意识形态,它延伸到政治、宗教以及社会生活每个可能设想得到的层面。这也是体制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的例证。“世界就是一幅无处不在的景观,所以我们无从选择,更加无以反抗。在购买景观和对景观生活方式的无意识顺从中,我们直接肯定着现存体制。”[16]
三、国家作为一种装置
按照杜梅泽尔的观点,政治的统治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可怕的帝王或魔法师以暴力或符号而实现,一种是国王—牧师—专家以条约、契约等工具而实现。[17]现代国家则以占有资源和提供服务实现对个体的控制,它是一种控制力,并以“独白式”回绝对话。城市化解除了最后一部分拥有资产者的资产拥有权,再将其安置到一个孤立的封闭空间,然后通过各种税收对其持续搜刮。另外,主体又自动地步入到媒介空间,在手机、游戏机、计算机所提供的娱乐和消费的快感中耗尽所有的革命热情。表面上看,主体是越来越实现了自由,其实他是一步步陷入到政治机器的监视和钳制之中。从此,主体被彻底纳入到国家装置②(the state apparatus)的永恒运转之中。可以说,主体和国家之间是一种“逃逸”和“捕获”的关系。
国家装置的最终目的是将人推向难民,即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bare life)的境地。它是纯粹的自然生命,纯粹的出生事实,即强调身体的一元性是权利的根源和载体,它强调政治和生命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赤裸生命不再限定于一个特定场所或一个明确的范畴。它现在寓居于每一个活的存在的生物身体之中。它是现代社会的“牲人”(homo sacer)。在空间殖民和景观社会中,经过国家装置的机械运作,人成为既“处于较低地位而同时又是最高贵的”的赤裸生命——身体被分离出来,重新成为“两面性的存在物,既负载着对最高权力的屈从,又负载着个体的自由”。[18]235
在阿甘本看来,身体与政治权力是天然相联的,民主与专制诞生的基础都源于身体。在福柯看来,身体的权利甚至一切权利都是对“权力程序的政治反应”,基于尼采的自我寄寓于身体中的观点,南希试图努力“询问意义的身体”,可身体行为是具有体制性环境的,资本主义对身体进行了严格的管制和编码,它已被祭献给国家装置“转向了欲望生产”,[19]“享乐—消费的人、游戏的人、想象的人,制造神话的人”都是“生产的人”的“派生的或异化的附属物”。[20]
国家是大众的全景监狱,也是一台规训身体的装置、监视大众生产的机器。“装置首先就是一种生产主体化的机器,只有这样,它才成其为治理的机器。”[21]阿甘本认为采用何种政治制度取决于哪一种组织形式将最适合于确保对赤裸生命的关注、控制和利用。而一旦他们的基本指涉对象变成赤裸生命,传统的政治区分就失去了他们的明确性和可理解性,从而进入一个模糊地带。他同时认为,决定人的赤裸生命的不仅仅是统治者,而且是散布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医生、科学家、专家以及牧师等,其中,“纯粹的身体”处于现代民主国家对作为新的政治主体的赤裸生命的保护法令的核心地位,即“民主恰恰是作为对这个‘身体’的维护和呈现而诞生的”,装置就是“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的交点”。[21]一如福柯在《性史》中所概括的,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是“一种具有附加的政治生存能力的活的动物”,人类建构主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将人的自然生命不断纳入权力的机制和算计之中的过程。[18]238于是,福柯集中探讨了医院和监狱的全景式窥视和监察。在需要的时候,国家装置“总是处于权力关系中”和“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它可使“违法合法化”。[22]国家的法律也“保留或悬浮于例外状态”。[23]通过分离,大众被抑制、被异化、被排除。结果是,身体不再出现在公共领域,它开始私人化,在城市空间隐藏,转而以景观的、暴露的和戏仿、镜像的方式行走于城际或媒介空间中。权力和政治被建构成纯粹与语言和文本关涉的事物。[24]阶级不见了,随之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大众,他们想法很简单,就是赚钱、生存。不间歇地拼命劳动,除了挣得维持自己生存的衣食所需以外,个体的幸福、自由、权力的欲求都成了国家装置得以运转的永恒动力。
政府通过城市化掠夺土地、建设房屋、提高房价,并限定使用期限、征收房产税实现对人的权利的控制,根据阿甘本的生命与权利观——从福柯那里汲取的思想资源——民主权利最先是和人的纯粹出生和自然身体密切相关的。据此,为我们解蔽了城市化的两种结果:身体的自由和权利的丧失。电子空间或者说媒介空间是一种结果的必然趋向,身体延伸到手机、游戏机、计算机所营造的电子空间以后,身体的意向性战胜了具身性并在窥视与展示、消费与快感的虚拟感受中被榨取掉现实生产中获得的劳动所得。可悲的是,为欲望而不断购买升级的机械,在麻木的兴奋中消费拟像。[25]此刻,人完全是一个“无器官身体”。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国家——作为一个装置,它的最终追求的——将主体变成一个彻底主体,即难民或“赤裸生命”的目的尚未达成。主体都是时代的“牲人”,透过身体、空间和政治在景观中的耦合性,以及身体的姿势学与身体的修辞语合二为一,可以看清国家作为一个装置和国家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装置景观一部分的新动向。
注释:
①德勒兹的无器官身体是一个歧义多生的概念,其目的是强调身体器官的无组织可生存性,是与organs(器官)相对的。但我们这里借用这一概念是强调身体的无意识和麻木状态。
②国家装置,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代表着对各种解辖域化的欲望流捕获和辖域的权力组织,其代表的是条纹空间,它与战争机器代表的平滑空间相对。有关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装置之中的景观的论述可参看陆兴华的《如何在景观社会原创出政治与艺术?——从德波尔-阿甘本的景观批判出发》一文,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7期。
[1]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M].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约翰·厄里.城市生活与感官[M]//苏颦,译.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5.
[3]大卫·哈维.时空之间[C]//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77.
[4]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5]哈维·莫勒奇.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地点的政治经济学[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9.
[6]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09.
[7]德波.景观社会评论[M].梁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
[8]让-鲍德里亚.仿真与拟象[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330.
[9]唐娜·哈拉维.赛博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M]//汪民安.生产:第6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3.
[10]Mark Poster,Davis Savat.Deleuze and New Technology[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396.
[11]麦永雄.论德勒兹哲学视域中的东方美学[J].文艺理论研究,2010(5):79-86.
[1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76.
[13]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1.
[15]让-鲍德里亚.身体,或符号的巨大坟墓[M]//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53.
[16]张一兵.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德波《景观社会》的文本学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1):5-17.
[17]吉尔·德勒兹.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611.
[18]乔治·阿甘本.生命的政治化[M]//汪民安.生产:第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9]吉尔·德勒兹.无器官的身体[M]//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13.
[20]埃德加·莫兰.人本政治导言[M].陈一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3.
[21]乔治·阿甘本.什么是装置[J].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9):64-69.
[22]Stephen Humphreys.Legalizing Lawlessness:On Giorgio Agamben’s State of Exception[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6(3):677-687.
[23]Paul A Passavant.The Contradictory State of Giorgio Agamben[J].Political Theory,2007(2):147-174.
[24]帕沙·查特吉.流行文化批判(节选)[J].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11):28-32.
[25]邵培仁.当“看到”打败“听到”:论景观在传媒时代的特殊地位[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5(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