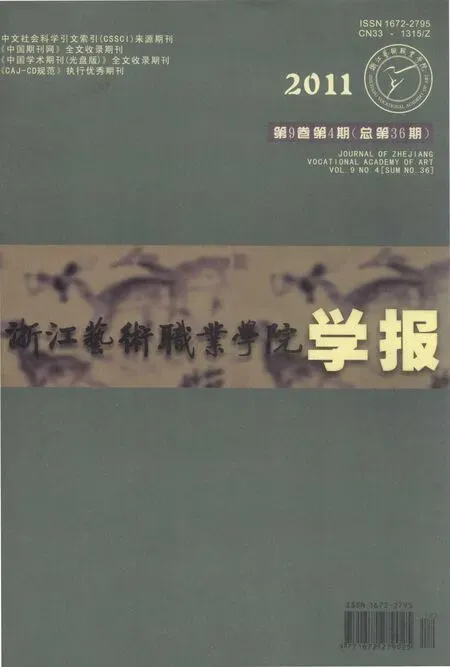疯癫的棋人与忧郁的王子*——试论林兆华和过士行的戏剧双簧
2011-02-19陈文勇
陈文勇
话剧《棋人》创作于1994年,这是过士行的“闲人三部曲”系列之第三部。该剧于1996年由中央实验话剧院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导演林兆华,这也是过士行的第二部被搬上舞台的作品。剧中“棋人”何云清下了五十年棋,几十年一直没离开过这块棋盘。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剧中小“棋人”司炎因在一盘决定命运的对弈中失利而丧命,更让人领略到围棋有着古希腊神话里海妖赛壬般的巨大的诱惑与魔力。人们往往为何云清五十年来“光低头下棋,没抬头看天”的岁月蹉跎而慨叹,却忽视了生命之花短暂绽放就迅速陨灭的围棋天才司炎。如果从司炎角度来解读,《棋人》则别有一番风致。《棋人》①该剧引文均出自过士行:《坏话一条街:过士行剧作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版。与同为林兆华导演的《哈姆莱特》②本文论述的舞台版《哈姆莱特》系1990年林兆华的导演版本。因引用文献不同,本论文出现哈姆莱特和哈姆雷特两种称谓,不作统一处理。不论在人物设置、情节安排还是导演处置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通过比较有助于我们分析和理解两剧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编剧过士行和导演林兆华的戏剧思想。
一
从表面上看,棋人司炎与王子哈姆莱特有太多的相似性:两人都思虑过多;都有些疯狂忧郁;两人生父均已死且与寡母相伴;剧中都有个象征性或名义上的父亲(棋人何云清与新王克劳狄斯);两人生父鬼魂也都曾出场;两人都对各自女友冷淡且加以嘲讽;剧终之时两人亦都抱憾而死。司炎的身上明显有着哈姆莱特的影子。
过士行在《棋人》剧中提示说:“司炎实际上是一个疯子,但是属于那种‘文疯子’,表面看不出来,只是稍微有些神经质。”司炎因何而发病,剧中的大夫聋子是这样解释的,“他是因智力过于旺盛而得病的”,“他的大脑一刻不停地在运转,非常痛苦,要不断地给它加油,才能使这部精密的机器不致损坏”。司炎也认同这种看法,他认为只有经常在大脑里与自己对局才能消耗不断增生的脑细胞。这难道就是司炎疯癫抑郁的病因吗?造成他“智力过于旺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剧中有一个细节,司炎老是爱摆弄那个永动仪,那是司炎的图腾。面对那个“只要给它一个力,它就会不停地动下去”的装置,他想宇宙大概也是这样,他不断地追问:“究竟是谁最初给了它一个力呢?”“地球是哪一天开始围绕太阳旋转?胎儿的心脏是怎么突然起跳的?”其实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他,也同样困扰着整个人类。过士行在《戏剧的精神及其他》一文中说:“无目的宇宙和有目的的人之间的游戏,正是戏剧永恒的主题。”[1]萨特强调人是绝对自由的,所以人必须担负责任。“人,由于命定是自由的,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2]但萨特同时认为,“在为自己选择受奴役或获自由的同时,人必将选择一个受奴役或有自由的天地,悲剧在于人必定尽心竭力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3]。当这种主动的选择与社会赋予他的身份、地位等自身的局限相冲突时,悲剧性就应运而生了。剧作家谈到司炎死因时说道:“作为青年人最苦恼的就是在精神上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所以司炎面临的是一个选择的话题,在一种压力和阻挠下,他什么都不能选择,最后只能选择生或是死,‘To be or not to be’,最后他选择了死,而且还是先斩后奏。”[4]其实司炎并非没有选择,只不过他的选择远远高于他自身的行为能力,他死于自己精心构造的牢笼之中。
过士行剧中的棋人、鱼人、鸟人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了自己选择的“受奴役”的困境,对此田本相的评论非常中肯:“在过士行的剧作中,反映着一种深刻的精神困惑。这种困惑是90年代知识分子在走向边缘的历史转折中所特有的……失去精神依托的痛苦,终生理想的幻灭,最依恋的成为最厌倦的,最醉心的却成为自己的牢笼……在这样一个没有回答的展示中,却深刻地揭示了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我看,这就是过士行剧作的历史真实的价值。”[5]
“To be or not to be”,这同样是困扰着哈姆莱特的重要命题。哈姆莱特的疯狂抑郁与延宕复仇历来就是人们着力解决的难题。德国学者史雷格尔 (Schlegel)解释说:“由于奇异的生活境遇,他高尚的天性中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不停思虑的理智上,他行动的能力却完全破坏了。”“这个心灵由于无止境地思虑着的理智而陷于覆灭,这种理智使他自己比所有接近他的人遭到更大的痛苦。”[6]弗洛伊德则把哈姆莱特复仇时的犹豫不决,乃至最后的自我毁灭归结为他的恋母情结,因为叔父杀兄娶嫂的行为正是自己童年被压抑的愿望。与弗洛伊德的性欲说不同,拉康用象征的性器官菲勒斯 (phallus)理论来解释哈姆莱特延宕的原因,哈姆雷特的母亲一开始是处于菲勒斯位置上的他者,现在菲勒斯被叔父僭取,“这个菲勒斯并不是真正的菲勒斯,它是一个篡位者,真正的菲勒斯并不在场”,人不可能去杀死一个“鬼魂”,特别是一个在菲勒斯位置上的鬼魂,哈姆雷特迟迟不能动手,不是胆怯,“因为他知道,他所必须除去的东西并不在那里”[7]。
俗语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对于造成哈姆莱特悲剧的原因的探讨历来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这也可归结为“无目的宇宙和有目的的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哈姆莱特在选择“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他同样选择了“受奴役”的义务,他的意志、情感与性格使他无力承担时代赋予的“重整乾坤”的重责,与司炎主动选择死亡不同,哈姆莱特死于他者为其精心构造的牢笼之内。
二
甚为巧合的是《棋人》的导演林兆华在1990年执导过解构版的《哈姆莱特》(以下称作《哈姆莱特1990》),该剧以简陋的服饰与舞台布景、无来由的人物角色互换和“人人都是哈姆莱特”的导演阐述震惊了中国当今剧坛。
“在《哈姆雷特》的演出中戏剧结构已经被解构,演出是以一种直接的感受方式来进行的,舞台结构第一次作为一个强烈的表现手段出现在舞台上,从布景到道具都以一种真实形态出现的。”[8]演出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小排练厅进行的。舞台后景整面墙挂满了肮脏的、折皱的黑灰色的幕布,左右两侧台口处,堆满了可以转动的轮子、废录音机、发电机和零乱的电线等物品;在舞台上空的吊杆上,悬吊着五台时转时停、残破不堪的电风扇;国王的御座,也是一张废旧的理发椅。
更为惊奇的是导演让三位演员共同扮演哈姆莱特、克劳狄斯和波洛涅斯,他们在演出进行之中,经常毫无过渡地互换角色。当克劳狄斯和王后劝说愁云笼罩、忧心忡忡的哈姆莱特不要离开他们之后,此时,扮演垂头丧气的哈姆莱特的演员,立即挺胸抬头,变成踌躇满志的国王,携起王后的手臂,昂然退场;而刚刚扮演国王克劳狄斯的演员,立即将头一低,脸色骤然阴沉下来,变成闷闷不乐的哈姆莱特。哈姆莱特的那段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是这三个扮演哈姆莱特的演员共同合作完成的。最后哈姆莱特持剑刺向克劳狄斯,转瞬之间,两人角色互换,倒下的竟是哈姆莱特,而扮演哈姆莱特的演员此刻已变成了克劳狄斯。
林兆华这样谈及《哈姆莱特1990》的导演意图:“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人人是哈姆莱特’,我没强调‘篡位复仇’,哪个宫廷哪个朝代都这样,国内国外都如此,哈姆莱特主要的痛苦是他有思想,而我觉得活着的有思想的人都可能面临哈姆莱特那样的命运。”[9]他在《导演的话》中写道:“哈姆莱特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在大街上我们也许会每天交错走过,那些折磨他的思想每天也在折磨我们,他面临的选择也是我们每天所要面临的。生存或者死亡是个哲学命题,也是生活中每一件具体的大事和小事。或者不是,你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我们今天面对哈姆莱特,不是面对为了正义复仇的王子,也不是面对人文主义的英雄,我们面对的是我们自己。”[10]其实“人人都是哈姆莱特”的观点并不新鲜,19 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家赫士列特(Hazlitt)早就说过:“我们就是哈姆莱特。这个戏具有一种先知的真理,这是高出于历史的真理的。”“谁若因自己或别人的不幸变得多有思虑和忧郁……谁的行动能力被思想所销蚀,谁若以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自己算不了什么;谁因心灵的仇恨痛苦而不计后果,谁若把看戏当作推开、挪开人生种种罪恶的最好办法,把戏当作表现罪恶来嘲弄罪恶的一种办法——谁就是真正的哈姆莱特。”[11]林兆华所做的是用三位演员共同扮演哈姆莱特、克劳狄斯和波洛涅斯,他让“人人都是哈姆莱特”的观点更加直观化和具体化。
1996年初,由林兆华导演的《棋人》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这出戏较之《哈姆莱特1990》更为嘈杂不堪,演出成了后现代的与行为艺术嫁接的产物。演员用铁丝网吊了顶,然后又用铁丝网把舞台围起来,接着他们装上了铁树、铁桌子、铁椅子、铁棋盘,剧终时铁丝网和铁棋盘都燃烧起来,麻雀乱窜,舞台上那些好不容易搭起来的装置也一起坍塌了。看到林兆华颠覆性的编排,过士行无计可施,他认为舞台上演的不是棋人,而是工人。他说笼子是《鸟人》剧本中的舞台提示,演出时因为舞台的限制没有用上,林兆华就把它用在了《棋人》上了。《棋人》是过士行的第三部戏,有着三一律的结构,有着第四堵墙。这是他对传统的一次回归,但“林兆华打破了我的回归梦,把她排成了一个后现代的与行为艺术嫁接的戏,我也无计可施”[12]。林兆华对此不以为然,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林兆华明确声称自己不做剧本的奴隶,他认为在舞台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说还是导演。因为最终呈现在舞台上演出的不只是戏剧文学,而是舞台艺术。他说:“我也设想过温馨的场面,很好的,在一个四合院,温馨地围一个小火炉,来一小灯儿,有个四方桌,有个小床儿,都可以演。但我不满足这样,这呈现出来就是一般的场景和人物关系,要表现那样一个主题冲击力不大。”[13]较之真实地再现棋人们的生活场景,他更关心庸常生命在铁硬的环境中的碰撞冲突,关注剧中生死轮回的直观传达,关注“曲终人散空愁暮”的悲剧氛围。
三
过士行的朋友止庵在看了林兆华执导的《鸟人》和《棋人》后有些伤心,他感觉演出与原剧本相比有些走样,“比如前者本是消解意义的,结尾却被赋予了一种意义;后者本是有意义的,却被大肆消解”[14]。过士行也“太不满意”林兆华对《棋人》一剧的解构性导演处理,但在20 世纪90年代继林兆华导演了过士行的“闲人三部曲”以后,进入新世纪,两人又合作演出了“尊严三部曲”。这确实有些匪夷所思,还是过士行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是林兆华吸引他走上了话剧创作道路的。“《闲人三部曲》在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林兆华就答应要排我的三部戏。第二部戏出来的时候,我已调到中央实验话剧院,按理说应该和自己剧院的导演合作,但是剧院接受了我的建议,由林兆华执导。第三部戏还是林兆华执导。因为我和他有约在先,这不是一般的许诺,这是人生的期许,是生命的承诺。一个人一生能承诺几次?所以尽管《棋人》导得不合我意,第三部戏还是要他导。”[12]是“生命的承诺”驱使他将剧本悉数交予曾赋予他戏剧生命的“教父”林兆华来执导(《坏话一条街》由孟京辉导演),这个“生命的承诺”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使得编剧过士行的形象始终或隐或现地掩映在导演林兆华的阴影之中,过士行的自我仿佛俨然存在于镜像之中的幻象。
“镜像”是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提出的重要概念,他把婴儿成长期的第6 至第18 个月称为“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从镜子阶段开始,人始终是在追寻某种性状某个形象而将它们视为是自己的自我。这种寻找的动力是人的欲望,从欲望出发去将心目中的形象据为‘自我’,这不得不导致幻象,导致异化”。“这个欲望就是想要使自己的欲望被承认的欲望。在这个欲望中完全证实了人的欲望是在他人的欲望中异化的。”拉康认为,“人在看自己时也是以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另一个的他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15]这也就是“人互为他者”的观点。
不论是《棋人》还是《哈姆莱特1990》,剧中都有“互为他者”的人物构成。《棋人》里老棋人何云清和小棋人司炎就是这样一组人物,过士行在《我的戏剧观》一文中说道:“事物的最高结构形式是同一的,是一个整体”,“譬如《棋人》,老国手和小神童互为对方的影子。他们都是棋的化身。”[16]何云清曾拒绝司慧让她儿子司炎放弃下棋的请求,何云清说:“他是围棋的儿子,几个世纪,千百万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懂得棋道的天才!他也是我生命的延续。”何云清把司炎当成“现在的寄托”,是司炎使他那枯寂的心灵重新燃起生命的火花。司炎可谓何云清青年时期的翻版,他对棋以外的事物真正能做到“古井无波”,他对女友媛媛的冷淡,对媛媛离去时的不屑一顾与当年何云清对待司慧的表现如出一辙。剧中的司慧和媛媛也是这样的一组人物。过士行特地提示说,在何云清幻觉中出现的青年时代的司慧可由司炎的未婚妻媛媛来串演。难怪何云清第一次见到媛媛时不禁慨叹道:“真像啊!你真像司慧。”林兆华在《哈姆莱特1990》中更是让三位演员共同扮演哈姆莱特、克劳狄斯和波洛涅斯,并在演出中,经常毫无过渡地互换角色。剧终之时哈姆莱特持剑刺向克劳狄斯,倒下的竟是哈姆莱特。究竟是哈姆莱特杀死了克劳狄斯,还是克劳狄斯杀死了哈姆莱特,不用深究,反正人人都是哈姆莱特,这就使得哈姆莱特的正义的复仇变成了人类的毫无意义的自残。
过士行的“闲人三部曲”中的《鱼人》写于1989年,《鸟人》和《棋人》也诞生于20 世纪90年代之初,进入新世纪后,他的“尊严三部曲”中的《厕所》、《活着还是死去》分别作于2002年和2003年,但他的《回家》却勉为其难,一直拖到2010年。可以说过士行有着“三部曲”情结,他说:“我是受超市启发,现在都是捆扎着卖东西,卖一个是卖,卖三个也是卖。有一位编剧跟我说:你就一块吆喝,说我这儿有仨呢。但当时没有另外那两个戏,我就先在说明书上写上了。”[17]这种明显主题先行的“捆扎着卖东西”的“三部曲”情结也是源于镜像中他者的“召唤”,他的灵魂深处涌动的无意识不是“他本己的本能冲动,而是种种大他者无形强制下的奴性物”。大写的他是人们无形中期望他成为的人,是其他人用目光交织铸成并且也被他自己认同了的大他者。[18]他的“尊严三部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大他者无形强制下的奴性物”,这是否可算是他在《鸟人》剧中所命名的“强迫性精神病症状”呢?
有论者指出:“20 世纪90年代的戏剧已经从剧作家本位转换成导演中心。如果说对于20 世纪80年代高行健和林兆华的合作,人们的关注点还在高行健的话(当时有关戏剧的观念更多的是高行健在言说),那么,90年代过士行和林兆华的合作,人们的关注点则更多地转向林兆华了(这时更多的是林兆华在言说)。”[19]过士行和林兆华的合作犹如中国曲艺中的双簧演出。台上明明是过士行在表演,但实际上是林兆华在幕后言说。双簧的笑料就在于双方故意错位的合作,过士行和林兆华的合作就是在这样磕磕碰碰中一路前行的。
20 世纪戏剧进入导演时代,“再现—写实”导演体系主张“导演死在演员身上”,强调导演是“演员的老师”。而“表现—写意”导演体系则坚持导演应独立创作,强调导演是“演出的作者”,也就是要求“导演活在舞台上”。林兆华就是个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都很强的导演,他坚称:“我自己也绝不愿意重复我自己。”他认为戏剧有两大主题:“第一主题是文学的。比如我排莎士比亚的剧可以不改他的台词,只作一点删节,可以按照他原来的台词去演。但我强烈地把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把我独立的一些思索、独立的状态,放在这个戏当中。这是导演的第二主题。”他说自己无论排《理查三世》还是《哈姆莱特》,“我不替莎士比亚说话,我替我林兆华说话”[20]。同样道理,林兆华排过士行的戏也是替自己说话,导演林兆华始终活跃在舞台上。
过士行的第四部话剧《坏话一条街》由孟京辉执导,对于这部戏的演出,导演和编剧都不太满意,这个戏的演出使得过士行产生了将来自己亲自导戏的念头。果然在10年之后的2008年10月,作为编剧的过士行导演了法国剧作家让·克劳德·卡里埃尔的戏剧《备忘录》,该剧讲述的是一位与134 名女性有过性关系的单身汉,与一位擅自闯进其公寓的神秘女人之间发生的故事。过士行在回答自己为什么选择这部戏并亲任导演时说道:“首先我喜欢这个剧本,其次是对别的导演不放心,怕他们乱加东西,我是站在编剧的立场去导戏的,我要维护这个剧本。我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把我最初读剧本的感受完整地体现出来,把导演隐藏在幕后。”[21]令人回味的是过士行请大导演林兆华和大设计师易立明担任灯光和舞美设计。这场演出是否可算是个“弑父”的隐喻,是过士行对林兆华“把导演亮相台前”的做法一次示威性的反拨?过士行能否召回自我、实现镜像突围,我们将拭目以待。
[1]过士行.戏剧的精神及其他[J].戏剧文学,2007 (1):11.
[2]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688.
[3]萨特.萨特文集(6)[M].沈志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75—576.
[4]张驰.过士行访谈录[J].戏剧文学,1999 (5):22.
[5]田本相.过士行剧作断想[M]∥过士行.坏话一条街:过士行剧作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322—323.
[6]史雷格尔.论哈姆莱特[G]∥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杨业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312.
[7]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325-327.
[8]易立明.关于这样一种实验戏剧——从《哈姆雷特》到《三姊妹·等待戈多》[G]∥蒋原伦.今日先锋(7).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8.
[9]吴文光.访问林兆华[G]∥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334.
[10]林兆华.导演的话[G]∥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9.
[11]赫士列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G]∥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柳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11.
[12]过士行.我的写作道路[M]∥过士行.坏话一条街:过士行剧作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359—360.
[13]张驰.林兆华访谈录[J].戏剧文学,2003 (8):10.
[14]止庵.我的朋友过士行[M]∥过士行.坏话一条街:过士行剧作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348.
[15]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7,361,408.
[16]过士行.我的戏剧观[J].文艺研究,2001 (3):85—86.
[17]张先.过士行谈创作[J].戏剧,2000 (1):51.
[18]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0,6.
[19]田本相.中国话剧艺术通史(第2 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304.
[20]林兆华.戏剧的生命力[J].文艺研究,2001 (3):80—82.
[21]德永健.过士行:中国戏剧“凶猛”的旁观者[J].中国新闻周刊,2008 (3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