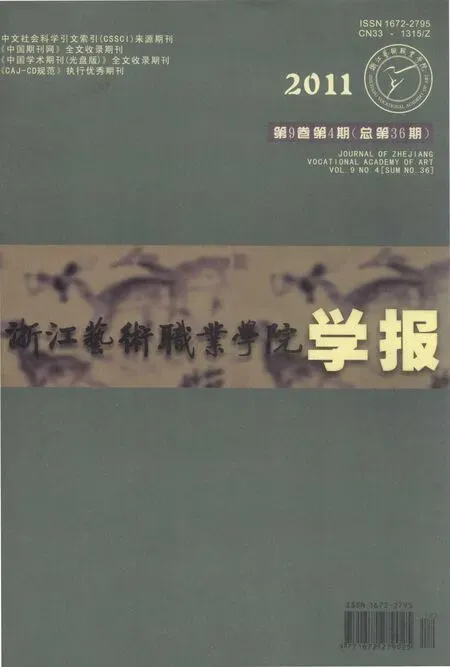歌舞以凌 羌声娱人
2011-11-28孔又专
孔又专
“5·12”汶川大地震,将一个没有文字,却在历史记忆中成功传承独特的原始习俗与神奇的宗教信仰的坚强民族—— “古羌民族”呈现在世人面前。《尚书》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屈原《九歌》感叹:“羌声色兮娱人。观者瞻兮忘归。”僻居岷江峡谷的古羌人民以古朴迷人的歌舞感恩高山神灵、祭祀先祖圣贤,在自然圣洁的韵律中传承多彩的古羌民族宗教文化。
一、遗存悠久:羌族舞蹈与羌族民间音乐相伴相生
羌族民间音乐历史悠久,风貌古朴,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创造谱写迷人的旋律。主要有羌族古歌、情歌、赞歌、酒歌、祭奠歌、山歌、舞歌、盘歌、决术歌、婚礼歌、丧葬歌等歌谣,在音乐结构上多数以两乐句为一个乐段,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抒发情感的需要而作叠加、反复处理。因此,羌族的民歌曲式主要以二乐句和以二乐句为基础的扩充乐段为主,也有以四乐句为基础的扩充乐曲。羌族“多声部”唱法,以二声部为主,有四声部、多声部、男女混合唱法,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研究表明,作为中国音乐体系中的一部分,羌族民间音乐以五声音阶、徽调式为基础,虽间或加入清角或变宫形成六声音阶,但一直少有七声音阶出现。徵调式外,也有宫调式、羽调式、商调式、角调式等多元调式。羌族民歌旋律起伏自然、曲调简单朴实,具有古朴悠远、粗犷明快的音乐特色。
“喜热木”,即羌语“酒歌”。羌民族生活离不开咂酒,有酒必有歌,有歌必有舞。“萨朗”按羌族北部方言,有唱起来、跳起来的意思,是羌族各种唱腔、唱词和舞蹈动作完全不同的歌舞形式的总称。萨朗有动听的腔调、丰富的唱词、优美的动作,是一种边唱边跳、串铃相伴的集体舞蹈,也是一种独唱、领唱、合唱、轮唱、对唱、多声部唱等多种形式相融合的民族民间歌唱艺术。除唱歌、串铃伴舞外,也可随时加入锣、鼓、响器、唢呐、口弦和羌笛等乐器伴奏助兴。羌族萨朗的唱词有历史文化传承和即兴即景创作两种,大都为口头创作,取材广泛,是羌族人民敬畏自然神灵、祭祀先祖圣贤、抒发情感的有效载体。
锅庄舞曲是羌族人在各种喜庆日子里或是迎送英雄时举行的群众性歌舞活动。随着欢快的音乐,身着盛装的人们在“释比”或能歌善舞者的带领下,男女排成两条长龙,有时是手牵手成弧形或圆圈,踏脚,甩手 (胯),转身,扭腰,拐腿,绕肩,踏歌酣舞。叙事歌即“热米”,婚礼歌即“日瓦热木”,颂歌即“卡普”,苦歌即“热鲁”等。每逢节日集会、婚丧嫁娶、修房造屋的日子,羌人都会身穿民族服装,饮着咂酒,借用歌曲追忆祖先伟业,颂扬羌民族英雄史迹,抒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情歌即“苕西”。在少数民族音乐中,情歌热辣奔放而又婉转幽怨。在节日庆典活动时,羌族男女在户外相互约定的地点自由对歌,相互倾诉衷肠,表明爱慕心迹。“苕西”的歌词丰富、准确,极富表现力,用比喻、夸张、拟人、拟物等手法,生动形象、细致入微,内容多数是表现爱情和婚姻。常是结亲时,女方对亲人、伙伴留恋的一种感情表白。羌族情歌通常采用三拍子节奏,一般有3/4、3/8、6/8等节奏。盘歌是情歌中形式广泛的一种体裁,盘歌即对唱,一般分男女对唱、女声对唱、男声对唱。[1]
山歌即“纳那”,是羌族人在山野田间割麦、薅草、赶羊、放牛、砍柴、背背子等生产劳作时对唱的,演唱形式有独唱、齐唱、对唱、轮唱等。如“戈西莫”等,遗存至今的山歌仍保持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原始民间歌舞形态特征。
释比文化的经年浸润、“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使得祭祀内容在岷江河谷遗存至今的羌族民间音乐中占有很大比重。丧歌即“勒衣布热木”,是伴随着丧葬礼仪唱诵的歌。释比作为人神中介充当领舞者,他头戴象征天神的金丝猴皮帽,手执神杖、响铃、法刀,脚踏“禹步”,羊皮鼓舞队追随其后,整个队伍先曲线后圆圈,随其节奏且歌且舞且鼓。舞步古朴、沉稳刚健,鼓声激烈,音乐旋律短促干脆,带来神秘的宗教氛围,寄托无尽的哀思。
二、古朴神秘:羌族舞蹈具有民族特色和宗教神性
“会说话就会唱歌,能走路就能跳舞”,“天上有多少颗星,锅庄就有多少调;山上有多少棵树,锅庄就有多少词;牦牛身上有多少毛,锅庄就有多少舞姿”。
古老的圈舞文化在千百年中流传,奠定了羌舞文化的基础。同时由于羌族对藏缅语族影响重大,原始时代的古羌遗风,一直较为完好地保留于藏缅语族之中。羌族联袂踏歌的圈舞形式也成为藏缅语族的舞蹈共性形式。羌族称跳舞为“处惹”或“日莫署得”。跳舞时,按古羌风俗,由老人带头,如果在婚礼上,则由母舅家的母舅或舅公带头,带头老人手拿旱烟杆做指挥,队形排成半圆,人多时排成两个圆圈。羌族这种汇集各种唱腔、唱词和舞蹈动作以舞载歌的舞蹈形式叫做“萨朗”(羌语音译)或“锅庄”(外来词汇)。杂谷脑河流域常见的“萨朗”有汶川的青菜花、白菜花,雁门的优西衣、木西、周周来,龙溪的夜从北、黄桑金桑马,卡子的店布惹,佳山的心给索、扯朵哪朵、其沙妹儿、玉米砖砖,薛城的简言错、共格索,蒲溪的筛筛哟、米全、三得里学,沙坝的龙比许、送达白马、马茶马茶、西来瓦夏,赤不苏的山山里、嘎妹等。
遗存至现在的萨朗一般分为五大类:喜庆萨朗、忧事萨朗、礼仪萨朗、祭祀萨朗、集会萨朗。[2]跳萨朗是羌人代代相传的古老习俗,尤以祭祀萨朗最具神秘性和民族性。主要用在还愿等宗教活动中,如麻龙舞 (图1)、羊皮鼓舞 (图2)等。①配图是为方便舞蹈创造并传承羌民族宗教文化。文中图4至图12及相关资料转引自《羌族铠甲舞研究》,图1、图2、图3、图15、图16以及相关资料转引自《绿野探踪——岷山羌藏族舞蹈采风录》,其余图片为课题组成员自拍。麻龙舞用以驱邪避鬼,是羌族“释比”借以沟通神灵的巫术性舞蹈。“羊皮鼓舞”即“莫恩纳萨”。现存的“莫恩纳萨”,通常都使用羊皮鼓等十种打击乐器敲击出不同音响的节奏组合作为伴奏,有时也有唢呐和海螺声穿插其中。恩格斯指出:“(印第安)各部落各有其定期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特别是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祀的主要组成部分。”[3]羌族舞蹈与羌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战争和生产劳动、民俗以及文学艺术相结合,具有原始宗教神秘性和古老的民族特色。[4]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三、歌舞以凌:卡斯达温舞从神性祭祀到世俗化的演变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铠甲舞”又名“卡斯达温舞”(藏语),“卡斯达”为“铠甲”之意,“温”是“穿”的意思。“卡斯达温”是古代黑水人出征前,勇士们祈祷胜利,亲人们为他们祈求平安的一种民间祭祀性歌舞活动。它是岷江峡谷地区氐羌系民族传统的舞蹈,也是羌族民众世代相传的一种古老的祭祀性舞蹈,主要在祭祀先祖时跳,后由于战争等原因,逐渐演变为征战前的祭祀活动。《尚书》曾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羌族铠甲舞的内容和形式都再现了“歌舞以凌”的场景,如图3所示。“男青年披甲戴盔,肩系铜铃,手执刀、矛、弓、剑等古老兵器……以歌开始,起舞止歌。”[5]该舞气势雄壮,规模庞大。“铠甲舞”的基本步法如下:屈伸前进步 (图4)—屈伸横移步—辗转步 (图5)—单踏行进步—碎踏行进步 (图6)、(图7)—执刀纵跳步 (图8)—拉弓纵跳步 (图9)、(图10)—对天笑(图11)—云步 (图12)。我们知道,羌族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数千年来,羌民族对于族源、民族历史文化及自然、社会的记忆和情感表达都依靠人神中介释比以及释比主持的各种祭祀仪式来完成。这些以释比文化为核心,依照释比图经,弥漫神圣宗教氛围的祭奠仪式,表达了古羌民族对天、地及自然神灵的整体认识,同时,“藏羌锅庄”逐渐仪式化、规范化、世俗化,以其古老神秘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艺术形式滋润着羌区人民的精神生活,成为岷江河谷地区羌民族不可或缺的民族传统体育舞蹈项目。
四、羌声娱人:岷江羌区“南水羌风”舞蹈韵律的遗存和传承
羌族舞蹈风格浓郁,具有“南水羌风”韵律。[6]屈原《九歌》记载:“羌声色兮娱人。观者瞻兮忘归。”南水羌族舞蹈起源于原始时代婚庆礼仪式舞蹈,其舞蹈的核心韵律是扭腰送胯,这个核心韵律影响到整个羌族舞蹈的传承发展。羌族舞蹈胯部的核心动作是远古人类生产力低下时期借助舞蹈表达对原始美感、生命力张扬和生殖力崇拜的一种古老舞蹈韵律遗存,对比战国时女巫 (图15)、魏晋时菩萨造型以及敦煌壁画中扭腰菩萨画像 (图16),则可清楚地看出古羌舞蹈亦折射出对原始性欲、繁衍后代、生产昌盛的无声讴歌和虔诚祈祀,体现了脱胎于游牧民族的古羌人尚曲线、丰满、肥壮的审美意识,包含着羌民族极其悠久和丰富的宗教文化意蕴。
羌族舞蹈朴素健康的风格特点有三:一是它用脚跟跪蹬的动作,即每一次出步都有一个附动作,以蹬地的力量过渡到另一只脚,使它或侧踢或绕转或后绕跪地;二是习惯从右脚开始顺圈进行,向右上步时,腿向上提升,放松踝部,略略带甩地,但脚落地时,则铿锵利落自然;三是左脚踏于左侧时,出现左顶胯的舞姿。
胯部动作是南水羌区羌族舞蹈的核心,即羌族舞步和动态可大致概括为:转胯—顶胯—顶脚跟动胯—伸膝送胯—踏步垮肩—悬空甩脚—蹁脚动胯—波浪撬步。 “踏步转臀”,在转动双膝时,由膝影响上腿而带动胯部扭转;“顶脚跟甩臂”,右脚向右侧踏出,松膝,胯部有力地右顶。然后脚向左侧横步踏出,同时右脚以脚跟擦地顶向左脚,顶后跟时,臀部向右甩,连续转圈,形成摆臀的动态。“踏步蹁脚甩臀”,右脚原地踏,同时将力点过渡到左脚,左脚用后跟擦地在低位上蹁开,连续舞动,形成特殊的摆扭动作;“波浪撬步”,在一组动作中,右脚轻踮时,左脚的脚踝部向前撬起,身随脚步向后仰;“单脚悬空甩脚”,右脚原地轻轻踮跳,同时左脚离地,在低位上悬空前甩。右脚原地轻轻踮跳时,左脚由前甩向后。
“甩脚送胯”和“拐脚”是羌族舞蹈中最常见的动作。在羌族舞蹈中,左脚向左侧踏下后再拉回来,此时右脚顶膝向左,就出现拐脚;除了上面归纳的基本特征外,羌族舞蹈在不同的地区也发展了不同的动作,如常出现在维城擀面舞和盔甲舞中的“踏步垮肩”动作,“踏步垮肩”指双膝微曲踏步时,脚尖向两侧,松膝,肩部放松,随着手部的摹拟动作自然地下垮,从而出现“踏步垮肩”动作。而“蹲跪叉腰”是赤不苏区锅庄舞中的动作。“逗脚”是喜事萨朗中庆祝禾苗破土的舞步。“绕脚”,左脚横步前踏,同时按掌,左脚悬空在低位上绕向前,这是龙溪、蒲溪锅庄中常见的动作。维城羌舞中有单脚悬空前后甩脚,维城羌舞“嘎妹”中还有单脚跪地另一只脚甩后点地动作。

图15
五、小 结
岷江峡谷、高山平台中,羌族人民没有向险要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生活屈服,相反,他们感恩雪山神灵,与自然和谐相处,淳朴乐观。在联袂踏歌的羌族歌舞中张扬古老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对美感的不懈追求。羌族歌舞是传承羌民族宗教文化的有效载体,是羌民族情感的朴素表达,也是抚慰羌族人民心灵创伤的良药。因此,在前辈学者艰辛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继续对羌族古朴、原始的歌舞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和遗存研究是地震灾区重建及灾后建设的必要内容。
[1]肖珣.羌族的民间音乐 [J].成都师专学报,1996(2):98—102.
[2]陈兴龙.羌族萨朗的价值及保护和利用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29.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卷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0.
[4]孔又专.论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社会适应性 [J].社会主义研究,2011(4):115—118.
[5]《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编委会,殷海山,李耀宗,郭洁,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 [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457.
[6]蒋亚雄.绿野探踪——岷山羌藏族舞蹈采风录[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6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