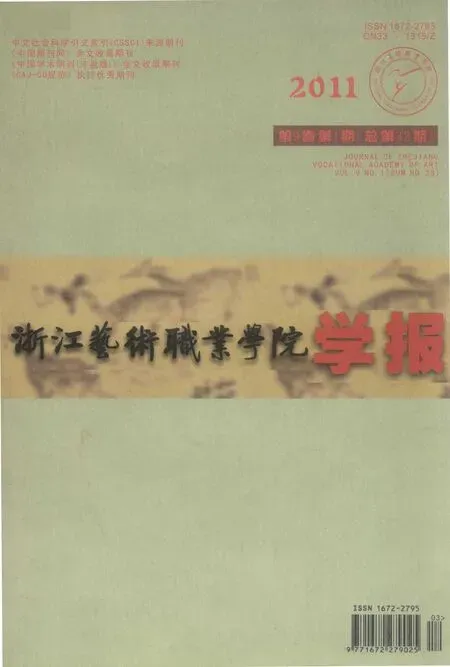权力/知识拘囿的挣扎*——评贝丝·亨利成名作 《心之罪》
2011-02-19邱佳岭
邱佳岭
权力/知识拘囿的挣扎*
——评贝丝·亨利成名作 《心之罪》
邱佳岭
《心之罪》是美国当代女剧作家贝丝·亨利的成名剧作。剧中人物明显的古怪行为经常被论者关注和批评。剧中人物的古怪行为以及剧作的美国南方背景使得此剧通常被划入美国南方戏剧范畴,并经常与其他南部剧作家的作品做比较研究,诸如田纳西·威廉斯的作品。也有论者从身份认同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剧中人为的古怪行为做多种诠释。本文借助福柯提出的知识与权力关系阐释,尝试对剧中人物的“怪异”做新的阐释。通过对剧情和剧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分析,本文提出剧中人物的古怪行为反映了剧中人在权力建构的文化拘囿下的挣扎。而这个主题是在剧情和观众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心之罪;知识/权力;福柯
《心之罪》是美国当代女剧作家贝丝·亨利的成名剧作。亨利的剧作因其剧中人明显的古怪行为通常被归入美国南部的哥特式戏剧范畴。她的戏剧人物的行为也常被认为“在荒诞、古怪和疯狂的边缘”[1]457,而亨利利用“变形的喜剧”[2]346来表现人的荒诞。也有论者认为剧中“亨利将疯狂、机智和情感以极端的方式融合起来”[3]82。对于亨利作品的古怪中人物,从女性主义视角来评论的论者认为:“表面上,在麦格诺斯 (Magrath)姐妹们所犯的罪之下,戏剧是在批评父权制的种种罪行。这包括父亲对家庭的抛弃,家庭暴力,种族歧视,性的双重道德体系,以祖父为象征的父权社会对麦格诺斯姐妹令人窒息的控制等等”[4]194。从上述对《心之罪》的评论可以看出,论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戏剧中所展示的人物的“怪异”行为并做出多重阐释。笔者试图借助福柯提出的知识与权力关系,尝试对剧中人物的“怪异”做新的阐述。通过对剧情和剧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分析,本文提出剧中人物的“怪异”行为反映了剧中人在权力建构的文化拘囿下的挣扎。
一
福柯在关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阐述中指出,权力以离散的形式建构出各种知识体系。“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在权力/知识的框架内”[5]142。所以,权力构成的知识经常以常识的形式出现,并主宰着人们的行为。因此,在权力与知识的框架内,个体的反抗在文化层面上考虑往往表现为违常。在“作者是谁”中,福柯从作者的界定到其文本的作用,阐释了话语如何成为“自我指涉”,成为“符号之间的相互作用”[6]1261的过程。在《真理和权力》一文中,福柯进而指出一切陈述的科学性的政治性特质。所以,“‘真理’应该被理解为是一整套制造、规则、分配、传播和陈述运作的有秩序的过程”;“‘真理’与制造和保持它的权力系统之间有循环的关系”。事实上,真理是“真理的‘政体’”[6]1279。真理的产生是一套完备的政治、经济和制度的体系。
《心之罪》讲述的正是在权力∕知识架构的文化拘囿中挣扎,被视作“疯子”的麦格诺斯三姐妹的故事。正如上文所述,权力的目的是要个体自觉地把权力架构的知识 (包括各种规则、概念)内在化为真理而无条件信仰、服从。作为普通个体,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生存的三姐妹不可避免地会为自己突破权力/知识的框架不安而充满了自责。自责,或者说自觉有罪的感觉从剧名“心之罪”就体现出来。“心之罪”作为剧名本身就有双重暗示。《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中“罪”(crime)这个词条第一个解释就是“为法律所惩罚的罪”(offenceforwhichhereisseverepunishmentbylaw)。这里,英文offence被译为“罪”,也就是“冒犯”的意思。很明显,“罪”这个行为是对法律等规则的冒犯,应当受到法律惩罚。由此,“心之罪”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则是“人心中的犯罪”。这样,“心之罪”这个剧名就有了双重内含:第一,剧中的“罪”与“权力”的关联,因为“罪”是要受到法律处罚的;第二,“心之罪”表明了作为剧中主人公的三姐妹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和自我精神放逐的潜在诉求。所以,从剧名开始,《心之罪》就涉及了权力/知识的问题。在剧情发展中,权力/知识所构建出的控制体系对个体所施加的控制由暗喻性人物体现出来。
福柯在对权力是如何运作的阐释中认为,如果权力只是压迫,如果权力只是用来说‘不’,人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权力。“使权力长久,使其被接受的因素仅仅是它不仅仅是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否定,而且创造出什么,它产生快乐,形成知识,生产话语。权力需要被视作渗透整个社会,不只是作为压迫的否定因素的建设性的网。”[6]1273这里,福柯所说的“建设性”是指权力非压制性特征。“它产生出环境、关系和主体”[5]143。对于个体和权力的关系,福柯认为“权力能够进入个体,进入他的行为、态度和日常行为模式”,使得“身体成为被控制和改变的高度复杂的系统”[6]1276。换句话说,权力的目的是使个体将各种规则内在化为真理,成为自我约束。所以,权力的运作不仅表现为令人不快的、强制性的压迫,更以真理、知识的形式出现,让人愉快而自觉地接受,它渗透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权力的两个运作方式和权力所作用的客体具象在《心之罪》的人物中,按矛盾冲突来划分,剧中人物可以分成两个阵营:一方是麦格诺斯三姐妹、律师,另一方是老祖父、琪格 (Chick)、贝琪的丈夫赞克雷 (Zackery),而后者又分为出场的和未出场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阵营视作权力运作和权力施加的客体双方,那么,剧中三姐妹则是权力施加的客体,可见的人物琪格则成为权力压制性的暗喻,而不可见的老祖父、贝琪的丈夫则成为权力建设性的暗喻。
作为权力压制性的暗喻的琪格从出场就表现出其控制欲望和控制力量。她指责三姐妹的生活方式,认为她们使家族蒙羞。在琪格面前,可怜的大姐莱妮不仅被指使得团团转,而且紧张得手足无措,一副自觉有罪的模样。琪格以审判者的姿态指责莱妮、莱妮的母亲和妹妹们,直截了当地否定和规训着三姐妹的行为。然而,尽管琪格来势汹汹,她依旧被忍无可忍的大姐——尽管她是姐妹中最温顺的一个——赶了出去。可见,表现为“压迫”的权力运作不仅令人不愉快,更容易遭到来自客体的抵抗。与琪格令人不愉快的“压迫”相反,未出场的祖父对三姐妹的控制不仅持久而且强大,因为三姐妹自觉地接受祖父的控制。通过姐妹三人的对话,观众认识了剧中的祖父。把姐妹三人关于祖父的对话串联起来,观众便得到祖父清晰的形象:慈爱而威严。在养育三姐妹的过程中,祖父获得姐妹们的敬畏和信任。在姐妹们看来,祖父是智慧、知识的化身,是她们精神的导师、生活的依靠。所以,姐妹三人心甘情愿地实践着祖父给她们规划的远大前程:小妹嫁进当地名门,二姐要去百老汇发展,可怜的大姐不得不关闭爱的大门,成为已经是老鳏夫的祖父的陪护,让祖父满意成为三姐妹生活的坐标。但是,事实是三姐妹的生活不能让祖父满意,这种感觉时时折磨着三姐妹,自觉有罪的感觉使她们焦躁不安。从知识/权力的角度来考虑,姐妹们的负罪感源自权力的作用。作为权力建设性暗喻的祖父无时无刻不把种种规训内化于三姐妹身上。而作为被权力施加方的三姐妹也自觉地接受种种规训。这表现在她们想尽办法让祖父高兴,使祖父满意。贝琪忍受被关进监狱或疯人院的恐惧,不敢告诉祖父她用枪伤了丈夫;二姐不得不撒谎,掩饰自己困苦的处境;可怜的大姐独自吞食着孤独寂寞的苦果。很显然,三姐妹的生活似乎都或多或少地脱离了祖父设定的轨迹。对于三姐妹来讲,这无疑是对规训的反抗,或者说是冒犯。就如打破禁忌本身便意味着对权威 (权力)的认可一样,三姐妹对规训的冒犯反而强化了作为权力象征的祖父的权威性。而祖父的权威性又决定了三姐妹必然背负的负罪感。
不能满足祖父的负罪感与为母亲的死找到合理的解释相辅相成,诠释着权力的运作模式。福柯认为,权力运作的一个重要策略便是榜样的树立。一个好榜样会“遵守规训,因为好榜样将规训内在化为真理而信仰,而一个坏榜样则是打破规训”[5]144,不接受规训的真理特质。权力的运作很重视榜样作用。因为一方面,将权力架构的知识内化为真理而绝对服从的个体被确立为好榜样本身就是权力的运作过程,而另一方面,对规则的突破本身加强了权力的运作和知识的权威性。《心之罪》中,母亲就是个典型的坏榜样。母亲自杀的阴影始终困扰、纠结着三姐妹,挥之不去。在三姐妹的堂姐妹琪格眼里,这个家庭的女性从她们的母亲开始,除了让她抬不起头来,几乎没有用途。单纯地看待母亲的自杀事件,特别是在现代人眼中,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行。自杀事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令人不愉快地出现。但是,三姐妹母亲的自杀却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她在自杀前先杀死了自己的宠物猫。杀死无辜的小动物在文明社会始终受社会舆论的谴责。谴责的同时,人们更容易联想到心理问题,甚至与变态、违常联系起来,而剧中未出场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小妹贝琪枪击亲夫事件使得姐妹三人相聚了。很有意思的是,三姐妹的谈话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母亲带着宠物猫自杀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又是三个人都想回避,但又不自觉地提到的话题。如前所述,对于文化权力构架的社会,母亲是彻头彻尾的坏榜样。而置身于其中的三姐妹也无法摆脱社会价值体系和意义判断取向的作用。与琪格明确地表示其否定性判断不同,三姐妹自感母亲有问题,但是她们试图找到母亲行为的合理逻辑。也就是说,三姐妹在接受母亲有罪,母亲违反了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的前提下,试图为母亲的错误找到合理的借口,希望以此减轻母亲的罪过,进而降低自己因为母亲的行为而承受的精神压力。姐妹们对母亲的行为做着各种各样的推测。麦琪反复地提到父亲让人不悦的“白牙齿”,似乎在暗示着母亲不愉快的家庭生活——家庭暴力完全有可能导致受害者的极端行为;贝琪也表示在做出自杀还是枪击丈夫的决定的关头,她有些理解母亲为何自杀了。两姐妹的话都在暗示母亲生前不快乐的家庭生活。或者说,母亲的行为是有理由的,因为有理由,也就值得原谅了。
三姐妹为母亲所犯下的罪过找到合理缘由的努力还体现在三姐妹的自杀情结中。《心之罪》中,三姐妹似乎都有强烈的自杀心结。小妹贝琪在得知自己愤怒的婆家人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时,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选择了自杀——把自己的头伸进烤炉,要烧死自己;二妹麦基在海啸来临时选择了待在危险的寓所中。剧中,大姐莱妮似乎没有明确的自杀情节,然而她不仅天生有身体缺陷——没有子宫,并因此而掉发,精神委靡,而且对自己的未来几乎没有任何规划和梦想。大姐与其说是活着,还不如说是个活死人。或者说,莱妮始终在慢性自杀。姐妹们的自杀情结也成为贝丝·亨利的女主角性情怪异的佐证。无缘无故地总是纠结于结束自己的生命,的确不能说是正常的行为,然而,三姐妹的自杀情结理由很充分,即她们试图体验母亲自杀的过程,理解母亲的行为,洗刷母亲在社会中的“恶名”。亲身体验自杀成为姐妹们试图找到母亲携宠物离开人世理由的最极端的做法。
这样,《心之罪》中姐妹们自觉有罪的矛盾心理所体现的恰是权力/知识所架构的精神拘囿。作为被拘囿的客体,接受权力的规约成为姐妹们的自觉。
二
有论者对《心之罪》中主人公的“怪异”从女性主义视角做过阐述,认为三姐妹的境遇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同样,如果将《心之罪》置于权力与知识的视域下来考察,读者就会看到三姐妹,特别是贝琪和麦基被视作“疯狂”、“不正常”的根源在于对理性权威的冒犯。与三姐妹的古怪相反,剧中祖父、贝琪的丈夫赞克雷以及琪格构成一个理性群体。除了出场的琪格,祖父和赞克雷只出现在人物的谈话中。不过,即便如此,观众也有足够的信息界定这两个人物。正如祖父严格地按照理性逻辑安排三个孙女的前程,赞克雷同样具备“理性素质”。从贝琪的只言片语中,读者可以勾勒出这个人物面貌。他出身地方名门,受到正统教育,事业成功。他几乎可以满足理性社会对男性公民的种种要求。作为丈夫,尽管贝琪聘请的律师想方设法地想把赞克雷与家庭暴力连在一起,读者却在情节中无从找到任何可以证明其家庭暴力的有效信息。不仅如此,读者似乎还隐隐感到所谓家庭暴力仅仅是贝琪的律师一厢情愿的假想。因为这位律师从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表明他与赞克雷有宿仇,他要借这个官司将赞克雷彻底打垮。律师公报私仇的企图本身就已经使他的言语变得不太可信。与律师试图证明存在家庭暴力相平行的是贝琪对自己家庭生活的描述。按贝琪的描述,她不能理解丈夫的幽默,而且常常被赞克雷和他的姐妹们嘲笑为不正常。而在贝琪枪击赞克雷事件发生后,赞克雷的反应不是送她进监狱,而是把她关进疯人院。赞克雷的反应和贝琪对家庭生活的描述使读者有理由认为贝琪被夫家视作“违常”而遭冷遇,甚至精神迫害的事实是可以成立的。而枪击赞克雷这个极端的事件使赞克雷有了充分的理由认为贝琪是应该被关起来的疯子。
与祖父和赞克雷构成的理性权威群体相对应的是麦格诺斯三姐妹构成的“非理性”,或者说“怪异”群体。从小妹枪击赞克雷后的异常冷静,到温顺的大姐一反常态地为琐事歇斯底里地大闹,再到二妹莫名其妙地失声、自闭,直至跑出去将自己的所有值钱的东西疯狂地塞入募捐箱,麦格诺斯三姐妹这一系列的行为按照理性逻辑来看,被判断为“违常”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将三姐妹的行为放置在具体戏剧情节中,这个判断背后的权力作用就清晰可见了——三姐妹“违常”之举的根源在于对理性权威的挑战,至少是对抗。正如上文对小妹贝琪的家庭生活的描述,因为贝琪的行为不符合赞克雷的要求而被视作“怪异”、“疯子”。或者说,贝琪是“疯子”,是因为赞克雷的言行被认为正常。如果贝琪被关进疯人院是她即将面对的未来,那么,同样违背了祖父意志的麦琪已经被当做疯子关进安定病房。与两个妹妹相比较,大姐莱妮最驯服。然而,即便如此,她也被琪格视作“违常”。从第一场始,琪格似乎无理由地,不停地指责大姐莱妮“没脑子”、“不正常”。在琪格看来,贝琪和麦基是使整个家族蒙羞的、不可救药的疯子。大姐对琪格的指责也总是自觉有罪地默默忍受。
尽管在作为权力象征的祖父死后,三姐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解脱和自由——她们放肆地大笑,大口地吃生日蛋糕,开心地庆贺莱妮的生日,然而,或许连她们自己也不清楚在祖父架构的权力框架内获得解脱和自由的不可能性。因为失去了祖父的控制,她们就如断了线的风筝没了根基,失去了方向。三姐妹前程未卜——大姐的幸福取决于心怡自己的男人的到来,三妹的未来掌握在赞克雷的手里,而二姐更是不清楚此番离开家后何去何从。未卜的前程似乎在呼唤着另一个新的权力体系的出现。或者说,作为个体的三姐妹不可避免地又会陷入另一个权力框架中。
三
贝丝·亨利在《初次社交》(TheDebutanteBall)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一部展示秘密、压制和渴望的戏,我要让我的剧中人看上去像动物一样撕扯、喷洒、刮掉他们自然的东西,再以谎言做装饰。”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贝丝有意公然冒犯观众的感觉。通常意义上说,百老汇戏剧观众的认知和判断力很难超出现今伦理范畴。所以,观众立刻感到麦格诺斯三姐妹的言行与普通人的差异,很自然地感到她们言行的违常、古怪。观众如此的反应是剧作家贝丝·亨利“苦心经营”的成果。
从《心之罪》的剧情结构可以看出,亨利有目的地使三姐妹的行为看上去怪异、违常。比如,开场时,亨利并没有交代大姐莱妮的生日。在舞台上,观众看到的只是莱妮鬼鬼祟祟地点蜡烛、精神紧张地许愿。而琪格上场时,莱妮慌慌张张地藏起小点心和蜡烛。这一连串的没有任何铺垫的动作使得观众对莱妮的行为不仅费解而且很不舒服,认为莱妮“怪异”的念头立刻就出现了。相反,如果亨利将情节线索稍加变动,对莱妮的行动做一些必要的解释,莱妮的行为在观众眼中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亨利对于小妹贝琪做了相似的处理。小妹枪击赞克雷以及随后的一系列行为被描述出来。枪击赞克雷后,贝琪丝毫不马虎地为自己和受伤的丈夫准备两杯果汁,还平静地询问丈夫是否口渴,是否想喝杯水。接着,她便给急救中心打电话。这一系列的行动显然超出了因果二元关系,无法用理性逻辑来推理。即便是贝琪聘请的律师——那个与赞克雷有宿仇,试图公报私仇的年轻人——也毫不犹豫地想以“一时的疯狂”来为贝琪枪击丈夫的行为辩护。而贝琪丝毫不透露其枪击的原因却只是说“我不喜欢他 (赞克雷)的样子”更让观众感到贝琪的违常。然而,贝丝对贝琪所有看似疯狂的举动在随后出现的情节中都做了解释性说明。先展示现象,再解释内在原因的叙述逻辑使观众对于自己对剧中人的判断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历程。亨利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将姐妹们的痛苦经历统统推到幕后。观众只能在剧中人的只言片语中感到她们曾经经历的某些极端不愉快,甚至恐怖的事件。比如,母亲杀死自己的宠物猫后自杀、贝琪令人窒息的婚姻、麦基在海啸中拒绝逃生、沉默寡言的大姐心中蕴藏的秘密……不难想象,如果贝丝不厌其烦地、细致地把三姐妹的经历展现给观众,对于剧中三姐妹的言行,观众的反应极有可能是认同,而不是感到违常。对过去的遮蔽,或者说,对剧中人物言行逻辑不充分的处理,使《心之罪》缺乏传统戏剧中使观众移情于剧中人物的剧情。观众无法在剧场幻觉中,对剧中人物的经历感同身受。进而,观众接纳、理解剧中人物的言行,而不是视之为不正常。如果我们忽略剧中可以看见的琪格,不可以看见的祖父、三姐妹的父亲以及贝琪的丈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仅仅把他们当成剧中人物,那么,观众的这个反应就与他们达成同谋。这样,虚构时空中人们的境况就扩展到了现实时空,而二者的区别则在于剧中三姐妹在下意识地挣扎、反抗,而后者则无意识地接受权力构成的文化拘囿。不可否认,剧中祖父对小妹贝琪嫁进当地名门所表现出的无比快乐欣慰、给麦基规划未来并且为她的虚构的成功所表现出的兴奋、对有生理缺陷的长孙女莱妮婚姻的担忧,或者说,善意的干涉,世俗地看祖父所有这些反应,尽管这些反应有些世故,但是依旧合情合理,甚至有远见卓识,充满了理性的智慧。而琪格这个出场虽然不多,但永远吵吵闹闹、充满怨气的女人,尽管看上去略显没有修养,甚至可以说刻薄,但是她的言语听起来不无道理。如果说,祖父体现了权力/知识架构的价值体系,那么琪格则是对打破这个体系的人直接的否定。而她否定的核心是麦格诺斯家三姐妹行为违常。她对三姐妹的断言正好契合了观众最初的反应,即这是古怪的三姐妹。这样,亨利以其巧妙的剧情构思让观众 (读者)经历了一次从精神拘囿到解放的过程,从剧情和观众两个层面上展示了权力/知识的关系以及权力构建中对个体的精神拘囿。
[1] Roudane,MatthewC.AmericanDramaSince1960:ACriticalHistory[M] .NewYork:Twayne,1997.
[2] Andreach,RobertJ.BethHenley’ssistersofthewintermadrigal. [J]TheMississippiQuarterly.2007:346.
[3] Simon,John.BadQuirks,GoodQuirks[N] .NewYork,1987:82-84.
[4] Burke,Sally.AmericanFeministPlaywrights:ACriticalHistory[M] .NewYork:Twayne,1996.
[5] Klages,Mary.LiteraryTheory:aGuideforthePerplexed [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9.[6] Adams,Hazard&LeroySearleEd.CriticalTheorySincePlato[G] .Peking:PekingU.P.,2007.
Struggle within the Control of Power and Knowledge—An Analysis on Crimes of the Heart by Beth Henley
QIUJia-ling
Crimes of the Heart earns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man playwright Beth Henley an honorableplace. The grotesque of the three sisters in the play draws the attentions of the critics all the time.Because of the grotesque and the Southern background,the play is often defined to be a Southern play,compared with other southern playwrights’works. Some critics tried to illustrate the grotesque from thepoints of identity and feminism. The paper tries to give 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grotesque withFoucault’s idea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By an analysis of the plot and therelationship among protagonists in the play,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grotesque of the three sisters reflectsthe struggle in the repression of culture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power. The theme is unfolded intwo layers,i. e. the story and the audience.
Crimes of the Heart; power and knowledge; Foucault
1672-2795(2011)01-0017-05
I106.3
A
2010-12-01
邱佳岭 (1966— )女,浙江金华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当代戏剧研究。(天津 300387)
* 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课题“当代美国戏剧生态环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52WN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