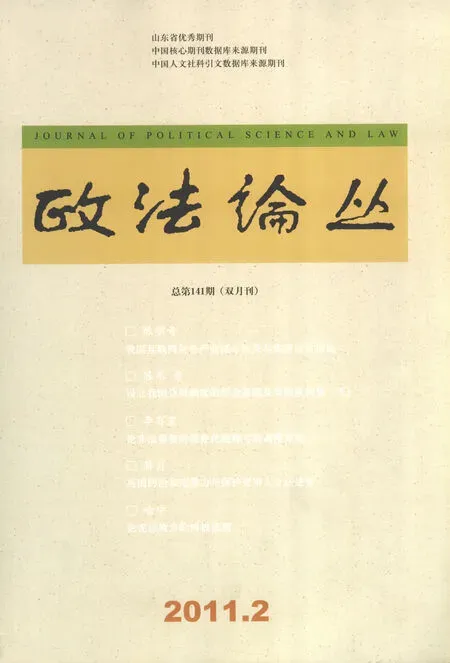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与司法推理*
——以意外死亡保险为例
2011-02-19周学峰
周学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191)
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与司法推理*
——以意外死亡保险为例
周学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191)
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其目的在于界定保险人的赔付责任范围,其背景是保险合同已对保险人的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都做出了规定。事实上,在保险案件中,法院在认定因果关系时,往往已融入了对保险合同条款的价值判断。在意外死亡保险中,有关因果关系认定的司法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当代社会,法院在认定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时,应遵循保护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的原则。
保险法 因果关系 司法推理 意外死亡保险
一、对问题的说明
无论法学界还是哲学界,因果关系问题都是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同时,它也是一直困扰司法实务界的难题。在保险法领域,有关因果关系的规则,被一些学者冠以“近因原则”的名义,并将其看作是保险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地位之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①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一原则性问题,却同时存在着表面上看起来相互冲突的多种答案。如何对这些答案进行解释,能否找到可将这些答案统一起来的理论,是当前保险法研究中的难题。
意外死亡保险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在实践中,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因素往往不止一项,可能存在多项,疾病与意外伤害因素往往并存或相互引发。为了回避问题的复杂性,避免产生争执和控制风险,许多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对其承保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定,例如,有的保险公司在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规定其承保范围为“被保险人于本合同有效期内,因遭遇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所导致的意外事故,并以此意外事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其身体伤害、残疾或身故。”②在这种情况下,受益人欲获得赔付不仅要证明被保险人死亡,还要证明其死亡是由于意外事故所导致的,并且,还需要排除被保险人死亡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③如何看待保险合同中有关“直接且单独原因”条款的效力,如何在此类合同条款的背景下认定被保险人死亡的法律上的原因,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问题。
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无论其在理论上有多大的分歧或争议,作为一个经常出现诉争的法律问题,最终要由司法机构来裁决,因此,探究法院在认定因果关系时的司法推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笔者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判例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从实践出发,以常识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将疾病与意外伤害的关系分为下三类:由意外伤害引发疾病并最终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由疾病引发意外伤害并最终导致被保险人死亡;意外伤害与疾病相互独立且共同促成被保险人死亡。笔者将分别针对上述三种情形下的因果关系认定和司法推理进行研究。
二、“意外伤害引发疾病”类型中的因果关系认定
被保险人由于意外事故而引发伤害,继而引发疾病,并最终由疾病导致被保险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从保险法的角度,是将意外事故还是疾病看作是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常成为保险诉讼的争执点。
在一起英国法院审理的判例中,被保险人因跌倒受伤并使肩膀脱臼,被人抬到床上休息,但由于其身体虚弱且肩膀无法撑重,被褥常常滑落,从而因受凉患上了肺炎,最终致其死亡。被保险人生前购买的保单中载明:当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而导致受伤并以此为原因而死亡时,保险人承担赔付责任。在该案中,被保险人跌倒属于意外事故,但被保险人所患肺炎则属于疾病,并且,该疾病是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最直接的因素,而疾病并不属于保险人的承保范围,尽管如此,法院仍然判决保险人负有赔付责任。法院判决的理由是,被保险人死亡的近因是意外伤害而非疾病。在该法院看来,意外伤害无须直接导致被保险人死亡,只要它启动了因果链条并最终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即可将其看作是被保险人死亡的近因。④
保险公司可否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保险人只对意外事故直接导致的被保险人伤亡后果负责,而将疾病等介入因素参与其中的损失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这恰是英国保险公司在上述判例发布后所做的事情。许多保险公司对其保险合同条款进行了修订,明确规定:当死亡的直接原因或近因为疾病或其他介入原因时,即使该疾病或其他介入原因,会由于意外事故的发生而加重,或是因意外事故的发生致被保险人虚弱或无力所导致的,保险人均不负赔付责任。但是,令保险公司失望的是,此后的判例表明,法院拒绝按照该条款的字面含义来执行。正如一位法官所言:“我们在解释保险单时不能仅从这一个案出发,我们必须记得,这份文件涉及的是保险公司与那些愿意投保的人们对保单中常见事项的争议;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我们采纳了保险公司所提出的解释方法,那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正如我所看到的,如果我们采纳了他们的观点,那么,结果将是除非被保险人在意外事故现场当场死亡,否则很难使保险人负赔付责任。如果我们采用保险单字面解释方法的话,任何人都将难期待能确定地依据保险单获得赔付。我想,对于保险单条款的限制,保险公司也应该欢迎,否则,在我看来,能够强制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的案件数量将大幅减少,这样一来,几乎没有人愿意投保。”⑤
三、“疾病引发意外伤害”类型中的因果关系认定
与前述情形恰好相反,实践中常见的另一种类型是,被保险人因其疾病发作而引发意外伤害,并最终致其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亦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如果按照上述意外伤害引发疾病案件类型中的推理方法,被保险人死亡的近因应该是触动因果关系链条发挥作用的那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被保险人死亡是由于意外伤害引发疾病所致时,应以意外伤害作为死亡的近因,那么,当被保险人死亡是由于疾病引发意外伤害所致时,则应以疾病作为死亡的近因。如果保险合同明确将疾病排除在保险人承保范围外,那就意味着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无权要求意外死亡保险金。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在“疾病引发意外伤害”的案件中采取了与“意外伤害引发疾病”案件不同的推理方式。例如,在英国的“劳伦斯诉事故保险公司”案中,被保险人在车站站台等车时突发昏厥,跌倒在车轨上,被一辆正驶来的火车撞死。被保险人投保了意外伤害险,但保险合同明确排除了疾病导致死亡或疾病作为死亡共同原因的情形。法院认定被保险人死亡的近因是火车事故而不是突发病症,因为,“如果某人在车站站台上发病,他并不是一定要落到火车下;如果此人确实掉到了火车下,伤害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并很可能死亡。”⑥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在认定因果关系时应注重那些与结果关系最为密切的因素,而无须理会所谓的因果关系链条。这种推理方式的后果是,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精心设计的关于保险范围的限制性和排除性规定将变得徒劳。
也有一些国家的法院在推理时采取了另类解释的策略。例如,有的法院在对保险单进行解释时认为,被保险人的眩晕或昏厥等状况,属于临时症状,不属于除外责任事项中的疾病,因此,如果被保险人由眩晕跌倒而受伤或死亡,仍属于意外伤害或死亡,保险人仍负有赔付责任。这种推理的后果是,法院可以将被保险人的眩晕或昏厥等症状从因果链条中摘除,从而绕开保险合同中有关对保险范围和赔付条件进行限制的规定,便于保险受益人获得赔付。例如,在一起美国案例中,被保险人由于眩晕跌入水中溺死,法院认为:从法律上来讲,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近因是溺水,而无论其落水的原因是由于疾病或滑倒;被保险人患有疾病只能是条件,而溺水才是唯一的近因。⑦
四、“意外伤害与疾病并存”类型中的因果关系认定
在有些案件中,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意外伤害与疾病并不存在相互依赖或连锁反应的关系,而是相互独立,单独发生,但共同促成结果的发生。在此类案件中,被保险人往往在遭受意外伤害之前就已患有某种疾病,意外伤害的发生加剧了被保险人的原有疾病,疾病与意外伤害一同促成被保险人的死亡。在许多案件中,被保险人死亡的医学上的原因并非是显而易见的,而是经过尸检后才可发现,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能事先并不知道其患有某种疾病或身体存在某种特质。由于许多意外伤害保险合同都将被保险人获得赔付的条件确定为意外事故是致其伤亡的“唯一原因”,因此,如果法院严格地按保险合同的字面意思来进行解释,那么,受益人很难在意外伤害与疾病并存类型的案件中获得赔付。为了使受益人获得赔付,法院往往在对因果认定方面费尽心机。
由于推理方式的不同,对于同一案件,不同的法院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判决,这一点在Shryock案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该案中,被保险人Shryock分别买了两份意外伤害保单,他在旅行时跌倒了并撞到硬物上,第二天晚上,人们发现他死在旅馆里,经验尸发现,除有跌倒的擦伤痕迹外,被保险人还患有心脏病。专业医师认为:或许被保险人的死亡是由跌倒引起的,但是,如果他先前不存在心脏病,跌倒决不会致其死亡。该案件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审理。英国法院认为:无论是认定被保险人的心脏病由于意外跌倒而加剧,或因心脏病发作而导致其跌倒,都不能使意外事故成为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而只能将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部分归于意外事故,部分归于疾病,因此,基于保险合同关于保险赔付条件的限制,受益人无权获得赔付。⑧而受理该案的美国法院则认为:跌倒是被保险人死亡的近因,即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因此,受益人有权获得赔付。⑨
上述两种司法推理和判决结果的差异,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英国主审法官认定多种原因的存在而美国主审法官只认定一种原因的存在。实际上,导致两种推理方式差异的真实原因在于,对待保险合同的态度。英国主审法官从契约自由出发,强调要尊重保险合同当事人对条款的约定;而美国主审法官则是从对附合合同的司法规制出发,强调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的保护。
在保险合同明确地将受益人获得赔付的条件限定为意外伤害是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时,任何一种欲使受益人顺理成章地获得赔付的司法推理都不能无视这一条款规定,都必须合理地跨越这一障碍。对于如何突破这一障碍,国内外的法院选取了不同的方式。
有些美国法院提出了所谓“实质性促成原因”规则,依该规则,只有那些实质性促成了被保险人伤亡的因素才可看作是保险法上的原因,因此,除非疾病实质性地促成了被保险人伤亡的发生,否则,即使被保险人先前患有某种疾病并且该疾病因意外事故的发生而恶化并导致被保险人伤亡,仍不能将疾病看作是被保险人伤亡的保险法上的原因。例如,普通人跌倒通常不会导致其死亡,但被保险人因患有某种疾病或身体虚弱,若跌倒致其疾病加重或难以康复并最终导致被保险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存在疾病因素,但由于其并不属于“实质性促成原因”,因而,受益人仍有权获得保险赔付。⑩
有些法院则仍坚持从近因理论出发,在特定案件中将意外事故认定为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例如,有的法院认为:人与人之间在健康、活力和对疾病的抵抗力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某些伤害对一个人意味着死亡,而对另一人而言则无足轻重,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不具有致死性的特定的伤害,并不能排除其在特定情形下具有致死性;当在导致死亡的各种因素中,伤害是积极的和有效的原因时,应将其看作是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被保险人特殊体质的存在仅仅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并不能因此而改变意外伤害是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的认定。
有的法院则进一步对被保险人所患疾病的状态进行了区分,如果被保险人的疾病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由于意外事故的发生激活了该疾病,并最终导致被保险人死亡,那么,应将意外事故看作是唯一的近因。例如,在“大陆事故公司诉劳埃德案”中,被保险人跌倒在路上,随后感到头痛,继而陷入昏迷,直至死亡。经验尸发现,被保险人患有脑瘤,被保险人死于跌倒撞击和脑瘤破裂出血。法院认为,如果不是跌倒,被保险人的脑瘤将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至少将维持现状,因此,应将跌倒看作是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的近因,而被保险人的疾病仅为死亡结果提供了条件。
中国的法院也曾处理过意外伤害与疾病并存类型的案件。例如,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被保险人不慎跌倒而死亡,经鉴定,其死亡原因系因不慎跌到致头部受伤,在其患有高血压的基础上造成脑血管破裂出血使颅内压升高、枕骨大疝形成压迫生命中枢所致,但是,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意外伤害保险金。审理该案的法院认为:不慎跌到是导致被保险人病理改变的重要因素,与其死亡有因果关系,故被保险人的死亡是意外死亡,保险公司负有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由此可见,中国的法院采取的是寻求唯一原因的方法,并且以意外伤害是否导致被保险人“病理改变”为标准,来认定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是意外伤害还是疾病。
五、对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难题的破解
就一般意义而言,对于一起事件的发生,通常会有多个促成因素,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条件”,但我们常讲的“原因”仅包括其中的一个或数个。在一个由若干条件组成的集合体中,我们依据什么规则来对其进行区分对待,只将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条件指定为原因,而抛弃剩余条件呢?这是因果关系认定的核心,也是所有因果关系理论都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不同的领域,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不同的。
正如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所言:“即使在法学家看来,随着观察视角的变化,同一种原因有可能既被看作是近因,又被看作是远因。一份保险合同规定,保险人不对由于锅炉爆炸而引发的损失负责。一起爆炸引发了火灾。如果不是因为保险合同有除外责任的规定,那么,火灾将被看作是近因而爆炸将被看作是远因。但是,基于合同的效力,爆炸成了近因。海上发起一起船舶碰撞,继而引发火灾。在有关保险合同的诉讼中,火灾将被看作是近因,而碰撞则是远因,但在起诉碰撞船舶的诉讼中,碰撞则成了近因。”
在保险合同已对保险人的承保事项和除外责任事项做出明确约定的情形下,应如何看待此类约定的效力,是法院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无外乎有两种答案,或尊重或否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院并不愿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借助因果关系的概念来重塑问题,从而使因果关系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例如,在意外死亡保险中,当意外伤害引发了疾病并最终导致被保险人死亡时,法院倾向于将启动因果链条的意外伤害认定为死亡的原因;而当疾病发作导致意外伤害并最终导致被保险人死亡时,若采用相同的推理方式,依照保险合同条款的规定受益人将无法获得赔付,于是,法院为了达到保护受益人利益的目的而改变了司法推理方式,将意外伤害认定为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而将疾病仅看作是条件;在意外伤害与疾病共同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案件中,法院如果依照普通人的理解,将意外伤害与疾病都看作是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那么,依照保险合同“唯一原因”条款约定,保险人的赔付责任将得以免除,于是,法院只承认意外伤害是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法律上的原因,从而表面上符合保险合同关于“唯一原因”的要求,并使得受益人有权获得赔付。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意外死亡保险合同将保险人的承保范围限定在以意外伤害为唯一原因且直接导致的死亡,并同时明确排除疾病、特殊体质等原因,这样一类条款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应得到法院的承认。正如有的法官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采纳了他们的观点,那么,结果将是除非被保险人在意外事故现场当场死亡,否则很难使保险人负赔付责任。”然而,许多法院并不是直接从法律效力的角度来否定该条款,而是借助因果关系的规则将这一问题绕开。当法院这样做时,虽然目的达到了,但是,有关因果关系认定的规则却陷入了混乱,从而出现了司法推理在形式上的不一致。
因此,要破解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谜题,就必须首先揭开被因果关系这个表面概念所掩饰的问题真相。只要当我们认清楚了问题的本质,我们才能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说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并不是简单的事实认定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那么,其所涉及到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保险合同有关承保事项和除外责任事项的约定的效力。
真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是建立在当事人具有平等的缔约地位,合同内容是由当事人双方自由协商而非单方确定的基础之上的。在历史上确实曾出现过与这一理论基本相符的现象,例如,在保险出现早期,特别是在海上保险时代,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商人,并且,经常出现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身份的互换,保险合同往往是由被保险人拟定后交由保险人签名承保。在这种条件下,契约自由的思想得到了法院认同,法院声称自己只能尊重并保证当事人的意思得以实现,而不能替代当事人订立合同或更改合同条款。
然而,自进入20世纪以来,保险业务从海上保险扩展至陆地保险,保险人从商人间的松散组织演变成专业的保险股份公司,在被保险人群体中,缺乏保险知识的普通消费者越来越多。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开始成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并且,在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经验和经济势力的不对称。保险合同已成为由保险人单方制定的格式合同,投保人只有“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选择。对于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往往并不知情或理解,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同意”。所谓的契约自由已仅具形式意义,建立在契约自由基础之上的保险赔付规则的合理性日益受到挑战。当保险公司为了限制自己的赔付责任而在保险合同中规定诸如“直接且单独原因”等条款时,虽然少数法院直接否定了此类条款的效力,然而,多数法院则是在形式上肯定了此类条款的效力,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成为一道难题,于是,又有一些法院开始在因果关系认定方面不断提出新规则。因此,有关因果关系认定的规则,变得日益复杂和难以理解。
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法院为什么不愿意直接否定保险合同条款,而是喜欢借助因果关系的概念来规避不合理条款的适用。在笔者看来,对于保险合同中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如果只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会产生其他问题。例如,否定保险人制定的条款的后果是要求保险人不受限制地承担全部责任,还是将保险人的责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呢?如果是后者,那么,应如何对保险人责任进行限定。在笔者看来,法院借助因果关系的概念来塑造保险人的责任,其用意就在于将保险人的责任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保险人的责任范围。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曾提出应当以“普通商人签订普通商业合同所持之合理期待与目的”作为认定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指导原则。50年以后,著名保险法学者基顿(Keeton)进一步明确提出:保险合同所提供的保障范围应以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为准;当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与保险合同条款的文字含义不符时,应注重保护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而不是刻板地执行合同条款的文字表面含义。基于合理期待原则的要求,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对承保原因事项和除外责任原因事项的规定不得违背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法院在认定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和确定保险人是否承担赔付责任时亦应从保护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角度出发。
虽然卡多佐和基顿都强调从合理期待的角度认定保险法的因果关系,然而,两者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卡多佐提出其主张是在1918年,其背景是合同当事人均为商人,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其对合理期待原则的解释并无偏袒任何一方的意图。然而,基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合理期待原则,是指保护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其倾向性非常明显,其背景是保险合同是由保险人单方制定的附和合同,而被保险人通常是对保险一无所知的普通人。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卡多佐和基顿的主张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即通过法律规则来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在不同的时代,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和地位的对比是不同的,因此,维系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的具体点位亦应相应地作出调整。
明了上述问题之后,如果再回过头来看有关因果关系认定与保险人赔责任的司法判例,我们就会发现,在形式上的逻辑不一致的背后,是实质上的价值判断原则的一以贯之。
结语
因果关系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难题,在于在这个概念的表象之下隐藏着许多政策性判断因素,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其本来面目。对此,美国学者普罗瑟(Prosser)一语道破,因果关系规则其实是一种责任限制规则,“这种限制有时属于因果关系方面的,而更多的属于与因果关系毫无关系的各种政策考虑。法院倾向于以因果关系语言来表达他们所作的这种考虑,但这常常掩盖了其中所包含的问题实质。”[1]p92
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其目的在于界定保险人的赔付责任范围,其背景是保险人已在其制定的保险合同中对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事项作出了规定。如果说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并不是单纯的事实认定,而是将价值判断蕴于其中,那么,在当代社会,在保险合同是由保险人单方制定的附和合同,而被保险人是对保险知识缺乏了解的普通人的情况下,法院在认定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时,应遵循保护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原则。
注释:
① 国内多部有关保险法和商法著作都将近因原则看作是保险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参见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页。
② 《友邦综合个人意外伤害保险(IPA)条款》第十条。
③ 在实践中,意外死亡保险有可能是规定在单独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或意外死亡保险合同中,也有可能是附加在人寿保险合同中的。有些人寿保险合同约定,如果被保险人是“意外”死亡,受益人不仅可获得通常的死亡保险金,而且还可获得意外死亡保险金,因此,关于被保险人死因的认定在实践中非常重要。
④ Isitt v. Railway Passengers Assurance Co., 22 QBD 504 (1889).
⑤ 在该案中,被保险人在骑马时跌落,并湿透了衣服,染上了肺炎而死亡。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只有当意外伤害是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时,保险人才负有赔付责任,并且,保险合同明确将疾病因素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虽然存在上述保险合同条款,法院仍判决保险公司负有赔付责任。参见:In the Matter of an Abitration between Etherington and the Lancashire and Yorkshire Accident Insurance Co (1909) 1KB 591, 598.
⑥ Lawrence v. Accidental Ins Co. Ltd. , 7QBD 216 (1881).
⑦ Mfrs.’ Accidents Indem. Co. v. Dorgan, 58 F. 945 (6th Cir. 1893).
⑧ Nat’l Masonic Accident Ass’n v. Shryock, 73 F.774 (8th Cir. 1896).
⑨ Modern Woodmen Accident Ass’n v. Shryock, 74 N.W. 607 (Neb. 1898).
⑩ Adam F. Scales, Man, God and the Serbonian Bog: The Evolution of Accidental Death Insurance, 86 Iowa L. Rev. 191 (2000).
[1] [美]哈特,奥诺尔.法律中的因果关系[M].张绍谦,孙张国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CausationinInsuranceLawandJudicialInference——TheCasesofAccidentalDeathInsurance
ZhouXue-feng
(Law School of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The purpose of determination of causation in insurance law is to define the insurer’s liability, and the determination should be done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insurance contracts have include the terms about insurance coverage and exception. In fact, the courts have mixe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ublic policy into the determination of causation in the insurance cases. The judicial decisions of causation in the cases of accidental death insurance have showed the above ideas. In modern society, the court should obey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ng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the insured in determining the causation in insurance cases.
insurance law;causation;judicial inference;accidental death insurance
DF438.4
A
(责任编辑:黄春燕)
1002—6274(2011)02—053—0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灾难性损害补偿制度研究》(YWF1006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周学峰(1973- ),男,山东临清人,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