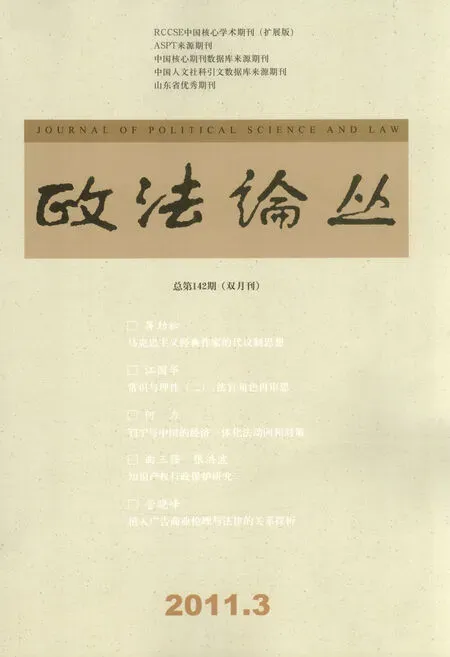中国法律解释权主体的历史演变*
2011-02-19魏胜强
魏胜强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中国法律解释权主体的历史演变*
魏胜强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非常丰富的法律解释权主体的内容。在奴隶社会时期,王权之下由神职人员和司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在封建社会时期,皇权之下以官府为主私人为辅行使法律解释权;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形式上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行使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并深受中国专制传统的影响。
法律解释权 配置 历史演变
在中国法律发展进程中,有不少内容涉及法律解释权的主体问题。探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法律解释权主体的历史演变,对于全面认识中国法律的发展历程,深刻理解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基本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一、奴隶社会时期——王权之下由神职人员和司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
夏、商和西周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这一历史阶段的法律发展水平非常低,法律适用很简单。尽管如此,当时仍然存在由谁来解释法律,即法律解释权的主体问题。
夏朝的法律主要是习惯法,包括礼和刑两部分,由于年代久远,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从后来的文献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某些内容。例如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夏朝统治者用宗教迷信维护其统治,当时神明裁判方法盛行,据说皋陶审判案件就是这样。“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论衡·是应》)皋陶既是法官,运用神灵的“指示”进行判决,又是通过司法实践创制法律的立法者。显然,皋陶在审判过程中解释了法律,但这种解释带有很大的神明色彩。
商朝的神明裁判得到进一步发展,“神判”与“天罚”是商代统治者假借鬼神意志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概括。商王是全国最高审判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最后裁判权。在商王之下,中央设最高司法机关司寇,司寇之下设有正、史佐理司法。地方司法官称士,基层称蒙士。从甲骨卜辞看,商朝大量的审判主要是由卜者进行的,卜者通过占卜向神请示做出判决。卜辞由从事占卜的人解释,神明对这些卜问的答复,实际就是卜者代表国王和司法官的旨意做出的决断。[1]P18-19在商朝国家机关中,见于卜辞的主要官职有乍册、卜巫、史等,通称作史官,掌管祭祀、贞卜和纪事,他们是所谓神和人之间的媒介,是神权的掌握者,也是国家的重要执政官,地位相当高,权力也很大,对国家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商朝后期,随着王权的进一步加强,史官的权势相对下降,武乙以后商王取得亲自贞卜的权力,进一步削弱了史官的职权。[2]P33史官,也就是神职人员,掌握着审判过程中对上天旨意的解释,因而也就掌握了对法律的解释权。“商人凡事无不通过占卜向鬼神请示,占卜官就成为鬼神与社会之间的媒介。作为神的旨意的法律,也是通过占卜官的解释传布于社会的,甚至定罪量刑都要诉诸鬼神。在神明裁判的古老司法模式中,占卜官实际上充当了法官的角色。”[3]
到了西周,中国的奴隶制法律有了很大的发展。西周的统治者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来调整不同地位的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规范形成一套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史称周礼。周礼以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的许多规定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法律效力。由于周礼突出了人的色彩,神的色彩在西周的法律当中不断淡化。有学者指出,西周时期,神权观念开始动摇,神明裁判不再盛行,但其影响似乎还保留下来,如当时的誓审,就是神明裁判的遗迹。[4]P295西周的诉讼制度较商朝有一定的发展。周王拥有最高审判权,他可以处理诸侯之间的争讼。周王以下,中央设置专门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2]P63司寇之下,设士师和士,其中士师掌管中央政府的“五禁(宫禁、官禁、国禁、野禁、军禁)之法”及“官中之政令”,解释法律,审理士一级的案件。士作为属吏,人数较多,故称群士,各负一责。[4]P259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逐渐瓦解,世卿制度逐渐崩溃,官僚制度开始萌芽,管理祭祀鬼神和贞卜的神职人员的地位在国家机关中处于次要地位,掌握司法权的官职司寇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2]P74-75在这一时期,一度掌握法律解释权的神职人员开始让位给司法官,由世俗的司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
总的来说,在夏商周时期,主要有三种人员行使法律解释权,其一是神职人员,其二是法官,其三是王。在中国奴隶社会里,这三种主体能够行使法律解释权,有其特定的原因。
神职人员行使法律解释权,跟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在恶劣的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而转向求助神灵有关,也是原始宗教在奴隶社会得以延续的表现。在奴隶制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宗教存在并对政治法律制度产生重大影响。而在商朝,统治阶级达到了迷信神灵的地步,占卜非常盛行。在这个充满宗教和迷信的社会里,神职人员掌握着对神灵意志的解释权,当然也就掌握了对法律的解释权。他们的解释就是所谓的上天的意志,能直接施用于案件的审判中。神职人员行使法律解释权也是统治阶级以上天的名义维护其统治的需要。统治者代表天意进行政治法律活动时,必然要寻找一个能够沟通人与神之间的渠道,这种渠道就是占卜,于是神职人员就起到了解释神的意志的作用。通过解释所谓的神意,统治者的活动便披上了神圣的光环,其司法审判就成了所谓的“天罚”。垄断神权需要专门的人对占卜进行解释,神职人员理所当然地成为行使法律解释权的主体。
司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主要是由当时的法律形式决定的。早期的法律主要是习惯法,内容相当粗略,在适用起来表现出很大的不明确性,因而必然会遇到解释的问题。在当时法律解释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的情况下,对习惯法进行解释的任务只能由具体的司法官来完成。到了西周,司法官解释法律的做法得到充分发展,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之上的周礼大大降低了“天”的色彩而突出了“人”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了司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权。司法官的裁判对法律制度的创建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为了制定客观有形的标准作为裁判依据,统治者将个别命令性的裁判进行积累和整理,选择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裁判并赋予其以先例的意义和作用,这就是最初的判例。判例越积越多,统治者便通过文字将其记载下来并予以分类汇编。夏商周三代在其建立之初都编制了判例汇编,称为刑书。这一过程就是《左传》所载的下列内容:“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①由于当时的习惯法非常落后,自然需要法律的适用者对法律进行创造性的解释,以调整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司法官的判例能够成为后来的法律,正说明了司法官在审判过程中通过对法律行使解释权而使落后的习惯法不断完善。
王行使法律解释权在古代的中国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奴隶社会不曾经历过像古希腊罗马那种发达的民主与共和制度,也不存在西方奴隶制国家中的执政官(王)、元老院、监察官以及平民大会等不同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中国一进入阶级社会就开始了君主制,君主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掌握着不受限制的权力。“家天下”的局面使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君主个人的私人问题,君主个人的私人问题又同时变成国家的问题,君主是国家也即是他的私家的所有问题的决策者,各种官员都是在君主的授权下,秉承君主的意志而行事,司法活动当然不会例外。无论在夏商西周哪个朝代,王都是最高司法官。尽管中央一级设有全国最高司法机关,但它不过是王之下的最高司法机关,它的一切决策、一切审判活动都必须遵循王的旨意。神职人员、司法官等行使法律解释权的结果要上报王,由王来决定,王成为法律解释权的最终行使者。即使在神职人员占据重要地位的商朝,对占卜的解释一度垄断在史官手中,史官对占卜的解释也只能顺从商王的意志,运用占卜为商王的活动镀上一层神光,而不是商王听命于史官的解释。后来商王取代了史官而亲自占卜,更赤裸裸地表明了商王是法律解释权的最终行使者。因而可以认为,在夏商西周时期,尽管有专门的人员行使法律解释权,但他们的权力都由王权派生出来并在王权之下行使。
二、封建社会时期——皇权之下以官府为主私人为辅行使法律解释权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发生了很多变化,出现了成文法。成文法的公布摧毁了奴隶主贵族对法律的垄断,限制了他们的一些特权,对于法律解释权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战国时期诸侯国在变法时大力推进立法,促进了封建制法律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法律解释活动的发展。秦国商鞅变法对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影响最深远,因此我们从秦国开始,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探寻中国封建社会法律解释权的主体。
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防止出现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商鞅主张,“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危险。”(《商君书·定分》)这大概是封建社会中国官方解释法律的开始。秦国和统一后的秦朝基本上采用了商鞅创立的法律制度,并做了很大的修订和补充。为了防止有人以古非今,秦始皇加强思想专制,实施了焚书坑儒的严厉措施。同时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秦始皇下令,只有国家官吏才有权解释法律,严禁私人解释法律,“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有执行政府法令的官吏才能做法律教师,教学的内容也只能是政府公布的法律,这就把对法律的解释权牢牢控制在官吏手中。以吏为师有利于刚刚建立的专制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巩固,但它使法律解释活动仅局限在特定的领域,不利于正处在发展初期的封建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且还引起了人们对法律的恐惧而不是崇敬。中国几千年来视法律为刑罚和统治工具的思想与秦朝的严刑峻法和以吏为师的做法不无关系。“从此中国古代律学便走上了以注释法律为根本特征的道路,而秦简的‘法律答问’便是注释律学的滥觞。”[5]P182
自从秦朝开始由官吏行使法律解释权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部分变革,但这一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制度保留了下来。汉朝初期,统治者吸取了秦朝因暴政而灭亡的教训,注重综合运用儒家和法家的理论治理国家。尤其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儒家经典被奉为神明,董仲舒利用自己的儒学声望和社会地位,对《春秋》进行注解,用以裁判案件,形成了“春秋决狱”制度。董仲舒根据儒家经义对法律的解释与他的官员身份以及朝廷的授权分不开,董仲舒以政府官员身份成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者。由于春秋决狱的盛行,两汉时期有许多儒家大师竞相以儒家经典注律,使得法律更加繁杂,带来法律适用的困难。三国曹魏时期,天子下诏,只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这些儒家大师们的解释是私家注律,虽不具有法律效力,却对司法实践产生了影响。其中个别儒家大师的解释经过皇帝的认可而具有了法律效力,他们成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者。西晋时期,法律解释权进一步控制在封建官员手中。在《晋律》颁行的同时,张裴、杜预为之做注,注解经武帝批准,“诏班天下”,从而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历史上总是把张裴、杜预的注解与晋律视为一体,后人称之为张杜律。[6]P175-176张杜二人皆为朝廷命官,他们对法律进行解释意味着法律解释权回归到了官方。
唐朝是中国古代法律解释活动非常发达的时期。唐朝的繁荣促进了立法的发达,立法的发达相应地又导致法律解释的发达。唐朝立法的杰出代表《永徽律》颁行全国后,高宗下诏由长孙无忌等人对《永徽律》逐条进行注解,叫做“律疏”。律疏经皇帝批准而颁行。律疏附于律文之后,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疏与律合在一起通称《永徽律疏》,后世又叫做《唐律疏议》。[2]P252-253《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唐以后的整个中国封建法制和中华法系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唐律疏议》由立法和法律解释组成,法律解释者本身又是立法者,对永徽律的解释实际上是由立法者进行的,这种解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立法解释,因而从这部法典中可以看到,法律解释权掌握在立法者手中。
唐朝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整个法律制度并没有多大的进展。宋元明清时代的法律所取得的成就难以超过唐律,在法律解释方面建树也不多,法律解释权的主体跟前朝比起来无甚大变。倒是官员以私人身份所进行的法律解释活动影响较大,如宋朝郑克的《折狱龟鉴》、宋慈的《洗冤录》等,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约束力,但影响甚广,事实上成为一些司法官判案的依据。明朝初期,法律解释活动开始复苏,但被严格限制在官府中。尤其是《大明律》制定后,除了编撰者奉命进行的官方注解外,朱元璋严禁对其进行议论和改动,私家注律失去了存在的环境。明朝中后期,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官方原来的注解难以适用了。“然而明中叶以后,政治极端腐败,官吏擅权,皇帝昏庸,政府已无力组织较大规模的官方注律,不得不委之于私家。只要体现国家的立法意图,符合当政者的利益需求,有利于现行法律的贯彻实施,私家注律不仅被认可,而且受到鼓励。”[5]P192明朝的法律解释权由早期的官方垄断逐渐转向由官方和被认可的私人行使。清朝的法律解释体制变化不大,官方的注律主要是由奉旨修订法律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同时对法律进行简单的解释,解释附于法律条文背后,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与此同时,私家注律在清朝相当兴盛,这种解释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并非无足轻重。“清代政府对私家注律较为重视,认为是‘备律所未备’,尤其是私家注律的广泛性和注律家身份的特殊性,使私家注律活动的影响力较官方注释更巨大。”[7]P327私人在清朝虽不具有法律解释权,但私人的解释却成为官方解释的补充。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法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法律解释活动非常发达,带动了“律学”的繁荣。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并未出现较大的变动,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从社会存在方面说,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每一个朝代的更替,从一定程度上说都不过是历史的反复而已,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变革。虽然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非常有限,不具有根本性。二是从意识形态方面说,中国自从秦开始建立君主专制统治以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君主制,“国不可一日无君”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这两个原因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然经历了朝代的更迭,但整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法律解释权的配置自然也不会发生多大的变革,始终保持较大的稳定性,受朝代更迭、国家分合、外族入侵、农民起义、政府革新等因素的影响甚小。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法律解释权主体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它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官府为主私人为辅行使法律解释权。自从秦朝开创“以吏为师”的制度以来,中国的法律解释权一直掌握在官府手中。在秦朝以及秦以后的几个朝代当中,都是由官吏代表政府解释法律。西晋时期由参与立法的杜预对法律的解释经皇帝批准而具有立法解释的雏形,唐朝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注解明显就是今天所谓的立法解释了,这种由立法者对法律进行解释的做法一直影响到后世的几个朝代。无论是特定官吏的解释,还是立法者的解释,都是官方进行的解释。在中国古代立法行政司法不分的政治体制下,这些官方的解释都是以官府名义做出的,因而可以说,封建社会的中国是由官府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官府行使法律解释权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确立统一的思想和制度、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为了防止出现对法律制度的不同见解和评论,损坏法律的权威性,进而危及君主的神圣性,几乎所有的封建统治者都要求特定的官员代表官府解释法律,这种做法发展到顶端就是由立法者在立法的同时对法律做出解释并赋予解释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然而官府的解释毕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至少它不能及时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这种解释在被具体运用时同样会显得不够具体。私人解释在一些方面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缺陷,特别是那些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私人解释,既能满足法律适用的需要,又能为统治者的统治行为辩护,深受统治者青睐,所以私人解释具有了生存的空间。当然,并非所有的私人解释都具有法律效力,只有经过官方批准的私人解释才是有权解释,这部分私人就成为法律解释权的另一部分行使者。从整个封建社会法律解释权的行使看,少数私人的解释权是对官府解释权的补充。官府与私人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法律解释活动的发展,对中国封建法律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第二,封建皇帝掌握最终的法律解释权。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封建君主专制独裁,操纵国家的所有活动。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封建君主成为国家一切活动的最高决策者。皇帝集全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于一身,当然也就拥有对法律的最终的解释权。无论是官府的法律解释权还是私人的法律解释权,都是经过皇帝恩准而行使的,因而法律解释只能按照皇帝的意志进行,至少不能违背皇帝的意志。皇帝行使最终的法律解释权是中国封建专制独裁制度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自秦朝以来,中国总体上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过于强大而危及中央,皇帝总是把国家的一切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把中央的一切大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任何一个朝代建立之初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统治,树立皇帝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法律解释权自然掌握在皇帝手中。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一种可以与皇权抗衡的宗教力量,因而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活动可以肆无忌惮。中国虽然有一个一统天下的儒家理论,但它的存在不是为了限制皇权,而是替专制皇权辩护的,它所宣扬的理论又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封建专制统治。所以在文化上,中国封建社会既没有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也没有一种可以制约君主专制的宗教,使封建皇帝的所作所为不受限制,皇帝解释法律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皇帝行使最终的法律解释权虽然有利于维护法律解释活动的权威性和法律解释内容的统一性,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皇帝的法律解释活动不受限制,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和情感上一时的喜怒哀乐,随意地对法律做出解释,而且他的解释又成为最高的法律,这必然会破坏法律的稳定性,动摇并不牢固的封建法律制度。
三、清末和民国时期——形式上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行使法律解释权
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惊醒了满清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满清统治者在其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年开始向西方学习,从形式上改变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年的封建法律制度,传统的中华法系逐渐走向解体。1902年,清廷宣布要改革司法制度,1906年正式进行。清廷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司法与行政相分离的原则,先行对中央及京师地区的审判机构进行改革,并颁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改刑部为法部,专职司法行政事务,不兼审判;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全国的最高审判机关;在京师效仿西方国家采用四级裁判所主义,分设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及城谳局,在大理院及各级审判厅内附设检察厅,负责检察事务,封建社会盛行的朝审、秋审、热审、九卿会审、三法司会审等制度一并废除。[4]P475大理院的职权在于,“正卿掌审枉理谳,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以一法权。少卿佐之。”[8]P3464这应当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宣布最高司法机关行使统一的法律解释权,相对于封建社会的法律解释体制来说,具有进步意义。随后的几年,清政府又对司法制度做了进一步的改革,其中对后来影响较大的是1910年颁行的《法院编制法》。按照《法院编制法》,审判衙门分为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实行四级三审制,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在审判制度上采用了资产阶级法律中的回避、辩护、公开审判等原则和制度,规定了审理程序,从而在法律上开始打破封建司法制度的束缚。[9]P58然而,这种改革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行,辛亥革命使清廷确立的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制度仅成为一种历史文献。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执掌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同晚清政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清末的许多法律在北京政府同样受到欢迎。袁世凯一上台就下令“暂时援用”清末的法律,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就在援用之列,一直到1932年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法院组织法》之前,中华民国一直采用清末的司法制度,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这种创立于清末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民国时期得以延续。1927年,国民党武汉国民政府将国民党原广州国民政府的大理院改名为最高法院,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由它继续行使法律解释权。②然而在民国的这一时期,由于群雄争霸,政局动荡,以武力维系统治地位的北洋军阀政权并不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最高司法机关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受到军阀政权的左右。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篡夺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是年10月,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最高法院组织暂行条例》,将北洋军阀政府的大理院改称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同时将各级审判厅一律改称法院。1928年,随着对全国的逐渐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即按照五权分立制度,分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同年11月公布司法院组织法,当月成立司法院,所属机关设有司法行政部及最高法院。[10]P59司法院院长总理全院事务,经最高法院院长及所属各廷廷长会议议决后,统一行使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之权。[1]P18-19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法院组织法》,于1935年7月1日实施,该法仿效法、德的司法体制,对法院设置采取三级三审制,即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隶属国民政府司法院的最高法院不设分院,以统一全国法律之解释。[11]P4961947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该法规定: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无抵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法律与宪法有无抵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依据宪法,南京国民政府同年3月重新制定了《法院组织法》,1948年7月1日司法院改组成立,司法院设大法官会议及所属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三机关。“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行使解释宪法及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在解释宪法方面不但阐明宪法之真谛,并不许任何法令与之抵触;更应因应时间与空间之因素,使宪法不为情势所格,而能澈底实行。在统一解释法律命令方面,使分歧之意见趋于一致,予政府与人民以共同之依据。”[10]P107-108国民党从执掌中华民国的政权以来,就继承了由最高司法机关解释法律的制度,并做了修正,尤其是在《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以来,关于司法院法律解释制度的改革基本上定形了。
通观清末和民国时期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无论是在满清贵族苟延残喘的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法律解释权都被配置给最高司法机关。尽管最高司法机关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称谓,其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具体机构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基本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由清末和民国前期大理院行使法律解释权到民国后期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行使法律解释权,说明法律解释权的行使越来越细化,法律解释制度逐渐走向完善。《中华民国宪法》刚刚颁布两年,国民党政权就被革命力量推翻,国民党所确立的由大法官会议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制度在中国大陆被废除,因而它对中国大陆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这些法律制度继续有效。虽然国民党执政的台湾地区在法律制度上也做过一些变革,但由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法律的制度一直坚持下来,并经过不断完善,至今仍在台湾地区发挥作用。
关于清末和民国时期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这一制度,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清末和民国时期确立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制度是向西方国家学习的结果。早在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列强的枪炮声惊醒的中国人就开始扔掉妄自尊大的心态,主张向西方学习。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洋务派抱着“师夷制夷”的目的而大搞洋务运动却仍然摆脱不了受洋人侵略的命运后,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洋务运动的失败当中反思中国的社会制度本身,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就必须从社会制度改起,而改革社会制度就必然要借鉴西方改革中国的法律制度。当时的西方主要国家经过不断的变革,已经认可了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使清末的司法改革也确立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尽管由于满清政权的迅速垮台,清末所修订的各种法律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施,但它所确立的许多制度却为中华民国所继承。这是因为,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华民国与满清末期的政府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反动透顶的腐朽政权,而且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许多制度都不完善,军阀们忙于内战无心创立新的法律制度,传统封建社会的法律又不能搬来运用,照搬清末的一些法律制度也就成为最简捷的选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时,同样面临着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和镇压进步力量的问题,自然也无心进行法制建设,因而民国前期的法律制度便是其法律的来源之一。同时,在国民党政权时期,为了标榜其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国民政府在许多制度上也向西方国家学习,因而在宪法当中明确宣布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进步,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分立和限制专制统治,这些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都是不存在的。
第二,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在当时的中国只具有形式意义。清末和民国时期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只是就法律规定来说的,其实际情况如何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单就法律来说,中华民国有相当一部分法律具有形式上的进步性,但在实际上却完全不同。清末修订的具有西方立宪君主制色彩的法律,不等实施就被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中。而在民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却四分五裂,战乱不断。法律的规定可能会令人满意,但军阀统治者根本不会遵守,这些规定更多的是一纸空文。法律虽然确立了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但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最高司法机关不可能独立于军阀统治者之外而处于超然地位,它的法律解释不可避免地会为当时的反动统治辩护。明确授予最高司法机关法律解释权的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国民党集团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打响内战时公布的,在军事上的胜败决定一切政局的当时,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又怎么可能做出受到不同主体遵守哪怕只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受人遵守的法律解释呢?在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满洲贵族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清末,在内战连绵、一盘散沙的中华民国,虽然法律规定了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但这种权力的行使仅是法律的规定,是形式上的,而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只有在相对稳定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中,法律的规定才会变成现实,而当时的中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营造出这种社会局面,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的法律解释权实际上只能控制在依靠武力掌握国家政权的大军阀手中。
注释:
① 《左传·昭公六年》。参见[春秋]左丘明:《左传》,覃遵祥等注,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540页。这种由判例到判例汇编再到《左传》中所讲的刑书的观点来自陈涛教授。他认为,经过整理汇编的判例集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就是刑书。其中“议”指评判,“事”或系事字误认,实为古“争”字,指争讼。“刑”为“侀”字省笔,指一成不变的常制。“辟”原指审理案件取信于民,引申为判例。“有”与“佑”通,作助讲。“乱”借为断,指裁判。“政”借为正,正与定通,指定罪量刑。“作”字有增益义,引申为整理、编订。“叔”系“俶”字省笔,俶(音chù)有始初之义,可指初期。参见陈涛:《中国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② 台湾学者廖与人对当时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状况做了概括。参见廖与人著:《中华民国现行司法制度》(上册),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07页。
[1] 薛梅卿,叶峰.中国法制史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 张晋藩等.中国法制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3] 陈兴良.法的解释与解释的法[J].法律科学,1997,4.
[4] 陈涛.中国法制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5]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6]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
[7] 何敏.从清代私家注律看传统注释律学的实用价值[A].梁治平.法律解释问题[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8]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十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 范明辛,雷晟生.中国近代法制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10] 廖与人.中华民国现行司法制度(上册)[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1982.
[11] 怀效峰.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TheHistoricalEvolutionofSubjectofthePowerofLegalInterpretationinChina
WeiSheng-qiang
(Law Schoo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 450001)
There were plenty of legal system on the subject of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legal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slavery society, below the kingship, the clergy and law-officer held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feudality society, below the imperial power, feudal official held the main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some parsonalconsults held the secondary one.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formally. These kinds of subject of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were determined by the spe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affected by the autocratic tradition.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disposition;historical evolution
DF08
A
(责任编辑:唐艳秋)
1002—6274(2011)03—099—07
郑州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子项目《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建设与公民教育》、重点课题《社会转型期中国法治建设模式研究》(LC-A004)阶段性成果。
魏胜强(1976-),男,河南遂平人,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律哲学,法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