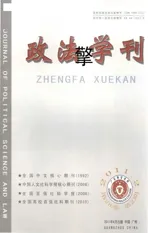刑诉中尿液证据采集问题研究——以德国为参照
2011-02-18屈奇
屈 奇
(韩山师范学院 政法系,广东 潮州 521041)
一、前言
随着科学进步与社会环境变迁,犯罪的样态也日趋复杂与多元化,尤其以毒品及麻醉药品的泛滥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身体健康,因此关于毒品犯罪证据的采集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对于因酒后驾车而致人伤亡或酒醉致人神智不清或丧失,也需要有专业的科技与鉴定方法予以配合,因此,人体的尿液、血液、呼气甚至唾液等,日渐成为不可获取的证据资料。人体在不断地在进行新陈代谢,作为人之代谢物,在液体方面主要表现为汗液、唾液、痰液与尿液等,其中以汗液与尿液居多。依据相关的研究结果,正常成年人每日排除的尿液量为一点八公升左右。由于麻醉药品进入人体后,其中一部分受体内代谢而被排除于尿液中,因此,对尿液进行检验便可发现排液之人是否使用麻醉药品,此外,毒品,比如冰毒在血液中的存留时间比较短 (一般为1至2小时),而在尿液中的存留时间较长,通常为1至2周,当尿液检验结果为阳性时,则提供尿液之人被检察官起诉,并被法官判决有罪,在刑事诉讼中,通常都是将其尿液检查结果作为判决有罪的主要依据,比如最近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歌星满文军吸毒案以及日本的著名女艺人酒井法子涉毒案等。尿液中水仅占百分之九十五,其余百分之五包括细胞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溶质以及外来物质,外来物质通常包括药物、毒物、酒精与矿物质,可以据此作为证据证明相关人员曾服用麻醉药品 (如上所述),还可以被用来证明相关人员曾饮用酒精、汞中毒、患有糖尿病等,尿液证据的运用有着广泛的前景。由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而排除体内的尿液或经过被采集人明知而主动予以认可所进行的尿液采集活动一般都不会关涉公民的诸多权利,因而讨论的必要性不大;而执法人员违背被采集人的意愿强制所进行的尿液证据的采集则通常会侵犯公民的诸多权利,比如人身自由权、身体权与隐私权,因此必须谨慎而为之,也很有必要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展开深入的研究以便在保障人权与发现案件真相中实现平衡,“采取一种妥协或互相调整形式可能要比‘二者取其一’的方法 (either-or solution)更为可取。”[1]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上,对于尿液证据等的采集过程,尤其是强制采集并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使得尿液证据的采集上出现无法可依,混乱无序的状态。有鉴于此,笔者在对大陆法系的德国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他们对于尿液证据的采集,特别是强制性采集进行有效规制的一些普遍做法与经验。
二、德国刑诉中关于尿液证据采集问题的立法规定
德国联邦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对于涉诉公民的身体检查有可能侵犯公民的人身权,为了有效地规范执法人员的行为以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保持一种均衡,因此德国刑事诉讼法对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引导针对涉诉公民的身体检查在合法、科学的限度内有效的进行。德国对于强制采集尿液样本的立法规定集中暗含于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a与c之中。德国刑事诉讼法将强制采样划分为对被追诉者的强制采样和对其他人员的强制采样。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a项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a与b中就对被追诉者的强制采样问题进行了规定,第八十一条a项规定:“为了确定对程序具有重要性的事实,允许命令检查被指控人的身体。为此目的,在对被指控人身体健康无害的条件下,许可不经被指控人同意,由医师根据医术规则,本着检查目的进行抽取血样验血和其他身体检查。命令权为法官所有,在延误就可能影响侦查结果时,检察院和它的辅助官员也有权命令。自被告所采取的血液样本,或者其他的身体细胞,只有在为了作为采取基础的程序或者是其他系属程序的目的,而允许被使用;一旦对此不再是必需的,就必须立刻销毁。”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非被指控人的强制采集样本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条件,比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c项规定:对于非被指控人的其他人员,如果他们有可能充当证人,只能在为了侦查事实真相必须查明他们身上是否带有犯罪行为的特定痕迹、后果时,才允许不经他们同意进行检查。
关于身体检查的适用问题,德国历史上最为典型、最富有指导意义的案件之一要算Robert.N.一案。在该案的主审程序中,慕尼黑区法院法官为了确定被告Robert.N是否具有责任能力而命被告接受医疗检查。法医根据诊断结果断定被告中枢神经系统可能患有疾病,认为有必要作血液检验以及液体抽检 (脑髓液体以及脊髓液体),该种检验必须以一根长针管刺入腰部脊髓 (腰部穿刺术)或颅骨与最上端颈椎之间的胫骨髓 (枕骨穿刺术)的椎骨柱中。因为被告拒绝实施这种检验,因此,区法院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a项之规定作出判决,命令慕尼黑大学神经专科医院进行该项检验。被告人不服此项判决而提起宪法诉求,主张液体抽检是一种最为痛苦的手术。对于此案,宪法法院指出:如同所有国家侵犯人身自由范围时的情形相同,在本案关于液体抽检的判决中,法官必须注意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比例原则,即使是根源于法治国家非常重要的合法性原则。基于调查犯罪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通常情况下可正当化其对于犯罪嫌疑人进行自由的侵犯,但对人民自由范围侵害得越严重,其实公共利益的满足就愈少。因此,为判断目的与措施间的比例关系,必须考量到该项拟制裁的犯罪行为具有何等重要性。这点特别在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a项所允许用以确定犯罪嫌疑人责任能力的重大措施时有其适用的必要性。在此,考量基本权精神实质基础上的法律适用要求的是:拟进行的手术侵犯与犯罪行为的重大性问题之间存在适当的关系,因而,为调查犯罪行为而造成后果不得重于该犯罪行为可能受到的最终刑罚的幅度。基于此,法官必须遵守宪法,在个案中衡量法律所允许采取的措施与禁止过度原则①按照该原则的要求,刑事追究措施,特别是侵犯基本权利的措施在其种类、轻重上,必须要与所追究的行为大小相适应。。就本案而言,法院忽略了此项原则。在本案中,被告虽被课以处罚锾,但并没有任何人因此受损,整体而言,本案所牵涉者乃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为此所受到课处的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刑罚,甚至在可能情况下,可以考虑因微罪而不予以起诉处分。相对与此,以上两种方式的液体抽检是一项并非紧要的人身侵害,因为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违反被告的意愿强令其接受此种手术,实在不足以构成正当化的理由。法院在基本法第二条第二项基本权范围内忽视了比例原则,因此上述判决应予以废弃,案件发回区法院。学者Sarstedt教授也指出:只有当对被告所作的手术与被告被指控罪责之严重程度、嫌疑的重大性、结果的可能性以及判决的价值处于适当关系时,此种符合该规定精神所作的人身侵犯才是允许的。此外,对隐藏在法律文义之后的人身不可侵犯性所作的侵犯,其实是存有一条绝对的界限的,一旦逾越将危及基本权的本质内涵。①高明哲:《刑事证据法实务之研究》,86年6月台湾地区司法年报第17辑第16篇,第57页。
从以上立法规定与典型司法案例的法理解读可以看出德国关于强制采集尿液的立法规定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强制采集尿液应具有正当性,即为了确定程序上的关键事实,而非无关紧要、无关痛痒的琐碎之事;第二,被强制采样的被指控人有忍受的义务,但忍受义务存在一定的界限,即强制采集尿液必须对被指控人的身体健康无害的情况下,方可为之,“达致刑事诉讼目的和有效地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是一度不可逾越的底线,因此亦对掌管司法的机关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内作出的强制介入划出一个该等机关活动不可逾越的范围;”②欧蔓莉:《澳门刑事诉讼制度及基本原则》,1995年北京研讨会宣读论文,转引自周士敏著:《澳门刑事诉讼制度论》,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第三,采取法律保留原则与原则上的司法令状主义,对于是否对被指控人进行强制采集尿液样本,原则上法官享有最终的话语权,但也有例外,即延误有可能影响侦查结果时,可以由检察院以及其辅助官员为之,“从理论上讲,当某一措施被视为极具侵犯性时,德国刑事诉讼法典首先试图通过司法命令的要求来实施控制。但是很明显,这一方式的固有局限限制了其活力。首先,现实中某些 (紧急)情况下要求等到司法机关批准是不明智的,换言之,事先的控制总会有例外,而例外无可避免的会削弱其效力。其次,即使有了司法控制,明智地说,法官实际上也常常因为工作负担而无法真正审核警方侦查策略和假设的合法性。因此司法的事先控制必须同其他措施相结合”;[2]187-188第四,强制采集尿液样本的运用与否应符合狭义的比例原则,即相称性原则;第五,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非被指控人强制采集尿液样本措施的运用设置了更为严格的条件;最后,德国刑事诉讼法涉及到对于强制采集尿液样本的结果使用目的予以限制,并规定了国家的销毁义务。
三、我国关于尿液证据采集与使用制度的建构设想
由于尿液证据的采集,特别是强制采集的过程通常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身体权与隐私权③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侵犯主要体现为:其一,强迫被采集尿液之人到指定的场所接受采样是对其人身来去自由的限制;其二,在强制采集的过程中,被采集人的人身行动受到了压制;最后,强制采集尿液后,相关法律手续的履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采集人的人身自由。对公民身体权的侵犯主要表现为对尿液的强制采集侵犯了人的身体完整权。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主要表现为:其一,采集尿液的过程侵犯了公民的个人生活安宁权;其二,尿液的分析可能会严重侵犯个人不愿公开的信息资料和秘密。。因此,我国对于尿液证据的采集必须慎重而为之。关于尿液证据采集的程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具体涉及,只是涉及身体检查问题,具有宽泛性、笼统性,没有彰显具有隐私性样本属性的尿液证据采集程序的严格性,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检察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检察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都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及时提取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证。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上述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观念上来看,为我国一贯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历史惯性思维使然;其次,从体制上来看,为我国刑事诉讼过度强调公检法三机关协同作战,互相配合地游刃有余,而对于其相互制约认识不够,导致权力的制约严重不足;最后,从我国立法的一贯宜粗不细的传统不无关系。
值得欣慰的是,该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①有学者建议将来的立法可就此相关问题进行相关规定:“为了查明犯罪事实,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提取犯罪嫌疑人的毛发、皮屑、指纹、掌纹、笔迹、声音等样本,但应以检查的实际需要为限。为查明犯罪确有必要的,可以强制提取犯罪嫌疑人的血液、精液、尿液等体液样本,但应以检查的实际需要为限。”关于强制采样的程序要求,立法建议如下:“采集样本之前,应当告知被采集人提取样本的原因、样本的用途。样本的提取,应当由医师或者专门的技术人员根据医学规则或者有关专门程序进行,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派员协助。禁止采取危及身体健康或有辱人格、贬损名誉的方法进行强制采样”,载于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428-429页。“对于被拘捕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强制采取其指纹、掌纹、脚印,予以照相、测量身高或其他采样措施。为侦查本案且有相当理由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采取犯罪嫌疑人的毛发、唾液、尿液、精液、声调、血液或其他出自或附于身体上的物。禁止采用危及人员生命、健康或贬低其名誉或人格的方法进行强制采样。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制采样,适用本节相关条文的规定”,载于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335页。“为了查明与犯罪有关的事实,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侦查人员可以从人体上采集血液、分泌物、排泄物、机体组织、体纹、印记及其他样本。采集样本,由侦查人员进行。必要的时候,公安机关可以聘请医师或者其他技术人员协助采集样本。采集样本之前,应当告知被采样人提取样本的原因、样本用途、采样程序与被采样人的权利义务。公开采样有碍侦查时,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秘密采样。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强制采样。采集样本,不得损害被采样人身体健康,不得有辱人格尊严。对于采集样本过程中熟悉的个人隐私,应当保密”,载于徐静村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136页。但仔细推敲,笔者发现其中有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尿液证据进行强制采集问题,通常要获取法官的批准,采取法官保留原则,而我国则是执法人员要获取其所在的执法机关负责人的批准,是一种行政化的运作方式,权力的运用难以受到有效的约束与限制;第二,在德国与日本,是否对被指控人采取强制采集尿液措施主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为尺度,比如尿液的强制采集其目的应出于证明程序上的关键性事实,强制措施的运用应是不得已而为之,从而从实质要件上严格限制其随意的启动,而我国学者对于强制采集尿液的启动的限制相对而言比较松动,具有易发性;第三,尿液的强制采集只适应于严重的犯罪。而我国的立法建议则没有指出强制采集尿液证据适用的案件性质,没有全面地体现比例原则的精神实质;第四,没有就针对非被指控人的强制采集尿液问题作出规定,有失偏颇;最后,没有规定尿液证据使用后如何处置问题;此外,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强制尿液证据的采集都是由具备专业资格的医师进行,这是一项硬性规定,能够保障采集过程的公正性与科学性,而我国的相关立法则没有就此作出硬性的规定,而带有很大弹性,是否聘请专业的医师进行,执法人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关于我国采集尿液样本制度的建构问题,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应提升人权保障意识,认识到尿液证据的采集关涉公民的诸多权利,尤其是强制采集必须慎之又慎;其二,应将身体样本细化为私密性样本与非私密性样本,将尿液证据归入前者,并根据前面的划分设置不同的应用程序,以便执法者有法可依,避免自由权过大而导致的恣意;其三,应采取任意采样为原则与常态,强制采集为例外,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应依据比例原则来衡量;其四;关于何机构对于强制采集尿液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与话语权的问题,涉及到司法体制的改革与权力的重新配置,改革应采取渐进式,从短期来看,最好将此权力配置给检察机关,对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可以由其内部与执行部门不同的另一部门来决策,以增加权力的制约保障民权;从长远来看,还是要采取司法令状主义的模式,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即原则上由职业法官来审查决定,但应设置一些例外情形以增加其可操作性;其五;应针对采集尿液的主体不同而设置不同的采集程序,对于非被指控者或非被逮捕者应设置更为严格的程序,而不能搞一刀切;最后,应规定尿液样本的使用范围与国家的销毁义务。
四、结束语
我国学者龙宗智教授指出:在法制建设问题上,应有一个小处着眼的问题,它涉及立法与司法的精密性。在立法上,法律规范应力求具体细致准确,避免大而划之,含糊笼统;在司法活动中,则要充分注意操作上的适当与合理,遵守科学的操作程序,不粗疏、不蛮干。正是从这种细致入微的规定中,能使人看到一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法治精神。而在涉及公民权利之处,这种细致严密的规定又体现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比如英国与澳大利亚将身体样本划分为私秘性样品与非私密性样品,对其进行了具体所指予以细化,并对其采取严格程度迥然不同的程序予以采集,这里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法治建设也许十分需要从小处做起,在每一个技术问题上都不苟且,“小处不可随便”。如果我们在诉讼的每一个具体环节都应做到在设计上较为严密而合理,在操作上也比较理性,例如法律人员每做一个调查每取一份证据都能采取比较理性的方法,那么这种“积薪”式的努力最终将导致制度及其功能的重大改变,从而有望实现“质的飞跃”。我想对于我国尿液证据的采集与运用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也应是如此。
[1]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中德强制措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M].陈光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