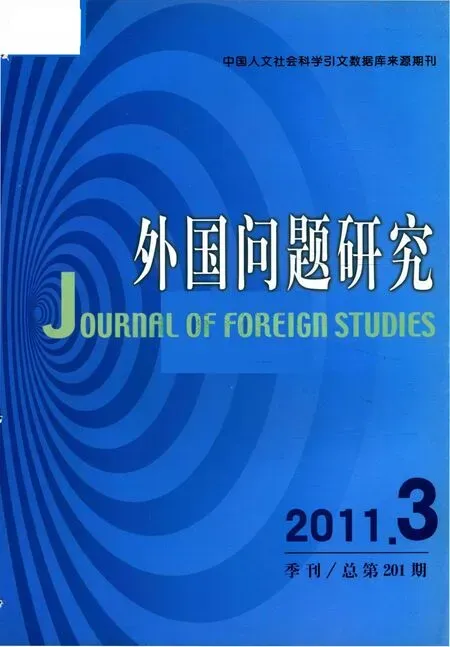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
2011-01-31郭冬梅
郭冬梅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24)
地方财政是地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研究地方制度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但是在我国现有的伪满洲国地方制度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只关注地方行政,对地方财政则缺乏相应的分析与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人认为,通过研究伪满洲国的地方财政,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伪满洲国地方制度的特点,从而更深刻地揭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地方进行统治的侵略本质。
街村是伪满洲国的最下级行政区划,对其统治的方式也是日本侵略者关心的重中之重,其财政特点体现着伪满洲国的街村统治特色。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出于治安上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度,通过组织反动保卫团、实行连坐制度等,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其所需经费以强征所谓的保甲费为支撑。1937年后,由于伪满洲国的主要任务向“国家建设”转变,对于基层地方,发布街制和村制,仿照日本基层的町村制度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制定了统一的街村财政税收制度。但是街村制度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也没有真正为中国东北基层地方带来自治的福音,不过是对中国东北基层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变形而已。
一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对于县市以下的地方基层还没有形成均一的统治方式。在“南满”地方,继承了旧奉天省于1929年发布施行的辽宁省暂行村制。在“北满”地方,由于“不具街村的实体”[1]20,因此,实行了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
大同二年(1933)12月22日,伪满政府以教令第96号公布《暂行保甲法》,大同三年(1934)1月17日又颁布了《暂行保甲法施行规则》,2月3日确定施行心得、保甲规约标准、职业自卫团的解散要领和义务自卫团的确立方案等,正式开始实施暂行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是中国自宋代以来施行的一种基层地方统治模式,其主要功能是治安及军事,对于历代统治势力渗入到基层起到了重要作用。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最初是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治安维持委员会,“在从满洲根绝马贼的方针下,进行扫匪工作及招抚工作。但是除了东边道路交通不便之地仍余有集团的匪贼外,其他基本上陷于分散状态……日满两当局为树立恒久的对策,以中央治安维持委员会为中心,考究了种种对策案,采用清朝时代的旧制度即满洲及支那独特的保甲制度的长处,目下令民政部当局进行保甲令起草工作。……保甲令即是为指导及取缔上述自治的细胞组织的法令,在防卫威胁良民生活的外匪同时,对内如果所属团体中出现匪贼或犯罪者时适用连坐法处罚责任者维持安宁秩序。”[2]明确其本质是借中国传统的地方统治模式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伪满洲国的保甲制度“是在县市依一定的户数编成保、甲和牌的团体,依靠邻保友爱的团体作为警察的补助机关,保持其团体内的康宁,以防止不断紧急的危害为其主要任务。”[3]1保甲制的单位和一般行政单位的对应情况是:牌为十户,甲为一村(旧暂行村制上的村),保为一区(警察署管区,约包含20个村)。《辽宁省暂行村制大纲》规定凡村内居民满300户以上为独立村,不足300户的联合附近各小村为一村,由县里指定户口稍多的村为主村。“根据这一制度,大致一村300户,一区6 000户,如果一户平均出1.2个壮丁的话,则一甲有360人,一保7 200人。一个警察署直接指挥监督一保。”[4]3关于保甲牌长的选定,规定以“地方德望家为第一,不拘资产多少和学识的有无”[5]8。保甲长受警察署长的指挥监督维持保甲内的治安,牌长接受警察署长和保甲长的指挥监督保持牌内的“安宁”。
保甲制度具有强制性,其规定:“除特殊由民政部大臣认可的地方外,皆依法强制实行,不依个人的喜好,成为保甲牌的一员是义务。”“加入者若违反规约将受处罚”,“保甲牌及自卫团的人员被指名或选任者无正当的事由不得辞任”,“团员除18岁以上、40岁以下者不得免除”,经费和租税同样由各家长负担。“即满洲国的保甲制,其施行是强制的,对于国民是义务的。”[3]23-24“保甲制度对于内乱罪、外患罪、公共危险罪等罪行实行连坐制度,而且设立自卫团,参加自卫团也是义务。”[3]1
到1935年,鉴于暂行保甲制度实施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吉林省,由于“匪患”比较严重,因此,“先于他省实施了保甲准备工作”,并“取得了预期以上的好成绩”)[5]7,因此伪满洲国决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并订立了新的具体实施计划:从康德二年(1935)开始以三年为计划,第一年50县,第二年49县,第三年60县,计划把保甲制度推及整个伪满洲国[6]21。第一年的50县选择的是治安交通良好的地方,预计把保甲工作员每县增加约百人,把各县担任警务指导官及职员者召集到中央及省进行教育,“以图成功”[6]21。
从保甲制的内容来看,他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极为野蛮的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实行保甲制度后,伪满洲国“治安现状得到显著的改善”[5]8,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日本侵略者镇压东北人民的预期目的。随着保甲制度的普及,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继续推进对东北基层地方的控制,主张“不仅仅是家长,也可以动员青少年妇女,特别是家庭主妇,设置青少年团乃至保甲妇人会等,把他们从家庭引导到社会的活动中。此外,和地方教化团、协和会、学校教职员、地方德望家乃至中心人物紧密联系,使之对保甲长进行侧面援助,以树立万无遗漏的方针。”[5]8另一方面开始强调“保甲制度作为地方自治的准备阶段”,称“我满洲国与国民政府本质不同,同样的保甲制却代表了民众的利益,成为民众自治确立的基石。保甲制指导方针所宣扬的王道主义的精神逐渐结出了果实,作为地方自治确立的一个有力的政策,对保甲制度的发展抱有无限的期待。”[5]9在具体实践上,在保甲制度“达到完成”的奉天和滨江等省,开始使保甲制向村的教育卫生等一般自治行政发展[4]3。但是对于这种倾向,日本侵略者内部亦不乏反对声音,指出它“赋予了比日本的町村更浓厚的官治行政的下层代行机关的性质;不仅采取了不适合村民利害的行政形态;而且走向了像朝鲜、台湾和关东州那样的警察政治浸润到部落,即和所谓的农村共同体自治的要求正相反的方向”[4]4。实则指出了伪满洲国保甲制度的“官治性”、警察性质和殖民地性,揭示了这种“自治”的虚伪性。
关于此阶段的财政制度,在实行旧奉天省的区村制的“南满”地方,街村税和原来一样,作为街村税赋课,也即其街村财政制度暂时没有改变。但是在“北满”,“以类似于街村税的公课,即保甲费的名称进行赋课。”[1]20“保甲制度不可缺少的费用由依保甲制度享利益的各家长负担,依土地房屋及其他资产的多寡等负担能力分担。保甲制还实行会计年度,编成预算经警察署长向地方行政官署长提出认可。”[3]1但是各地方有很大差别,“税种不同,赋课额也有显著差异。”[1]20基本上呈现出一种混乱状态。
二
保甲制度毕竟具有非常时期的临时过渡的性质,随着各地“治安”的恢复,伪满政府开始考虑对基层地方的统治方式回归到正常轨道上。为了探索新的统治方法,日本侵略者调查了东北村落的发展过程。他们对于东北农村形成的描绘是:“既没有国家的保护,也没有武力统帅者,只是通过一脉相承的血缘和由于集团生活的地缘关系自然产生的团结,进行自卫自救。”[7]184这种村落自治体游离于地方官治行政之外。但是到了军阀时代,则把区村编入了行政机构的统治中。因此上,“满洲虽然有村落自治,但从所谓近代的行政观念看来,有观点认为是没有自治的。”[7]185“满洲农村的农民八成以上是无学文盲,墨守旧习旧法,既没有农事改良的方法,也没有合理的农业经营知识,村政的中枢机关村公所依然是土豪劣绅、地方资产阶级专断,不能充分发挥村自治的机能。”[7]185
1935年2月,奉天省率先设地方制度调查委员会,对张氏东北政权时代的暂行村制大纲和区村制的实态进行调查。并在调查日本、台湾和朝鲜制度的基础上,制定街制村制实施基准案,同年6月召开县长会议,形成成案,对管下24县实行暂行街村制。1936年民政部大臣向各县长示达,“得到民政部大臣的认可根据省令设置暂行街村制”,基于此,间岛、锦州、安东、热河各省也施行暂行街村制。
而后,民政部地方司根据奉天省的暂行街村制实行的实际效果,在进行种种探讨和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伪满洲国的街村制准则。1936年5月 21日,中央发布《保甲特别工作方针及要领》,“宣布向街村制转变”[3]1。
1937年10月在《满洲国地方行政机构改革案要纲》中提出“关于街村的育成、制度的确立,当局最为致力,以期成为国家最下级行政单位的团体,振兴邻保共同生活,增进地方民的福祉,使之具备保甲的职能、经济的职能、行政的职能。”并同时强调,“鉴于目下的情况,强化官治的色彩是当前最必要的,街区村的长给其官僚待遇。”[8]
12月1日,伪满政府发布《街村制度确立基本要纲》,同时以敕令第412号和415号公布《街制》和《村制》,规定各县随着治安的恢复,渐次开始撤销保甲制,向街村制转变。21日,公布《街制村制施行规则》,规定法令即日实施。23日,以敕令公布《市街村自卫法》。
街和村的差别,主要是依人口密度划分,街相当于日本的市,村主要是农村部落,采用以“民族协和”为基调的“大街大村主义”[9]502。法令规定街和村同样都是法人,受官僚的监督,在法令范围内根据公共事务、法令及惯例处理属于街村的事务。街村长由县长任免,受县长、省长和国务总理大臣的监督。在原来满铁附属地的街,以敕令设置指定街,其包括开原、公主岭、本溪湖、苏家屯、海城、大石桥、盖平、熊岳城、瓦房店、郭家店和桥头等。其街政相当于市政,设置咨议会。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只在日本人占多数的地方设置议会或咨议会的特点。但尽管如此,1941年4月1日,指定街制废止,而实际上咨议会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
对于如此的街村制度,日本侵略者竟厚颜无耻地说“除了没有议决机关和理事者不公选外,和我国(日本)的町村制度大同小异。”[10]形成于明治时代中期的日本町村自治制度,经过大正民主时期已经趋于成熟,而议决机关和理事机关公选从一开始就作为町村自治的重要特点而存在,去除这两点,何谈自治可言?
街村制对街村的财政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关于街村的税收,法律规定街村的课税及其他赋课征收。(1)使用费和手续费的征收。街村关于建筑物的使用可以征收使用费,为特殊的个人的事务可以征收手续费,同时可进行罚款等。(2)街村税的种类。支办委任事务和固有事务的费用,以使用费和手续费支付,但在使用费和手续费不足时,街村可以征收街村税及劳役和实物。街税的种类包括门户费、地费、房屋费、杂费。村税有门户费和地费。门户费以街村内构成一户者或未构成一户但经营独立生计者为对象,并斟酌其所得、资产、生计或营业状况等进行赋课。地费以土地面积(房屋宅地除外)及其他为标准,对土地所有者赋课,以谷类交付。房屋费以房屋的租赁价格为标准对房屋所有者进行赋课。所有赋税均设有一定的课税率或课税额,超过这个额度必须得到监督官厅的许可。对于滞纳者可以征收督促手续费和滞纳金。(3)对于劳务和实物的征收在町村收入不足时进行[11]380-383。
其次,规定街村“为了增进街村居民的共同利益,可以形成以收益为目的的财产”。以此为基础产生的费用作为支办町村的经常费,以达到二分之一以上为目的。基本财产除因负债偿还、天灾事变及其他不得已的事由的支出外,为街村的永久利益的支出,除街村民的负担显著增加时外,不得处分[11]380。
再次,街村可以起债,但只限特定的条件: (1)进行应成为永久利益的支出;(2)为了偿还负债;(3)只限于天灾事变等必要情况。街村为了预算内的支出可以临时借款,但必须在其会计年度内偿还[11]385。
最后,规定了街村的预算和决算等制度。街村必须制定预测一年的收入支出的预算书,同时确定街村居民赋税的课率。街村长每会计年度要制定岁入岁出预算,在年度开始前受县长的认可。进行既定预算的追加或更正时要得到县长的认可。街村的会计年度依国家的会计年度。关于预算外支出或充当超过预算的支出可设预备费。预备费不能充当县长否认的经费的支出,充当此外的预算外支出或超过预算外支出,需得到县长认可。但既定预算的追加或更正不在此限。岁入岁出预算分为经常临时二部,岁入岁出预算区分为各款项,附预算说明。预算所定的条款金额不得彼此混淆,但关于各项金额可经县长同意后混用。预算在会计年度后不得追加或更正,必须在其年度内为之。决算是岁入岁出实行的现实计算表,街村长在出纳闭锁后二个月以内制作决算表,向县长报告[11]380-383。
从伪满洲国制定的街村制度的法律条文来看:其把街村视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地方团体,一定程度上赋予街村以财政权利,同时规定实行预算决算制度等,似乎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一方面这些权力受到了上级县长、省长和总理大臣的严格监督,实际上自主性有限;另一方面,日本的町村预算决算是由町村会来决定的,而伪满洲国的街村预算决算由街村长专断,其主要职能仍用于治安,反映了街制和村制,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仍是为了日伪统治便利而设定的,以此攫取作为侵略者的最大权益。
三
由于战争长期化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洲国和日本一样走向战时体制,因此日本侵略者再次加强了对基层街村的控制,对其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1939年6月7日,伪满政府以国务院训令第71号发布《街村育成要纲》,宣布其目的为:(1)“确立对于国民及领土之基本统治组织,以图国家行政之浸透为第一目的。”(2)“排除地方、乡、镇并农村之不合理不明朗之封建榨取政治,基于合理的且明朗之王道自治,以图建设农村为第二目的。”[9]519
其具体的内容:(1)关于街村内部区划,街下分区,村下分屯,区与屯下再组织牌。(2)明确街村区划与警察区域、农事合作社、学区、协和会分会等的关系,尽量使其区域一致。(3)将街村长的选任委托给协和会,将农事合作社村办事处和协和会分会事务局建在街村公所内,建立与协和会等为一体的关系。(4)加强街村在户口调查、教育、土木、劝业、卫生保健、街村自卫、义仓和征税事务等的行政能力。(5)设立街村协议会,“街村协议会以街村内区屯长会充之,然于设有协和会分会与班组织结成之街村内,以分会之常务会充之。”“须经协议会协议之事项,街村之预决算及其他街村行政中与街村民有重大影响之事项。”(6)“为新兴王道国家公吏之精神的训练”,在省地方职员训练所和各县街村吏员训练所进行定期的街村吏员训练。(7)加强县和省对街村财政等的监督[9]519-528。
有关街村财政的内容是:(1)税征收的合理化,防止偷税漏税。主要是做成课税台账、发行纳税告知书和要求纳税人亲自缴纳;(2)确立预算制度,要求将预决算公示于民众。(3)整备岁入岁出之会计,“以明了街村之经理状况”;(4)形成街村的基本财产,实现以其收入支用街村经常费二分之一的目标,为此,努力调查隐匿之“公有财产”。(5)设立街村协议会,街村之预决算由协议会议决等等[9]522-523。
1940年,为了解决地方财政大半依存于国库补助金,缺乏自主性和弹性的问题,以为战时体制服务,12月11日,伪满政府制定了《地方财政确立要纲》,决定自1941年开始实施,三年完成。要纲主要是对国家和地方团体及地方团体之间的负担区分进行再探讨、在调整合理化的同时,积极谋划形成地方团体的基本财产,特别是税制的“合理”改正,增加地方团体的税收。其有关街村的内容有第二条:“积极形成地方团体(特别是县旗市街村)基本财产。(1)随着现在正在实施的地籍整理事业的实行,无主或因其他原因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尽可能地下放给县旗及市街村。(2)其他的国有财产,但是适合成为县旗或市街村的财产的,以有利的方法交给附近的县旗市街村。”[12]
1941年2月3日,伪满政府以国务院训令发布《国民邻保组织确立要纲》,仿照日本国内在市町村下设町内会和部落会的组织,在街村实施“国民邻保组织”,以使国家政策彻底渗透到最基层。在伪满洲国的农村中设屯、牌组织,城市中设班、组组织,以班、屯、牌为“国民邻保组织”,组成“乡民邻保互助生活的协同体。”并要求屯长、牌长、班长、组长“务以协和会员充之”[9]528,明确了邻保组织与协和会的关系。
1943年12月6日,随着战事的日益紧迫,伪满政府进一步要求“政府的施策,快速且正确地浸透到国民中。”[13]为此又制定了《村建设要纲》。其方针是“迅速健全村一级的邻里组织,加强其实践力,以期及时而彻底地完成战时任务。”[9]536在同日发布的《村建设要纲具体要领》中,指出“本要纲的重点在于加强对屯的扶持,使之成为道义农村的基础……作为共同完成战时各项要求的生活共同体”[9]540-541。由此,伪满洲国彻底把战时法西斯统治的触角伸展到村的下级单位屯中。
总结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在中国东北的地方基层实行最严密和残酷的保甲制度。随着抗日斗争的沉寂,伪满洲国的“建设”开始走向正轨,通过制定街制和村制,在中国东北基层实行所谓的街村“自治”。街村制某种程度吸取了日本的町村制度的内容,但是却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不过是保甲制度的变形而已。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了建立法西斯协力体制,同日本国内复活邻保组织一样,在伪满洲国,也设置屯牌班组等,保障日伪的法西斯统治到达地方的最基层。在财政制度上,最初在实行保甲制度时只强行征收保甲费,无街村财政可言。1937年设立街村制度后对街村的财政也进行了具体规定,使街村具有了某种财政和税收的权力,并进行编制预算与决算等。在战时体制下则图谋街村财政的“健全化”,加强对街村的税收监管。纵观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街村税成为中国东北人民最为沉重的负担。以康德四年(1937)为例,该年度的街村税总额为30 402 276圆,岁入合计34 359 130圆,而同年度市县旗收入预算总额为31 166 175圆,二者几乎持平。市县旗税平均1人为96钱,1户相当于5圆85钱,而街村税去除市和其他不属于街村的地区后,其人均额度远远高于此。连日本侵略者也承认:“由此可见街村税对街村民是多大的负担。”[1]20
此外在所有街村课税中土地课税占最大比重。仍以康德四年(1937)为例,其各项税收(见表1)中,土地课税所占比重除间岛省外,基本都占80%左右,安东省最高甚至达到91.8%。
再以康德六年(1939)为例,当年伪满洲国街村财政的主要收入亦是税收入。其中占最多的是土地课税额,占街村税收入的80%左右。此外占第二位的是户别课税,但只约占10%左右。由此可见,街村税是“专门由土地课税和构户税成立的。”[14]10土地课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反映了在其他经济不发达的东北基层社会,中国农民遭受着日本侵略者非同寻常的掠夺和压榨。
第二,从伪满街村税的税种看,采用的是“独立税主义”[1]23,国家和上级团体的“补助费少”[14]10。这一点既不同于伪满省和县市旗等高度依附于国家补助金的状况,也不同于日本町村的附加税主义,成为伪满洲国街村税的重要特点之一。其原因为,一方面由于国家对省县市等“其他的地方财政补助多”[14]10;另一方面是由于税外收入少。仍以康德四年为例,当年街村税总额30 402 276圆,占街村收入总额34 359 130圆中的大宗[1]23。

表1 康德四年(1937)度伪满洲国部分省街村税(包含保甲费)收入预算表(单位:圆)
第三,在街村财政的岁出中,公所费和保甲费占重要比重。康德四年度伪满洲国“街村岁出3 400万圆中,临时部支出只有400万圆,在经常部支出中,公所费明显最多,其额度超过1 000万圆,比例占29%以上。”反映了伪满街村以“国内治安的确保为主要的任务。”[14]16此后占第二位的是教育费,第三位的是保甲费,“性质共同的公所费和保甲费合起来,达到1 700多万圆,约占经常岁出的60%”[14]16。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人民斗争的镇压。只有在奉天省的街和村教育费占第一位,这是因为其经济力比较雄厚的同时,“治安”状态较好。除此而外,劝业费70万圆,卫生费40万圆,社会事业费不足30万圆,福利经费合计不过一百二三十万圆左右。再加上临时部的土木费和建筑费,街村的福利费的支出不过二百五六十万圆[14]16。到1940年,公所费和警察费合起来虽然已经降到约40%,但仍然占街村岁出中最重大的比例(见表2)。

表2 康德七年(1940)度街村一般会计岁出总览(单位:千圆)
[1]岡本泰次.街村税制の概要[J].満洲行政,第六巻第二号.
[2]保甲制度を復活[J].満洲評論,第五巻第十二号:23.
[3]民政部警務司.保甲制度論[M].
[4]満洲国保甲制度の進出[J].満洲評論,第十巻第十号.
[5]満洲国保甲制の進展とその意義[J].満洲評論,第九巻第十一号.
[6]保甲制を全満に实施[J].満洲評論,第九巻第七号.
[7]満洲国史編纂刊行会編.満洲国史各論[M].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昭和46年.
[8]満洲評論,第十三巻第十三号:23.
[9]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M]中华书局,1994.
[10]東次郎.満洲国地方財政の瞥見[J].都市問題,第二十八巻第三号:61.
[11]高橋貞三.満州国行政法(第二分冊)[M].満洲図書株式会社,康徳八年.
[12]満洲地方財政の確立——中央依存の域を脱す——[J].都市問題,第三十二巻第二号:131-132.
[13]高橋正信.地方政治の動態[J].満洲評論,第二十七巻第六号:11.
[14]関口猛夫.街村財政の現状とその諸問題[J].満洲評論,第十六巻第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