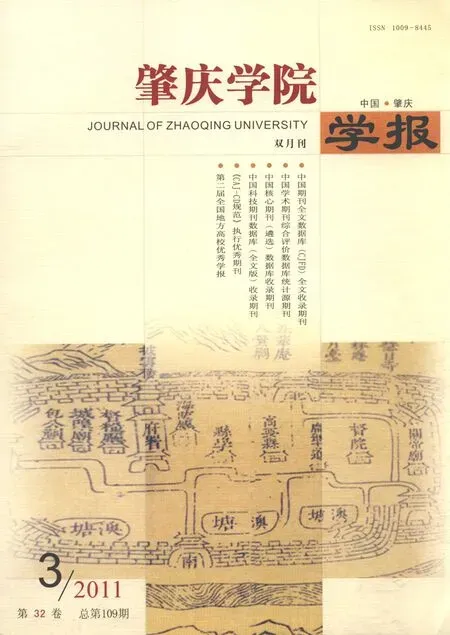河套地区汉墓出土鸮壶述略
2011-01-10谌璐琳
谌璐琳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2)
“河套”一词,最早见于何史籍,今已不详。《明史》有载:“北有大河,自宁县卫东北流经此地,西经旧丰洲西折而东经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经旧东胜卫,又东入山西平虏卫界,地可二千里,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1]近代以来的河套地区,一般泛指黄河“几”字形大回折及其周边流域。
本文讨论内容所涉及的河套地区,仅是指现今内蒙古汉代墓葬考古发现较为集中的巴彦淖尔市的磴口县所辖区域,地理单元上覆盖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山前地带的河套灌区。该地区及周边广大区域,在两汉时期属朔方、五原二郡辖境。
近年来,随着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普遍深入,河套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特别是大量汉代墓葬的发掘,使出土随葬品的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汉墓出土的陶质鸮壶以其独特的形制和专门的用途,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拟以河套地区汉代中小型墓葬出土的鸮壶为对象,对此类随葬品的发现和形制特征、渊源,以及文化内涵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鸮壶在河套地区的发现及其基本特征
据《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以下简称《墓葬》)一书[2]47-113介绍,目前河套地区出土鸮壶的汉代墓葬,均分布在北流黄河以西的河套西北部区域的内蒙古磴口县。据《墓葬》,该区域共发掘汉墓132座,其中,纳林套海45座,包尔陶勒盖25座,沙金套海39座,补隆淖23座。上述4处墓地除补隆淖墓地无鸮壶出土外,其余3处墓地随葬品中共出土鸮壶37件。鸮壶一般一墓1件,个别墓葬有2件者。分别是纳林套海墓地15座墓葬出土15件,包尔陶勒盖墓地9座墓葬出土11件,沙金套海墓地11座墓葬出土11件。另据《墓葬》中的年代分期,纳林套海墓地出土鸮壶的15座墓葬均为西汉晚期;包尔陶勒盖墓地出土鸮壶的9座墓葬中,有6座墓葬及出土的7件鸮壶属于西汉晚期,余下3座墓中的4件鸮壶属于新莽前后;沙金套海墓地出土鸮壶的11座墓葬中,有4座墓葬为西汉晚期,7座墓葬属于西汉末至东汉初。
河套地区出土的鸮壶,形制基本相仿。鸮壶通体呈鸮形,束颈,鼓腹,平底,呈直立型,绝大多数身材矮胖,分由头和身体两部分组成。头部一般浮雕出鸮的眼睛和喙,通常为圆目勾喙,个别有耳。身体部分以刻划和凹凸表现出鸮的翅膀和腿。鸮壶顶部开圆口,口上一般有圆形小盖,上多贴塑三蒂或四蒂纹饰,也有模印或饰其他纹饰者。高度一般在16.9-21厘米之间,绝大多数约为18厘米左右。
以上,河套地区磴口县出土鸮壶的35座墓葬中,有纳林套海15座,包尔陶勒盖6座和沙金套海4座,共25座墓葬年代属西汉晚期;包尔陶勒盖3座和沙金套海7座,共10座墓葬年代属新莽前后。从出土鸮壶的形制来看,属西汉晚期的鸮壶一般只表现喙和勾勒出翅膀的线条,刻划较为简单(图一,3)。而属年代较晚的西汉晚期至新莽前后的鸮壶,大多凹凸有致,轮廓分明,更加逼真,个别甚至刻划出耳朵(图一,4、5)。
综上可见,河套地区汉墓以鸮壶随葬的风俗出现于西汉晚期,流行至新莽至东汉初年以后渐渐消失不见。鸮壶的形制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

图1 各地汉墓出土的鸮壶(俑)
二、鸮壶(俑)的传布与流变
鸮形陶壶在汉墓中的考古发现,并不仅见于内蒙古河套地区,与此类鸮壶相类的鸮形陶俑在河南新乡、山西侯马的汉墓中也有出土。据考古发掘资料,河南新乡五陵村汉墓出土鸮俑30件[3],新乡火电厂出土鸮俑12件[4],共计42件。据发掘者对此两处墓地的墓葬分期,其中15件属于西汉早期,28件属西汉中期。山西侯马市出土鸮俑4件[5],侯马曲村出土7件[6]1059-1063,共计11件,年代均属于西汉中期。此外,据《汉代墓葬出土鸱枭俑(壶)浅析》[7]一文的统计数据,河南西部、山东阳谷、宁夏银川等地的西汉晚期墓葬中也有零星的鸮俑或鸮壶出土。
从目前公布的发掘资料来看,随葬有鸮俑或鸮壶的汉墓在所属地区和年代上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中,以鸮形陶俑随葬年代最早的出现在河南新乡,为西汉早期至中期;其次为山西侯马地区,年代在西汉中期;年代最晚的则是内蒙古河套地区,直到西汉晚期才出现以鸮壶随葬的现象,并延续到东汉早期。据此可以推断,鸮俑及鸮壶的流行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河南逐渐向北呈扇形传播,即由中原地区逐渐向边疆地区流布的过程。
内蒙古磴口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西南部,在西汉属朔方郡辖境,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设置。据史载“(元朔二年)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8]170。可见,在西汉中期,河套地区就已被汉王朝正式纳入版图。其实早在西汉文帝时,就有晁错上《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之事,建议移民实边。于是,终汉之世,在移民实边思想的影响下,边塞移民不断。河套地区自匈奴退出之后,成为汉匈争夺的前哨之地,汉武帝便多次从内地移民充实这一地区。元朔三年(前126年)“三月己亥,晦日有蚀之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8]170,元狩三年(前120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9]1162元狩五年(前118年),武帝又“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8]179,元鼎六年(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9]1173可见仅武帝一朝就陆续有大约150万人迁入河套及周边地区。因此,从武帝开边,匈奴尽数被逐,朔方郡的居民构成应基本为内地迁来屯田、戍边之人。故内蒙古磴口县发掘出土的这批鸮壶的墓葬主人绝大部分应该是由内地迁徙而来的汉人及其后代。这些从内地迁来的汉人,沿袭了汉文化中恶鸮的观念,并将中原地区以鸮壶(俑)随葬的习俗带到了河套地区。
从类型学角度来看,鸮壶(俑)在传布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形态变化过程。从河南新乡、山西侯马和内蒙古磴口县三地汉墓中所出鸮壶(俑)的形制来看,河南新乡和山西侯马汉墓中出土的皆为鸮形实心陶俑,且多体型瘦长(图一,1、2);内蒙古磴口县出土的37件皆为鸮壶,均身材矮胖,腹部稍鼓(图一,3、4、5)。此种随着地域和时代变迁而产生的器形变化,笔者以为可能出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从时间上来看,河南新乡、山西侯马墓葬年代为西汉早期及中期,此时鸮以俑的形制随葬于墓中,且体型较为瘦长,与鸮自然的形象较为相似。以鸮陪葬,利用的除了其古已有之的文化内涵外,大概还因为鸮为夜间活动的动物,随葬于墓中,可以为墓主人在冥间降魔驱邪,以为镇墓之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发掘其实用意义,由于汉墓中的生活用具多以模型化的陶冥器代替,鸮俑也被改进成肥硕的鸮壶,作为盛放粮食的陶仓而存在。西汉建立之初,接手的是暴秦留下的烂摊子,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而至武帝时,又一心开边拓疆,储粮备战备荒被当做治国之本。因此,各地广建粮仓,以粮仓作为冥器陪葬的习俗也应运而生。于是,造型饱满、中空的鸮形陶仓与其他形制的陶仓,就有了较大量的制作与随葬。
第二,从空间上来看,随着鸮壶(俑)由中原传入河套地区,一定会发生一些适应地方环境的变化。如前文所述,西汉中期以后河套地区的人口大多由内地迁去的汉人构成,而迁往国土西陲的百姓身上担负着一项尤为特殊的任务——屯垦戍边。对于处在屯戍状态的边疆地区来说,粮食的储备是维持边境安定和军队需求的最重要的物资,而由中原补给边防的方式,存在运输线过长,物资和时间都耗费严重的问题。而河套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有黄河灌溉之利,有着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汉代移民屯田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在当地种植粮食,以给养边防军队。所以相较于内地,粮食的种植在河套地区人民的生活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作为随葬品的鸮壶自然就承载了这一文化意义,以鸮形陶仓的形态出现。这与鸮作为老鼠的天敌,对保护粮食大有裨益或许不无关系。内蒙古磴口县汉墓出土的鸮壶中多残留有谷黍朽壳[2]94也说明了这一点。
据《墓葬》一书所载,河套地区发掘的东汉初期以后墓葬中,再未见有鸮壶出土,反映了河套地区以鸮壶随葬的习俗在东汉初期开始逐渐消失了。而在河南新乡、山西侯马、山东等地区的鸮壶(俑),则在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就已消失。
三、鸮在先民心中的地位——由神鸟到夭鸟
鸮,即枭,古时又叫“鸱”、“鸱鸺”,俗称“猫头鹰”。鸮形纹饰和鸮形器在我国远古时期就多有发现。自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先民们对鸮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崇拜走向厌恶的过程。
早在新石器时代,鸮的形象就出现于各大考古学文化当中。黄河、长江以及辽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等遗址中都出土了造型各异的鸮形器。例如仰韶文化的陶鸮尊[10],红山文化的玉鸮配饰[11],齐家文化的鸮面陶罐[12]56等,大到鸮尊之类祭器,小到随身配饰,均有体现。可见鸮在原始社会的人们心中已经占据了特殊地位。
到了殷商时期,先民尤其爱鸮重鸮,鸮崇拜盛行于世。史料显示,商人有着浓厚的鸟崇拜传统观念,而鸮正是其主要的崇拜对象之一。有关上古先民对鸮的崇拜,已有多位学者论及。叶舒宪先生认为:“从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证据看,史前宗教艺术集中表现的母体,往往与先民对禽鸟类的崇拜和神话有联系。而鹰与猫头鹰无疑是最普遍和最重要的现象。”[12]51而德国学者汉斯·比德曼也认识到,“在中国,猫头鹰作为厄运之象征……然而在商朝,猫头鹰却是美好的象征,许多出土的青铜容器上都刻有它的图案。”[13]鸮在商代被看作是能通神的灵物,湖南长沙、湖北应城均出土了商代晚期青铜鸮卣[14],河南安阳妇好墓也有大型鸮尊,诸如此类的把祭器制成鸮的形状的做法,就是寄意于鸮来通达神灵。而鸮凌厉凶猛,善于捕猎和飞翔,在远古有辟邪压胜的意义。同时它又是勇健和克敌制胜的象征,在商代素有“战神鸟”之称。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鸮尊,神态端庄,大气雄浑,符合妇好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身份,也更说明了鸮在商代的“战神”意义。
进入西周以后,源远流长的鸮崇拜完全中断,鸮不再为人们所喜爱,而是转化成了凶鸟、恶鸟或不祥之鸟。《诗经·大雅·瞻昂》说“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意思是女子长舌,就像鸱枭(鸮)夜鸣一样,容易招致邦国灾难。《诗经·陈风·墓门》也说“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15]把鸮与墓地联系在一起,可见它在当时确有不祥之意。
汉代人对鸮尤为忌讳,人皆以之为恶并且赋予其“不孝鸟”“贪鸟”“祸鸟”的涵义。“百善孝为先”,而汉代尤重孝道,讲求“以孝治天下”。在汉代,鸮被认为有“食母”的习性,因而被看做是凶残不孝、忘恩负义、大逆不道的“不孝鸟”。东汉许慎首先给鸮冠以恶名,他在《说文解字》中说“枭,不孝鸟也。”北齐刘昼(一说梁刘勰)撰《刘子》曰:“枭,伛伏其子百日而长,羽翼既成食母而飞。”[16]除了不孝之外,鸮在汉人心中还有贪婪、品行低下的特点。汉朱穆 《与刘伯宗绝交诗》说“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览,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17]葛洪亦撰《抱朴子》曰“梧禽不与鸱枭同枝,麟虞不与豺狼连群,清源不与浊潦混流,仁明不与凶暗同处。”[18]表示鸮心性不洁,即贪且腐。又,汉人以鸮为“夭鸟”,以见其形或者闻其声为不祥。西汉刘向《说苑·说丛》篇有寓言一则,曰:“枭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19]足见鸮在汉人心中是人性卑俗、丑恶的象征,是灾祸的征兆。
四、汉代以鸮壶陪葬之内涵
如前文所言,既然鸮在汉代人们心目中形象如此不堪,那么汉代又为何将其作为随葬品与墓主人共眠呢?目前,大多学者认为以鸮陪葬是出于古人的迷信,也有学者认为随葬鸮与“祛禳”观念有关[6]1042,还有学者指出鸮有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作用。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鸮形器的随葬存在于从西汉早期至东汉初期的汉墓中,且基本以俑、壶的形式出现,多为单数。笔者认为,汉人以鸮壶(俑)陪葬,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首先,上文已论述鸮作为不孝之鸟在汉代为人民所深恶痛绝。《太平广记》记载“汉书曰: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鸮炙及枭羹,盖欲灭其族类也。”[20]可以推论,以鸮陪葬就如同制作“鸮炙”,是欲灭其族绝其类的体现,使其不再给人们带来不祥和灾祸,也暗合了汉人尤奉行孝道这一时代特征。
其次,被殷商奉为神灵的鸮虽然在汉代遭到了鄙弃,但它辟邪镇墓的意义依然存在。鸮外形丑陋,性情凶猛,昼伏夜出,习性奇特,故而给人以神秘之感。《诗经·豳风·鸱鸮》言“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有学者分析此诗“所言鸱鸮具有取人生命和毁人房室的超自然能力,似乎不是指自然界的世俗之鸟,应该属于神灵世界中的重要一员。……从‘今女下民’这样的措辞方式判断,它显然是上界或者天界之神灵的口吻,不会是一只普通的母鸟所说出的话。”[21]所以,鸮 “是神圣女神的重要化身——兼司死亡与再生的命运之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司命之神地位很高,人们对其相当崇拜,鸮既然是具有超能力的司命之神,自然能镇压一切邪恶;另一方面,鸮作为生命之神,有能给予人新生的神秘力量,以其陪葬大概也表明了先民消除灾难,开始新生活的美好愿望。
再者,我国古人丧葬文化中历来有“事死如生”的传统,他们相信人死后生命以灵魂的形式在阴间得到延续,养生和送死同等重要。故《荀子·礼论》有“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22]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以死者生前用具作为随葬品的习俗。河套地区发掘的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后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丰富的陶灶、陶仓、陶井、陶圈厕、陶鸡、陶猪、陶狗等生活实用器。可见,汉代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在河套地区也深入人心。《史记·武帝本纪》引如淳注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23]《太平广记》卷第四六二《禽鸟三》也称其“其肉美,堪为炙。故庄子云:‘见弹思鸮炙。’又云古人重鸮炙,尚肥美也。”[20]故汉墓中以鸮随葬,或许也有为墓主人的灵魂提供食物的用意。
西汉晚期以后,鸮壶逐渐取代鸮俑随葬于墓中,除了镇墓、辟邪功用之外,其实用性较西汉早期增强。内蒙古磴口县沙金套海墓葬发掘出土的鸮壶其腹内多残留有谷黍朽壳[2]94,同时出土的还有各式各样的陶仓。这都表明,盛有黍的鸮壶蕴含着人们对逝者在地下也能有食之不尽的粮食的希冀,寄托了人民“仓廪丰实”的美好愿望。
从远古时期源远流长的鸮崇拜在广博的华夏大地上流传数千载,在商周以后则完全中断了。其后,鸮形器物和图案在汉代又重新广泛出现,而河套地区汉墓出土的鸮壶就是这一文化现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数十只造型各异的鸮壶,不仅向我们诉说了鸮的文化内涵,更让我们透过器物,看到了时代与地域赋予它的独特意义。
[1] 张廷玉.明史:第四册卷四十二·地理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 新乡市博物馆.河南新乡五陵村战国两汉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0(1):103-135.
[4] 新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95年新乡火电厂汉墓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1997(4):15-26.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东周、两汉墓[J].文物季刊,1994(2):29-48.
[6]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7] 张抒.汉代墓葬出土鸱枭俑(壶)浅析[J].考古与文物,2010(2):86-89.
[8] 班固.汉书:第一册卷六·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9] 班固.汉书:第三册卷二四·食货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 倪建林.传统青铜艺术冶铸文明[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
[11]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地发现[J].文物,1984(6):1-5.
[12] 叶舒宪.神话意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3] 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辞典[M].刘玉红,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214.
[14] 余家海.应城县出土商代鸮卣[J].江汉考古,1986(1):94.
[15] 方玉润.诗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6] 刘昼.刘子[M].袁孝政,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 吕晴飞.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31.
[18] 葛洪.抱朴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9] 刘向.说苑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0] 李昉.太平广记:第十二册卷四六二·禽鸟三[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
[21] 叶舒宪.经典的误读与知识考古——以《诗经·鸱鸮》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4):56-64.
[22] 荀子.荀子[M].安小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23] 司马迁.史记:第一册卷一·武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