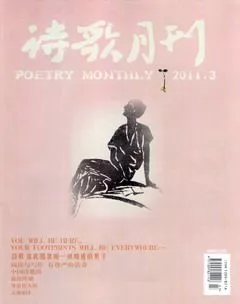在虚无中冒雨赶路
2011-01-01洛盏
诗歌月刊 2011年3期
主持人语:
从上个世纪末以来似乎中国诗歌批评界一直都不缺乏争论甚至争吵,以及各种极富想象力的炒作和包装。作为批评者身份的“知识分子”似乎被僵化的“学院派”和利比多过剩的 “伪民间派”所遮蔽和几近消弭。更多的评论文章专注于所谓的“多元化”、“个人化”、“叙事性”的诗歌话语方式,众多的发言者们也在众多的诗学名词和空间中说着看似有理实则空洞无物、无效的呓语。而真正意义上具有针对性、问题性的对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传统、现状、精神向度以及写作向度等诸多诗学问题予以关注、反思和讨论的文章却少得可怜。当下的中国汉语诗歌写作者和批评者是需要静下心来潜入诗歌和诗学内核的时候了!请为你们后社会主义时代不断提速的欲望踩下刹车。“在虚无中冒雨赶路”是否可以多向度地理解为是现代诗人的生存命运、诗歌困境、语言难题、精神向度和文学场域的寓言性警语?
——霍俊明
E_mail:hongshailibai@sina.com
写作本文的前些天,由于网络的崩溃,居于贵州一隅的我经历了长时间信息的真空,直到今天网络恢复,才得知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花落德国女诗人赫塔·缪勒,并从“诗生活”王家新的文章中看到了原版授奖辞,大致是说她的作品具备了“theconcentrationofpoetryandthefranknessofprose”,描绘了“thelandscapeofthedispossessed.”王家新敏锐地感受到了“dispossessed”这个词的尖锐和分量,并“恢复了对老诺的信心”。Dispossessed,这个生存意义上的“被剥夺者、被驱逐者”,却被中新社首发的消息中,降格为生活意义上的“失业人群”,着实让人忍俊不禁。媒体的暧昧彰显着时代的复杂,历史由于“不怎么幸运”的变故又一次显得暧昧不明时,诗者须站出来申明自身,这种申明并非决裂,而是一种“反向的切中”,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
必须提及的是,对于现代诗歌写作的精神向度问题的强调,本应该属于不需强调的“废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却必须要重提,成为我们写作的良心绕不开的话题,也再次凸显了时代的复杂性。再者,本文属于一份笔者个人的回顾和反思,期待着同行的诘问与修正。此外,本文例证时,所关注的是中国当代较为“成熟”的诗人,是目前最先锋也是最具有现代性的诗人,正是他们的努力有望最初建立传统,“使得中国先锋派们有一个可靠的起点以及一个连续成长的营养库,避免反复开机,避免常识性错误”(引自桑克《当代诗歌的先锋性:从肆无忌惮的破坏到惊心动魄的细致》,《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4卷第4期)。
一 精神向度:“向下的超越”
笔者认为精神向度和写作向度是诗者最基本的两种向度,前者在“对现实世界的接近或疏远”的地方移动,后者则在“对语言本身的依赖或怀疑”之间摇摆不定。而自1985年先锋诗歌运动以来,现代诗歌有两项基本成果:一是集体顺役的权力话语的破产,“国家庆典终于失去了一副嗓子/她太艺术,太壮硕、又太爱吃醋,/她本质的阴冷的器官,/冻结我的活力和创造性。”(陈东东《炼狱故事》)二是对于语言的关注,语言不再是“中心思想”的喉舌,而一定程度上成为诗歌本体存在的依据。但权力仍然是权力,而且“它的机器更加高效率,已经深入生活的隐私部分”(孙文波《续节目单》)。当时代的意识形态势能和一种物质主义宣传亲和结盟时,权力与日常消费主义美学之间暧昧不清且相互置换,形成“擦去隐痛,回避质询,快乐逍遥”的主流价值漩涡。这个漩涡如同变形金刚里的大力神,吸收着一切可以吸收的东西——包括诗歌。因此,上文提及的两项成果,很有可能“可叹地由诗学向度的系统转换衰退为系统因子的微调”,缺乏生命灵魂疼痛和更高意义上的离心冲突(或曰“弃家”)的再铸乌托邦、以及低劣的神性写作、乡土写作等等,最终都被吸纳为权力的淘气的同道。
那些草莓似乎在晃动的小桶中
也能继续它们的睡眠
它们的睡眠是关于我们的口味的。
它们的梦想,如果有
则涉及我们怎样为新的生态信仰
而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
——臧棣《采草莓》
在市场偶像、娱乐工业取代了一切的今天,置身于社会这只漂亮的、美学的、不再暴力的、晃动的“小桶”中,我们和社会的关系似乎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于是自弃为娇滴滴的草莓,做着翩然的美梦——“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的个人生存正是一个人自弃的生活”(耿占春《一场诗学和社会学的内心争论》)。万众挥舞的荧光棒厘定着我们的“信仰”,中央三套的星光大道言说着我们的“梦想”,“它们的睡眠”一再符合判决者的“口味”,被判决者和判决者达成一种致命的共谋。即便出现了诗人之类的“异端”,判决者们会机巧地“为新的生态信仰,而改变饮食习惯”,不费力地实现对诗人们的“招安”(以文联、权力选本等形式)。诗人们“被安排在金鸟笼里,/绿翅膀收拾得更绿,/更符合一个观赏禽类的荣誉和身份”(陈东东《炼狱故事》),从而使“自己的名字划归到安全一栏”。市场时代的意识形态技术娴熟地将这种自弃描述为唯一去享受的生活,让我们沉浸于其间继续我们的睡眠。
有人会反对,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不是最难以被强暴的权力所利用的东西么?没错,但如学者、诗人陈超所言,难以利用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关痛痒的个人迷醉书和乌托邦,权力主义者可以放心忽略掉,这也是上文所指涉的“诗人”;另一种则是锐利而广阔的对生存的衡估与揭示,准确而奋不顾身地切中这个时代。这种诗歌的重要性不在于单向的挑衅和叛离,而在于整体包容地去创造新的精神话语历史。优秀的,或者说合格的诗人,无不广泛地重新占有词语的命名权,而非向权力和庸众妥协;在将自己放逐到社会常轨以外的同时,以身受难,准确而有力地反向切中社会的“噬心主题”,实现个体生命对整体生存包容的个人主体性。“我坐在沙发上/有站在拳击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