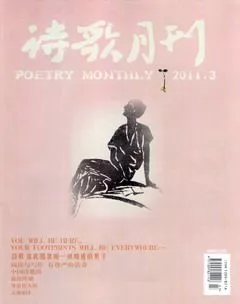那一片冲破暗夜的霞光
2011-01-01沈奇
诗歌月刊 2011年3期
沈奇(1951-) 男,汉族,陕西勉县人。1981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现为西安财经学院文艺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迄今已出版诗集《沈奇诗选》(2010·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版)、《寻找那只奇异的鸟》(2001·台北·尔雅版),诗学文集《沈奇诗学论集》三卷(200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版),诗评论集《台湾诗人散论》(1996·台北·尔雅版)、《谁永远居住在诗歌的体内——两岸论诗》(2008·台北·唐山版),文艺评论集《文本与肉身》(2007·西安·太白文艺版)等12种;编选《西方诗论精华》、《台湾诗论精华》、《现代小诗三百首》等8种。在海内外发表诗歌评论及文艺评论文章100余篇。诗论及诗歌作品入选数十种选本及年鉴,部分被译为英、日、德、瑞典、丹麦、拉脱维亚等多国文字。
读书是生命的“初稿”,这“初稿”不一定切合实际,但却常常会影响到此后人生展开的方向。我从小喜欢梦想,脚下的日子太泥泞,便总是要仰起头来想象理想中的一切,而这想象的源头,多来自于读书所得。
2008年四川汶川“5·12”大地震那天下午,西安受波及也震了一下,我刚好给中文班同学上“诗歌欣赏”课。组织学生撤出教室后,在全校都自行停课的情况下,我动员同学们围坐在操场草坪上继续上课。讲课中我给大家背诵了普希金的几首诗,并告知这是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时读到的,同学很惊讶我这么多年了还能如此熟记,且背诵得那样痴情,实不知这些诗歌在我生命的“初稿”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1971年春天,二十岁的我终于告别知青生活招工到陕西汉中地区钢铁厂当高炉炼铁工,没高兴几天就发现实在只是由“水深”转为“火热”:不到九十斤重的小身板要干重体力活,长期神经衰弱却偏得上三班倒的班,工友和家里父母都担心我熬不下去。其实吃苦再多都能扛住,下乡三年比这苦的日子都过来了,毕竟青春年少,关键是精神苦闷。时值“文革”后期,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都一片渺茫,更看不到情感的归宿在哪里——全厂上千号人,未婚青年女职工不到二十分之一,像星星在天上挂着,望一眼都难!再就是没书看。手中常保存的两本书,一本《古代散文选》上册,一本《唐宋名家词选》,都读过好几遍了,还抄写了不少,并仿照着写了一些旧体诗词,算是最早的诗歌写作练习。但毕竟是现代汉语造就下的青年人,老看古典作品写旧体诗,总觉着还是与当下的生命体验隔了一层。
记得大概是1973年夏天,在一位同样是知青的工友那里看到一本翻得稀烂的《普希金抒情诗集》,连封面都没有,说半天好话,答应借我看三天,因他也是借外厂朋友的。拿回宿舍细读之下,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的那种感觉,兴奋得像终于见着了梦中情人一样。匆匆一遍翻完,看还有时间,便找了一个本子狂抄起来:《致大海》、《致恰尔达耶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给娜塔莎》、《致凯恩》、《我多么羡慕你》……三天后还了书,人却整个被普希金的诗歌所淹没又被高举了起来——这位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高尔基称之为“一切开端的开端”的普希金,真的在一个无望于暗夜时代中的中国青年心里,成了精神之父和灵魂的太阳,并成为我日后走上诗人和诗评家道路的“一切开端的开端”。
自从有了那半本子手抄的普希金的诗,此后的钢厂单身生活中,再没有那么孤寒,心中像揣着一团野火似的,燃烧着初生的诗性生命意识。现实生活中遇到什么苦闷的事或情绪低落时,便独自跑到离工厂不远的一条小河边,大声背诵普希金的诗,过后心情就好许多。有时也会更伤感,譬如背诵到《我多么羡慕你》一诗的最后几行:“让我们一起离开这颓旧的、欧罗巴的海岸 / 去漫游于遥远的天空、遥远的地方 / 我也在地面住厌了,渴求另一种自然 / 让我跨进你的领域吧——自由的海洋!”常常会泪流满面,不过过后却又有一种被洗礼后的坚强和自信,复生于困顿的岁月年华。
慢慢的,普希金的诗在年轻的心底里扎下了根,化成了我精神生命的一部分,随之并渐渐有了“仿写”的欲望,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写作的摸索。当然写成之后大部分都是自我偷偷欣赏,也不敢拿出去和人交流,有时遇到知己的朋友,才敢让对方看一下,随后赶紧又藏起来。不过说老实话,这个时期的作品尽管不乏真情实感,但语言形式上只能是普希金中文版的仿写,还没有自己的风格。“文革”结束后,我于1978年考上大学离开工厂,这些作品先后都发表了。其中有一首写于1975年秋的《红叶》,还发表在当时最具影响的《诗刊》1979年12期上,让与我同班的大学同学、后来也成了诗人的丁当很是羡慕了好一阵子。
当然,许多年后,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我也逐渐摆脱了普希金在我早年的写作中,那种笼罩性的影响,找到并渐次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语言形态和精神形态,但作为精神之父的“普希金”,却一直没离开过我,有如冲破暗夜的第一抹霞光,永久珍藏在生命初稿的记忆中。即或是作为诗歌艺术的启蒙人“普希金”,也在我后来的创作中时时“霞光返照”,遇到合适的题材,就不妨来一次“模仿秀”,既过一把怀旧式的、浪漫主义的瘾,也向诗歌界展示一下个人创作风格的多面。2007年秋天偶尔得来的一首《永生——致缪斯和她的女儿》,便是这样的一首旧式风格之作,没想到在“诗生活”网站贴出后,成为我的作品中点击率最高的一首诗,并入选当年的一部年度诗选。看来即或在“后现代”之后,浪漫依然是永远的诱惑,而普希金还是不朽的普希金。
行文至此,不妨将这首源自早年读抄《普希金抒情诗集》“遗传”的小诗附录于后,也就此做了这篇读书故事的结尾吧——
虚构一生的荣誉
被一只手 一只
小小的纤手 轻轻
轻轻 抹去……
抹去纹饰 让玉
回到月光与花的呼吸
抹去油漆 让木头
重返青枝绿叶的节日
再从暮色中打捞出
晨辉 烂漫的气息
没有云的日子里 也能
在自己的心里悄悄下雨
或者下一场大雪
静静地埋葬了过去
死去 又活过来
活在只为爱活着的第五季
呵,此后的日子里
我 只握住这只手
用她熨平 岁月的苦痕
好好接纳 阳光和水滴
然后,在最后的憔悴里
让生命 复归一张白纸
写一首 再也不必重复的
小小的情诗 陪你老去……
2010-12-24于西安印若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