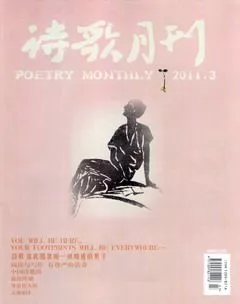诗人们寄养在马莉的画
2011-01-01夏榆
诗歌月刊 2011年3期
在我们时代,诗人由于被市场社会放逐而成为一种国家污点。他们像吉普赛人一样,流浪于时代之荒野,独立于争先恐后要“先富起来”的人群。马莉看到诗人在此时代中的真正面目:在时代的深处,诗人像五百罗汉那样安贫乐道,持着灯,继续亘古事业。
——于坚
马莉养大了一个孩子/还养大了一群肖像画/诗人们寄养在马莉的画中/得到了永生
——吴祚来
马莉对自己的画作以“业余”自居。马莉首先是南方周末高级编辑,同时还是一位诗人。
2009年春天,马莉在完成了包括女性与神性组画和抽象系列画之后,开始诗人肖像的创作。最先画的是诗人梁小斌——诗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作者。“他是我敬重的诗人,也是我信赖的朋友,如果我画得不像他肯定不会骂我。”马莉说。
从这幅肖像开始,马莉一个个地画开去,艾青、牛汉、北岛、芒克、江河、食指、顾城……“她恐怕不晓得‘业余画家’这句话是十分骄傲的。”陈丹青说,“欧洲现代主义初起,毕卡比亚之流公然宣称自己是业余画家,画也果然画得半生不熟,毫无羁绊——他的腻友和同志,可都是达达团伙的悍将,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杜尚……画画而无以自拔,可就不是画得好坏,而是进入情况了。弄艺术,顶要紧就是进入情况。什么情况呢?请看马莉同志的画。”
2011年1月7日,《触·马莉当代中国诗人肖像画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门口海报上的口号是:遇见画中人。画中人西川、芒克、梁小斌纷纷到场。这是一个典型的跨界美术展,到场的除了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还有作家张抗抗、麦家,艺术家刘索拉,诗人、出版人岳建一等。
刘索拉自称自己不懂画,无权评价作品,她只是强调自己观赏画作时的直觉:“马莉把诗人表现得特别轻松,特别亮,特别明朗,具有装饰性,特别好玩儿。”她对赶来看画展的诗人们说:“你们诗人能在她笔下出现是荣幸的。”
诗人这群兄弟姐妹
头发花白的诗人芒克在展厅逐一看着那些悬挂起来的诗人肖像。
《诗人芒克》是马莉画的一幅42×56cm的油画,画中的芒克围着绿色围巾,黑衣,灰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睛,芒克看着画中的自己说:“很像。”因为喜欢这幅肖像,芒克把它印在了自己在宋庄画展的请柬上。
在人声鼎沸的展厅里,芒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诗人都是我的朋友,神态极像,每幅画都有特点,技法独特,神态别致,能画出这么多诗人的肖像,马莉是头一个。”
在《触·马莉当代中国诗人肖像画展》展厅里,一个个诗人被挂在墙上:食指面色沉郁闭目沉思,手指间是一支燃烧的香烟;杨炼的头颅如破土而出的蘑菇,肩膀长出的根须和斜披的长发长在一起;艾青的耳朵里长出缀花的植物;牛汉的双颊长出虎须;舒婷被画成植物……这是一个以八十年代诗人为主体的诗人画展,也是一个被抽象和变形了的诗人群像。
西川在展厅里走了一圈,看到自己的肖像:纷乱的披垂的长发,黑框眼镜后冷视的眼睛,挺直拉长的鼻子,嘴边黑色的胡须,他觉得“画得很准”:“中国的诗人在中国的今天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这些人自1970年代末走过来,他们和别的文学家不同,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时代里,诗人简直就像一群兄弟姐妹。马莉把这样一群兄弟姐妹画下来让人觉得非常温暖。”
1985年5月,《诗刊》举办首届全国青年未名诗人笔会,马莉作为广东青年诗人参加。笔会结束前一天,青年未名诗人被安排与在京的著名诗人面对面交流,这些著名诗人包括艾青、绿原、牛汉、流沙河。交流会在京西宾馆,马莉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诗刊社》小红皮笔记本,请老诗人签名。艾青的签名是:祝马莉小朋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艾青1985年5月11日。
“有一个人坐在靠窗的圆桌上,默默地看着现场,他看的不是签名的人群,而是一个很深很远的地方。我马上认出,他是顾城!我走过去把小红皮笔记本打开请他签名,他接过来向前翻了几页,没有表情,用很低的声音问我:‘有没有一张白纸?’他在一张纯净的白纸上写下‘顾城’两个字。”马莉回忆着“小朋友”年代。
后来朗诵会开始,顾城也被请上台来,他没有拿手稿,站得很直,一动不动,声音像日常生活一样平铺直叙,没有抑扬顿挫,眼睛向上挑战着自己的眉毛,仿佛眼睛和眉毛势不两立。“我记不得他是朗诵还是发言,只记得他说的内容简短、优美、锐利,像他本人。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还是没有表情,即使我们这些笔会的诗人为他使劲鼓掌。”马莉回忆道。
1993年10月9日,顾城杀妻自缢。2009年,顾城辞世16年后,马莉为他画了一幅50×40cm的布面油画肖像。马莉用线条和色彩画出了顾城留给她的记忆。“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朦胧诗人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他诗歌血液的至纯与怪诞无法不让人迷恋。”马莉回忆说。“马莉画的诗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在诗人的公共形象开始消散,或被解构、自我解构的时候,现在以如此之多的肖像画集中地展示,通过对当代——三代或四代诗人的肖像绘画,让我们在看到诗人肖像的同时也看到诗歌自身的处境,诗人内在的精神和内心的世界。”唐晓渡说,马莉的画是对诗人这个群体的穿刺。
养大了孩子也养大了一群肖像画
马莉自己也是诗人,她形容诗歌和绘画就像她的姐妹:“我一手牵着一个,来去自如。”她开始绘画是1989年夏天,她把两岁的儿子从北京奶奶家接回来,一边带孩子,一边自修西方美术史,还经常跑到附近的广州美院听课。
“有一天,孩子睡觉的时候我给他缝小衣服的扣子,缝好后,我想弄点图案在小衣服上面。就用我的派克笔在孩子的小上衣背后画来画去,发现很好玩,画好之后晾干给孩子穿上,孩子很快乐地拍着小手,于是我就把孩子的每一件小衣服找出来,可以画的我都画了。”马莉不仅画完了孩子的小衣服,还有她自己的衣裳和裙子,桌布、窗帘、碟子、白瓷片,甚至汤匙的木把手……后来老公单位的同事知道她画画,就送给她很多白色铜版纸。
早期的绘画没有主题,主要是线条和色块,下笔的时候没有想,只是凭直觉,一笔跟着一笔来画,有时候随笔涂几下,发现这里面有看见的某个物象,就把那个物象画出来,这些画被马莉挂在家中的客厅里、卧室里、走廊上。
一次,马莉牵着儿子去广州美院“105画室”看画展,遇见了广州艺术家画廊的艺术总监陈小丹,她看见马莉儿子穿的小T恤背后画着好看的画,好奇地问:“这小衣服上的画是你画的吗?太棒了!”马莉告诉她还画有好多,都挂在家里的墙壁上。陈小丹兴冲冲地去马莉家看画,当即拍板要赞助马莉办一个画展。1991年春天,马莉举办了她的第一次画展。
这次画展引起媒体关注,画展结束后,马莉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被调到南方周末。进入南方周末做副刊编辑之前,马莉的工作是在一家报纸编“当代旧体诗”。
“198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刚刚影响全国,给人们带来的是思想的解禁和生活的开放,唱歌跳舞,阅读外国文学,带着理想主义的余热,带着新生活的祈盼。”马莉说,但当时的诗坛相当保守,她被认为是“现代派”的异端。加盟南方周末对马莉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她不再是“异端”。
2009年前,马莉一直在画抽象作品。
一次朋友聚会,有人说马莉的老公长得很像蒋介石,马莉回家就给老公画了一个速写,“往蒋介石方向靠”。拿给朋友看了,大家都觉得很像,有人说画成油画更好。
2009年春节,报社发了台历,马莉就在台历背面画,画得非常顺手,三天时间涂色,画完了贴在博客里,朋友又来表扬,她很得意,又画了一幅自己的肖像。“有人看了说像莫迪里尼阿的风格,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上网查了一下,好像真的很棒,我就稍微关注起来。”马莉就这样一步步开始了人物油画系列。
画人物肖像她怕侵犯肖像权,想到跟梁小斌关系非常好,自己第一次诗歌获奖也是他写的颁奖词,就用台历的硬纸壳画了梁小斌,依旧受到鼓励。
北岛、芒克……就这样一个个画下去,也不知道自己笔的顺序对不对。画多多时她第一次买了画布,从纸面油画转向了布面油画。画布越来越大,就去买了大的画框。
开幕式后的《诗人的艺术形象与公共形象》研讨会由艺术批评家李公明主持,如何看待艺术创作中的非专业性是研讨会的一个议题。
栗宪庭第一个发言:“这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受西方的影响,要把形画得很准,把结构画得很准,往往要训练一二十年才可以,这带来一个坏处,就是为了脸上的某个结构的准确性,把神态也破坏掉了,这是这么多年所有专业画家都感觉困惑的。”
“业余”也是栗宪庭认为颇为珍贵的:“现代艺术的出现,就是对文艺复兴时代艺术非常烦难的技巧的一种抛弃。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很多业余作者,就是不再受技术的束缚,其实中国过去的诗歌、画坛、书法,很多杰出作品的创作者都不是专业的,作者基本都是官僚,官僚的主业是做官。很多年我突然明白,中国古代诗人讲过一句话,就是功夫在诗外,就是要做人,而不仅仅是要做诗,他首先是个人,而不是职业的诗人,或职业的作家。”
马莉准备到2017年——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的作者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00年的时候,画够100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