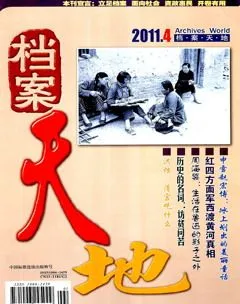新中国驻外大使夫妇的奇趣婚姻
2011-01-01王乐飞
档案天地 2011年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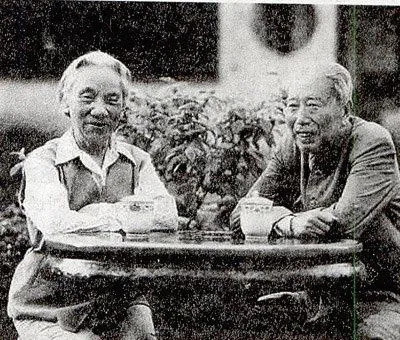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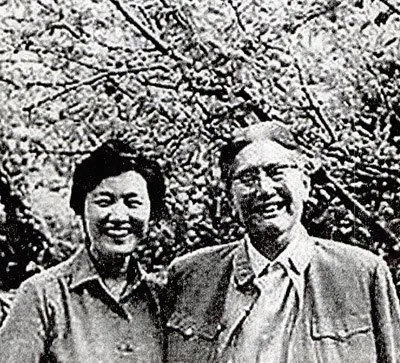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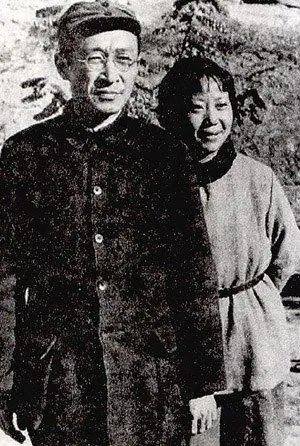
一、乔冠华归龚澎领导
乔冠华和龚澎是中国外交战线上著名的伉俪外交家。
1939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宣传组成立,周恩来的新闻秘书龚澎成了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在外国记者中,龚澎是很受欢迎的。因此,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青睐。事实上。龚澎和外国记者们很友好地合作,并没有个人感情掺杂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
1942年岁末,命运之神把乔冠华从千里之外牵到了龚澎身旁。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对乔冠华说:“我要为你引荐外事组的几位同事。”几分钟之后,门口出现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位干练的年轻女士,瘦高苗条的身材,一头浓黑的头发随意盘起。当看见新来的战友时,她爽朗地笑起来,深邃的眼睛里闪动着真诚和快乐:你好,欢迎你!
周恩来对乔冠华说,这位就是龚澎同志。
因为是同事,乔冠华和龚澎有大量的时间接触。不久,他们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的经历与共同的话题,还有共同的爱好和品味。一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渐渐心心相印。
一天,周恩来急了:“唉,你们到底准备拖到什么时候?”乔冠华局促地掏口袋摸烟。他一看周恩来的桌上放了一块“请勿吸烟”的小牌子,便将掏烟的手垂了下来。龚澎看在眼里,对周恩来说:“我从小说里看的,人家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你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看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说的?”周恩来望着乔冠华,拿着禁烟的小牌子,哈哈大笑:“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
1943年深秋,乔冠华和龚澎结婚了。曾家岩50号三楼右侧第一间屋子是他们的新房。两个人的被子叠放在一起就成了一家人。
相对乔冠华来说,龚澎更理性,政治上更成熟,她善于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乔冠华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为人处事质朴耿直。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像一艘向着灯塔行驶的船。一个划桨,一个掌舵。因此,同行们把他们称为“绝配”。
新中国成立后,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乔冠华负责亚洲司和国际新闻局的工作。他们双双成为外交部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1954年4月,乔冠华和龚澎跟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
每次会议结束后,龚澎都要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对各种问题她总是能够对答如流。对于一些恶意刁难,她也能出色地进行驳斥。后来一些西方记者攻击另一些称赞龚澎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的记者时,说他们是被女发言人的美貌所迷惑。还有记者追问龚澎一些私人问题,媒体还登出一些花边新闻。新闻组的同志给翻译出来,有些不便译成文字的,就口头讲给龚澎听。龚澎听后哈哈大笑,对此,她一直抱着宽容豁达的态度。
龚澎是全家的主心骨,也是乔冠华的主心骨。乔冠华是个心里有事存不住的人,他遇到问题总要和龚澎商量,特别是在大的决策上。有老同志半开玩笑地说:乔冠华归龚澎领导。
或许正因为他们两人不相上下,龚澎就更加注意维护乔冠华的自尊,经常“调试”比翼双飞的距离。1950年代初,组织部门曾准备提升龚澎担任部长助理,龚澎得知这个安排后找到了周恩来。她诚恳地说:“老乔比我更合适。如果是在我们两人中间选一人,请组织上还是先考虑他吧!”周恩来笑了。龚澎说:“在家里,老乔是一家之主。”
夫妻有很多类型,乔冠华和龚澎是平等互补型的。他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开会、一起出国。很多时候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70年初,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去乔冠华家里送一个特急件。本来这文件是由龚澎负责的。可等候在家里的不是龚澎而是乔冠华。乔冠华对通讯员说:“龚澎不太舒服,已经睡了,我来批吧。”他接过文件瞟了一眼,说:“这个事情我清楚。”他用铅笔画了一个圈,认真地写上了“乔冠华”三个字。
在家里,乔冠华称呼龚澎“达令”。女儿乔松都一直认为这是母亲的小名。和“小石头”、“小三子”一样平常。直到有一次听到母亲也叫父亲“达令”,她感到十分好奇。龚澎不动声色地解释道:“那也是你爸爸的小名啊,在家里两个人用一个名字方便,省得浪费时间。”她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两人之间使用。”女儿对龚澎的说法深信不疑。后来,她在《新英汉词典》上终于看到了“真相”:Darling原来是“亲爱的”。
“文革”中,一个造反派将龚澎的照片翻出来,举到乔冠华面前:“说!这个人是谁?”乔冠华认真地端详着照片,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的妻子龚澎。”造反派大声训斥说:“她是不是三反分子龚澎?”乔冠华像纠正学生发音似的,一板一眼地说:“她是我的妻子龚澎。”造反派厉声说:“你说!这是三反分子龚澎!”乔冠华不紧不慢地再次纠正说:“这是我的妻子龚澎!”
1968年初,龚澎恢复工作,在东交民巷8号院的主楼内上班,当时半天上班。半天搞运动。在这里,龚澎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龚澎的身上有一种坚韧不拔的东西。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镇定自若。
在脑溢血的病情稍稳定后,龚澎试图和乔冠华谈谈他今后的生活选择和安排。可是龚澎刚刚张口,乔冠华就泪流满面。几乎不能自制:“达令!达令!不要说了!”乔冠华大声哽咽着,“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
1969年岁末,龚澎对儿子说;“你爸爸是一个非常正直、对革命充满热情的人。但他没有经过党内复杂的斗争,在变幻的风云中,把握不住分寸。‘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我用身体挡住枪弹来保护你爸爸,以后你要多照顾他。”
1970年4月10日。龚澎脑血管再次出血,不得不接受开颅手术。
得知消息后,周恩来到医院探望龚澎。见到周恩来,乔冠华就像孩子见到家长一样,靠在床栏上大声痛哭:“龚澎不行了!我实在受不了!”
周恩来心情沉痛地走到乔冠华身边,镇定地对他说:“冠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坚强一些!还有孩子们在这里呢!”
1970年9月20日,龚澎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龚澎去世后,乔冠华一直非常哀伤,身体也大不如前。1983年,在龚澎去世13年后,乔冠华也离开了人世。
二、王稼祥的身体主要靠朱仲丽
王稼祥与朱仲丽的相识纯属偶然。1938年11月,中共六中全会闭幕那天的会餐结束后,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慢步走出餐厅,迎面走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毛泽东在和她热情地打招呼后。转身对王稼祥说:“稼祥同志。来,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同志,她是我们的保健医生,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都归她管,你以后也要同她打交道的。”毛泽东幽默的介绍,把王稼祥和朱仲丽都逗乐了。王稼祥热情而礼貌地同朱仲丽握手。
有一天,王稼祥给萧劲光写了一张纸条:你有时间带妻妹(朱仲丽)来玩。萧劲光看了看条子,高兴地将王稼祥的意思告诉了朱仲丽。朱仲丽心想,王稼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地位很高,自己不过是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应当尊重他。于是,在一个星期天,萧劲光兴致勃勃地带着朱仲丽到王家坪去玩。王稼祥与朱仲丽在打了一阵网球后,又到窑洞里下围棋。经过一段时期的接触,他们对彼此的了解更深了,感情也更近了。1939年正月,33岁的王稼祥和24岁的朱仲丽在延安喜结良缘。
在一个家庭,生儿育女是头等大事,但在王稼祥和朱仲丽看来,却微不足道。朱仲丽怀孕以后,意外地患了盲肠炎,需要做手术。她想,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党和国家的处境如此艰难,自己生了孩子怎么养呢?不如在做盲肠手术时,顺便做结扎手术算了。一天晚上。她将这个大胆的想法对丈夫说了,王稼祥却一点也没在意,随口说:“好啊,那就结扎吧!”朱仲丽说:“那将来可就没有孩子!”王稼祥还是不紧不慢地说:“没有就没有吧!”朱仲丽又说:“那就这样做了!”王稼祥点点头,表示同意。对于这种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两个人竟然在谈笑之间就定下来了,并且谁都没有反悔或抱怨过。
新中国诞生后,王稼祥担任了中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朱仲丽随之到了莫斯科。王稼祥生活相当朴素,每月给自己定的薪金与使馆里的汽车司机的工资相等。朱仲丽不但不要工资,就连原来应得的供给也取消了。
长期在苏联生活,语言不通是很不方便的。王稼祥俄文水平很高,尽管工作很忙,他还是认真、耐心地给朱仲丽辅导俄语。
王稼祥吃饭快,朱仲丽害怕他消化不好,就常常提醒他:“慢点吃!”王稼祥在朱仲丽的照顾下,身体有很大的好转。有一次,毛泽东对朱仲丽说:“我们以为稼祥不会治好的,他现在每天工作10小时,主要是靠你。”
十年动乱中,王稼祥和朱仲丽都未能幸免。他们一起被揪上台去批斗,一起被关押在“牛棚”里,又一起被送到河南一个有高墙的干休所。在那里,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差。朱仲丽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活。她步行到乡下去给王稼祥买稻草铺床,给他熬药、烧饭。然而,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还是离开了人世。
粉碎“四人帮”以后。王稼祥与朱仲丽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王稼祥去世后,朱仲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她开始尝试用文字来慰藉自己的感情,将自己对王稼祥的思念之情全部都写在了书里边。
三、耿飚和赵兰香用军犬保持联系
将军大使耿飚和赵兰香的爱情故事是很多人心中的传奇。
1937年秋,八路军129师385旅进驻陇东防区,旅部就设在庆阳城外田家城。当时耿飚担任385旅参谋长,并兼任庆阳县城防司令。
1940年夏季的一天,在庆阳女子小学任教的赵兰香注意到学校来了一位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的八路军首长,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有些清瘦,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他的粗布军装已经洗得发白,风纪扣却系得严严的,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但讲起话来却文雅和气。他就是耿飚。耿飚和蔼地和赵兰香聊起了家常,询问了她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渐渐地,赵兰香感到这位首长对人诚恳、亲切,没有一点官架子,心中暗暗对他有了好感。
1941年7月5日,赵兰香与耿飚的婚礼在庆阳女子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举行。
1942年,耿飚接到调令,离开385旅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赵兰香也骑马来到了延安,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
作为一员骁将,耿飚不甘心长期在后方留守。他多次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要求上前线杀敌。1944年秋,中央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他立即启程,奔赴前线。
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赵兰香也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和耿飚在一个部队工作。由于战事紧张,他们相聚的时间很少。在进攻宁夏的战役中,为了能保持联系。他们用军犬做通信员。赵兰香将信拴在军犬的脖子上,军犬可以凭嗅觉很快找到耿飚,把赵兰香的信带给他。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调耿飚到外交部工作。耿飚和赵兰香经过简单的准备就踏上了外交岗位的漫长旅途,开始了他们长达20年的外交生涯。耿飚是毛泽东的老乡,毛泽东曾热情地鼓励他说:“将军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
一开始,赵兰香无法适应从军营到使馆的工作转变。更令她难以接受的还是“大使夫人”的生活。在她看来,“大使夫人”就是官太太。还要化妆,和外国人打交道,比带兵打仗困难得多。
为此,周恩来专门请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胡济邦负责教“大使夫人”们外交礼仪。赵兰香从最基本的穿着、仪容开始学起。大使和夫人们还进行过一次关于吃西餐的彩排,内容包括安排主客座位,如何正确吃西餐等具体细节。几经演练,赵兰香终于顺利过关,走上了“大使夫人”的岗位。
大使馆的司机忙不过来时,耿飚就亲自驾车,后来他还拿到了瑞典的驾驶执照,被称为“自己开车的大使”。
一位瑞典的军官问耿飚:听说您是位将军,不知您带过多少兵?耿飚回答:“大概十几万吧。”军官一听,马上“啪”的一个立正,给他敬礼,说:“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啊。”
1950年10月,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邀请了500多位贵宾。赵兰香身着绣有牡丹图案的中国传统丝绸旗袍,妆容淡雅,落落大方,令众多贵宾眼前一亮。
耿飚夫妇庄重而亲切的笑容,给各国政要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地报纸和电台盛赞这次国庆招待会开得很成功,“盛况空前”。
1969年耿飚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在抵达阿尔巴尼亚以后,耿飚夫妇积极开展与兄弟党的友好工作,但同时他们也发现一些问题:中国援阿物资中,属国内紧缺的钢材、水泥,阿尔巴尼亚并没有用来搞经济建设,而是热衷于到处修纪念碑;援助的化肥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根本不用。这些状况令人心痛。耿飚如实将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为此专门调整了援阿政策。
1970年耿飚回国,又先后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赵兰香则调回了外交部。夫妇俩还多次陪同周恩来出访。
2000年6月23日,耿飚走完了他非同寻常的一生,享年91岁。赵兰香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设立了赵兰香庆阳女童教育基金,资金全部来自于耿飚收藏字画拍卖所得款。
四、黄镇和朱霖的结合有条件
黄镇和朱霖,也是在战争年代恋爱、结婚的,只是与其他人的“一见钟情”和“一拍即合”不同,他们的结合事先是有“条件”的。
1938年,在晋察冀军区工作的黄镇与在地方工作的朱霖相互认识。当黄镇提出结婚时,朱霖明确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结过婚的不要,对于高干,她信不过;二是自己婚后要坚持工作,决不闲在家里;三是不生孩子,怕影响工作。
黄镇表示,一定以无产阶级的道德和共产党员的人格对待她。于是经党组织批准,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婚后不久,他们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1941年朱霖奉调八路军129师政治部组织处干部科任营级组织干事,黄镇任政治部副主任,他让妻子住到组织部,避免与他同进同出。黄镇对朱霖说:“部队结婚的人很少,要注意影响。”
1950年7月,黄镇出任驻匈牙利大使。朱霖任二秘,负责大使馆的行政工作。使馆条件简陋,他们就亲自动手改进使馆的环境。黄镇布置使馆,朱霖脱去鞋袜整理使馆大院。
1964年黄镇出任驻法国大使。6月18日,朱霖去爱丽舍宫拜会戴高乐夫人。一见面,朱霖说:“今天是6月18日,23年前的今天,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发表了自由法国宣言,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戴高乐夫人非常高兴:“噢,你们还记得呀?”朱霖又说起戴高乐夫人在儿童和残疾人事业方面的贡献,勾起了对方对自己残疾女儿不幸夭折的怀念。
不久,戴高乐夫人到中国大使馆回拜朱霖。这在巴黎和各国外交界都少见。
1966年朱霖回国开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她时说:“朱霖,你是世界有名啊!”朱霖不知其故,要总理明说。周恩来说:“戴高乐夫人到使馆回拜你这个大使夫人,这不是世界闻名的消息呀?”
朱霖最后一次见到戴高乐夫人。已是“文革”时期。大使夫人们早已不敢穿旗袍,朱霖便穿着军绿色的首都服到了爱丽舍宫。次日,巴黎各大报纸都登出大幅图片,报道说:中国大使夫人穿着“文化裤”来了,爱丽舍宫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了一位穿长裤子的女人。
1973年5月,黄镇被派往华盛顿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工作。尼克松邀请黄镇和夫人朱霖一起去“西部白宫”作客,并且安排总统专机接送。总统专机从华盛顿军用机场出发时,一位安全官员开玩笑说:“黄镇大使。你现在可以拿起话筒给美国三军下命令,像尼克松总统一样。”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1973年10月,黄镇邀请基辛格到中国驻美联络处作客。基辛格本来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任何大使馆的晚宴他都不去。他担心一旦破了例,就得跑遍各国驻华盛顿的150个使馆。黄镇对此风趣地回答:“我们可不是大使馆,而是联络处。”基辛格也诙谐地说:“对驻华盛顿的联络处的邀请,我都接受。”
此后,基辛格成了联络处的常客。美方还为联络处安装了一部直通白宫的热线电话,礼遇之高,确实是“比大使馆还大使馆”。
1989年12月11日,黄镇逝世。美国总统布什向朱霖发来唁电,对黄镇在美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