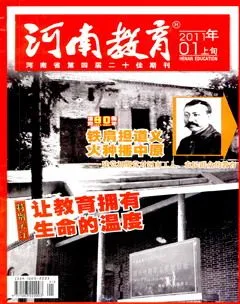营造非胁迫性的课堂气氛
2011-01-01王晓春
河南教育·基教版 2011年1期
上一篇文章我们说到,学生在课堂上能够基本上不焦虑、不恐惧、不孤独,这样的课堂就称得上是“安全的”课堂。为了创建这样的课堂,教师有意识地营造一种非胁迫性的课堂气氛是很重要的。非胁迫性的课堂气氛这个提法,我是在一位美国学者撰写的有关课堂管理的书上见到的。
所谓非胁迫,即“不威胁,不强迫”。比起我们所倡导的“诗意课堂”“春风课堂”“百花园课堂”“亲如一家课堂”,“营造非胁迫性的课堂气氛”这个口号似乎太平常了。然而细想起来,这一提法恰恰是切合实际的。我要是学生,我对课堂的要求首先肯定是安全感。连安全感都没有,如何体验课堂的“诗意”?学生要的是雪中送炭,而非雪中送花。试想:人若冻得要死,哪有闲心欣赏什么花儿呀朵儿呀!
我们来看一位美国中学教师怎样在课堂上创造“非胁迫性的”气氛——
桑迪努力在自己的班上创造出一种适当的非胁迫性气氛。比如,在开学的第一天,她给学生每人发了一张索引卡,要求他们回答四个问题:(1)你怎样才能学得更好?(2)你希望化学课上哪些东西让你激动?(3)你对什么感到紧张?(4)我可以怎样帮助你?
请注意,桑迪老师的这四个问题都是在询问,而不是在“教导”;是想知道学生的感觉,而不是告诉学生“你应该”如何如何;问题本身就是平等的、不施加压力的、非胁迫性的。尤其“你对什么感到紧张”这个问题非常好,教师只有知道学生害怕什么,才能有意识地避免什么。我非常遗憾地发现,我们有些教师正好相反,学生越是怕什么他越来什么,为的是控制住学生,让学生不得不照他的话去做。也就是说,这种教师恰恰是“胁迫性”气氛的爱好者。
我看不但中国如此,美国也差不多,否则美国的教育家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桑迪这类做法当做先进经验来介绍。为什么差不多?因为大家实行的都是义务教育。所谓义务教育,就是强制的教育,就是你不上学不行。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教师要创造“非胁迫性”的课堂,当然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正因为不容易,所以只有优秀教师才能做到。
遥想当年,苏格拉底的教育是非胁迫性的,孔子的教育是非胁迫性的,因为那些学生都是自愿来上学的。后来我国的书院,也比较有非胁迫性气氛。私塾就差一点了,因为很多孩子是奉家长之命上学的,但私塾的教师对学生的压力还不算太大,因为私塾没有升学指标。自打学校教育尤其是班级授课制一诞生,课堂的胁迫性就变得比较强了。久而久之,胁迫性似乎早已成为惯性,成为定势。后来,当行政部门对学校进行指标管理的时候,这种胁迫性就非同小可——教育异化了!本来学校和教师应该是帮助学生发展自我的,现在反过来了,学生成了完成学校指标的工具。于是就要搞各种评比,就要搞分数排队,就要用各种管卡压的手段胁迫学生达到教师的要求。本来分数高低、学业优劣是学生自己的事情,现在不然,家长和教师比孩子还着急。皇帝不急大臣急,皇帝越不急大臣越急,大臣越急皇帝越不急(对不起,快变成绕口令了),于是教师和家长就加紧胁迫学生、吓唬学生、控制学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谁都活得难受。
在胁迫性的大气候下,有办法创造非胁迫性的课堂小气候吗?桑迪的做法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我国有很多优秀教师做到了这一点。战略上胁迫,战术上却可以不胁迫或少胁迫;战略上强制,战术上却可以不强制或少强制。这并不费解。当年毛主席不就说过“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术上的速决战”吗?这里有个思维方式问题。培养人,这是一项高度精细、复杂的事业,因此教育者必须能够辩证地思考问题,可惜我们的很多老师头脑硬邦邦,想事直通通,不是黑白表里就是走极端,不碰钉子是不可能的。从社会的角度看教育,当然需要强迫;从孩子的角度看教育,胁迫自然是越少越好。你看桑迪老师向学生提的问题,就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思路,着眼于调动学生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种办法,当然可以给学生更多安全感。
我们再看另一位美国教师用什么办法避免课堂上的胁迫性气氛——
我对学生说,我们的课堂是个圣堂。他们必须先界定这个词组——“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一起进行头脑风暴,寻找“怎样才能使课堂变得安全”这一问题的答案。大家讨论的结果都列在公告栏上,而且都必须得到尊重。如果有谁伤害了别人的感情,我会马上停下来问:“我们的课堂是什么呀?”学生就会回答:“是圣堂。”我会这样不断重复,直到学生都学会了,而且会互相提醒:“嗨,安静!这里可是圣堂。”我并不认为这条策略一旦实施就马上会有效果,但学生确实看重课堂上的安全感。一开始这可能只是个玩笑,但慢慢地就变成了产生舒适感的源泉。过去从不大声朗读的学生现在愿意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了,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自己犯了错误,也没有人会嘲笑自己。
这个管理策略非常重要。这是软管理,是一种班级文化。如果教师能想办法让学生感觉到课堂是个神圣的地方,不可造次,不得无礼,那么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有些问题则根本不会发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无论多么不拘小节,在佛堂庙宇里一般都会有所收敛,在博物馆里也很少大喊大叫,在图书馆里则多会轻声细语。为什么?因为有一种庄重严肃的氛围在那里无形中约束着他。在我国古代,人们读书前要焚香沐浴,书院里充满宁静的气氛,处处让你感觉到这是斯文之乡、弦歌之地,不同于市井。教师千万不要小看这种氛围的力量,它们具有战略性意义。
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美国教师可以借助宗教文化,把课堂说成“圣堂”,便于学生把教堂的气氛迁移到课堂来(西方教堂确实有一种庄严安全的气氛),我们则很难这样做。所以,教师就要另想办法,比如说可以把自己的课堂命名为“杏坛”(孔子讲学的地方),或者借一个历史上有名的书院的名字来提升课堂的品级,逐渐养成大家的自尊和自信。这既不是胁迫,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用无形的渗透影响学生。
此事千万不可急躁,它不会立竿见影的。开始确实有点像玩笑,但是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它在不知不觉中发挥了作用——你的学生日渐斯文。朗读古代经典(比如唐诗)也有这种作用,关键是坚持。
下面这种做法就不妥当了。这是公然用群众性的胁迫手段控制课堂,也许能有眼前效果,但是会给学生造成不安全感。
一位老师因为家中有事,班级管理有些放松,一个月下来课堂上说话的较多,纪律明显下降,班里乱了套。于是教师专门抽一节课,要求大家投票“选出”违纪的学生,并写明其如何违纪。然后在班上公开统计票数,5票以下不批评,5票以上进行单独的批评教育,3名违纪特别严重的学生则被通知了家长。
这位老师在网上希望我评论他的做法。我回答——
感觉您是靠群众揭发和舆论施压来维持纪律(发动群众对付“不良现象”),这种办法也是教师们最常用的,有点像文革中的“大批判”。学生年龄小的时候可能还行,年级高一点怕就不灵了。班风稍差,教师威信不高,这种办法用了会更糟。我个人对这种管理思路持怀疑态度,因为这样可能会激化学生之间的矛盾,无法培养自觉纪律。不过这种办法有时能迅速见到表面效果。
有些老师会问,在课堂上树立正气、打击歪风邪气,难道不对吗?对,但是最好温和一些,不到迫不得已时,不要剑拔弩张,以免形成胁迫性的气氛。我们可以搞“暗中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而且不难掌握。我希望每个教师都能自觉运用这个策略。
多年前我做班主任的时候,如果发现班级不稳,我就会把班里的骨干和最老实、最沉默的学生(约占班级人数1/4到1/3)召集起来开会。我对他们说:“我不要求你们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也不要求你们向我反映捣乱生的情况,你们只要管好自己,对扰乱班级的言行不理不睬,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这种办法效果相当好。因为我提的要求不高,容易做到,而一旦做到,我就有了根据地,后院不着火,进退都从容。我把这种学生称之为“定海神针”,用当年的语言说就是“基本群众”。他们很不起眼,却是班级的栋梁。毛主席总是说要“相信群众”,此话含义很深,眼里没有“基本群众”的教师,不是好教师。
还有,你会发现有些问题男生捣乱,显示自己,是给女生看的。青春期的孩子,这种事不奇怪。我的对策是把班里最漂亮的女孩召集起来开会。我对她们说:“拜托各位,如果有人在课上逞能,你们只要像木头人一样毫无反应,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我先谢谢!”这招儿很灵,那些捣蛋鬼很快就扫了兴,有所收敛了。我把这一招叫做“木头人”。
我这两招其实和美国洛登老师说的“暗地里的支持”是一回事。对于学生来说,同龄人的态度是极其要紧的,抓住了这一点,就牵住了牛鼻子。很多老师与问题生“单挑独斗”,这不是明智的战术。要善于发动群众,解决捣蛋生的“土壤”问题。各位一定要记住,离开了一定的环境,问题生就不是问题生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网上有一位老师看了我上面的发言,有不同的看法。他斗志昂扬地说:
呵呵,我是让学生光明正大地支持我。经我工作和教育后,许多同学会异口同声地指责破坏课堂纪律的和捣蛋的学生:“人至贱则无耻!”
对此我回复道——
愚以为这不是教育者应该做的。暗中的支持,实际上是温和的教育,给犯错的学生留有余地,照顾他的面子,保护他的人格,有利于他的反思。这位老师让学生公然指责犯错者“无耻”,有辱学生人格,很不合适。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教师所做的事情,实际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很有压服和审判的味道。这种办法,势必造成一些学生说假话讨好教师;而一旦遇到那些厉害的问题生激烈反抗,就可能出状况。所以,此法在策略上不可取,太莽撞了。
这位教师的此种策略显然是要在课堂坚决地制造胁迫性气氛。教师公然站在问题生的对立面,一副亮剑的架势。愚以为,此种办法,不可轻易使用。
有时候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造成胁迫式的压力,并不是故意的。教师一片好心,但没有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效果也不好。
高二新分班,一个学生从原2班(实验班)分到4班(普通班)。学生找到新班老师,说自己感觉怪怪的,但也说不上是哪儿不适应。聊着聊着,他终于说出一个自己很不适应的方面——座位。
他比较高,从小学到现在,从未坐过第一排,而教师安排座位的习惯,是新入这个班的同学基本都坐在前面。他们猜想:“老师是不是对我们新入班的同学不放心呀?”
老师解释道,之所以这样做,绝非同学们想象的原因。相反,老师一是考虑你们刚入一个陌生的集体,要有一个过渡期,回头还让你们原班的同学坐一起;二是想让你们给老同学做个榜样。这学生还是不愿意,于是老师答应下周一给他调整座位。
此事我这样看:从实验班降到普通班,不是多么有脸面的事情。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比较正常的心态是赶快混进人群,最好大家谁也别提这件事。可是这位老师却偏偏把这些“失败者”集中起来,而且安排到前面座位,弄得更显眼了。这是不是有点“往伤口上撒盐”的味道?反正我要是新来的,我会很难堪。
我若是班主任,会一声不响、若无其事地把他们打散排座位,至少在一个月之内,绝口不提实验班之事——让孩子养养伤口。
所以,教师要注意,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就在课堂上制造了某种胁迫性的气氛,伤害到了学生。避免这种失误最好的办法是经常听听学生的呼声,少点“想当然”。
(责 编 若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