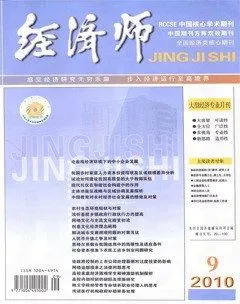清代“发冢”犯罪类型研究
2010-12-31王小丹
经济师 2010年9期
摘 要:清代《刑案汇览》之发冢案例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形形色色,包括毁损尸体的行为、不当的丧葬行为、破坏风水的行为、破坏棺椁的行为和从死者身上不义获利的行为,绝非盗墓这一种犯罪行为所能涵盖。因此,“发冢”并不等同于“盗墓”。清代刑律对不同类型的“发冢”均科以重刑,反映出中国古人“慎终追远”、“视死如生”的文化观念。
关键词:发冢 刑案汇览 犯罪类型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9-129-02
清代著名的判例汇编《刑案汇览》编纂了43个有关“发冢”的案例。内容十分丰富。《刑案汇览》中的“发冢”非盗墓(掘取他人坟墓获得钱财)所能涵盖。本文试以《刑案汇览》为中心,梳理出“发冢”这类行为的犯罪类型,并探寻重刑惩治“发冢”之文化内涵。依照“发冢”律法所保护的法益之不同,可以将“发冢”划分为以下几种犯罪类型。
一、毁损尸体的行为
中国古人相信,死人的世界与活人的世界是两个不能混同的世界。人们一方面在痛惜死者、悼念死者;另一方面,却也是在担心着死者的灵魂会“侵入”活人的世界,更担心更多的活人会被“带入”死者的世界。人们认为接触死人就会引来死亡之类的不祥之事。基于此,中国古人会对尸体妥善处理,禁止随意毁损,重视保护尸体的完整性。《刑案汇览》中有不少严厉打击毁损尸体行为的案例反映了中国古人的这种观念。
1.将他人尸首抛弃河中——弃尸。在“地邻虑恐受累将尸移弃水中”一案中,霍敬盛发现邻居赵套的尸身在自己地里,怕受牵连,让雇工将该尸身移走,扔进河里,后来河水退了,尸体露出。判官依律对霍敬盛作出“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失尸减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的判决。霍敬盛本不是杀人凶手,但是由于他对尸首设有进行妥善处理,而是随意抛弃河中,受到法律的严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水退尸露(不失尸),判官减轻了该犯的刑罚。可见,律法所保护的是尸体的完整性,如果对尸体的完整性破坏性越小,则刑罚越轻。
2.道途格杀拒捕盗贼,烧尸灭迹——毁尸。失主追捕盗贼时将盗贼打死,后来畏罪将尸体焚化灭迹,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个案件所保护的尸首身份很特殊——生前是盗贼。这说明当时的法律对所有死者的尸体都无一例外加以保护,即使是死者是罪犯也不得随意处置其尸体。
3.殴妻致死,狡不吐实,致妻尸两遭蒸检,情同残毁——无端尸检。丈夫隐瞒殴妻致死的实情,间接导致妻尸在官府查验中两次遭蒸检,最后判官判定此行为情同残毁。此案中,丈夫并没有亲手毁损妻子的尸体,他只是隐瞒了犯罪事实,导致官府对妻尸进行查验(两遭蒸检)。那时,妻尸仍在,只是经过两次蒸检,尸体不再完好如初。可见,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尸身的完整性,即使是间接导致尸体毁坏,也会被追究。
4.刨掘坟角,用灰水灌入;刨掘烧尸——伤残尸身。马成贵因家宅不安,妻子患病沉重,疑心已死雇工阴魂作祟,先将雇工坟角刨掘窟窿,用石灰水灌人镇压,后将另一坟冢刨掘烧尸,判官认定罪犯应按照开棺见尸拟绞。众所周知,石灰水有腐蚀的作用,灌入坟冢,尸体当然会被毁坏。另一尸体被焚烧,更是严重毁坏。残害尸体的行为被判死刑,与故意杀人所判之刑比肩,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5.开沟挖出古冢枯骨多桶——将他人骨殖恣意狼藉。李春明开挖新沟,从古义冢中穿过,挖出骨殖,盛于木桶,枯骨至二十一桶之多,判官认定该犯赋性残忍,其人行事恣横,按律法应缳首。该案中,被损害的是年代久远的孤坟,同样受到当时律法的保护。
二、违礼的迁葬行为
在中国传统礼法社会,子女爱其双亲,不单在父母生前要尽心侍奉,即使在父母死后亦必须按照礼制要求为父母办丧事。让亲人的遗体暴尸荒野有违孝道。正如《孟子·滕文公上篇》所云:“盖世上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呐姑嘬之,其颡有睨而不视。……盖归反(铲土用具)而掩之。……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选择一块吉地葬其祖上的遗体,既是儿孙尽孝的一个方面,又可使祖上的灵魂得以安固,保佑后代子孙繁荣昌盛。
通常,古人会选择本家族墓地区域内的合适地点作为亲属的坟地。死后葬人本家族祖坟区域,这是一种身份的认可(承认死者是本族承认的合法子嗣)。家族墓地只接纳同一血缘死者。家族墓地按男性辈分算世系,排列墓次。相同辈的坟墓排成一列,后代同辈的死者接左长右幼的秩序排列遗体。因此,家族墓地的穴位是有位次的,不容混淆,一旦遗体人土,不能随意迁葬。《刑案汇览》记载了一些擅自迁坟的案例,因其违反礼制,当时的刑律把这些行为归入“发冢”,施以重罚。
1.族人私挪乞养子孙浮厝尸棺——擅挪尸棺。同一宗族的人将被同宗收养的子孙的棺木挪出本姓坟地,按律拟杖八十。这种行为与直接挖掘被人坟墓不同,只是移动了棺木,并未破坏尸身。死后埋人本姓坟地,是身份的认可。擅自挪尸棺实际上是侮辱死者尊严的行为(不承认死者是本族合法子孙)。
2.义地浮埋旅榇年久焚化眷葬——誊葬。地藏寺义地依照当地起旧葬新的习俗,焚化携骸,誊葬他处,照毁损律定罪。此后,官方颁布饬令即使义地无隙地可以继续安葬,也不得将已葬尸棺起出替葬,若犯,从重治罪。这反映出中国古人事死如生的观念,死者一旦按照礼制被埋葬,其他人不得随意迁移其坟冢,打扰死者的安宁。
3.远祖禁山盗葬父棺被人掘移——盗葬。王逢世图谋风水,将父棺切近远祖坟旁盗葬,致被族人等掘移他处,比照切近坟旁盗葬,尚无侵犯,致被地主发掘例拟杖八十,徒三年。古人对坟地的地点的选择十分讲究的,不能对死者随便埋葬。禁止埋入本族坟地的人,若子孙将其偷偷埋入,则属于盗葬,导致他人掘棺,这同样是对死者不敬。
三、破坏风水的行为
中国古人的住宅讲究风水布局,重视房屋周围的环境。例如,古人认为庭院应该保持整洁,不可有废弃秽物,否则会遭致家人不平安。如果院落里出现了无名尸骸,煞气升腾,乃是风水大忌。《刑案汇览》中的一则特殊发冢案凸显了这种观念。
将兽残食尸骸掷人他人园内图害——弃尸骸遗害。吕海青因挟吕怀珍不允借贷之嫌,将野兽残食之尸头弃置吕怀珍园内遗害,比照弃他人尸于水中不失减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该案犯为了泄愤将无名尸骸残体弃置他人庭院中。该行为似乎谈不上坏损他人财物或是破坏尸体的完整性。但是该行为会对庭院的主人造成困扰:一是让其官司缠身,脱不得干系;二是通过弃置不祥的秽物,破坏其风水,让其走霉运。无名尸骸残体肯定是不祥之物,放置他人园内,有诅咒之意。
四、破坏棺椁或坟墓的行为
中国传统礼制推崇“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死者的棺椁与坟墓也被认为是死者存在的延伸象征。对棺椁或坟地的保护,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心理追求:一是让先人魂魄人土为安,确保不受恶地之害;二是希望祖先的骨殖能有好的地理感应,汇聚灵力,能使后人得于成就,告慰祖先在天之灵。反之,对于破坏棺椁或坟墓的行为被认为是故意侵扰死者的安宁,同时也伤害了死者的亲人对其缅怀之情。《刑案汇览》中汇集了不少破坏棺椁和破坏坟墓的发冢案例。
1.撬损祖母尸棺(企图捏造事实诬赖他人)——撬损尸棺。李昭郓将停放自家屋内的祖母尸棺于旧有开列处撬损,意图捏造事实陷害他人,比照盗祖父母、父母未埋尸枢,为开棺椁例拟绞立决。判官认定此种行为与祖母生前对其殴詈(殴打辱骂)无异,即使并未图财也不得宽贷。该行为伤害了父母子女之间的人伦关系,晚辈没有尽孝道,反而让已逝的亲人不得安宁,被视作是殴打辱骂长辈的不孝行为。
2.挖圹葬亲误伤无服族主棺角——误伤棺角。马利贞在祖坟余地内挖圹葬亲,误伤无服族主棺角,照发掘他人坟冢见棺拟军,杖一百,徒三年。该行为其实是一种过失行为(并非有心发掘破坏别人的棺木),危害性也不大(只是棺材一角受损,财产性损失不大),因此,律法所保护的对象仍然是死者的尊严不得侵犯。
3.误信阴阳迁葬父棺抽盖露尸——露尸。李作华听信阴阳将伊父迁葬,抽取棺盖,虽无洗检毁弃重情,第已取盖露尸,以毁弃论,于毁弃父母死尸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此案中,李作华并未故意损害父亲尸棺,只是在迁葬时把棺盖打开了,将父亲尸身暴露在空气中,被认作打搅了其父之灵,不符合礼俗传统。
4.平治祖坟为田,并无露有棺椁形迹——平坟为田。韩玉命因贫将祖坟平治为田,栽种麦禾,至六十一冢之多,并无露有棺椁形迹,请发黑龙江为奴。该案中,韩玉命未对祖坟发掘或是盗窃,只是在坟冢土壤之上耕种粮食,也是无奈之举。但是判宫认为,若对此行为不严加管治,日后刨棺弃尸的行为犯罪会愈演愈烈。归根到底,为了维护死者的尊严,维护封建礼制传统,当时的律法才会对平坟为田的行为严惩不贷。
五、严厉打击从死者身上获取财物的行为——不义获利
中国古人把坟墓称作“阴宅”、与此相对的把活着的人的住宅称作“阳宅”,表达出“视死如生”的意识。为了死者在另一世界继续生活衣食无忧,人们会在死者棺中放置一些物品,钱财、衣物以及一些生活用品。这些财物将随着死者一同埋人地下。这么做一方面是对死者尽心,设法满足死者在另一世界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不如意,殃及亲人以至他人。因此,从死者身上获得的财物,是不义之财,影响了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正常生活,而死者灵魂不安,将会对生者造成困扰。当然律法中要明文规定严惩这种行为。
1.翁主令常人盗子妇未埋尸棺——侵占随葬物。姚德茂指使他人在媳妇尸体临埋之时开棺抽取陪葬绸褥,以致暴露媳尸,比照发子孙坟冢开棺见尸律杖八十,未埋者酌减一等拟杖七十。即使是作为家长的公公,也不能违背丧葬之礼,将媳妇随葬的绸褥据为己有,这是一种违背人伦的不义获利。
2.刨高祖以上坟三冢,盗取金银器物,卖钱花用——盗墓。吕祥因贫起意刨窈祖墓财物,开棺见尸,盗取金银器物,卖钱花用,依子孙发掘祖父母坟冢,开棺尸例凌迟处死,子嗣均行发遣(流放)。可见,子孙对于祖先的随葬品并没有所有权,如果盗发此类财物,会被认为是残忍蔑伦的禽兽之举。
3.葬父无资盗棺剥衣当钱埋葬——典当随葬物充当丧资。宇文焕因父亲病故停柩在室,无钱埋葬,起意开棺剥取尸衣当钱葬父,照子孙盗祖父母、父母未殡未埋尸枢,开棺见尸斩立决。这个案子很特别,宇文焕是出于善意(典卖尸衣葬父)而剥取尸衣。当时,坟冢无掘动形迹,尸身亦未残毁。但是良善的动机没有成为法律宽宥他的理由,他最终仍被判以酷刑。可见,封建社会绝对禁止从死者身上获取不义之财。不论此财物的实际用途如何。
4.发冢起棺勒赎索财取赎——发掘他人骨坛勒索死者亲属。陈石伟等发掘邱中元故祖母蔡氏骨坛藏匿勒赎,比照强盗得财律拟斩立决。
这是一种特殊的获取不义之财的犯罪。案犯发掘他人骨灰坛,利用生者对已故亲属的感情,趁机勒索钱财的行为被当作强盗行径。
综上所述,清代发冢罪是有关破坏坟墓、棺椁或尸身和以发掘财物为目的盗墓、盗棺犯罪行为的总称。而盗墓仅是发冢这类犯罪行为中的一种。当时的律法对发冢行为施以重罚,不但要保护死者随葬财物,而且还要保护死者尸体、死者的尊严、死者亲属的风水,折射出中国古代礼法社会独特的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