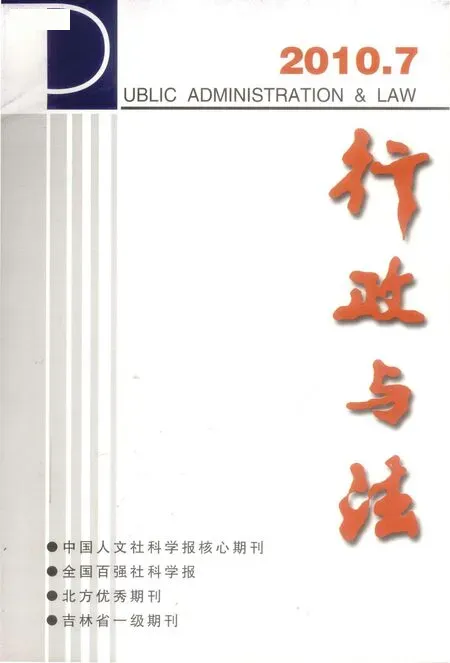“农民工”的身份位阶与法律保护
2010-12-26童列春
□童列春,章 群
(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3;⒉西南财经大学,四川成都610074)
“农民工”的身份位阶与法律保护
□童列春1,章 群2
(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3;⒉西南财经大学,四川成都610074)
农民工在企业中处于顺应地位,在社会分配体系之中处于弱势地位,在转型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地位;农民工作为生产诸要素的合作者具有分享社会财富合理份额的诉求,作为人和公民具有享有基本权利保护的诉求,也有通过社会群体力量表达利益的诉求;农民工身份群体的利益应通过基本权利保护机制、结社机制、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与行政保护机制获得实现。
农民工;身份位阶;法律保护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形成所谓“农民工”群体。如果依据户籍制度,这些劳动群体属于“农民”,被排除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如果依据所从事的职业划分,他们从事工业劳动,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工业劳动中的要求和风险同样加在他们身上。劳动者是弱者,“农民工”又是劳动者中的弱者,对农民工加强保护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主题。问题是,农民工为何要受到特殊保护,保护到何种程度可以认为适当,劳动保护适当性的衡量依据如何建立,只有从身份视角,剖析农民工所处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层次,分析农民工在社会差序格局中的身份位阶,发现农民工劳动关系的本质;探究农民工身份属性提出的法律诉求,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设计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才能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一、农民工的身份位阶
社会通过农民工身份为特定的劳动群体界定利益范围、设计行为模式。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的身份位阶具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⒈农民工在企业组织关系之中的身份位阶。在企业制度中,人被要素化,全面完整的人被片面化,抽出符合企业要求的秉赋——劳动能力;人的其他属性被舍弃,整个人屈从于企业组织需要。企业内部以效率为中心的“科层制,”摒弃了岗位任职者的人格特征,将其纳入理性程序。于是,整个世界被理性化、逻辑化,成为实现功利理性的工具。[1]在企业中,劳动者因为劳动任务而具有价值,所以,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必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只有这样才能符合特定企业的生产经营要素。同时,按照企业的要求进行培训,可以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从而提高其人力资本,所以,培训也就变为农民工的权利;但是,劳动培训是依据企业需要的,将劳动能力进行专用化塑造,产生锁定效应。
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代工业经济中,企业整合了社会资源,劳动者是依据企业组织需要而存在,企业处于主动地位,劳动者处于顺应地位。在企业组织过程中,劳动力是作为生产要素进入企业的,劳动者是作为劳动力的载体而存在的。虽然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形成是依据契约,但是,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雇佣契约把劳动商品化。
作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雇佣关系取决于企业需要。企业依据需要聘用农民工,并依据企业运作需要安排工作;在特定情形下,法律允许企业单方面意志和利益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例如: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甚至是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⒉农民工在企业运行关系之中的身份位阶。在企业运行关系中,以行政体制替代市场机制,以“命令——服从”形式替代协商机制。在企业运行关系中,管理者处于主动地位,劳动者处于顺应地位。管理者依据商业运作要求安排劳动者工作,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按照商业运作甚至是机器的节奏来安排。在企业体内部的支配控制关系中,管理者权力的存在会衍生出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被支配者的认同或者忍受。被支配者的认同或者忍受是身份制度内部控制关系的运行基础,管理者权威总体上得到当时社会的一般认可。理由在于:在现代社会中,组织管理技术进步可以带来控制方式的文明化,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被整合进入企业体系内部,生存强制引导人们接受身份带来的控制,企业中的工人普遍认同经营者的控制;管理者执行组织管理功能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管理者的职权行为是企业运行的意志,管理者权威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二是对于支配者的权力制约。如果单纯依据企业的意志,劳动者的生理节奏会无条件服从商业节奏。企业内部控制关系中一般均存在权力制约机制,在法律之外,权力制约机制包括道德伦理、社会舆论、宗教信仰。此时法律引进行政部门的权力,来平衡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利益。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法律规定的一般工作节奏,需要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才能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有特殊情形,延长工作时间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一般限制,例如,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时抢修的。
⒊农民工在社会分配体系之中的身份位阶。农民工是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之中来参与分配的,这种制度安排为农民工提供了预定的利益空间,“制度安排本身具有倾向性”。[2](p108)社会分配有三种机制,第一种是市场机制;第二种是政府机制;第三种是社会机制。社会分配体系之中的身份位阶讨论,主要集中于第一种机制。企业主、管理者、劳动者共同面对并参加其中的是现代社会一系列程序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分配关系之中,谁掌握现有的制度,谁在其中拥有主导权,谁就可以获得明确份额以外的剩余财富;拥有主导权的群体成为分配关系中强势群体,处于顺应地位的群体属于分配关系中的弱势群体。
劳动者在市场机制分配体系中,主要实行薪金制,在薪金决定过程中,国家通过立法、制定规章确定最低工资;工资分配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企业设定工作岗位,依据劳动任务决定工资数额;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虽然劳动者可以通过谈判主张自己利益,但是,受到谈判能力的限制、失业人口等劳动力市场压力的影响,其应有的利益份额容易被侵夺。首先是工资低廉,其次是工资经常被拖欠,并且常常被逃废。在现有法律调整范围内部,不能有效地衡平利益,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济措施。在分配领域依据特定标准界定的卑微身份地位,其消极后果会扩散到相关或无关的其他社会领域,导致农民工群体在社会整体中的弱势,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并在其他社会领域处于被排斥状态。在中国经济二十余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劳动群体的利益份额处于下降状态,不能有效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⒋农民工在转型社会结构中的身份位阶。“农民工”的存在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建国后国家政策安排导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建国后的‘农民’在中国社会就是这种身份,它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国家集中和动员社会资源,协调社会流动的工具。我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镇必须持有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镇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3](p158)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属于几种身份系列。⑴户籍身份系列。全国人口群体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村人口不经政府有关部门许可不得变更农村户籍。⑵人事身份系列。城镇中的在业者分为干部身份(人事部门管理)和工人身份(劳动部门管理)。这样的身份类别划分和与相应的等级工资制构建了城市中的社会等级。⑶所有制身份系列。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职工在工资、劳保福利待遇上都有较大的差别。户籍身份、人事身份、所有制身份并不是先赋的,它不是从上一代遗传下来的,而是由行政力量赋予的。但人们获得这种身份时,不需要依靠平等竞争,而且一旦得到了这种身份,便不能轻易改变。这些特性又有了某种先赋性的因素。[4]改革开发以后,推行市场经济,农民有了进城务工的机会,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在城市身份地位的差序结构同样处于卑微地位。中国城市主要身份阶层为:⑴上层官员和大业主阶层;⑵中下层官员和中下层业主阶层;⑶管理人员阶层;⑷技术工人阶层;⑸半技术半体力工人阶层;⑹体力劳动阶层;⑺失业者阶层。[5]农民工应该属于体力劳动阶层。在差序结构中,职业地位是个人地位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职业改变就成为社会流动的途径;进城务工是农民工改变自己身份位置的一种努力,其目的是争取得到更多的社会性资源。进城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境况,获得了比务农农民更好的经济地位;但是,在城市生活体系中,农民工处于底层地位;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农民工也处于底层位置。
二、农民工身份位阶的法律诉求
有关农民工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单纯依据合同而是应该同时基于双方关系;法律上权利义务状况并非仅仅来自双方订立合同时所作的选择,而是来自各方在社会中地位以及其与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有关雇主与雇员关系的立法,将责任和义务强加在雇主身上,不是因为雇主有此意愿,也不是因为他有过错,而是为了保护雇员的利益。”[6](p19)基于特定的身份地位,才能观察他们真实的法律诉求,回应农民工的法律诉求,我们才能够制定出符合社会正义的法律制度。
⒈作为生产诸要素的合作者分享社会财富合理份额的诉求。剩余价值的创造,并非仅仅依据资本这单一要素,资本、劳动、管理与社会制度的合力创造了财富。“那些认为他‘造就了’他自己和他的生意的产业组织者们会发现,在他手边的全部社会制度都是预备好了的,如技术工人、机器、市场、治安与秩序——这些大量的机构与周边的氛围,是千百万人与数十代人共同创造的结果。……我们不应当说甲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创造了若干财富,乙创造了若干财富,而应当说利用和借助现存的社会制度,财富的增加属于甲者比属于乙者较多或较少。如果只涉及甲和乙两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所增加的财富或许会成为决定报酬的基础,但如果涉及到甲和乙与社会之间,那么,这个依据就不再适用。”[7](p108)在此,从劳动法理论上不能仅仅将工资理解为劳动力的价格,通过劳动合同完成了所有的交易,企业所创造的财富不再与他们无关。农民工对于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分享同样存在诉求,象所有的弱势群体一样,他们的诉求通过消极的形式表现。“在我们能够想到的这些相对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阶级斗争的形式有其共同特点。他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他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8](p2)让农民工分享他们所处的社会的文明成果是一种自然权,需要通过税收体系调节社会收入,完善社会保险,协调劳动关系,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⒉作为人和公民享有基本权利保护的诉求。“中国农民社会身份的形成是国家制度性安排的结果,农民身份所包含的责任远远大于所享受的权利,不平等和弱势是农民身份的特点,对农民的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形成今天社会冲突的隐患。”[9]这种制度安排和现代宪政制度存在冲突,忽视了农民作为一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rank Pakin)把这种身份制看作是“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他认为,多种社会集团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社会资源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当某人属于某一民族或地域的成员、或掌握某种语言、或参加某种宗教,即获得了一种有别于他人的身份,并取得了与此相应的身份利益。在社会屏蔽下,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明显差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利,并且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终身的社会定位,很难依赖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10](p208)特别在有专制传统的国家,统治者往往严格控制各种身份之间的差别和转换。身份成为人们获得某种职业、地位,享有某种社会资源,占有某种社会声望的基本前提条件。
在现代法治视野中,农民工也应该享有作为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劳动权是现代人的基本权利,是生存权的表现方式。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
立法中应努力将劳动者非要素化,还原为人,人的基本生理和心理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例如,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不得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活动。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产假。
⒊作为民主社会力量平衡的群体化表达的要求。现代社会的职业身份是主导性的社会身份,决定了在社会中占据何种位置,农民工占据的是社会弱者的位置。一般情形下,一个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总是组织能力强的群体,而弱势群体总是组织能力差的群体。农民工总是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缺乏有效的组织,所以,在社会中难以形成可以保护该群体利益的社会势力。“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11](p2)所以,农民在社会生活中一般不能有效地运用正式的社会保护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现代社会中,结社是积聚特定身份群体力量的基本形式,舆论是公共表达的有效手段,立法、行政、司法等社会机制构成公共权力系统,这些组织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和行为宗旨均是“为人民服务”,从理论上讲,这些公共权力资源可以为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公民享有。但是,由于利用公共权力资源所需要的信息成本、程序成本均超出中国农民的支付范围,农民利用结社、舆论、司法、立法、行政等政治社会机制追求身份利益的机会也被排斥。由于利用正当渠道的机会被排斥,农民可能的选择只剩下非理性的表达方式,农民工的“跳楼讨薪”现象就是这种社会排斥的衍生品。农民缺乏自己群体利益的组织(诸如农会),在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权力机关或政协这样民主监督机构也没有真正的自己代表。法院等司法机关虽然不会排除农民,劳动争议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但是,司法保护机制存在启动成本,劳动者个人不能够方便使用。农民工没有成为社会博弈中有效的一方,在民主政治的群言堂中,并不包括农民工的声音。如果不考虑社会势力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劳动关系的契约性,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本身就成为一种非正义。“劳动契约据说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而只要法律在字面上规定双方平等,这个法律就算是自愿缔结。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的实际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此方或彼方没有明白表示放弃,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放弃掉,这又是与法律无关”。[12](p74)如何在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安排中追求社会正义?罗尔斯第二个正义原则要求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⑴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并且⑵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均等原则)。[13](p292)
三、农民工的法律保护机制
现代社会通过立法规定社会的基本保障基准,企业法中规定了职工的权益,企业法外制定专门的劳动法保护职工利益,宪法从公民权的层次提供保障,而国际人权公约则为“人”界定了基本的利益范围。
⒈基本权利保护机制。农民工具有职业身份与社会等级身份两重性质,保护农民工的合理做法是以职业身份为基点,淡化等级身份,构建基本权利保护机制。
⑴生存权利与促进就业。对于现代人来说,职业身份包含了综合的生存利益,失业是巨大的灾难。人们加入组织的原因就是为了获得安全、身份、自尊、社会关系、权力和成就目标。[14](p87)政府通过保护人权和兑现公民权来提供符合正义要求的利益,农民工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国家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就业条件,扩大就业机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兴办产业或者拓展经营,增加就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多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就业服务。
⑵外部规定替代合同与企业内部安排。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合同自由的实现应以交易双方力量大致均等、信息对称、交易技巧相当为条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主体间的力量均衡在许多情况下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仅是强势方享有合同自由,合同正义更是无从谈起。”[15]劳动合同中需要强行法介入,进行控制,包括缔约控制、内容控制、形式自由控制。例如,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从事特种作业的劳动者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资格。
⒉农会与工会对接的结社保护机制。中国农民身份制度使农村社会横向联系的纽带极为脆弱,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协商、对话成本极为昂贵。弱势身份群体的政治与社会表达应该被关注。中国农民身份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少权,农民没有表意权,没有真正享有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缺乏和政府对话的平台和渠道。给农民以政治信任,允许农民成立农会,建立和政府对话机制,降低对话成本,给农民体制内表达的机会,减少其体制外寻求实现利益表达的方式。[16]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指出:“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我们等三年,真正需要即可筹办”。[17]
农民工参加工会,并通过工会实现自己的利益保护。“劳动者是工会的基础,工会是劳动者的代表,劳动者与工会共同形成了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劳方主体。”[18](p111)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运用劳动合同中的集体缔约机制。由于劳动者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凭单个雇员一己之力或者少数雇员的努力不可能达到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的目的。在劳动合同中,通过工会或其他雇员组织与雇主进行谈判,可藉集体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争取较为有利的工时、工资、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合同条款。集体合同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劳动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⒊社会风险保障机制。社会风险保障机制的基本形式是社会保险和福利。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农民工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退休、患病、负伤、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失业、生育。劳动者死亡后,其遗属依法享受遗属津贴。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国家鼓励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为劳动者建立补充保险。国家提倡劳动者个人进行储蓄性保险。国家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兴建公共福利设施,为劳动者休息、休养和疗养提供条件。用人单位应当创造条件,改善集体福利,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
⒋行政保护机制。
⑴劳动行政部门的问责制。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主管全国劳动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有权进入用人单位了解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查阅必要的资料,并对劳动场所进行检查。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既有法律规定确认了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职责,但是没有突出劳动行政部门本身的约束,确立劳动行政部门的问责制。对于恶性的伤害农民工事件,政府部门有关人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⑵行政惩罚机制。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用人单位有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1]鲁品越,骆祖望.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J].中国社会科学,2005,(03).
[2][7](英)伦纳德·霍布豪斯.社会正义要素[M].孔兆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3]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运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朱力.准市民的身份定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06).
[5]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传统意识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04).
[6](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M].唐前宏译.法律出版社,2001.
[8][11](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
[9][16]柏骏.农民身份——一个社会学研究的视角[J].唯实,2003,(12).
[10]李路路.中国非均衡的结构转型[J].载裘方.社会学家的眼光[M].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12]恩格斯.恩格斯论宗教[M].人民出版社,2001.
[13](美)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4](美)斯蒂芬·P·罗宾斯著.组织行为学精要[M].柯江华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15]张金海.重思“从身份到契约”命题[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02).
[17]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经给邓小平建议过要恢复农民协会。邓小平当时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见:凤凰网,2007-02-09.又见肖瑞,李利明.农村土地变迁之路[J].经济管理文摘,2003,(02).
[18]常凯.劳权论[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张雅光)
Status Rank of“Migrant Workers”and Legal Protection
Tong Liechun,Zhang Qun
The migrant workers are responsive position in the enterprise,among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system in a weak position,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ransition at the bottom position;farmers working partners for the produ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have to share the aspirations of the community fair share of wealth,as people and citizens have access to basic rights protection demands,but also through social groups,the power to express their interest demands;migrant workers as group interests,through fundamental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s,docking association mechanism,the social risk protection mechanism and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be achieved.
migrant workers;status rank;legal protection
D422.7
A
1007-8207(2010)07-0020-05
2010-03-09
童列春(1968—),男,安徽桐城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民商法;章群(1963—),女,四川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劳动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6XFX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