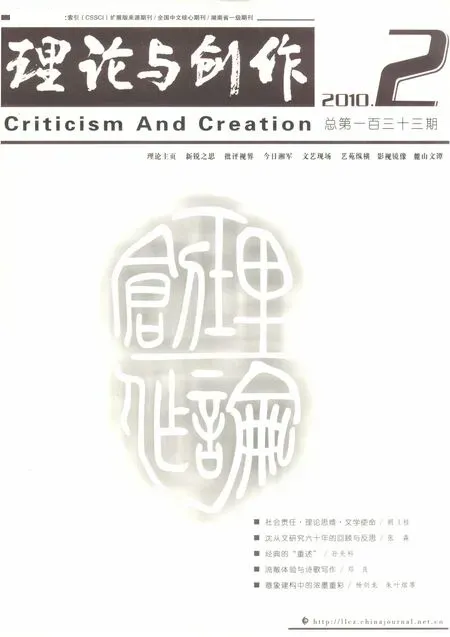多元语境下的多元呈现——论影片《建国大业》中的空间书写
2010-11-25庞弘
■庞弘
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新政协会议召开60周年的献礼大片,影片《建国大业》以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这一对中国而言最具历史意义的时段为区间,展现了包括重庆谈判、内战爆发、三大战役、开国大典等等在内的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交锋中英勇无畏的抗争历程以及与各界民主人士久经考验的深厚友谊。作为拥有政策支持与投资眷顾双重优势的“主旋律”大片,《建国大业》充分调动各方资源,依凭广阔视野、宏大制作,再加上群星璀璨的编、导、演阵容,不断刷新同类型影片的多项纪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影片中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层次鲜明的多元化空间呈现,既贴合了多元文化交织的当下语境,充溢着新时代的气质、风范,又紧扣那一汹涌澎湃的历史进程,展现出一种趋向本真的不懈努力。
一、空间问题在电影研究中的勃兴
在传统理论视域内,对时间之重要性的强调要远远超过对空间的关注。在古老农耕时代,人们同自然环境的关系格外紧密,日出日落、四季轮转的规律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圆满、循环式的时间格局的崇尚;在启蒙精神的促发之下,随着现代性话语的不断推进,一种进步、连贯、不断否定过往的时间模式又渐渐占据了人们思考的核心。正因为如此,在传统意义上,时间往往被定义为一种丰满、生动、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本体性存在,相较而言,空间的重要性则被缩减到了极致,它往往被视作死板、僵硬、麻木的化身,被视作时间逻辑得以践履的被动所在。
然而,在一种“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下,对空间之重要性的强调已经愈发显著。众所周知,全球化突出了地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顺应这样的要求,极端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使地区之间的位移时间得到了极大缩减,而以英特网为代表的新兴传播媒介更是能实现几乎同步性的区域间讯息交换。在这样的状况下,时间曾经具有的强大威慑力遭受了极大的淡化,相形之下,空间多元、异质的魅力却得到了重新发掘,在现今文化语境下,空间不再是一处封闭、凝滞的所在,而是被视为一种敞开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生动场域。于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研究的空间视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潮流。
无论是列斐伏尔对空间之消费特质的描述,还是福柯对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梳理,抑或爱德华·索亚对“第三空间”理念的引入,都是现今“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趋势的集中体现。具体到电影研究中,对空间维度的强调也得到了愈发明确的凸显。可以说,以展现形象为主导的电影本来便同空间保持着与生俱来的紧密关联——一方面,电影空间的包容性与涵盖力适合形象在其中演绎,另一方面,形象的视觉特性适合反映、演绎具象化的空间。在现今空间研究潮流的推进下,电影中的空间形象更是愈发受到关注,比较著名的研究个案是哈维对影片《银翼杀手》中城市的细致分析,在他看来,片中的都市景观体现出了后现代空间的最鲜明特色。①
当然,必须注意,哈维等人的论述主要来源于一种与中国文化状况存在诸多殊异的空间状况与体验,对中国影片的空间解析还必须以国产影片为依托,结合本土文化语境加以探讨。在这方面,《建国大业》以其波澜壮阔的气度、错落有致的手法,在钩沉历史的同时呈现出了真正富于本土特质的空间状貌,成为人们思考中国电影空间书写的有益范例。
二、城市与乡村——二元话语的建构与改写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二元对立模式的设立是支撑电影叙事展开的最基本样态,而这种二元模式最集中、最具普遍性的展开方式则是一种城市同乡村之间的对立格局,在影像的铺展中,前者往往被指认为反革命(反党)、非正义、阴暗、堕落的罪恶渊薮,而后者才是集革命(党)、正义、光明、进步于一体的理想化所在,当然,这样的空间定式与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历程紧密相关。作为主旋律献礼大片,《建国大业》在空间设置上仍然延续了“城市-乡村”的经典对立模式,同时又结合时代、文化状况,在这样的对立性空间中加入了独特的修正与改写,一定程度上冲淡乃至消除了城乡之间曾经难以弥合的裂痕,在维系影片精神基调的同时也彰显了更加鲜明的本土特色。
(一)都市——多元文化的复调交织。伊芙特·皮洛曾这样道出了城市空间对于电影的巨大意义:“电影神话的真正用武之地仍然是大城市,仍然是生存搏斗场——都市。”②可以说,1945-1949年的中国城市(多为蒋管区域)呈现出了极为驳杂多样的色调:殖民侵略的刻骨创痛、帝国主义强制施加的现代性影响,国民党统治的军事化背景,再加上其自身根深蒂固的文化气质与历史积淀,以不同方式、不同侧重表现出来,不可避免地呈现为一种多重特质交织、混合的复杂形态。而这样的城市状貌也成为了《建国大业》重点的书写对象。具体而言,影片以令人目眩的镜头在众多的城市之间不停地跳跃、剪接、变换,从而营造出了一种多重特质交织、混杂的复调状态。然而,如果就空间演绎的典型性而言,电影依然凸显出了某些别具一格且不乏象征意味的城市状态,其中对重庆、南京、上海三处的空间呈现也许最值得玩味。
在《建国大业》中,重庆的形象在两个向度上得到了体现——重庆谈判前排场盛大、名流云集的酒会大厅与阴暗、低沉、令人抑郁的校场口。不过,貌似截然相异的场景却隐含着同质化的内核:酒会的豪华气派掩藏不了隐匿其中的冷漠、审慎乃至裹挟着危机的不安感受,巨大的官邸中潜伏着躁动不安的因子,在场人士看似随心所欲实则暗藏玄机的交谈遮盖不住剑拔弩张的焦虑气息;而在随后发生的校场口血案中,这样的不安与焦虑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迸发,阴冷、低沉的青灰色场景在低沉、抑郁的音乐中以摇晃、闪烁、残破不堪的方式呈现出来,它不仅见证了国民党打手特务疯狂的镇压暴行,更把作为国民党最森严统治地区的重庆所充斥着的阴森恐怖的凶险体验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当然,持续压抑的必然结局是无可遏止的爆发,校场口集会呐喊的人群,冯玉祥愤怒的枪声都清晰昭示了这种爆发即将到来。
如果说作为国民党陪都的重庆也许代表着中国最初的、关于城市空间的惨痛记忆,那么作为国民政府正式首都的南京在片中则呈现出一种凝重深沉的历史底蕴,一种与中国最传统、最深层的文化之根的密切关联。影片中古旧庄重的庭院、沧桑肃穆的楼宇、高大茂密的古树,甚至连每一块石板、每一扇窗格皆无不传达着一种刻骨铭心的绵延、悠远感受。南京代表着被最传统的中国文明充溢的历史与文化感怀,在这里,流淌着和谐、温情、宽容这些积淀在中华文化最深处的古老记忆,因此,即便是在惯常影像呈现中显得机械、多疑、充满威胁的蒋介石,也会在开阔寂寥、白鸽盘旋的广场倾诉衷肠,也会与儿子一道坐在冰凉孤寂的石阶上,在父子亲情的陪伴下一道品味失败的伤感凄惶。然而,在浑厚静穆的空间体验背后,一种颓废与悲凉也在不可阻遏地伸展、扩张:毫无疑问,南京是中国传统的最鲜明表征,然而,在过于厚重的传统中同样难以避免地埋藏着落后与衰颓,多次遭受凌辱的悲凉记忆已经验证了这种落后、衰颓所必将带来的失落与苦涩。城市空间中过于保守以致陈腐的一面必须得到彻底的改写,而影片尾声解放军攻占总统府的景象也许正是这种改写的一个契机。
在李欧梵看来,上海是中国现代性最早蓬勃生长的场所,“……上海在20世纪的上半期也可以说是中国惟一的国际性大都会。”③同样,《建国大业》中的上海也清晰体现了这种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的现代感受:高大华丽的洋房、成排的商铺、奔走的黄包车、豪华炫目的陈设,女人婀娜多姿的旗袍……无不造就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震惊”感受,可以说,在这一层面上,上海是中国城市中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现代性的空间所在。然而,在奢华绚丽的表象下,上海同样也隐藏着深刻的忧郁与伤痛。首先,是一种商业文明、一种金钱至上观念高度演进所引发的“商品拜物教”(fetishism)效应。恰如片中孔令侃所言:“我是商人,不是慈善家。”正是这种对金钱、利益的不顾一切的追求,才会有上海各大豪门的疯狂囤积居奇,才会导致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经济紊乱以致影响到整个国统区。其次,在富丽堂皇的现代表象下,作为中国最古老都市之一的上海依然在以自己巨大的包容性承载着传统文化中最阴暗、堕落、污浊的部分。当蒋经国来到上海整顿经济时,第一个向其挑衅的黑帮头子杜月笙便是上海这种藏污纳垢性的鲜明体现,而蒋在与孔家扬子公司的争锋相对中,又由于其经理孔令侃与蒋家千丝万缕的亲族关联而只得作罢,从而暗示出个人力量在传统积淀面前的渺小无力。
当然,上述被凸显的空间形象也并非绝对孤立,它们同样以视觉形象频繁交织更替的方式呈现,在照应影片整体风格的同时也体现出一种总体化、综合性感受,从而基本涵盖了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城市风貌。同时,它们对当下中国都市的空间状况也有所指涉:如果说重庆代表着一种对现代城市反感、拒斥的危机体验,南京彰显着都市空间中传统文明宿命性的渐渐式微的话,那么上海代表的也许是当前中国都市中最普遍的感受:惊喜与失望、欢愉与尴尬并存的鱼龙混杂。
(二)乡村——浪漫牧歌中的怀旧感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新中国的最终开创都与乡村有着难以抹煞的关联。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以乡村为据点,对侵略者展开了不懈抗争,而在与国民党的交锋中,中共更是依托广阔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最终取得伟大胜利。因此,在主流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定式中,乡村素来占据着革命策源地的核心位置,素来充当着活力的所在,希望的来源。在这一层面上,《建国大业》同样凸显了乡村对于革命而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正如片中毛泽东那句戏谑性的调侃:“蒋介石在南京当了总统,我毛泽东就在山沟里自封万岁。”在电影里,作为革命根据地、绵延浩瀚的乡村空间,朴素而气概豪迈,简陋而激情澎湃:在乡村,中共掀起了由战略防御转向全面反击的宏伟浪潮;在乡村,事关历史变迁的重大会议一次次地重演;在乡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点起香烟,在黑灯瞎火的茅屋里,在短促的早餐中,在看似随心所欲的闲谈时指点江山,气定神闲。
如果说以上对乡村革命枢纽地位的积极书写延续了中国革命影片中惯常的空间逻辑的话,那么可以说,在《建国大业》中,乡村形象还得到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主义渲染。影片中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不再是一味的血与火、宣誓与硝烟的交织,不再一味指涉胜利抑或失败的二项对立,在影片中,乡村在某种程度上揭去了严肃的革命面纱,流露出一种欢欣愉悦的柔婉情调。于是,我们才能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在山花烂漫的野外一字一句地教着小姑娘写“我是中国人”,领袖、孩子其乐融融,才能看到在胜利前夕的欢宴上,主要领导人高唱《国际歌》的狂欢,毛泽东“老夫聊发少年狂”般的幸福沉醉,甚至在烈士郭厨师的墓前,被当做香火供奉的三支香烟也在悲慨中增添了几许温情与传奇色彩。
也许,影片对乡村空间的牧歌化渲染来源于一种对本土之根的当代诉求。在费孝通看来,中国自古便存在着一种“乡土中国”的深厚传统积淀与思维定式,以农业文明为立身之本的中国人从一开始便同乡村建构了难以磨灭的深切关联,而以乡土生活为基础建立的家族宗法关系则成为了支撑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础。因此,乡村视域在中国人的空间体验中便占据着无法回避的重要地位,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乡村意味着温馨、自然、充实,意味着一种同周遭一切融汇和合的家园性存在。然而,在现今语境下,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消费主义的渐趋盛行打破了城乡之间冰封已久的局面,使二者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交流,同时也使得乡村在这样的交流中不可避免地失却了曾经为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家园地位,不可避免地蜕变为都市的他者:一方面,在高扬现代性的时代语境下,乡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等一系列缺陷在同城市的对照中遭到了超常规的放大,另一方面城市在乡村视阈内愈发成为一处性感、迷人的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无数人与生俱来的乡土文化积淀被都市文明不断篡改、异化,他们内心深处与整个乡村文化体系千丝万缕的关联被撕扯得破烂不堪,利益至上的公理使越来越多人在都市资源的争夺中漂泊徘徊、游走不定。《建国大业》在彰显城市文明的复调交织的同时,又依凭自身的壮阔视野,将乡村悲壮崇高的革命地位与其曾经拥有的浪漫怀旧意义融合一体,不仅使乡村的空间特质更加多元、丰富,也更为便利地将乡村和城市置于更加宏阔的彼此映衬之中,在带给人们广博空间感受的同时,也唤起了些许温情怀旧的当代惆怅。
三、对历史的空间化书写
在《建国大业》中,城市同乡村的独特交织构筑了气势雄浑而又颇具民族特色的空间体验,在愈加趋同的全球化进程中,这样的空间体验无疑能彰显本土的民族特性,在影片观众中激起强烈民族认同。然而,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认为的那样,民族国家的确立在诉求明确空间体验的同时,也在时间向度上热烈询唤着对共同历史的确定性感受。“他的答案部分在于,民族通过一种新的时间感(一种线性的‘历史’而不是循环的时间感)和一种新的空间感(世界被划分成边界明确的‘领土’)代替了更宽泛的、‘垂直’有序的宗教和王朝的社会组织形式……为现代世界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身份意识和安全感。”④空间的呈现固然重要,但历史依旧是民族体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空间铺展的目标之一便在于引导人们去直面一段沉痛抑或欣悦的真实历史,而《建国大业》也正践履着这一目标。
杰姆逊曾这样论述过后现代语境下时间的存在状态:“形象这一现象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时间体验,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⑤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在后现代语境下,传统的由过去通往未来、由开端走向结局的延续性时间已经被分割、碾碎,继而烟消云散;其二,在他看来,传统时间感的消失并非意味着时间的不复存在,相反,时间获得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表达方式:与深沉、厚重而又充满哲理气质,似乎不可捉摸的传统时间相比,后现代时间更多依赖于一种直接诉诸感性、尤其是视觉感性的空间化形象呈现出来。且不论杰姆逊的观点是否符合当前中国实际,在《建国大业》的具体演绎中,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获得了一种空间化、形象化的视觉表征。可以说,作为注脚在片中出现的、提示历史演进的字幕仅仅是时常为观众所忽略的陪衬,真正贯穿电影之中的是影片制作者精心打造的空间化的视觉意象,正是这样的视觉意象,在指涉别具一格的当下体验的同时,也促使观众去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的脉动,感受沉淀在民族记忆中的破茧而出的欢悦。
首先,是影片中黑白景象对于空间的独特渲染。可以说,在彩色电影时代来临后,依旧能巧妙运用黑白画面,造就别样视觉效果的影片仍不在少数,比较著名的有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以及中国导演陆川的《南京!南京!》。然而,如果说以上两部影片的宗旨在于通过低沉、哀伤的黑白色调传达战争暴行所带来的恐怖、凄惶、绝望的话,那么,《建国大业》却借助黑白场景的穿插营造出了一种历史叙述的视觉姿态,一种具体化、形象化的历史感受。在影片中,凡是涉及历史重大转折的时刻——如内战爆发、解放军撤离延安、三大战役、开国大典等等皆通过纪录片式的黑白镜头得以呈现,从而造成了某种古旧、悠远的历史体验。同时,与那些经年累月、画质低下的真正历史影片不同,影片的黑白视像经历了毋庸置疑的精心编排、打造,从而能够冲淡观者对于历史镜头古老乏味的固有印象,以一种更加清晰、精致的姿态询唤他们的参与,令其在历史瞬间的激情重现中产生更加刻骨铭心的追溯历史的深切感受。
其次,是影片对历史场景的努力还原。与此前许多炮制于影视基地的同类影片不同,《建国大业》在具体拍摄过程中更加注重历史情境恰如其分的如实复现,甚至不惜精确到细节。且不提剧组辗转于北京、南京、天津、上海等多处取景,力求发掘更本真的时空记忆,就是影片对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展现,无论是每位与会者的出场顺序,还是他们的神情、动作,都力求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实,如片中叼着烟斗的贺龙在进入会场时竟没有注意到会场大门,一直跟着摄影机镜头向前,直到发现自己出错才笑着返回,而历史上的真实场景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无论初衷怎样,这样的精确还原都能够彰显一种贴近历史的真诚姿态,更能使人产生置身其中的真切体会。
更进一步,在追溯历史真实的同时,影片还对某些已在类似题材影片中形成定式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为人性化、生活化的改写。如服用安眠药的毛泽东在根据地遭受轰炸时,昏昏沉沉地被人架到担架上转移,豪迈气魄尽失而孱弱得像个孩子;而素来以和蔼、冷静形象出现的周恩来也在得知冯玉祥遇难时失去理智、大发雷霆……这样的改写并非全然是一种当代语境下的“反英雄”姿态,而是要在使人物形象立体化的同时减少人们对过分脱离生活、过分机械化的教科书式历史叙事的抗拒,从而更容易产生一种庄重肃穆而又生动多元的历史感受。
综上所述,空间在《建国大业》的影像演绎中得到了雄浑壮阔的多元呈现,这种空间的复杂演绎、延伸,在大大拓展影片深、广度的同时也呼唤着积蓄于民族情感深层的真切记忆,体现出多元文化语境下博大开阔的时代特色。也许最为关键的是,借助多元化的空间书写,影片还以一种异常严肃的姿态去趋近历史,去正视那新中国诞生历程中最为慷慨激昂的岁月。虽然在新历史主义者们看来,还原残破、琐碎的历史的努力只能是异想天开的虚构,然而,在这个越来越多人遗忘历史的当下,在这个事物更迭如此迅疾以致人们只能如杰姆逊所言一般“缅怀此刻”(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的时代,这样的努力已经弥足珍贵。
注 释
①[美]大卫·哈维著,梁伟诗、庄婷译:《后现代电影中的时间与空间》,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73页。
②[匈]伊芙特·皮洛著,崔君衍译:《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③[美]李欧梵讲演:《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④[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⑤[美]杰姆逊讲演,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